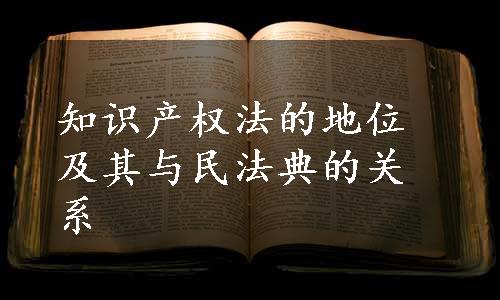
二、知识产权法的地位
知识产权法的地位,是指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所处的位置,即它是否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或它应当归类于哪一个部门法。对于这个问题,在知识产权法研究日臻成熟的今天,答案早已不言而喻。由前述知识产权是一种新型民事权利的性质就可以得出其应当归属于民法的结论。(81)必须指出,无论在我国还是世界范围内,知识产权法的发展从无到有,其重要程度也由小渐大,尤其是随着“网络环境”和“数字技术”以及相关技术的发展,知识产权在整个财产权体系中的地位逐渐向主导性转化,“知识产权肯定会在无形财产中占头等重要的地位,也有可能在一切财产中占头等重要的地位。”(82)那么,知识产权法的地位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与知识产权法的地位相联系,需要说明的是知识产权法与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关系问题。(83)民法是一般法,知识产权法是特别法,这是两者关系的简单概括。但是,作为民法的特别法,由于其客体的无体性,知识产权法又有别于如物权法、合同法等其他民法特别法。其原因就在于即使考虑到例外的情况,民法的一般原则也不完全适用于知识产权的保护。这在许多国际条约中都有反映,《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也明确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适用现行民商法的条文。
从世界各国民法的立法例来看,制定有民法典的国家不少,但是将知识产权法置于其中的则不多。就知识产权立法的体例看,自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在历史上建立以来,采取的一直就是民事特别法或单行法的形式,与民法典编纂没有发生过任何关系。然而,进入20世纪之后,为了回应知识产权客体的不断拓展和知识产权在整个财产权中地位的不断强化,大陆法系一些国家开始尝试将知识产权纳入到民法典体系。(84)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将作品权和工业发明权列为民法典的劳动篇,但这一做法并不成功;(85)1994年《蒙古民法典》和1995年《越南民法典》所规定的“知识产权篇”未能涵盖现代知识产权的所有内容;而1992年《荷兰民法典》拟在第九编专门规定知识产权,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放弃。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两大民法典的诞生地,法国在《法国民法典》之外又制定了《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并于1992年颁布;德国在《德国民法典》颁布后的百余年间,修订了百次以上,近年更是将一些比较成熟的单行法(如《一般交易条件法》、《消费者信贷法》)纳入其中,但始终未把知识产权法吸纳进去。1996年,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主持的华盛顿会议上,各国与会专家达成了“不将知识产权法纳入民法典”的共识。从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法的发展来看,也能得出不宜将知识产权法纳入民法典的结论。现代科技进步迅猛,各种新型的知识产品不断涌现,与之相应的知识产权法也总是处于不断修订、不断推陈出新的动态过程之中。如法国自1992年颁布《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后,在短短的6年时间里先后12次对法典进行了修改和增补,涉及条目有112条,占总条目的1/4;(86)《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颁布20余年以来也修正了3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亦是如此。那么,将一套经常处于变动之中的法律制度纳入讲究系统性和稳定性的民法典之中自然就是不妥之举。基于上述原因,我国《民法(草案)》只是在“民事权利”专章中用一个法条对知识产权作出了列举式规定,其他内容有待将来的知识产权法典去规定。
令人瞩目的是,2006年12月通过、2008年1月1日生效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四部分满足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于该法典如何调整知识产权关系的期待,(87)成为目前为止比较成功地将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的典范。该部分为法典的第七编,共分为九章:第69章属于总则性的“一般规定”;第70章和第71章分别是“著作权”和“邻接权”;第72章是“专利法”;第73章是“育种成果的权利”,相当于植物新品种权;第74~77章分别是“对集成电路布局设计的权利”、“生产秘密权”、“法人、商品、工作服务和企业个别化手段的权利”(包括商业名称权、商标权和服务标志权、商品产地名称权和商业标识权)和“统一技术中的智力活动成果权”。从该部分的章节目录来看,除了与个别尚无定论的客体如域名、数据库等有关的权利之外,基本上涵盖了目前已知的知识产权种类。
【注释】
(1)参见袁秀挺:《正本清源——评〈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之“基本理论编”》,载易继明主编:《私法》(第2辑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袁秀挺:《知识产权在财产权体系中的定位》,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6~7页。
(2)参见程啸:《知识产权法若干基本问题之反思》,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77页。
(3)有学者明确指出,知识产权是一种支配权。参见张玉敏:《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5期,第103~110页;陶鑫良、袁真富:《知识产权法总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对此,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知识产权权利的最大特征不是直接控制和支配知识产权本身,而是控制和支配他人的行为。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4)参见陶鑫良、袁真富:《知识产权法总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
(5)关于知识产权与物权更全面、更详细的比较可参见朱谢群:《创新性智力成果与知识产权》,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168页。
(6)参见唐德华:《民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有的学者认为,“知识产权”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18世纪中叶的德国。参见Geller主编:《国际版权的法律与实践》,MatthewBender出版社,旧金山2002年版,瑞士篇(英文)。转引自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版,第1页。
(7)有的学者将之译为“无体财产权”或“无形财产权”,对这一英文词汇的译法及其含义存在着不同看法,尤其是有的学者认真进行了“无形”与“无体”的区别。参见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7~9页;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再版前言”第3页,第37~38页。为了论述的方便,如无特别说明,本书对Intangible Property统一采“无体财产权”的译法。
(8)参见郭寿康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9)参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制度基础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10)参见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4~5页;曹新明:《中国知识产权法典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5页。
(11)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3页。
(12)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版,第81页。
(13)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立法体例与民法典编纂》,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第56~57页。
(14)参见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5)例如,《伯尔尼公约》对作者的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即“一体两权”给予同等保护,规定作者身份权和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应不少于经济权利的保护期。TRIPs协议将《伯尔尼公约》等主要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实体条款吸收,并作为该协定的基础性条款,但又声称“对于伯尔尼公约第6条之第2规定的权利或对于从该条引申的权利,不受本协定保护,各缔约方应免除其权利和义务”。这即是明确排除《伯尔尼公约》保护的精神权利。其后果将会造成缔约方之间权利义务的不平等,兼为TRIPs协议和《伯尔尼公约》的缔约方有义务保护精神权利,但仅为TRIPs协议的缔约方却可以以未参加《伯尔尼公约》为由免除该项义务。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本质的多维度解读》,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5期,第105页。
(16)我们认为,采用“商号”的提法更为妥当,理由见本书第五编第二十六章“商号权”的有关内容。
(17)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18)与专述知识产权客体的著作的有关内容相互对照可以得到证明。参见王太平:《知识产权客体的理论范畴》,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19)由于笔者未能查阅到《民法(草案)》的说明,所以不知该草案所规定之生物多样化确指何物,但非指植物新品种则可肯定。
(20)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版,第104页。
(21)参见李明德:《美国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22)参见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14~15页;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23~24页;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版,第3页;曹新明:《中国知识产权法典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9页。
(23)参见刘春茂主编:《知识产权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24)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新现象是,在一些国家,功能基因的发现开始被授予专利,这无疑是对传统的科学发现不能被授予专利原则的大胆修正。参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制度基础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28页。
(25)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版,第102~104页;严永和:《论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4~96页;管育鹰:《知识产权视野中的民间文艺保护》,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8~43、50~67页;黄玉烨:《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54~78页。有学者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所谓“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问题完全是一个假问题。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26)SeeWIPODraft Report on Fact-finding Missions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raditonal Knowledge(1998-1999),Chapter 5“Terminology”,July 3,2000.
(27)See The Secretariat ofWIPO,Revised Version of Traditonal Konwledge Policy and Legal Options,Intergovermental Committee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enetic Resources,Traditonal Konwledge and Folklore,Sixth Session(Geneva,Match 15 to 19,2004),Paragraph 58.转引自严永和:《论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28)参见严永和:《论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页;黄玉烨:《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5页。
(29)严永和:《论传统知识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30)1996年欧盟议会通过的《数据库保护指令》将不具有原创性的数据库列为知识产权的保护对象。《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112~3条将数据库纳入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范围,并以第三卷第四编详细规定了数据库制作者权。第L.112~3条规定为:“翻译、改编、改动或整理智力作品的作者,在不损害原作品著作权的情况下,享有本法典的保护。各种作品或数据的选集或汇编,如数据库的作者,因对材料的选取或编排构成智力创作的,享有同样之保护。数据库是指以系统或有条理的方式编排的,并可由个人通过电子或任何其他手段访问的作品、数据或其他独立成分的汇编。”引自黄晖译:《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页。
(31)参见[澳]马克·戴维森:《数据库的法律保护》,朱理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32)陶鑫良、袁真富:《知识产权法总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
(33)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34)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5页。
(35)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版,第5页。
(36)详细理由和论述见第三章第二节的相关内容。
(37)参见程啸:《知识产权法若干基本问题之反思》,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76~77页;张玉敏:《知识产权的概念和法律特征》,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5期,第103~105页。
(38)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包括知识产权权利和知识产权利益。前者指被知识产权制定法明文类型化的权利,如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等;后者指尚未被知识产权制定法明文类型化为权利的利益和按照现有知识产权法无法解释为某种权利但又应当受到保护的某种利益,如域名和数据库。该观点值得重视。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39)参见刘剑文、张里安主编:《现代中国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40)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室编译:《各国宪政制度和民商法概要》欧洲分册(下),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205页。
(41)河山等:《著作权法概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www.zuozong.com)
(42)有学者指出,国内外关于知识产权的观念大致存在三种观点,即知识产权自然权利观念、知识产权法定观念和知识产权折中主义的观念。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43)有关论述可参见王太平:《知识产权客体的理论范畴》,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44)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39页。
(45)参见[日]吉藤幸朔:《专利法概论》,宋永林、魏启学译,专利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05页。转引自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5页。
(46)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8~9页。
(47)参见刘春田主编:《知识产权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9页;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再版前言”第3页。
(48)谢铭洋:《智慧财产权之概念与法律体系》,载刘春田主编:《中国知识产权评论》(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48页。
(49)正如无体财产不是只有知识产品一种,无体财产权也不只是知识产权,还包括以票据等形式体现出来的财产权。
(50)也必须指出,“无形财产权与知识产权作为精神领域的民事权利范畴,具有同等内涵,但外延却有明显区别,前者较之后者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引自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修订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51)与此类似,有的学者从是否创作出新信息的角度,将知识产权法分为创作法和标识法。或者,还可以分为行为规制法和权利赋予法:前者指规制侵害行为,但并不特别关注被侵害的主体拥有的是具有确定内容的财产权利还是一般性利益的法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后者指赋予知识产权创造者具有特定内容的财产权利的法律,如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植物新品种保护法、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法等。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52)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161~162页。
(53)参见陶鑫良、袁真富:《知识产权法总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李扬:《知识产权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54)关于“知识产权为私权”的更多论证,可参见金海军:《知识产权私权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9~14页;肖志远:《知识产权权利属性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55)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版,第2页;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制度基础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47~49页。
(56)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9页。
(57)参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制度基础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58)参见刘春茂:《知识产权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
(59)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8~9页。
(60)参见[美]奥德丽·R.查普曼:《将知识产权视为人权:与第15条第1款第3项有关的义务》,载《版权公报》2001年第3期。转引自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16页。
(61)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17页;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制度基础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57~65页。
(62)人权与知识产权存在如下区别:(1)人权具有基本性和普遍性,而知识产权具有国家授予性和可让与性;(2)人权具有道德性和终极性,而知识产权具有经济性和工具性。参见郑万青:《全球化条件下的知识产权与人权》,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97~110页。
(63)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22页。
(64)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版,第64页。
(65)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版,第64~68页。
(66)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9页;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21页。
(67)参见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23页。
(68)参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制度基础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7页。
(69)[美]阿瑟·R.米勒、迈克尔·H.戴维斯:《知识产权法概要》,周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70)比如,商标权或专利权被错判无效,而后来又得到纠正,是行政或司法实践中可能发生的特殊情况,在错判得到纠正之前,有关专有权“暂时”进入公有领域。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版,第14页。
(71)参见黄道雄:《论知识产权的法律冲突与法律适用》,载《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第98~101页。
(72)参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制度基础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73)参见刘春茂主编:《知识产权原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74)参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版,第9页。
(75)知识产权的时间性与他物权、债权的“时间性”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参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制度基础理论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76)见《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L.123-1条,“作者对其作品终身享有一切形式的独占权及获得报酬权。作者死亡后,该权利由其权利继受人在当年及其后70年内享有。”引自黄晖译:《法国知识产权法典》,郑成思审校,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8页。
(77)Eldred v.Ashcroft(01-618)537 U.S.186(2003).
(78)参见陶鑫良、袁真富:《知识产权法总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77~79页;李扬:《知识产权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19页。
(79)参见陶鑫良、袁真富:《知识产权法总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60~61页。
(80)唐广良:《值得敬佩的尝试——写在〈知识产权法总论〉之前》,引自陶鑫良、袁真富:《知识产权法总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1~2页。
(81)有学者指出知识产权法是属于私法但不属于民法的独立法律部门,值得研究和商榷。参见齐爱民:《知识产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30页。
(82)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版,第31页。
(83)更深入的研究可参见陶鑫良、袁真富:《知识产权法总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405页;曹新明:《中国知识产权法典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2页。
(84)参见李扬:《知识产权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页。
(85)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3版,第77页;吴汉东:《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186~187页。
(86)参见黄晖译:《法国知识产权法典(法律部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译者序”第8~10页。
(87)参见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全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62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