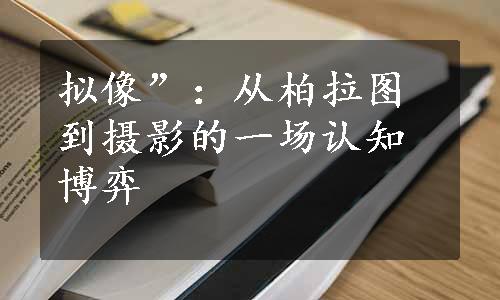
所谓“拟像”(simulacrum)本来是一个哲学名词,《牛津英语字典》对其定义为:“一种似是而非的模仿,有其外形而无其实质的图像。”[3]在《文化理论的关键概念》一书中的解释则为:
“从传统意义上,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中,一个拟像是复制品的复制品。一个复制品低劣于它的理形(ideal form),因为这个复制品是理形的复制品。而拟像比理形的复制品更遥远,因此比复制品更低劣。”[4]
拟像的哲学根源来自于柏拉图的对话录。从柏拉图的哲学思考开始的一种倾向,认为人眼可见的世界都不是真实的,人类生活的世界是被具有欺骗性的表象统治的。柏拉图试图区分“真实”[5]与真实的复制品,从总体上来说,柏拉图认为人眼所见的世界只是更为高级与超验的理念(idea)或理形(form)的幻影,因此人眼所见的事物形象,是次等的、低级的、片面的。在柏拉图看来,人要想直接感悟“绝对的真实”,最理想的方式是放弃任何中介物的再现。但是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必须通过一些中介的转译才能理解抽象的“真实”,所以,作为中介的复制品有其存在的必要,尽管它是残缺的、低级的。好的复制品能接近于这种哲学上的抽象真实,坏的复制品则是只模仿其形而不具备其实。按照柏拉图的哲学观,即便忠实反映了抽象真实的好的复制品,也只是对真实的管中窥豹而已。拟像作为极具误导性的、坏的复制品则更为恶劣,它不仅仅完全与柏拉图心中的那个绝对真实背道而驰,甚至盗世欺名地以假为真。
柏拉图提出的哲学角度的拟像概念,其实质上对于任何形式的中介物和再现(无论图像、文字或是别的媒介)都抱有敌意,它与摄影史中出现的拟像说是具有一定差异性的。摄影史中的拟像说,借用哲学中的拟像术语指代失去外在本源的、以“再现的再现”状态呈现的、纯形式的影像符号。如本书导论中已经指出的:虽然拟像说在兴起之初呈现出“影像谋杀现实”的理论外壳[6],质疑摄影图像制造影像幻觉,然而在此外壳之内,是对于当代社会的信息获取层面单向度推崇视觉感官而贬抑文字理性,是对于当代社会的思考认知层面极度强调“视觉性”的一种反抗。它是潜藏在文化深处的对于泛滥无度并侵占到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纯形式的视觉符号的厌恶感(或不信任感)的集体爆发。
拟像说在摄影史中是由潜在到显在,一步步发展、明晰起来的,呈现一种递进式的拓展和反向的回溯。拟像说正式登场于20世纪60年代,在伴随着时代发展前行中不断地回顾审视摄影图像一路走来的前身。在人类心灵对于想象及梦境的图像追溯中,拟像有着久远的历史和充分的存在基础。对于更为自由的制像方式的渴望,是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在摄影术产生前这种愿望只能通过绘画与工艺得到部分的满足,摄影术的发明极大地激励了这种想象力的扩展。虽然早期的摄影图像被19世纪的文化精英们(以波德莱尔为典型)斥之为扼杀梦想的堕落的机械艺术,但是达盖尔银版摄影术的发明者之一路易斯·达盖尔却是一个制造三维舞台梦境的高手[7]。耐人寻味的是,作为制造拟像的行家里手达盖尔所发明的银版摄影,却被本雅明赞叹为拥有上帝般真实灵光的唯一显现。摄影图像自诞生之日的这种矛盾性,为摄影拟像说的浮现预埋下深刻的心理渊源;20世纪30年代关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思想中已经可以找到明晰的理论踪迹,经历了50年代摄影技术与图像传播技术的成熟与普及,拟像的摄影实践与理论探索终于在20世纪中期喷涌而出,形成不可抑制的发展之势,不仅在进入90年代之后,拟像摄影大有成为主流摄影手段之势,它与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再次点燃了古老的柏拉图洞穴的幻想。今天,拟像仍然以当代摄影图像的名义活跃于时代舞台,并与越来越多处于“模拟”、“虚拟”状态下的视觉认知相呼应,激起众多的思想涟漪,它是文化理论界自摄影诞生之日起就众说纷纭的、关于摄影图像本质角色讨论的持续,并伴随着现代视像科技的进一步演变,将许多事关人类文化经验和未来认知形态的探讨推向新的焦点。
作为视觉媒介这样一种中介物,摄影图像与生俱来就是缺陷的,并且在社会文化定位上具有双重性。达弥施在《落差:经受摄影的考验》一书的前言中指出:
“摄影图像并不属于自然世界:它是人类工业的一个产品,是一种假象。其本质,从现象学的意义来讲,不能与它的历史意义区分开来,也不能区分于决定了它的产生的那种规划与意图,而这些规划与意图肯定是受到时间局限的。然而,这一图像的特点就是让人觉得它好像是一种自然程序的产物……摄影是这样一种悖论式的图像,它没有厚度,没有物质,甚至可以说是完全“非真实的”,但人们无法不认为,它……以某种方式,留住了现实中的某种事物,而它就属于这一现实。这就是摄影图像本质上的欺骗性。”[8](www.zuozong.com)
然而,游戏只有先设定规则才有游戏本身的存在。任何理论都有其语言的相对性与支持其成立的语法逻辑,只有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下,理论的判断才有意义。对于摄影图像的真实性而言,假设存在一个没有“歧义”的观点,那应该就是:任何摄影图像都只能是摄影图像本身,并不代表它所指涉的其他任何事物或意义。如果摄影图像试图通过它的视觉再现指涉别的事物,那么它就是从本质上具有“欺骗性”的。这种解说的逻辑看起来无懈可击,但如果真是这样,就意味着放弃包括摄影在内的任何图像作为视觉媒介的再现功能。这对于人类社会的认知能力而言,显然无法做到。与此相同的还有文字。作为媒介(medium),其本身意味着一种居中(居间)。媒介如同桥梁,沟通与连接着原型和对原型进行理解的人。人类必须依赖于媒介的存在,因为只有通过媒介这一中介物,才能把一端的原型所传递出的信息,转译成另一端的人能够接收到并理解的事物。人类不可能做到如传说中的得道高僧那样,“不可言说”地进行灵魂上的直接体悟。以上是本书进行讨论的理论前提之一。
其二,共识(common sense)。《剑桥词典》对此解释是:“我们必须知晓的,让我们以理智和安全的方式生存的最为基础的知识和判断。”[9]《韦氏词典》定义为:“建立在对于形势或事实的简单认知基础上的恰当判断。”[10]虽然共识的具体标准无法精确定论,不同的时代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共识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但毫无疑问的是,共识在维系人类日常生活的正常运作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承担着无法替代的重任。摄影图像在当今人类社会中的文化共识,尽管一直遭受着种种非议(拟像说是其中之一),但如巴特所言,“照片的实质在于认可它所反映的东西”[11],最为简单有效的例子就是我们对待身份证件照、各种新闻图片报道、科学考察图片、X光影像、旅游明信片、家庭相册等等的态度。基于相同的文化共识,我们或许会认为某些摄影图像遭到了“美化”(如旅游明信片),但几乎没有人会否认这些图像的肯定性意义——肯定什么呢——这是照片之外确实存在的某个事物,这是其现实影像的图像再现,即巴特《明室》中所言的,绝不可以妥协的摄影核心价值:“这存在过”(that-has-been)。
因此,尽管摄影的“忠诚度”一直遭到思想文化领域内的种种挑战,但这并不妨碍当代人类社会以及其中的每一个人,运用摄影图像见证、确立并保存对于周遭世界的肯定性认识。实际上,拟像作为对于摄影共识的质疑,也从反面印证了摄影图像在当代社会认知层面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本书的讨论正是建立这一根深蒂固的(或曰一厢情愿的)“肯定性”价值认知的基础上。反过来说,如果当代社会文化对于摄影图像的定位从一开始就是具有否定意义的欺骗,那么拟像问题就不会产生,而整个摄影的基本功能也会遭到彻底的颠覆,从而我们当今的社会生活面貌也会呈现出某种与现在截然不同的形态。
所以本书的讨论前提是:摄影图像是一种在社会文化中具有根深蒂固的“肯定意愿”[12]的图像,这种肯定意愿一方面来自于人类自身在认识、表达、交流层面的物种局限性(在前面段落已说明),一方面来自于为了维系和确立当代社会视觉认知的正常运作这一共识。
当代社会文化赋予摄影图像直观的、肯定性的指涉出现在镜头前的某个外在之物这一价值判断(或曰特权),以此为基础,让摄影图像在极大程度上参与到维系社会文化正常运转的方方面面,并借由对于摄影图像的这种价值判断,塑造自身的面貌。摄影史中的拟像说,也正是建立在摄影图像这种具有特权的、肯定性的社会文化共识基础上。虽然,其貌似表现为对于摄影图像的肯定性价值提出质疑和反论,甚至不无激进地试图对其基本社会文化角色进行全盘颠覆。而实际上,拟像说的这种“反摄影共识”的激进态度,从反面加深了对于摄影图像肯定性文化共识的深层理解。拟像说并未从社会事实上推翻摄影在认知层面担负的重要角色,而是作为对于摄影图像本质属性的一种觉醒,提醒人们在与影像营造的绚丽世界狂欢共舞的同时,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