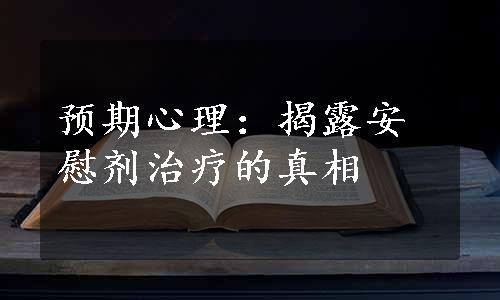
怀特先生不幸得了淋巴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胸肺以下,医生也开始逐渐减少治疗。不过怀特先生却相信,有一种药物可以治好他的病,这种药物就是根据1957年某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对癌症病人研究报告制成的抗癌新药。
当第一次注射这种新药时,怀特先生在病床上呼吸困难。但3天后,他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了,他甚至还会同值班护士开玩笑。在肿瘤缩小一半后,他从医院回家;但是,其他用这种新药的病人却没有任何效果。
两个月后,质疑新药无效的报告出来了,怀特先生看到这份报告时,病情出现了反弹。为了稳定他的情绪,医生决定对他撒谎:还有一个病人服用新药后情况也有所改善,新的关于药物有效的报告应该明天就会出来,而怀特先生是其中改善最好的。然后,医生给怀特先生注射了完全不含新药的假新药。这次,他的病情改善得比第一次还要好,直到两个月后,怀特先生仍然十分健康。不幸的是,当他偶然读到新报告说最终证明新药完全无效的时候,几天后就去世了。
对于怀特先生的病情和死因,医生们解释说:“怀特先生不是死于癌症和并发症,他看到报告的时候,他的癌症基本上已经痊愈了,这本来是个奇迹。但是,他的死因很蹊跷,他死于心脏病突发。”医生们相信“安慰剂效应”(指病人虽然获得无效的治疗,但“预料”或“相信”治疗有效,而让病患症状得到舒缓的现象)可能既帮了怀特先生,同时也害了他。
怀特先生是死于心理预期的疾病。事前怎么想,我们就会得到心中的所想结果,这说明预期想法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虽然医学家们还不能解释这种现象在生理构造上的原因,但对我们日常生活来说,这是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我们的心理预期和我们的各种行为高度关联。比如,感冒药的情绪推高美国人的医疗成本,导致过度医疗,往往成为教授们考察的重要现象。
预期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斯坦福大学教授肯尼斯·阿罗完成不确定和风险经典研究后才确定下来的。现实的价格,通常所做的经济行为,可以看作人类的理智和情感纠缠不清的决定,这种决定是心理的各种因素异动的结果。预期在市场中很有意思的一些表现,主要是像安慰剂效应这类无法说清的人类心理行为现象。把心理放到所有的市场经济活动中,给它起个诸如预期、理性预期、不确定性、风险偏好之类的名词,其实就是我们要说的不确定性经济学的主要部分。
感冒是一种常见的病症,这种病症的典型特点是:可能带来头痛和发烧、呼吸不畅、口腔溃疡和咽喉感染等不舒服的感觉。特别是头痛,大脑作为人类最敏感的部位,患脑病对人类的影响常常是致命的或损害最大的。止痛常常是一种感冒药物的首要疗效要求,但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一美元的阿司匹林吃下去后总感觉头痛,让你担心无法治好感冒,但是如果处方上写的是两美元的阿司匹林,居然就可以止痛了。事实上,一美元的阿司匹林和两美元的阿司匹林并无本质上的药理差异,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区别。
头痛和感冒、感冒药没有关系,治好头痛仅因“花钱就有效”的预期,更进一步的说法是,人们的消费行为受制于这种想法。一片免费的阿司匹林可能被视为根本不能治病的假药,假如美国出现比黄金还贵的感冒新药,人们马上会相信它是灵丹妙药,甚至夸张到这种新药可以让人不再感冒和头痛。
科学研究表明,目前治疗感冒病毒没有任何特效药。头痛、发烧、溃疡之类的症状,是人类的免疫行为,就如同人要吃饭喝水一样自然。唯一的问题是,这种症状会引起我们感觉上的不舒服。(www.zuozong.com)
欧洲和美国的多数人对感冒病毒的抵抗力相对要低些,几个世纪以来,流行感冒夺走的美国人的生命远比艾滋病和天花要多得多。1918年,战后流行性感冒的死亡率几乎和战争时期相当。在感冒药物的使用频率和药效要求上,美国人的标准也比其他地方的人群要高一些。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人在这方面开发的药物种类仅仅比心理药物种类少一点而已,全世界主要的感冒药基本上都是美国各大药品公司开发的,比如强生公司就很擅长开发新的感冒药样品。
你可能想不到,正是因为这种大公司不断开发的感冒药,促成了人们那种药效和美元的联系。阿司匹林后开发的新药,多半是针对用惯了阿司匹林的人,这种安慰剂的效果大幅降低,但是安慰剂效应并没有消失,医生们即使不用阿司匹林,嘱咐病人喝水或者开一些更加无足轻重的药欺骗病人仍然会收到效果,就像怀特先生的医生那样。但是药品公司不这么想,像强生、辉瑞这样的大公司是很理解医生们的困境的,稍稍修改不痛不痒的复方成分表,一种新药就炮制出来了。
举个例子,美国在2010年开发出一种所谓的速效感冒药,这种药的唯一优点是比阿司匹林能更好地缓解那些头痛脑热的问题,然而化学分析的结果自然是惊人的,因为这种新药的主要成分不是别的,正是阿司匹林。2000年前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中国类似治感冒的药物,分别是柳树皮、杨树皮,甚至柳树根等,现代化学家最后的结论是止痛成分现在和过去都是一模一样的——阿司匹林。意思就是,我们2000多年来都在“炮制”同样的药品。
对于药品公司来说,这不过是编造一个新的加工工艺,进行新的开发项目,然后推出貌似不一样的外观生产过程。药品的药名、价签上发生了变化,人们既然在安慰剂上喜新厌旧,药品公司也不担心在价签上不断标出不同的数字,从利润的角度出发,自然是越大的数字,看起来越可爱。医生们在没有发现安慰剂的副作用的时候,自然愿意使自己的腰包更鼓,结果一个可怕的问题出现了:美国人在这些小小的病症上过度医疗的麻烦接踵而来,药费升高,跟着手术费用也在升高,最终全美国的人都喜欢不治病也要去医院。
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禁止给6岁以下的儿童服用任何感冒药,其实不是因为感冒药无效,主要因为儿童的处方药量对于药品公司而言,根本构不成可观的利润,还可能有副作用的道德谴责。但有些父母可能不管这些,他们发现,某种感冒药偶然给某个孩子使用,药效居然比大人要好得多。其实,那也是我们的心理在作祟。孩子没用过的药,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新药,不论这种药是原始的柳树皮还是速效感冒药。
事实上,也许我们可以作个另类的比喻,如果让医生们停止使用无效的感冒药和其他类似的过度使用的安慰剂,美国的医疗费可能马上会减少2/3,健康的美国人马上会多出1/3。也许正如那句俏皮话所说:“病人太多,是因为医生和药品太多。”
中国的镇痛剂和感冒药一类的安慰剂,可能比美国要严重得多,一些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有1/3以上的人将感冒药等同于镇痛药。中国常见病症的自我诊疗比例中最高的就是感冒,占常见病症的89.6%。中国也是世界上引入高价感冒药最急迫的国家。
中国的感冒药同样廉价和无用,但是感冒以外的安慰剂同样虚高,比如一些被证明无效的中药或者所谓药用保健品。实际上,并不是中国的医生特别贪婪,而是因为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更多的安慰剂只会让感冒药更快地黔驴技穷。结果为了赢利,除去抬高要价,病人自我诊疗增加,还将大量的更有效的其他药物的资金也统统占用。反过来,因为其他药物成本太高,价格也跟着升高,成了典型的医疗供应极端不足。除非降低有效药物的成本价格,否则这种怪圈很难打破,所谓以药养医,会不断地折磨中国的医疗体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