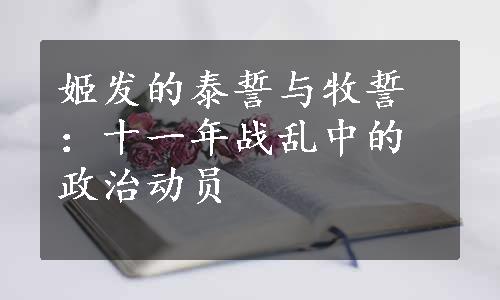
这一年是姬发上台的第十一年,由于他后来称周武王,故而称为武王十一年。
十一月戊午这天,诸侯联军在盟津誓师。大家宣誓的口号是:“孳孳(zī)无怠。”就是说,要孜孜不倦,不要懈怠。宣誓完毕后,由姬发发表战前动员演说,这篇演说词又称为《泰誓》。在《史记》中,只记录一篇,且行文较短。在《古文尚书》中,《泰誓》共有三篇,也就是姬发前后有过三次演说,篇幅较长。
姬发都说了些什么呢?主要是三个方面:其一是列举纣王的种种恶行;其二是说明自己造反的理由;其三是鼓励全体将士奋勇杀敌。
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首先是揭露纣王的暴行:
“商王纣对上天不敬,给人民带来灾难,他沉溺酒色,残忍暴虐,采用灭族的恐怖手段。生活奢侈,大兴土木,大造宫室楼榭,以盘剥百姓。以炮烙之刑炙杀忠良,以剖腹之法残害孕妇。”(《泰誓》上篇)
“如今商王拼命干坏事,抛弃老成持重的大臣,亲近奸佞小人,淫乱酗酒,放纵暴虐,致使朝廷朋党林立,互相攻伐。而无辜之人却只能呼天喊地,无处诉冤。”(《泰誓》中篇)
其次是说明自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上天要护佑万民,这才有了君主,才有了百官。君主要恭从天命,安抚、爱护四方之民。纣是有罪还是无罪,这由上天来决定,不是我一个人敢自作主张的。纣有亿万臣民,就有亿万条心,不能同心同德;我就算只有三千臣民,也可以上下一心。殷商已是恶贯满盈,上天已经命令我诛杀之,我若不顺承天命,罪恶与纣相同。”(《泰誓》上篇)
在这里,什么是天命,姬发说得不清不楚。
他在第二篇演讲中,就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他把“天”与“民”结合起来,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姬发思想的一大突破。我估计他之前第一次演说,未能得到认同,特别是讲到天命时,凭什么说你知道天命呢?你是如何知道的呢?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讲清楚。他把不可捉摸的天意,与可以理解的民意视为一体,那问题就变得简单了。上天的意愿,就是人民的意愿,这是多高明的见解呀,神从天上回归到人间了。
最后是激励将士奋勇杀敌:
“我将率领你们诸将士,消灭仇敌。尔等应奋勇向前,以坚毅果敢之精神成就伟大的事业。功多者有厚赏,怯懦不前者杀无赦。”(《泰誓》下篇)
政治动员是必要的,战斗力的由来,在于明了为何而战。姬发强调此役乃是惩恶扬善,乃是除暴安良,救民于水火之中。
还有比这个更崇高的事业吗?
次年二月,诸侯联军抵达殷都郊外的牧野,兵力有所增强,据《史记》的说法,此时,联军的兵车已经有四千辆之多。那么纣王的兵力又有多少呢?《史记》给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七十万人。
以我的看法,这个数字很有水分。
在纣王之前,通过卜辞所查到的资料,在武丁大帝时代,我们看到一次征集的军队最多也就一万人。在当时,一万人就算得上是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纣王孤注一掷,把能上战场的人都征入队伍,数量可能远不止一万人,但也不可能比武丁时代要多出七十倍。再说了,就算临时征召七十万人,哪来那么多武器配给呢?难不成赤手空拳上阵吗?因此,我猜想纣王所称的七十万人,只是虚张声势,能有二十万人就算很了不起了。
那么诸侯联军的兵力有多少呢?
这个不太好估算。
在联军中,周派出的兵力,共计有三百辆车,四万八千人,平均每车对应一百六十人。按照后来周的定制,每车应该配置七十五名战士,这说明姬发手中的战车数量不够,他必须从诸侯那里调来更多的战车。诸侯国提供了三千七百辆战车,但每车配置多少人,却是未知数。我想,周军至少占联军的一半兵力,如果没占到这个比例,指挥系统就会出现问题。倘若以此来推算,联军的数量,大约在八万人到九万人之间。
从数量上来说,诸侯联军远不及纣王的军队,但是武器上应该占有绝对优势,因为四千辆的战车,绝对不是小数目。中国战车发展的巅峰期是春秋时代,晋文公称霸之时,也只有战车七百辆。到了春秋晚期,当时最强大的两个诸侯:晋国与楚国,所拥有的战车,也不过是四千辆。
尽管战车很早之前便出现在战场,但是把战车变为一支“装甲集群”,那可就是破天荒的变革了。这种军事思想的变革,正是由姜太公来完成的。在《六韬》中,可以看出姜太公对战车的重视程度:“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北走也。”“十乘败千人,百乘败万人。”在姜太公看来,战车足以摧毁敌人坚固的阵地,是以少胜多的利器。十辆战车可以打败一千名敌人,而百辆战车可以打败一万名敌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什么姬发要征集那么多的战车,因为他必须一击致命,终结殷商的历史。
双方决战的时间是在二月甲子。
地点:牧野。
决战是在黎明时打响的。
姬发派太师姜尚带着一百名勇士,前往殷商兵营前挑战。古代打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双方列阵而战,只消一天打下来,胜败立判。纣王仗着自己人多,接受挑战,把阵式排开。战车与步兵交错分布,大家手里操着戈戟或弓箭,排列齐整。在空旷的原野上,不时有风袭来,旌旗猎猎。
擅长鼓舞士气的姬发又一次发表战前演说,因为是在牧野前线,故而该篇演说又称为《牧誓》。只见姬发左手持着象征权力的大黄钺,右手挥舞着大旗,对众人说道:“路途多遥远啊,从西方来的人们!”演说的开篇就不落俗套。
“啊!来自友邦的诸位国君,各位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都是官名)、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髳(máo)、徽、卢、彭、濮等诸部,举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竖起你们的矛,我就要宣誓了。
“古人曾这样说:‘母鸡不应该在清晨啼叫,如果母鸡啼叫了,这个家就要败落。’如今的殷商,就是母鸡在啼叫。商王受(即纣王)只听妇人之言,抛弃对先祖的祭祀,抛弃同族兄弟,不肯任用。他不用贤人,却任用那些从四方逃来的罪犯,把他们提拔为大夫、卿士,尊崇他们、信任他们,而他们却是残暴地虐待人民。面对这种情况,我姬发只能恭行天罚,替天行道。对于今天即将面临的战斗,我有几个要求:每前进六七步,就要停下来整理好队形。进攻的时候,用武器刺击四五次或六七次后,就应该停下来重新整好队形。诸位将士,要努力啊,拿出勇敢精神,像虎豹熊罴那样凶狠,在殷都的郊野与敌人一决死战。注意不要杀死前来投降的人,这些人以后可以带回西方服劳役。如果你们不奋勇战斗,那么我告诉你们,将会带来杀身之祸的。”(www.zuozong.com)
这是一篇很有名的演说词。
周武王姬发的《牧誓》与夏启的《甘誓》、商汤的《汤誓》都是开国君主在战场上的讲演,《牧誓》有一个明显不同于另两篇的特点,该文对行军布阵时的队列要求做了明确指示,无论是在前进时还是攻击时,都必须要保持队形的完整。为什么姬发要强调这一点呢?诸侯联军的力量是居于劣势的,要扭转这种劣势,就必须以严明的纪律约束,战士不是各自为战,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进退。这显示了诸侯军队,特别是周军的军事素质是相当过硬的,这应该与姜太公的训练有直接的关系。
这一年,纣王上台已经整整五十二年了。
已经看不到当年那个神勇无敌的纣王的影子,取而代之的是老态龙钟的形象,比肉体衰老更为可悲的是,他的思想早在靡靡之音中变得萎靡不振了。但他似乎还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他拥有的军队更多,不过这些军队的战斗力很令人怀疑。很明显,数十万大军中的绝大多数只是临时拼凑而成,既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技能训练,更谈不上有铁的纪律。
纣王把临时拼凑的杂牌军置于前,中央军则置于后。他的算盘是先让杂牌军胡乱抵挡一阵,占着人多消耗诸侯联军的实力。等到诸侯军精疲力竭之时,精锐的中央军再投入战场,必定可以大获全胜。这个想法固然很美,只是早已不理兵事的纣王哪里晓得世界军事地发展趋势,周的武装力量之强大,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联军的进攻有条不紊,战车部队发动进攻,四千辆战车,足以撕破敌方的防线。后续跟进的步兵,严格遵守姬发的命令,始终维持着进攻队形的整齐,步步为营,不急不缓地向前推进。反观殷商军队,那些被临时拖上战场当炮灰的人,哪里有什么士气可言,他们究竟为何而战斗呢?为了保护暴君、独夫、压迫者纣王吗?他压迫我,我却要保卫他,有这个道理吗?谁也不想打仗,看到诸侯军冲杀过来,殷商军队中就有人喊了:咱们为纣王拼啥命啊,干吗不加入联军一方,倒转枪头去对付暴君呢?
起来,不愿当炮灰的人民!
于是乎令人惊愕的一幕发生了:殷师的前军突然纷纷倒戈,反倒成为诸侯联军的前锋,攻打纣王的后军。这下子可乱了套,纣王哪里料得到有如此变故,他辛辛苦苦招来的数十万大军,却成了敌方的帮手,他就像给姬发打义工。
这仗没法打了。
商纣的中央军在诸侯联军及倒戈者的双重打击之下,伤亡惨重。
《尚书》的《武成》篇中记录牧野之战的惨烈场面时,用了一个词:“血流漂杵。”对于这个说法,后来孟子表示强烈的怀疑,他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认为周武王姬发是“至仁”,而纣王是“至不仁”,正义摧毁邪恶,理应是摧枯拉朽,哪来的血流成河?
这种说法实在太过于主观,太过于幼稚了。
姬发一战定江山,纣王狗急跳墙,不遗余力把所有家当都投入了,要是没点实力,他能坐得了五十年江山吗?即便是正义战胜邪恶,就像“二战”中同盟国打败法西斯一样,也同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牧野之战是周与商的生死之战,血流漂杵的惨烈并不奇怪,但显然殷商人的血流得更多。
牧野之战,决定了殷商帝国的命运。
纣王战败了,他逃回殷都。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殷都的守备形同虚设,很快诸侯联军如潮水般涌入城内,谁都知道,一个旧王朝结束了,一个新王朝开始了。
诸侯联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入城,在队伍之中,有几辆华丽的马车,车上所坐的人,当然都是重要人物。殷都的百姓夹道观看,指指点点。混在人群中的人里,有一个著名人物,他名叫商容,曾经是殷商重臣,只是因得罪纣王而被罢官。
当第一辆马车驶过来时,一望便知是个地位极高之人,百姓们便纷纷议论说:“这个人是不是新的君王呢?”商容笑道:“不是的。你们看这个人,看上去十分严肃,但脸上带着焦急的神情,这是遇到大事时表现出的敬畏之心,但他不是君王。”商容说得一点也没错,车上的这个人,便是姬发的左右手毕公。
第二辆马车驶过,大家又在猜测此人是不是君王。商容又评论道:“不是的。你们看这个人,坐在车上虎虎生威,又像雄鹰一样振翅欲飞,他若率领将士迎战强敌,一定会奋力向前,决不退缩。这个人也不是君王。”那是谁呢?太师姜尚姜子牙,看来此公是老当益壮。
又一辆马车过来,这坐的是不是君王呢?商容又点评道:“不是的。此人温和宽厚而又悠然自得,他志在除贼,安定天下,但他不是天子,他应该是周的相国吧。”来者正是姬发最得力的副手,一代名臣周公旦(姬旦)。
此时第四辆马车迎面而来,大家想,这回总该是君王现身了吧。商容喝彩道:“是了。你们看这个人,有圣人的气象,为什么呢?他为海内征讨暴虐,可是无论是善或是恶都不会影响他内心的平静,你们看他外表,也没有表现出丝毫喜怒的神色。所以我知道他就是新的君王。”这回,商容又猜对了,来人正是征服者姬发。
看来商容是懂得一点相人之术的。在他看来,前三人,即毕公、姜太公、周公旦三人,还未臻最高明的境界,他们或有焦急之相、或有威武之相、或有得意之相。而姬发则深沉如海,不动如山,真正有帝王之相。
倘说姬发不食人间烟火,却也未必,凡人之心,他皆有之,特别是复仇之心。如不是为了复仇,又哪来的兴师动众?
姬发、周公旦、姜子牙、毕公等人都进城了,这时候纣王躲哪去了呢?一生都自以为是的纣王,做梦也没想到,仅仅是一场战役,他就彻底输光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可惜他没有时间去总结经验教训了。高傲的他当然不愿意向臣子缴械投降,再说了,投降能有活路吗?
关于纣王的结局,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称纣王自焚于鹿台,临死之际,他还不忘把所珍藏的珠玉戴在自己身上,是不是担心到了九泉之下成了一名穷鬼呢?这是《史记》的说法。
另一种说法见于《竹书纪年》,称纣王乃是被周武王姬发所俘,他逃到一个名为南单之台时,被周军擒获,后来被处决。
不管哪种说法属实,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纣王最后死了。据说,姬发对着纣王的尸体射了三箭,并用一把名为“轻吕”的剑在他身上捅了几个窟窿,最后用大黄钺砍下他的脑袋。
清算完纣王后,紧接着是清算他的女人。史书上多次提到纣王听信妇人之言,至于他后宫的女人在政治中扮演什么角色,着实不容易搞清楚。妲己被视为“祸国殃民”的女人,自然难逃一死,她被处决后,与纣王一样被悬首示众。我估计到了商纣晚年,妲己也未必受宠,毕竟人老珠黄,而帝王后宫不缺的就是年轻美貌的女人。
真正受到纣王宠幸的两个妃子,自知没有活路,索性悬梁自尽。姬发为了报当年父亲被囚之仇,冲着这两个妃子的尸体各射三箭,然后用剑戳了几个窟窿,最后用玄钺砍下她们的脑袋,悬挂在小白旗上。
殷周之战,以周的全面胜利而告终。商朝寿终正寝,自成汤到纣王,商代共计有二十九个王,四百九十六年,在中国历史上是长命王朝之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