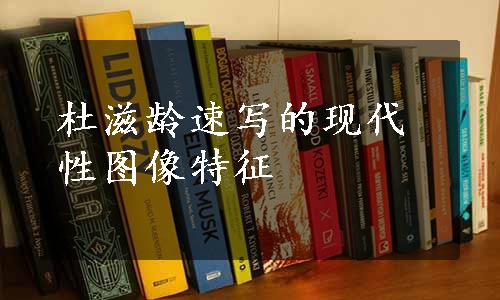
杜滋龄的速写有铅笔、钢笔、水墨几类,为了便于分析,本节主要选用铅笔和钢笔速写,毛笔速写写生将在第二节专门论述。表面看,虽然只是表现材料与工具,以及两者行笔快慢的不同,但实质上是审美方向和趣味的不同。
【草原飘香】 2001年 杜滋龄作品
【做铜器工艺品的老人】 2000年 杜滋龄作品
【姑娘追】 2002年 杜滋龄作品
杜滋龄速写的现代性首先体现在价值理念上,因为其速写无一不是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即数十年如一日地表现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致力于发掘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他的速写和创作几乎看不到英雄、领导等伟大人物,这无疑体现了杜滋龄一种艺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价值观。所以仅凭这一点,杜滋龄就在精神价值层面上将当今一些献媚取宠嫌疑的艺术远远抛在了后面。中国社会自“五四”运动以来民智开启,观念进步,并对绘画领域也产生深远影响如胡适、鲁迅等人倡导科学、平等、民主、自由的精神在杜滋龄身上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杜滋龄的艺术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谦逊地低头放眼众生,其速写体现着人性的伟大力量,所以不论任何人站在其作品面前都会倍感亲切。至此,我们不妨来看看其《草原飘香》、《藏区速写》、《朝拜》、《牧场之藏女》、《奶香飘飘》、《新疆甜瓜》、《新疆哈萨克老猎手》、《做铜器工艺品的老人》、《母爱》等作品,就能体会到上述所说的现代性。
《草原飘香》为例,该作品表现的就是边疆少数民族劳动生活的场面。在杜滋龄笔下,他们靠双手辛勤劳动养活家人,乐观积极,从不怨天尤人。杜滋龄非常注重以极其朴实的手法将他们这种精神状态与自己真挚的情感诠释出来,这种自然而然的刻画与直观表现正体现了艺术家本人的个性与主体意识。
而《做铜器工艺品的老人》更是将艺术家的个人主体意识与社会人对生活的理解、思考联系起来。在该作品中,杜滋龄将一个普通人对铜器匠人的观察视角表现得独特而生动。在艺术家的笔下,老人一直默默地敲打着正在成形的铜器,这既是他几十年来的职业,也是他日复一日生活中的一部分。虽然他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杜滋龄却将这种习以为常表现为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浓浓依恋。在我们看来这正是一个艺术家需要向观众传达的——艺术家应该表达人们能理解的东西,而不是像中世纪神学画家一样画一些深奥神秘和令人费解的物象。从这个意义看,杜滋龄的速写内涵与当今社会人文的发展规律是一致的,即在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中加入艺术家能与观众相互理解与交流的因素,从而将日常生活引入到能引人深思和遐想的境界。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杜滋龄的思想是自由的,不受任何束缚,他没有刻意去回避或者迎合什么,所以其速写中这种意识与价值观正是一种现代性。
除了有很强的艺术主体意识之外,杜滋龄的速写在艺术语言上也有很强的创造力,并与传统古典速写和中国传统线描拉开了距离。即不以再现为目的,线条不再是以往意义上物象的轮廓线,而是表现人存在状态的假设与符号,并且有强烈的情感震撼力,这也是杜滋龄速写现代性的第二个特征。速写最重要的语言就是线条,没有线条,速写将失去其生命,杜滋龄恰恰将线条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正如荷加斯的速写以“波状线”和“蛇形线”为标志和符号,杜滋龄的线条也有鲜明个性和深度,我们从《埃及民间舞》、《草原漫步》、《高原骑手》等作品中可见一斑。如《埃及民间舞》中,线条极富人格气质。他在不大的纸上书写人物,构图疏密有致,前与后、左与右、人与人、人与马皆有各自不同的动态,这种动态差异也反映了不同速度。那飘逸奔腾的线条既将激烈的动态表现出来,又衬托出艺术家个人鲜明的人格魅力。可以说杜滋龄速写中的这种气度和力量完全是一种现代品格,一种竞争精神的洋溢,在此一扫古代静谧含蓄和柔靡病态的人物积习。具体来看,线条均放逸不羁、灵活多变,充满了热情。而在《奔腾在草原上》中,表现人物时不以细微的细枝末节为局限,敞开胸怀放眼于大的动态来表现人物气势。这种宏大的概括能力与组织能力赋予了作品一种卓尔不凡的气度,正所谓“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www.zuozong.com)
由于文化习惯改变,中国画的欣赏方式亦由手卷、卷轴变为裱于画框之物,欣赏距离也大大增加,这也就要求现代中国画有更多视觉化的因素和符号的语言,从而能在不同距离都能抓住观者的眼球。杜滋龄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恰恰在潜移默化中表现出这一新的艺术发展趋势。在《姑娘追》、《印度速写》、《印度劳动妇女》、《埃及吸烟老人》等速写中,更是将线条语言的视觉气势发挥到了极致。如《姑娘追》,其线条没任何拘束,仿佛一个个畅游于天地之间的精灵一般,作品一气呵成。我们既看不到线条是从何开始的,也看不到从何结束,或许只有气吞山河才能形容这种气魄。这种自由豪迈的表达我们可以在现代西方艺术中找到相似之处。杜滋龄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其线条不完全是轮廓,更多的是表现人自身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才是其线条的真谛之一。他的线条抛弃了传统模式和硬性形态,既不同于安格尔、毕加索、席勒,也不同于吴道子、李公麟、任伯年,我们可从这些线条中深深感受到艺术家本人鲜活的生命力与个性,感动于艺术家和表现对象之间擦出的火花。艺术家最真实的想法与最直接的冲动没有任何阻隔的形式得以表达,没有严苛的规则、法度、条框。由此可见杜滋龄的速写就是一个自由世界,一个可以任人遨游、畅想的空间,这里既有儿童般的纯真,青壮年的生机与活力,也有老年人的丰富经验,艺术家的直率和坦诚,这些足以让人震惊和感动。古典绘画最大的弊端就是画家往往被物象所奴役,难以表现出画家强大的人格力量和艺术本身的价值,现代绘画需要克服的就是这些弊端,显然杜滋龄已经深谙其中之道。
【老阿妈】 杜滋龄作品
【途中休息】 杜滋龄作品
杜滋龄速写的线条既能放也能收,这就深刻反映了艺术家的全面功力以及对艺术本体的思辨性认识。我们可以从杜滋龄一批情感丰富细腻的书写作品中一窥究竟,如在《藏族夫妇》中,线条有紧有松,有纵贯整体的大笔长线,也有轻柔似水的抒情短线。人物的内心也仿佛如同这长线与短线、阳刚与柔美的合奏一般婉约动人。在这里不必拘泥于某家古法,只任由情感释放与宣泄。
在《老阿妈》中,杜滋龄以极其敏感和生动的线条表现了一位虔诚祈祷的藏族老阿妈。画面的线条从上到下极富节奏,各色音符与音色一应俱全,通过这些线条我们能够感知到杜滋龄当时内心的跳动与激动。或许杜滋龄面对这位老阿妈曾经深思过自己母亲和蔼可亲的样子,在这里他将孩子对母亲的敬意与感激之情完全在作品中释放出来,而线条无疑成为了杜滋龄扣动观者心灵的琴弦。而在《途中休息》中我们可以看到维吾尔族妇女孩子以及牛车的特征,这三者仿佛浑然一体,与马蒂斯和毕加索线条的神秘性、原始意味以及平面的绝对化相比,杜滋龄更注重从传统中国画的绘画空间来诠释线条的表现力和生命存在感,西方理性机械的平面分割以及科学主义的思考不是杜滋龄想要的。但是杜滋龄与西方现代以来的画家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对线条形式语言的重视,这正如塞尚所说:“要给画家的情感与观念以具体形式。”
纵览杜滋龄上述速写,可以看出他始终以个人睿智的视角来把握对象,不为物象所累,其作品有着高度的可辨识性,可以说杜滋龄表面是在表现人象与物象,其实是在写心,他画画的最终目的不是单纯图像层面的,更是表露自己的心机和想法,并寻找合适的形式语言来将内心所思所感展现出来。基于上述意义,我们可以用现代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来的观点来揭示杜滋龄的速写,即“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于是,我们也可以说,速写是杜滋龄的情感符号。他的速写不故弄玄虚、狐假虎威,也不是画的越多、越繁密、越复杂、越生涩难懂。其实速写最终的一点就是表现艺术家本人在想什么,如此简单地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袒露出来越能打动人。五代石恪、南宋梁楷以道禅之气注入简笔人物画,而今杜滋龄则以生命之真实感悟赋万物以生机,表现出一种当代的人文关怀。
此外,杜滋龄的速写语言也是值得研究、探讨和总结的。因为他这些速写语言,我们即使上溯古代,无论是南北朝,还是唐宋,都没有这种类似的表达。他的语言有着诸多现代社会文化属性,包括同西方艺术的联系。在速写形式语言以及表达内涵上,西方的艺术家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如荷加斯、安格尔、雷诺阿、席勒等都有过非常精彩绝伦的速写,尤其是到了现代以来如席勒等现代艺术家,他们的速写与创作的隔阂,与时空的鸿沟被史无前例地拉近,其表现方式也逐渐由再现客观物象转向形式语言的探索与精神性的表达。如果说文艺复兴以来的艺术还仅仅局限于对客观物象本身的挖掘,到了近现代已经出现了新的艺术方向,即关注于艺术语言以及人自身的自觉自省方面。对自我与他的个体化与人性化的表达,对人存在的诘问与关爱已经成为现代以来艺术的新主题。这显然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对此反思的结果。战争的残酷激起了人们对生命内涵的珍惜与怜爱,以及对传统价值观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影响延续至今。
杜滋龄在速写中很好地借鉴吸收了这些世界艺术的成果,对一个人物画家来说,能够注意到西方现代艺术的新发展和新成果无疑需要开阔的眼界和包容的胸襟,同时对西方艺术的借鉴和反思也极大地丰富了杜滋龄的艺术。今天立足于21世纪的艺术家更不应该关起门来搞艺术,在把握民族性的同时还要放眼世界,杜滋龄的艺术经理无疑给处于发展与创新中的现代中国画提供了这样一条宝贵的经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