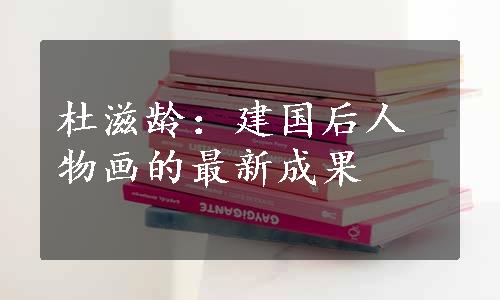
2.师出名门、博采众长
【卖小吃的老人】 74cm×65cm 1936年 蒋兆和作品
【奔腾在草原上】 杜滋龄作品
杜滋龄作为成长于建国初期的一代画家,其艺术生涯起点显然无法回避当时中国的艺术教育格局。虽然建国后的美术教育格局一度存在着相对单一和封闭的问题,但是这一时期由于艺术教育家的热情和务实以及学生们对艺术知识的渴求,所以培养出来的人才甚至要比今天多元文化格局下的更加稳重和老练。
建国之后水墨人物画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发展道路,这个过程中各种意见的争论为写实人物画在融合西方与保留传统的基本方向上铺平了道路。同时由于执牛耳者的教育思想与地域特点这两方面的差异,造成了不同地区写实人物画的不同侧重点。中国近现代虽然名家辈出,但是真正形成了完善的中国画教学体系的只有徐悲鸿和潘天寿。林风眠和黄宾虹等虽然也是很好的老师,但是他们没有建立严格的体系,没有纳入科学教学的轨道。而徐悲鸿和潘天寿都有各自不同的体系,徐悲鸿将西洋素描融入中国画,潘天寿则偏重于传统。1949年以来,徐悲鸿的写实教育体系与延安的革命写实传统,以及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三者合流,被官方认可而推行至全国。在北方徐悲鸿和蒋兆和是最重要的倡导者,传承者有叶浅予、黄胄、卢沉、周思聪等。杜滋龄最初受到的就是这一脉的写实主义教育体系的影响,包括严谨的西方人物造型训练、速写捕捉能力训练、线条表现力锻炼、绘画视野的开拓等。到杜滋龄近40岁时,他有机会接受到浙江传统文人氛围的陶冶。1979年杜滋龄考上李震坚的研究生,追随李震坚学习浙派写意水墨人物画,这是他另外的一脉师承。当时浙江的中央美院华东分院由于有着深厚的传统根基,写实主义教育体系推行到这里时有了更多的传统特色。尤其是院长潘天寿非常重视传统理法和因材施教,建立起了非常有特色的现代中国画教育体系。受用于这一体系的重要人物画家有周昌谷、李震坚、方增先等,即后来所谓的新浙派人物画。因此杜滋龄其实是融合了北方写实人物画与新浙派人物画两者的特点,并且以古为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面貌。
杜滋龄最初学画从写实体系入手。自幼父亲、哥哥热爱传统书法丹青的兴趣早已潜移默化地在他心中埋下了国画的种子,正如他自己深情地回忆“我是闻着父亲写字时的墨香成长起来的。”由于出身原因,杜滋龄与心仪的中央美院附中擦肩而过,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艺术的执著,后来他考入了天津美术出版社的荣宝斋学员班,在这期间他又有机会亲眼目睹如詹建俊、靳尚谊等名家的原作,这些作品展现了中国绘画在建国后吸取西方写实营养的面貌,可以说是建国后人物画的最新成果。曾是延安时期鲁迅艺术学院老教师的马达先生将杜滋龄引入了艺术的殿堂,使他深刻领悟到速写、素描作为基础的重要性,杜滋龄对以写生、速写深入生活的热忱就是从这时萌发的。通过学习,杜滋龄打下了坚实的人物画造型基础。在美术出版社工作后,插图、连环画等美术工作极大地锻炼了杜滋龄的实践能力。为了响应国家的文艺政策,这一时期全国很多著名人物画家都创作过新年画、连环画等通俗美术作品,由于他们的加入,这方面的艺术创作水平和数量也是空前的。杜滋龄就是在上述这样的文艺环境中默默地提升着自己的艺术修养与基本功的,而他在这一时期基本的学画思路还是以写实主义为主的。
【山西小煤矿】 68cm×68cm 2007年 杜滋龄作品
杜滋龄于1961年有幸拜叶浅予为师——叶浅予是徐悲鸿学派的重要传人。他1946年任教于北平艺专,50年代先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和中国画系主任。徐悲鸿1948年曾经专门撰文介绍他的人物画:“此种能力实为造型艺术之原子能!……作风之爽利亦为表现人之重要功能,浅予笔法轻快,动中 ,此乃积千万幅精密观察忠诚摹写之结果!……中国此时倘有十个叶浅予,便是文艺复兴之大时代来临了!”在教学上叶浅予继承了徐悲鸿的写实教育体系,但是同时又有所区别。由于徐悲鸿英年早逝,当时的徐悲鸿教学体系实际是由叶浅予具体执行和维持的。叶浅予有较深的传统基础,他对引入苏式素描教学体系的弊端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坚持将传统线描引入国画教学。叶浅予最富盛名的中国画作品是各种舞蹈人物,他善于捕捉有运动趋向的瞬间情态,用色鲜艳、单纯,笔线生动简练,吸取了敦煌壁画风格和传统线描特点,将中国画的用线特色发挥到了一个极致。在戏曲人物画《梅兰芳》、《程砚秋在舞台上》等作品中,将其经年累月的速写功力融入到水墨和线条的表现力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意境与气韵。
,此乃积千万幅精密观察忠诚摹写之结果!……中国此时倘有十个叶浅予,便是文艺复兴之大时代来临了!”在教学上叶浅予继承了徐悲鸿的写实教育体系,但是同时又有所区别。由于徐悲鸿英年早逝,当时的徐悲鸿教学体系实际是由叶浅予具体执行和维持的。叶浅予有较深的传统基础,他对引入苏式素描教学体系的弊端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坚持将传统线描引入国画教学。叶浅予最富盛名的中国画作品是各种舞蹈人物,他善于捕捉有运动趋向的瞬间情态,用色鲜艳、单纯,笔线生动简练,吸取了敦煌壁画风格和传统线描特点,将中国画的用线特色发挥到了一个极致。在戏曲人物画《梅兰芳》、《程砚秋在舞台上》等作品中,将其经年累月的速写功力融入到水墨和线条的表现力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意境与气韵。
【印度婆罗多舞】 96.9cm×57.2cm 1962年 叶浅予作品
【禄曲爷孙】 杜滋龄作品
【张思德同志】 140cm×96cm 1977年 杜滋龄作品
拜叶浅予为师是杜滋龄艺术道路上的一次转折,在叶浅予的指导下他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艺术方向,在写生过程中也有了更加清晰的思路与广阔的表现空间。叶浅予在速写上的造诣给杜滋龄以很大的启发与感染,以至于杜滋龄自己曾回忆说:“叶浅予先生在速写上的教导促成了我这种随笔即画的毕生习惯,这在我的创作过程中也是很重要的。”由此杜滋龄完成了一个由美术工作者向艺术家身份的转变与跨越。
杜滋龄在这期间谨遵叶浅予的教诲,画完速写总要集中挑出一批拿到北京给叶浅予看,叶浅予对他要求很严格,经常给他的作品提出意见和要求:“不能学得太像我,要注意观察,锻炼自己在生活中的观察能力……要用七分观察,三分作画。”这些教诲杜滋龄都牢牢记在心中,正如杜滋龄自己所言:“恩师叶浅予先生是漫长艺术道路上指导我最多的导师,和他接触不仅提高了艺术修养,还学到了不少受用终身的东西,如做人与刻苦的学习精神,以及多读书,不断提高艺术修养。”
由此可见杜滋龄学习叶浅予并不是去模仿叶浅予的用笔用线,而是学习叶浅予长期坚持不懈地以海量速写来锻炼艺术表现力的行艺之道与绘事之魂。当我们对杜滋龄作品中深厚的线条以及意境表现力钦佩不已时,也不能忽略他为该创作所画过的几十上百或上千张速写,亦或是他对某类题材几年、十几年的奋勉涤生。正是这种通过速写不断的积累,最终汇成绘事之江河的苦修,成就了杜滋龄面对物象信手拈来、从容挥洒的扛鼎之力。当然在大的艺术审美取向上,杜滋龄和叶浅予有相似之处,即对线条如痴如醉的钟爱,这或许是两人刻苦勤奋的性情方面义气相投使然。叶浅予在速写以及笔墨用线方面对杜滋龄有直接的影响,在他的指导下杜滋龄更加坚定了自己对中国画线条用笔的探索。所以到了新时期,当西方现当代艺术涌入国门,青年艺术家们纷纷效仿学习之时,杜滋龄始终不为所动,就是因为他深知中国画用线是东方艺术区别于西方绘画形态的重要因素,也是其重要的民族特色。要提高水墨人物画水平,锻炼线条功力的速写历练是不可缺少的。杜滋龄的速写采风遍及国内国外,且不论南方的秀丽山水,也不论北方的雄浑之地,就说那远至西北边陲、大漠高原的西域景色以及高至青海西藏的雪域高原,杜滋龄也是常来常往,所画少数民族以及当地民情风俗无数,以至杜滋龄自己也曾说能画出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生活景色,可见其功力之深。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真正深入生活,观察和体验生活就不可能具备这种功力和造化。邻国的印度、巴基斯坦、日本等国,欧美的美国、希腊、瑞典、挪威、芬兰等国,杜滋龄在这些地方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说明什么?一个艺术家不光要坐得住,专注国内艺术;有条件还应该放眼世界,去看看国外的山山水水、异域文化风情,这对一个艺术家放眼世界艺术格局和发扬创新民族艺术大有裨益。“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这句话虽是1000多年前的北宋郭若虚所说,但今天对现当代画家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郭若虚所说的人品并不局限于道德方面,更深层次是指大修养和视野。杜滋龄学习叶浅予表面看是技法层面,但实际上是学习以怎样的手段去提高大修养、大视野,领悟并达到这个层面相当不易。
这种大修养、大视野在杜滋龄早期作品中就有所体现,如在出版社时期创作的《李双双》、《朝阳沟》和《张思德》等作品,造型严谨扎实,人物刻画充满力度,线条稳健厚重。虽然这其中有些人物是小说创造的,但是杜滋龄没有随意编造,而是综合无数人物速写题材原型精炼而成,所以画面人物非常生动和富有生活气息。其连环画《李双双》作品获得全国连环画创作三等奖,《朝阳沟》亦参加全国美展,这些无疑是对杜滋龄早期艺术实践的肯定。
【露气】 130cm×154cm 1958年 潘天寿作品
【藏族妇女】 96cm×90cm 1990年 杜滋龄作品(www.zuozong.com)
即使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现代美术思潮涌动的年代,杜滋龄也没有心猿意马,而是专注于绘画修养的历练。1979年杜滋龄考上了浙江美院李震坚教授的研究生,在浙江美院的学习经历为他日后的绘画成就积淀了深厚的学养。浙江美院自潘天寿以来的教学风气浸润与磨砺着杜滋龄的艺术,在这期间他学到的不仅是新浙派人物画的笔墨与格调,也积累了坚实的学识修养。如果我们由李震坚再往前推,就会发现潘天寿的现代中国画教育体系才是杜滋龄艺术的初始源头,所以有必要对潘天寿的教育体系进行一个综述,并可以此为参照来准确辨析20世纪暗流涌动、鱼目混杂的人物画坛。
潘天寿教育体系建立与艺术思想的形成跟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界虚无主义泛滥的大环境密切相关。1949年7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上,周恩来提出旧文艺的改造问题,按照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提出了新的文艺方向。1950年《人民美术》创刊,按照文代会的精神将传统国画纳入了旧文艺的范畴,推动了一场“新国画运动”,即国画的改造运动。参加国画改造运动的讨论者纷纷表示,从改造画家的思想情感入手,深入人民生活。国画改造运动创造人民需要的内容和形式,清算了文人士大夫的封建趣味,高扬写实主义,使整个画坛的艺术观念转向了劳动大众。但是在这个运动发起之后,国画曾一度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甚至有被清洗的危险。
新国画运动发起后不少传统画家无所适从,于是便有了所谓的“旧瓶装新酒”的批评,认为中国画“不科学”、“不能反映现代生活”、“不能为政治服务”。1953年,艾青和王逊等撰文讨伐文人画,他们以客观对象的“真实性”作为标准对科学写实技术过分推崇、对传统笔墨大加批判,这种做法都受到了传统派老画家们的批评,尤其是秦仲文,认为王逊的主张是“有意识地消灭国画”,并且强调“笔墨并未过去,而且永远不会过去”,国画创作不应该被限制在“如何反映现实之内”。潘天寿的教育体系就是在上述背景下诞生的,他有一句名言:“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个人风格要有独创性。”在实际的教育实践中他认清了吸收西画因素作为改造、革新中国画的途径,往往存在两种危险的倾向:一是脱离中国画固有观念;二是丧失中国画固有形式。所以潘天寿认为中国画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性,中国画教学也必须有自己的独立性。在20世纪中国画所面临的大环境下,他把世界绘画分为东西两大系统,并认定“两大统系的绘画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就如两大高峰”,“这两者之间,尽可互取所长,以为两峰增加高度与阔度,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绝不能够随随便便吸收,不问所吸收的成分是否适合彼此的需要,是否与各自的民族历史所形成的民族风格相协调”。
其次,中国传统绘画师徒相传的教学方式发展到近现代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但若植入西方的美术教学方式往往存在缺憾,所以潘天寿担任院长期间非常注重教学模式。他不仅重新制定教学大纲、教学计划,甚至直接授课。面对不符合艺术创作和艺术教学规律的干预,他毫不妥协,例如他曾发言表示在山水或者花鸟画中牵强附会地表现阶级斗争是不好的(马丽华《从档案看潘天寿的艺术教育》)。1961年潘天寿提出分科教学,浙江美院在中国画教学上实现了人物、山水、花鸟分科,而后推广至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几十年来分科教学的深入,培养了一大批有专长的画家和教师,潘天寿这种分科教学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其分科教学理念与他在学术上的主张“中西绘画要拉开距离,个人风格要有独创性”,“中国画要以特长取胜”一脉相承。他的主张在中西融合的大趋势中显得非常特别,学术界称其为与“融合说”不同的“距离说”,这种“距离说”从本质上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民族传统的艺术特色。潘天寿的“特色论”是基于他对民族艺术的自信,而且这种自信与坚持贯穿于其艺术创作与学术生涯始终,在他的周围也形成了强有力的学术集群——对民族艺术的共鸣将他们凝聚在一块,所造成的影响亦是全国性的。此外,潘天寿当时组织收集了大量传统国画,建立起全国最为齐全的国画资料库,这些对于中国画注重师承以及理法学习的传统影响不可估量。
【山民】 68cm×68cm 1987年 杜滋龄作品
综上,潘天寿对杜滋龄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画发展观的继承,包括潘天寿的“特色论”和“距离说”这些坚持传统中国画原则的理论,在杜滋龄的艺术创作和艺术理论实践中都有清晰明确的体现。如杜滋龄画人物始终坚持以线条来表现民族特色,“润含春雨,干裂秋风”般的线条已经成为他作品的重要标志。他不认同借用西方形式语言来套中国画条框的方法,因此极尽所能去探索民族绘画特色,花鸟和山水画的用笔用墨都是他借鉴和参考的对象。此外不盲目借鉴和照搬西洋画法,用墨用色有严格的规范。上述种种实践的目的就是为了突出中国画自身特色,与西洋绘画以及融合派拉开距离,从宏观上说就是对潘天寿东西艺术两大系统划分的深化与实践。杜滋龄在艺术理论方面强调:“在外来艺术涌入时,更要吸收中华民族内在的艺术精神去研究如何同时代同步。不能用西画去改造中国画,也不是用西画替代中国画”,这其实就是潘天寿的“特色论”以及“距离说”的精髓。
另一方面就是潘天寿教育体系和教育方法对杜滋龄的影响,直接作用环节包括下面将要提到的新浙派人物画和李震坚等。
新浙派人物画的发展与当时潘天寿对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国画系人物造型基础课程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当时在高等院校中对于中国画人物造型基础教学存在着不同看法,潘天寿认为把西洋素描作为中国人物画造型基础“作用不大,费时很多”,但他主张学西洋素描中明暗少线条多的速写,取其线与中国画用线的联系,可使学生快速地抓住对象的姿态、动作、神情,有助于把握群像创作中的动态和布局,即以素描中速写的长处补中国画写生抓形不够和人物间缺少关联的缺点。潘天寿当时看到青年教师的作品后说“太脏,要洗洗脸”,就是针对人物画素描化的倾向提出的批评。
李震坚是新浙派人物画的奠基人之一,在杭州国立艺专学习期间师从潘天寿、吴
【在风浪里成长】 1972年李震坚作品
【卡拉奇妇女】 68cm×68cm 1987年 杜滋龄作品
之学习花鸟和书法,向黄宾虹学习山水,具备良好的传统水墨画的基础,同时又具备扎实的西画造型功底。1950年他担负起人物画教学的重担,为新浙派人物画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画风凝重质朴,更多体现了书法性笔墨语言对体面造型的阐释,而且借鉴了花鸟画的“勾花点叶法”的用笔,一笔下去夹墨夹色,形成多层次的色阶。
在李震坚的指导下,杜滋龄有机会接触到前辈国画大师的作品,在资料室和展览会上也看到了很多国外流派和知名油画家的作品,这进一步开阔了杜滋龄的眼界。研习中国画非常需要这种开阔视野,潘天寿曾说过“学高不学低”也是这个道理。在李震坚的教育下,杜滋龄开始能够较好地处理好造型与笔墨的关系,以及如何继承传统,深入刻画人物的形体等诸多问题。从杜滋龄80年代早中期的作品中我们也能够体察到新浙派人物画对他的影响,如《回眸》、《山民》、《卡拉奇妇女》等作品都非常注重用点染的技法来表现,画面形神兼备、笔精墨妙、逸趣横生,极富文人气质。这批作品与20世纪70年代之前相比面貌焕然一新,杜滋龄曾这样说:“我一开始是用毛笔、宣纸到生活中去写生,初步地使用中国画工具。但距离如何掌握和运用中国画技巧,却经过了几十年的摸索,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到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读研究生时,才逐渐地了解了中国画技巧中最重要的意境、传神、笔墨、气韵等,也知道这是中国画的真谛,非一日之功而能达到。”
当我们面对杜滋龄的作品时既能感受到新颖形式与深远意境,又能意会到其笔墨以及意境中与传统中国绘画美学一脉相承的哲学皈依,吸收传统但是又不使它外露,这无疑与杜滋龄处在浙美这个传统文化氛围浓厚的教育环境中密不可分。
纵观杜滋龄的师承脉络,无论是叶浅予还是李震坚,包括他自己都非常注重对传统的保留与吸收,并将最大限度发挥中国画用笔用线特色贯穿杜滋龄学画的始终。杜滋龄这种深厚的传统基础和广阔的艺术视野为其日后的艺术创新以及艺术眼光的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没有这样的基础就不可能站在较高的高度来反思历史、审视自身,也就不可能有他日后在少数民族题材领域的成功。但是杜滋龄并非一个保守派,他对西方艺术的态度同潘天寿相仿,速写他不排斥,并且吸收利用得非常好;笔墨用线这些中国画中最重要的传统因素他也一样没落下,而且功力深厚,这就使他能够鲜明地区别于简单融合西方绘画语言的其他画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