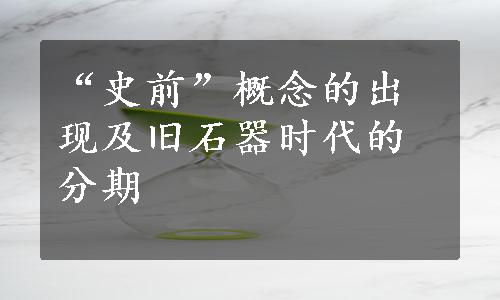
欧洲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们使用“prehistory”(史前)一词已经很久了,但却很少去解释它。有些人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两部分:把书写发明之前(或无文字记录)的历史称之为史前史;把书写发明之后(或有文字记录)的历史称之为历史。“史前”概念的出现距今不过100多年。有人认为,最早使用prehistory(史前)一词的是1851年由丹尼尔·威尔逊(Daniel Wilson)在他的一本书的书名中使用的。这本书的书名是《考古学与苏格兰的史前记录》(The Archaeology and Prehistoric Annals of Scotland)。在1863年这本书的第二版前言中威尔逊说:“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我是第一个在本书中使用史前(prehistoric)这一术语的人。”[42]不过,威尔逊错了。1833年,在法国纳博讷博物馆(Narbonne Museum)当馆长的图内尔(Tournal)就使用了“prehistoire”(史前)一词。[43]
1829年,图内尔提到在法国奥得河(Aude)的格罗特—德比兹(Grotte de Bize)发现了一些人类的骨骼和一些动物骨骼放在一起的陶器。这些动物有些还存在,大多数则早已灭绝。另一个考古学家马塞尔·德·塞维尔思(Marcel de Sevres)则认为,这些古代人类的骨骼是和那些灭绝动物的骨骼同时被保存在那里的,而那些灭绝动物的骨骼明显留下了曾被用来作为切割工具的痕迹。[44]1829年,塞维尔思又在法国蒙比利埃(Montpellier)的德·克利斯托尔(de Christol)的一个岩棚里发现了一些人类的骨骼和鬣狗、犀牛的骨骼放在一起。1830年他出版了《关于洞穴人类骸骨的简介》(Notice sur les Ossements Humains des Cavernes du Gard)一书。受这些著作的影响和鼓舞,P.C.施梅林(P.C.Schmerling)开始在比利时的列日(Liege)发掘一些洞穴,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在昂日(Engis)发现的洞穴,他发现了一些人类的头盖骨,许多人工制品,其中有些和犀牛及猛犸象的骨骼放在一起。他在1833年出版的著作中写道:“毫无疑问,这些人类的骸骨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原因的情况下,和这些灭绝动物的骸骨埋葬在一起的。”但是他的这种看法没有引起他同时代人认真的思考。之后,爱德华·泰勒于1871年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也用了“prehistory”这个词。在19世纪后半叶,“史前”一词不仅在英格兰,而且也在法国、瑞士、德国、北欧诸国、西班牙和意大利流行开来。并把它作为对人类过去历史研究的一个特殊的、有别于其他阶段的专门术语来使用。当然,这个词在各国自然有所不同,其含义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法文prehistoire,意大利文preistoria,德文Vorgeschichte都是后来才有的,而丹麦文oldtid则是自古就有的。史前通常是指人类过去最为古老的时代,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时间最早而又最长的一个阶段。史前考古学家始终是个考古学家,因此,史前考古学(prehistoric archaeology)是和史前学(prehistory)同义的。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对人类起源和初始阶段文化的兴趣是自然和正常的,在图内尔和丹尼尔·威尔逊用“史前”一词之前,人类的早期历史的研究就早已开始了。
在西方思想史上,只有极少数的思想家才曾经推测人类的历史必然有一个更为古老的石器时代。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出于要论证罗马文化高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曾经提出过“人类是从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状态”的主张。[45]古人曾经有意或无意地涉及到石器的使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注意到了古埃及人为了给尸体涂抹防腐剂而使用燧石制成的小刀;《旧约·约书亚记》第5章第3节中描述约书亚给以色列儿童施行割礼用的是“燧石刀”。赫西俄德(Hesiod)在《神谱》中曾提到克洛诺斯在地母的授意之下用燧石制成的大镰刀割下其父的生殖器。[46]卢克莱修(Lucretius)以一种哲学家的洞察力,想象人类必然有一个石器、铜器、铁器时代的连续:“那时候没有壮健的人驶着歪曲的犁,也没有人知道用铁器去耕作田地。”“之后慢慢地铁的刀剑兴起了,铜制的镰刀就转而受人鄙夷。”[47]不过他们都没有明确意识到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一个石器时代。
英国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在1830~1833年出版了《地质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Geology)。他在1863年出版的《古人类的地质证据》(The Geological Evidences for the Antiquity of Man)一书中支持约翰·弗里尔的看法:古人类存在是无可置疑的,认为在25年前,就连(比利时)列日大学的教授们都出来证明他的不屈不挠精神和目光锐利的同胞的诚实性。与他同时代的专门研究洪水的英国地质学家迪安·科尼比尔(Dean Conybeare)认为,赖尔的《地质学原理》一书由于在科学的进步中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其本身就具有充分的重要性。还有人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深受赖尔《地质学原理》的影响。不过,在整个18世纪,极少有学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可能有一段漫长的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直到19世纪,考古学家才开始接受“旧石器时代”的概念。
虽然发掘的技术在考古学活动最早的50年中很少得到改进,但序列(sequence)这个从地质学和历史学中借来的重要概念却变得愈来愈清晰,并有效地运用在早期考古报告中。这个发育不全的概念被有效地用来对遗址所隐含的连续变化作出记录,也正是这种记录使按年代次序记载成为可能,从而构成了文化发展的观念。[48]1784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首先采用了地层学(stratigraphy)原理去进行发掘。[49]杰斐逊还写下了《关于维吉尼亚州的笔记》(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一书,对印第安人史前土墩的起源产生了很大兴趣。他挖掘了一个土墩并认识到其中的骨骼是按照层次(strata)一层又一层地排列的。以至于最高的土墩有12英尺高。莱曼—哈特莱本(Lehmann-Hartleben)说:杰斐逊的发掘“提前接近了现代考古学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此外,杰斐逊还强调树轮年代学(dendrochronology)的价值。它是根据对树轮的分析,去测定古代气候及其变化趋势的科学,至今仍然在使用。
到了1865年,史前的观念已推进到这种地步,以至于英国博物学家约翰·卢伯克(后改名为洛德·埃夫伯里(Lord Avebury))出版了一本当时很畅销的书,书名就叫做《史前时代》(Prehistoric Times)。《史前时代》这本书畅销了几乎半个世纪,到1913年它出第7版后几个月,卢伯克就去世了。到1932年时,它已经出了17版。卢伯克在《史前时代》中坦言:欧洲最早人类的出现,其时代是那样的遥远,以至于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传统的角度,都无法对他们的起源及生活方式有哪怕是丝毫的了解。卢伯克接受了法国考古学家把史前时代和后来的历史区分开来的做法,但他发明了“Palaeolithic”(旧石器时代)和“Neolithic”(新石器时代)这两个词。旧石器时代是“一个漂泊不定的时代,那时的欧洲人还和猛犸象、洞熊、长着羊毛似的卷毛的犀牛以及其他灭绝动物生活在一起”。而新石器时代则是“石器时代的后期或是磨光石器的时代,其时代特征就是由燧石或其他石头制成的光滑的武器和工具,不过,在那个时代里,除了黄金之外,还没有发现当时的人类具有对任何其他金属的知识的踪影,黄金有时被用来制作装饰品”。
丹麦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安·于恩森·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是最早把欧洲史前时代划分为石器、青铜和铁器三个连续时代的人。在1838~1843年间,他积20年考古工作的经验,完成了《北方考古指南》(Skandinaviska Nordens Urinvanare)一书。汤姆森的学生,另一位丹麦考古学家J.J.A.沃尔索(J.J.A.Worsaae)对汤姆森的三分法加以修正,使之更为精确。沃尔索也是首先提倡野外发掘的创始者,所以被称之为科学考古学的奠基人。但三分法终于被卢伯克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四时期说所代替,直到19世纪60年代还在被使用。不久,旧石器时代本身还要进一步被划分这一点变得愈来愈清楚了。在霍克斯尼遗址所发现的手斧和索姆河谷发现的墓葬被认为具有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特征,而从法国南部岩石棚发现的石器则具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特征,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发现总是和法国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爱德华·拉尔泰(Edouard Lartet)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本来是热尔(Gers)省的地方行政长官,为爱好古生物学而抛弃了法律。1852年,一个在法国上加龙省(Haute-Garonne)奥瑞纳(Aurignac)地方工作的修路工人把他从一个兔子洞里掏出来的人骨交到拉尔泰的手里,出于好奇,拉尔泰继续发掘,发现一个被一块石片挡住了的岩棚,里面埋葬着17具人类的骨架,它们和一些灭绝动物的残留物、燧石、象牙工具以及骨雕埋在一起。而在基督教仪式中,却实行着人类骨架二次葬的习俗,这种区别直到拉尔泰的发现之前一直未受到人们注意。实际上,这是一种葬礼仪式的残留物。最初,拉尔泰也认为这是一种新石器时代集体埋葬的方式,后来他改变了看法,宣告它们是新石器时代之前的墓葬。在1860年,拉尔泰又勘探了另一个位于阿列日河(Ariege)马萨(Massat)附近的佩里明(Pyrenean)洞穴,发现在炉灶的旁边放着驯鹿的骨骼、燧石工具、带钩的鱼叉、骨针以及雕有熊头形象的一片鹿角。这些发现连同他和安德烈·布鲁耶(Andre Brouillet)在1834年和1845年在维纳(Vienne)的查菲特洞穴(Chaffaud)发现的一块雕有两只驯鹿形象的鹿骨一起发表于1861年。
查菲特洞穴发现的这块鹿骨往往被许多史前考古学家看作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史前雕刻。布鲁耶和其他一些人认为它是克尔特人(Celte)的作品,而拉尔泰认为它是非常早的作品,并对从查菲特洞穴、奥瑞纳遗址、马萨等处所发现遗存的古老深信不疑,实际上,所有这些都属于我们现在统称为“法兰西—坎塔布连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Franco-Cantabrian Upper Palaeolithic art)范畴,它专指在法国西南部和西班牙坎塔布连山区北部发现的奥瑞纳文化期和马格德林文化期的艺术传统,距今约40000~10000年,其艺术类型包括岩画、小型雕像及骨雕、牙雕等。著名的阿尔塔米拉洞穴和拉斯柯洞穴(Lascaux)都属于它的范畴。从1863年起,拉尔泰又开始对一系列遗址和洞穴进行发掘,包括拉马德莱娜洞穴(La Madeleine)和勒穆斯捷(Le Moustier)等著名遗址和洞穴。在此期间,拉尔泰受到了一个英国银行家亨利·克里斯蒂(Henry Christy)的资助。在1864年他们合作出版了一本书,本来计划好的是一部巨著,由于克里斯蒂在1865年去世,拉尔泰在1871年相继去世而被搁置。但这部巨著后来终于由鲁珀特·琼斯和约翰·伊文思编辑,在1865~1875年间出版,书名为《阿基坦的古生物化石:法国南部的佩里戈尔文化及其比邻的省份对考古学和古生物学的贡献》(Reliquiae Aquitanicae:being contributions to the Archaeology and Palaeontology of Perigord and the adjoining provines of Southern France)。它是一部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发展的划时代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拉尔泰认为对勒穆斯捷、拉马德莱娜等遗址和洞穴的考察“虽然简单地按照石器使用的年代顺序作出了区分,但没有伴随着对周边动物的考察,以及把人类对工具的制造集合在一起进行比较,以作出各个阶段并不具有同一性的结论。”W.博伊德·道金斯(W.Boyd Dawkins)采用了和拉尔泰同样的方法按照石器使用的年代顺序,在1874年出版了《洞穴狩猎》(Cave Hunting)一书。
19世纪下半叶,英国考古学家弗林德斯·皮特里发明了地层断代法,并把它用之于耶路撒冷城南泰勒哈希遗址的地层分析。从此结束了以往盲目发掘的方法。然而,到了那时,考古学家更加喜爱那种基于物质残留物的分类。卢伯克四时期的分期框架也显得过于宽泛了,它被进一步细化。这样,拉尔泰对旧石器时代晚期进行了区分,他假设不同的阶段可以建立在某一时代特有的动物的基础上。他制定出旧石器时代的分期的初步方案,这种分期是按照地层所发掘到的主要动物的骨骼来划分的。分期如下:
一、河马期。当时的原始人类在露天生活,并制作圣—阿舍利(Saint-Acheul)类型的石斧。这种文化层处于老的河床的底层。
二、洞熊和猛犸象期。法国的勒穆斯捷是这一文化层的代表。这一阶段和奥瑞纳期的来临相衔接,正是在这一时期,在韦泽尔地区,有丰富的燧石工具、象牙、骨质和角质的工具、锐利而经过打磨的工具一起出现。
三、驯鹿期。驯鹿在这一时期频繁出现并占有主要地位,最初驯鹿和马、牛一起出现,后又出现了牡鹿。有两种石器工艺同时并存。这是一种革命性的假设,它介绍了一种完全新的原则——一种对考古学上的残留物的分类却是建立在非考古学的材料上的。
后来,法国史前考古学家加布里埃尔·德·莫尔蒂耶(Gabriel de Mortillet)认为,尽管某一地区和某一时代的一切动植物能通过发掘者的发掘去断定它所处的时代的气候是冷还是暖,也能够和冰河期活动的地质学证据相联系,但它们并不能再作进一步的细分了。因此,他在1881年的《史前博物馆》(Musee prehistorique)和1883年的《史前时代》(Le Prehistorique)中,又在拉尔泰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莫尔蒂耶对拉尔泰的分期用考古学上的术语作了重新解释,重新分期如下:
一、把河马期称之为阿舍利文化期(Acheulian)。它是人类处于最早的直立人和早期智人之间的漫长时期,延续时间有100万年。
二、把洞熊和猛犸象期称之为穆斯特文化期(Mousterian)。
三、把旧石器时代晚期分为两期:(一)梭鲁特文化期(Solutrean);(二)马格德林文化期(Magdalenian)。欧洲旧石器时代艺术的黄金时代始于梭鲁特文化期。梭鲁特文化最早是以在法国索恩—卢瓦尔省(Saone-et-Loire)的梭鲁特(Solutre)地方发现的骨雕而著称。后来,他在1882年出版的《史前时代:人类的古代》(Le prehistorique: antiquite de l'homme)中,又进一步把旧石器时代分为五期,即:舍利文化期(Chellean)、阿舍利文化期(Acheulian)、穆斯特文化期(Mousterian)、梭鲁特文化期、马格德林文化期等。约翰·伊文思采纳了莫尔蒂耶的分期法,但直到19世纪结束,奥瑞纳文化期(Aurignacian)的地位始终未能决定。直到1909年,法国著名考古学家H.步日耶又在莫尔蒂耶的分期基础上,在穆斯特文化期和梭鲁特文化期之间加入了奥瑞纳文化期,并得到学术界的公认,这种旧石器时代的六期分期法直至目前仍然作为欧洲史前考古学分期的主要依据。“自1900年以来,年代学研究的重要进展部分是考古学上的;部分则是地质学上的。在考古学上,H.步日耶尤为著名。在1905年,他和E.卡塔尔克(E.Carthailac)、L.卡皮唐和D.佩龙等考古学家一起完成了许多发掘工作,确立了奥瑞纳文化期的地位,从那时起直到1909年才赢得了世界的普遍接受。人们可以从J.德谢莱特(J.Dechelette)1908年的《考古学指南》(Manuel d'Archeologie)一书中发现,从那时开始,舍利文化期、阿舍利文化期、穆斯特文化期、梭鲁特文化期、奥瑞纳文化期、马格德林文化期和阿齐利文化期(Azilian)的分期次序才算真正确立。”[50]
过于宽泛的“史前”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之前已遭到严厉的批评。在20世纪上半叶,有4件事情促使了这个划时代的概念变得更加黯然失色。第一,是欧洲处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和中石器时代早期之间的阿齐利文化的发现。第二,是法国考古学家加布里埃尔·德·莫尔蒂耶对旧石器时代的分期从法国扩大到欧洲、非洲甚至渐渐扩大到世界的其他地区,但是法国的分期框架有时并不能普遍适用于其他地区。第三,是由于史前史学家全神贯注于欧洲的现代原始民族,对考古学理论和一些专门名词的运用在爱琴海和近东地区得到了发展。例如,当海因里希·谢里曼在希腊的梯林斯(Tiryns)和迈锡尼(Mycenaean)研究考古遗物时,并没有把它们进行分期,哪些属于石器时代,哪些属于青铜时代,他认为它们全部都是迈锡尼文明的遗物。同样,英国考古学家阿瑟·伊文思(Arthur Evans)也把他从发掘克里特岛上的克诺索斯(Knossos)古城所得的遗物看作是属于米诺斯文化的。当时,“爱琴文明(Aegean)”、“基克拉泽斯文化(Cycladic)”、“希腊青铜文化(Helladic)”都被用来指一种文明或一个人种,而不是指一个时代。在那些研究欧洲西北部地区的考古学家看来,所有地中海地区的这些文明在性质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第四,在20世纪早期,考古学家所全神贯注的是从人文地理学和人类学中派生出来的一些观念。人类学家和人文地理学家(Anthropogeographers)则研究现代原始民族,并把这些都纳入了文化的范畴,而“史前”的概念对他们来说都显得太宽泛了。[51]
按照保罗G.巴恩和让·韦尔蒂(Jean Vertut)最新的研究,对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分期如下:[52]
沙泰勒佩龙文化期(Chatelperronian) 始于公元前35000年
奥瑞纳文化期(Aurignacian) 始于公元前30000年
格拉维特文化期(Gravettian) 始于公元前25000年
梭鲁特文化期(Solutrean) 始于公元前20000年
马格德林文化期早期(Early Magdalenian) 始于公元前15000年
马格德林文化期中期(Middle Magdalenian) 始于公元前13500年
马格德林文化期晚期(Late Magdalenian) 始于公元前10000年
阿齐尔文化期(Azilian) 始于公元前8000年
沙泰勒佩龙文化期是以法国和西班牙北部的沙泰勒佩龙人(Chatelperronian)的文化来命名的。沙泰勒佩龙人是早期的克罗马侬人的一种变种。法国和西班牙的沙泰勒佩龙人创造了穆斯特文化的人工制品以及用来制造刀具和矛头的石片。以上的分期严格地说,是为欧洲洞穴艺术的分期而制定出来的,它对世界其他地区并没有普遍意义。
一般说来,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存在着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但也有例外。例如非洲大部分地区都不采用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这些概念。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非洲旧石器时代考古”条:“在撒哈拉以南的东非、西非和南非地区,发展的情况与欧洲有所不同,因此使用了一套单独的分期体系:早期石器时代,从最早的石器出现到大约10万年前;中期石器时代,从大约10万年前到1.5万年前;晚期石器时代,从大约1.5万年前到铁器时代的开始。”[53]因此,在非洲的某些地区,可以作这样的等式:“早期石器时代”等于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石器时代”等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石器时代”等于旧石器时代晚期。[54]A.J.H.古德温(A.J.H.Goodwin)和C.冯·利特·洛(C.Van Riet Lowe)在《南非石器时代的文化》(The Stone Age Culture of South Africa)一书中专门讲到过这一点。所以“Middle Stone Age”,有的英汉词典把它译为“中石器时代”,实际上是误译,应该译为“中期石器时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譬如,不久前在报纸上看到有一篇题为《人类7.5万年前就佩戴珠宝》的报导,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在南非印度洋沿岸的‘布隆博斯洞穴’中新发现了不少贝壳,贝壳位于中石器时代地层中,经测定有7.5万年历史。”世界上怎么可能有7.5万年前的“中石器时代”?这明显是对“Middle Stone Age”的误译所致。
在史前考古学断代的问题上,没有比碳14的断代法的发明更重要了。威拉德·弗兰克·利比(Willard Frank Libby)因在1949年研制出碳14的断代技术,于1960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这种用放射性碳同位素测量物质中辐射性碳素含量来断代的方法,在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为考古学上的断代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对史前时代考古学上的残留物的断代来说,尤其如此。后来,牛津大学的一批学者又在考古学和艺术史的实验室里发明了热释光法(Thermoluminescence),简称TL,它是一种利用把结晶质和玻璃质加热到摄氏450度时发出的光去测定矿物和古代残留物年代的方法,特别适用于石器和陶器的断代,但由于放射性元素会产生衰变,因而会影响它的精确度。1969年,唐·布拉泽维尔(Don Brothwell)和埃里克·希格斯(Eric Higgs)编了一本书,名为《考古学中的科学:对进步和研究的眺望》(Science in Archaeology:a survey of progress and research),对各种应用在考古学中的科学技术进行了探讨。
在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由于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几乎都是在欧洲发现的,因此,欧洲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成了人们讨论的焦点。当然,“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艺术”和“最早的旧石器时代的艺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现在所发现的欧洲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最早不超过35000年前。但这个记录已被史前考古学不断地刷新。在20世纪末,在澳大利亚那诺米替发现的一件岩雕,据说已有45118年的历史。
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特别死板,延续的时间特别长,它们几乎没有采用任何发明创造的能力,甚至也许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发明创造的能力。它们依靠一套固定的习俗,仪式和禁忌,以及相应的神话和信仰体系实现自我维持。旧石器时代占现代人类历史全部时间的99.5%。[55]
旧石器时代是一个漫长而又在文化发展上不成比例的时代。它的早期约有200万年,中期约有20万年,而晚期只有3~4万年。也就是说,在整个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生命中的99%是在毫无变化和进展的时间中度过的。有一位史前学家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假如将地球生物的整个进化过程浓缩为一年,那么就是:1月1日,生命诞生;12月31日下午5点左右,猿人诞生;晚上11点40分左右,尼安德特人降生;而剩下的20分钟就是智人(homo sapiens)的一生——即从石器时代直至今日。[56]整个旧石器时代人类进展的步伐是那样的缓慢,直到最后的10万年情况才开始产生变化,人类只是在最后的3.5万年前,才产生出了真正的艺术。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的确可以说史前艺术是它惟一的亮点,无怪许多人类学家都把史前艺术的出现用“创造力的爆炸”一词来形容。“我们相信艺术是人类顶天立地、别开生面的发明,时间是在4万年前。也就是说,我们花了696万年蜕化猿性,终于在4万年前修成正果。”[57]
【注释】
[1]转引自H.步日耶(H.Breuil)和R.朗捷(R.Lantier):《旧石器时代的人们》(The Men of the Old Stong Age),伦敦、多伦多、惠灵顿和悉尼1965年版,第15页。
[2]埃德蒙·波尼翁:《公元1000年的欧洲》,中译本,2005年版,第62~63页。
[3]参见罗德尼·斯达克和罗杰尔·芬克:《信仰的法则》,中译本,2004年版,第98页。
[4]罗素:《宗教与科学》,中译本,1982年版,第25~26页。
[5]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发现特洛伊——寻金者谢尔曼的故事》,中译本,2006年版,第149页。路德维西认为:“他(谢里曼)找到的荷马时代的特洛伊其实是荷马之前的特洛伊。……今天,我们知道,在特洛伊的最下面一层地里挖掘出的一切,那些断垣残壁,兵器,甚至黄金本身,都是比谢里曼所寻找的那个荷马世界要早大约一千年的时代的产物。”见同上书,第6页,序言。马克斯·穆勒(Max Müller)则“以一种很恰当的方式称谢里曼的发现与荷马毫无关系:‘你知道我多么不赞同你的解释……它们的核心不是历史而是传奇,但这些传奇又与历史与真实的地理情况相联系。不过,虽然我怀疑是否你财宝中的某些东西曾被海伦触摸过,但是我得承认,这个曾被你坚定不移并认真地考察过的地方由于从中能了解当地的文明史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见同上书,第189~190页。
[6]詹姆斯A.贝尔(James A.Bell):《重建史前史:考古学中的科学方法》(Reconstructing Prehistory:Scientific method in archaeology),坦普尔大学1994年版,第22页。J.L.迈尔斯(J.L.Myres):《谁是希腊人?》(Who Were the Greeks?),伯克利1930年版,第xxvi页。
[7]参见威廉A.哈维兰(William A.Haviland):《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纽约1975年版,第353页彩色插图。
[8]伦纳德·伍利:《死城与活人》(Dead towns and living men),纽约1959年版,第1~2页。转引自弗兰克·霍尔(Frank Hole):《史前考古学介绍》(An introduction to prehistoric archeology),纽约1973年版,第25页。
[9]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和C.伦弗罗(C.Renfrew)著:《史前史的观念》(The idea of prehistory),爱丁堡大学1988年版,第157页。
[10]T.K.彭尼曼:《人类学100年》,伦敦1935年版,第14页。
[11]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中译本,1988年版,第1页。
[12]格林·丹尼尔:《考古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伦敦1982年版,第13页。(www.zuozong.com)
[13]沃尔特·泰勒(Walter Taylor):《考古学研究》(A Study of Archeology),伦敦1967年版,第37页。
[14]E.M.休姆:《历史学和它的邻居》(History and Its Neighbours),牛津大学1942年版,第147页。
[15]格雷厄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史前史面面观》(Aspects of prehistory),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1970年版,第4页。
[16]格雷厄姆·克拉克:《史前欧洲的经济基础》(Prehistoric Europe;the economic basis),伦敦1952年版,第1页。
[17]A.R.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结构与功能》,英汉对照本,2007年版,第1卷,导论。
[18]贾兰坡、甄朔南:《千里追踪猎化石》,1981年版,第43页。
[19]G.艾萨克(G.Isaac):《考古学何去何从?》(Whither archaeology?),载《古代》(Antiquity)杂志1971年第45卷,第123页。
[20]格林·丹尼尔和C.伦弗罗著:《史前史的观念》,爱丁堡大学1988年版,第158页。
[21]沃尔特W.泰勒:《考古学研究》(A Study of Aecheology),伦敦1967年版,第5页。
[22]沃尔特W.泰勒:《考古学研究》,伦敦1967年版,第41~42页。
[23]莫蒂默·惠勒:《陆地考古学》(Archaeology from the earth),巴尔的摩1956年版,第228~229页。
[24]罗伯特·洛伊:《人种学理论史》,纽约1937年版,第22页。
[25]詹姆斯A.贝尔:《重建史前史:考古学中的科学方法》,坦普尔大学1994年版,第22页。
[26]刘易斯R.宾福德:《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载《美洲的古代》(American Antiquity)杂志,1962年第28卷,第217页。
[27]刘易斯R.宾福德:《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载《美洲的古代》杂志,1962年第28卷,第225页。
[28]刘易斯R.宾福德:《人种志材料在考古学上的使用其方法论上的理由》(Methological considerations of the archeological use of ethnographic data),载R.B.李(R.B.Lee)和I.德沃尔(I.DeVore)编:《人,狩猎者》(Man,the hunter),芝加哥1968年版,第268~273页。
[29]刘易斯R.宾福德:《考古学的工作》(Working at Archaeology),纽约1982年版,第23页。
[30]M.埃格特(M.Eggert):《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载《加拿大西部人类学杂志》(Western Canad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1976年第6卷,第57页。
[31]刘易斯R.宾福德:《考古学的工作》,纽约1982年版,第51页。
[32]刘易斯R.宾福德:《考古学的工作》,纽约1982年版,第67页。
[33]刘易斯R.宾福德:《考古学的工作》,纽约1982年版,第425~426页。
[34]G.R.威利(G.R.Willey)和P.菲利普斯(P.Phillips):《美国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Method and Theory in American Archaeology),芝加哥大学1958年版,第2页。
[35]F.奥杜和安德烈·勒鲁瓦—古昂:《法国;一种欧洲大陆的褊狭》(France;a continental insularity),载《世界考古学》(World Archaeology)杂志,1981年,第13卷,第170~189页。
[36]戴维·克拉克:《分析的考古学》(Analytical Archaeology),伦敦1968年版,第13页。
[37]克里斯托弗·戈斯登:《人类学和考古学,一种变化的关系》(Anthropology and Archaeology,A changing relationship),伦敦和纽约1999年版,第1~11页。
[38]R.惠伦:《人类学的考古学杂志》(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1982年创刊号的编辑介绍,第1~4页。
[39]布鲁斯·炊格尔:《时间与传统》,中译本,1991年版,第20页。
[40]参见霍斯特·塞德勒(Horst Seidler)等:《史前蒂罗尔冰人的人类学面面观》(Some Anthropological Aspects of the Prehistoric Tyrolean Ice Man),载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1992年,第258卷(11月,第6期),第455~457页。参见保罗G.巴恩(Paul G.Bahn)编:《考古的故事——世界100次考古大发现》,中译本,2002年版,第99~101页;戴尔·布朗编:《早期欧洲·凝固在巨石中的神秘》,中译本,2002年版,第105~114页。
[41]史蒂夫·吉尔伯特编:《文身的历史》,中译本,2006年版,第280~281页。
[42]格林·丹尼尔和C.伦弗罗:《史前史的观念》,爱丁堡大学1988年版,第1页。
[43]格林·丹尼尔:《考古学简史》,伦敦1982年版,第48页。
[44]参见图内尔:《自然科学史》第XVIII卷,第244页。
[45]西塞罗:《讲演集》(De Oratore),第1卷,第8节。
[46]赫西俄德:《神谱》,中译本,1991年版,第31页。
[47]卢克莱修:《物性论》,中译本,1981年版,第321、341页。
[48]弗兰克·霍尔:《史前考古学介绍》(An introduction to prehistoric archeology),纽约1973年版,第66页。
[49]罗伯特F.海泽(Robert F.Heizer):《考古学家的工作》(The archeologist at work),纽约1959年版,第218~221页。
[50]T.K.彭尼曼:《人类学100年》,伦敦1935年版,第232页。
[51]格林·丹尼尔:《考古学简史》,伦敦1982年版,第148页。
[52]保罗G.巴恩和让·韦尔蒂:《冰河时代的形象》(Images of The Ice Age)纽约1988年版,第16页。
[53]《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1986年版,第123页。
[54]何芳川和宁骚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1995年版,第34、45页。
[55]E.拉兹洛(E.Laszlo):《进化——广义综合理论》,中译本,1988年版,第95页。
[56]转引自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中译本,2005年版,第17页。
[57]杰拉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第三种猩猩》,中译本,2004年版,第175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