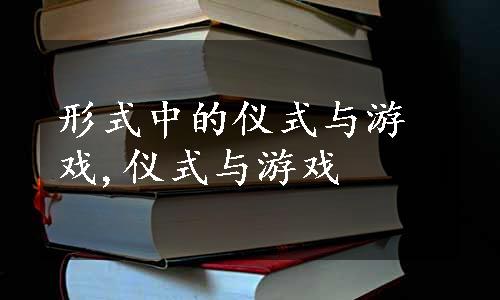
第四节 仪式与游戏
列维—斯特劳斯曾经说过:“而要研究礼仪,我们就应该往游戏理论的方向探索。游戏由一套规则来定义,而这套规则可以演变出无数的赛局,礼仪就像一场特殊的比赛,它出现在所有可能的赛局之中。”[64]可见,仪式和游戏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最早把仪式看作是种游戏是现代荷兰著名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按照他的看法,游戏要比文化还古老。不管人们对“文化”怎么下定义,它必须以社会的存在为先决条件,而游戏则不然,动物也游戏,而且无需人类教给它们游戏。因此可以断言,游戏并非人类文明的产物,也非人类文明的一种必要补充,因此它的产生就必然非常古老。如果这种几乎覆盖了人类日常生活中所有事物的与生俱来的心理倾向事实上都根植于游戏,那么我们将面临非常严肃的问题:游戏的态度必然在人类文化和语言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我们可以发现,游戏有一种它自己明确的行为特质,正是这种特质使它和日常生活相区别。它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模式,一种“有意义的形式”,如果我们能够把游戏作为游戏来加以探讨,即探讨它的原始意义,那么就可以发现它总是建立在某种形象化的操作上,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即把现实转化为形象,因此重要的是要把握这些形象和想象的价值和意义。
由于游戏的古老性,人类社会最巨大的原型活动从一开始起就被游戏所渗透。以神话为例,它就是外部世界的一种变形或想象,只有在神话的领域里,语言的加工使它更显华丽。原始人类处于神性力量的包围之中,在神话思维中,人们试图对现实世界作出解释,富于想像力的精神总是在认真和玩笑之间来回嬉戏。最后,我们可以以祭礼仪式为例子。原始社会所履行的各种神圣的祭礼,它的各种献祭、典礼和秘密的宗教仪式,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世界的安宁。“正是在这些祭礼仪式中,一种纯粹的游戏精神才能被真正理解。正是在这种神话和祭礼仪式中,文明生活的巨大潜在力量开始萌芽:法律和秩序,商业和利润,手艺和艺术,诗歌,智慧和科学,所有这一切都无不根植于原始时代游戏的土壤之中。”因此,他认为祭礼仪式是一种游戏。
按照赫伊津哈的看法,所有祭礼仪式中都包含着游戏的因素,造型艺术也不例外:不管造型艺术和音乐的区别有多大,仍然可能在造型艺术中发现游戏的因素。在古代文化中,艺术作品的地位和作用很大一部分都和祭礼仪式相关,它被看作是种具有神圣意义的对象。无论建筑、雕像、衣着、武器的装饰美化,都从属于宗教世界。当它们作为一种神秘实体出现之际,都具有巫术的力量,并充满着符号价值。由于祭礼仪式和游戏的关系是那样的密切,因此在艺术作品的创造和鉴赏中不能发现它的游戏性质,那倒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拟人化和幻想作品必然有一个遥远的过去。人类学和比较宗教学告诉我们的是,神的拟人化和兽性形式中的精神在古代宗教中都是一种最重要的因素。受崇拜的兽形神的幻觉是整个图腾崇拜的基础。”[65]
赫伊津哈把祭礼仪式作为追溯游戏起源的出发点,在检验了游戏的概念并指出它的一些主要特征之后,赫伊津哈还指出那种导致祭礼仪式的过程是很难为我们所接近的,但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够说它的形象的产生过程或形象化是一种诗化作用,更明确地说也就是游戏作用,也可以说是种滑稽作用。如果我们把游戏作为一种文化作用而不是把它看作像动物或儿童身上所显现出来的那种东西,那么可以说,我们开始的地方也正是生物学和心理学所要结束的地方。秩序井然的游戏不是游戏,儿童和动物之所以游戏是因为它能使他们快活,能精确地显示出他们的自由状态,它把美和崇高推向顶点,又把严肃性远远地抛在脑后。它无关利害,永远处于欲望的满足之外,并把自己变成一种昙花一现的活动。祭礼和神话正好处于各种欲望的直接满足之外的领域。它们像游戏一样,以同样的理由而有着自己的领域。
我们现在常常说“游戏规则”,究竟什么是“游戏规则”?在赫伊津哈的著作里,这一点也有所启示。在他看来,游戏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空间性。所有游戏都在一块场地上进行,它预先以有形或无形的观念划出一定的界域,这块特殊的空间就和神圣的惯例构成了联系。从形式上看,“神圣区域”是和游戏场地不可分的。无论是牌桌、魔圈、神殿、舞台、屏幕、网球场、法院在形式上都是一种游戏场地,凡是一块闲人免进的场地,一块篱笆围起来的孤立的被视为神圣的场地都会获得一种特殊的规则。按照他的这种思路推演下去,必然会达到这样的结论:由游戏创造出来的规则也就是游戏规则。每一种游戏都有它自己的游戏规则。例如,象棋有象棋的规则,扑克有扑克的规则,你不能把象棋的游戏规则用到扑克中来,反之亦然。
祭礼仪式中游戏所处的特殊地位即它拥有的那种神秘气氛,它和其他活动的差异最生动地表现在穿戴漂亮,甚至化妆或戴上面具,使某人扮演另一个人,另一种存在物,而他就是那个存在物。游戏过程有它自己的时空限制,并按照固定化了的规则进行,并助长社会群体的形成。基于对游戏的分析,赫伊津哈在祭礼仪式中发现许多重复出现的游戏因素,但祭礼仪式总是非常严肃而且带有神圣的意味,那么它可能是种游戏吗?他的解答是这样:就我们的思考方式而言,游戏当然是和严肃性相对立的,乍看起来,这种对立之于游戏是无法缩减的。然而,只要更为缜密地考察一下就能发现,游戏和严肃性的对立既非是决定性因素又非固定不变的。我们可以说游戏是不严肃的,但这种说法并没有真正揭示游戏的特质,它是容易反驳的。一旦我们认为“游戏是非严肃的”,“游戏是不严肃的”,我们就在作茧自缚了。因为某些游戏可以是非常严肃的。例如,在某种意义上,对立于严肃性的笑声就并非是游戏所必需具备的,无论是儿童游戏、足球比赛、棋赛都是非常严肃认真的游戏,在这些游戏中,游戏者哪怕是最轻微的笑的倾向都不会有。儿童在全神贯注地游戏时也是神圣的,就像一个运动员那样,他以全部热情和狂喜进行游戏,在自己的王国里忘掉现实,游戏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把游戏者送进另一个世界中去。
“祭礼仪式意味着某种表演,一种演出活动,它是一种扮演,或具有某种演出的要素,是一种戏剧,它是一种呈现于舞台的演出,一种表演或一种竞赛。祭礼活动或‘祭礼演出活动’可以再现宇宙的产生或发生在自然过程中的一个事件。不过,‘再现’一词并不能精确覆盖这种演出活动的意义,至少在比较宽泛的现代意义上并非如此。因为这里神话所要再现的事件只是一种确认。”[66]
在祭礼仪式中,有些东西是不可见的、不真实的,例如祭礼的参与者认为一些动作会带来赐福的效果,所有这一切,通过扮演的现实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留下了游戏的形式特征。因此,祭礼、巫术、膜拜、洗礼、圣餐等等,都将不可避免地纳入游戏的概念之中。祭礼活动有着游戏的形式和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他也承认祭礼活动有它自己的本质。和儿童的游戏相比较,就不难发现祭礼仪式有更多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它比单纯的游戏所创造出来的虚幻现实要多一点东西,它是一种神秘的游戏,一种神秘体验的现实化。例如古代印度整个吠陀的祭献仪式都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上:通过再现某种渴望得到的宇宙事件,仪式通过祭献、竞赛或演出,去迫使神灵把他幻想中的事件变成现实。而这一切我们可以说都是通过游戏来完成的。人的意识先是全神贯注于神圣活动,渐渐这种神圣活动中渗入了游戏成分,祭礼就移植在它上面,但最基本的还是游戏。
伽达默尔(H.-G.Gadamer)曾经对约翰·赫伊津哈的理论表示认同。他说:“赫伊津哈已经在所有文化中研究了游戏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他解决了儿童游戏及动物游戏和‘神圣游戏’(holy play)之间的联系。这导致他认识到了在游戏者意识中那种反常的不明确性,正是这种不明确性使人们想在信仰的游戏和非信仰的游戏之间作出区别是绝对不可能的。赫伊津哈说:‘野蛮人自己并不知道存在和游戏之间的概念区别,他们对形象与符号之间的同一性同样一无所知,这就是为什么当人们即使把游戏看作是一种原始活动,也未必就能在野蛮人神圣的活动中真正了解他们的心理条件。而在我们的游戏观念中,信仰和虚假之间的区别也就这样消解掉了。’因此,游戏先于游戏者的意识,这是最基本的常识。”伽达默尔还指出:“宗教仪式(religious rite)和剧场中所表演的游戏明显和儿童游戏并不具有同样的意义。它们不像儿童游戏那样,耗尽其所有精力仅仅是为了他自己。无论是宗教仪式中的游戏还是剧场中的游戏都是超越了游戏者本人而面对着注视他们的观众。游戏不再是安排就绪的一种动作的自我表现,也不是像儿童全神贯注于其中的游戏,而仅仅是为了‘某些人而表演’。……在宗教仪式中神的呈现也就是一个神话在游戏中的呈现。”[67]
在所有的祭礼仪式中,节日的仪式和游戏最接近,两者都宣告日常生活处于暂停状态,都处于享乐原则的支配之下;两者都受时空的限制;都把严格的规则和真正的自由联结在一起。为了论证庆典的祭礼仪式和游戏的同一性,赫伊津哈引证了当代匈牙利比较宗教学家卡洛伊·凯伦伊(Karoly Kerenyi)的观点,认为所有祭礼都是庆典,所有庆典都是游戏。例如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的科拉印第安人(Cora Indians)在玉米快要成熟和烤玉米的神圣节日里,把他们为最高神所表演的舞蹈称之为“游戏”(play)。按照凯伦伊的说法,节日所具有的最重要、最纯粹的特征依赖于游戏。他把节日看作是一种有“自主权”的文化概念:“在精神的现实性中,节日是一种自在之物,它不能和世界上其他任何东西相混淆。”而节日的这种现象被人种学家完全忽略了。[68]
但祭礼有种附加的心理因素,它和游戏有两点区别:一、它与现实有种更深、更基本的联系;二、它有一种特殊的心理状态,一种参加庆典特有的赞美和严肃的气氛。祭礼仪式无需制定规则,它本身就是规则,人们在这种规则下生活,并决定着人对现实的各种印象。庆典和节日是重复的,但它们都被原始的创造力所感染,这类自我的再创造不可能不重复。原始人也知道这一点,但他不辞劳苦地重复祖先的宗教需要,这是他必须遵循的宗教原则。正是在每次宗教活动的重复中,创造性因素才保留了下来,只要这种重复一旦停止,那么创造性因素也就会立即停止。
其他一些学者也有类似于赫伊津哈的看法。例如R.R.马雷特认为,所谓神圣仪式,就是一种由观众“参与的演出”。认为在所有原始宗教中都存在着一种“假扮”的因素。无论是巫师还是魔法师,对于这一点完全是心知肚明的,但他终得去选择这种“欺骗”。“野蛮人是个好演员,他们能完全沉浸于自己的角色,就像儿童在游戏时那样;并且他们也能像儿童那样,成为一个好观众,即使明明知道他眼前并不是一只真狮子,他也会为一只假狮子的咆哮而怕得要死。”[69]
在遥远的过去,人类首先去把动植物的生命现象进行神化,而后才构想出时间、空间、月份、季节、太阳、月亮等等种种被神化了的观念。在一种神圣化了的仪式性游戏中,人类不但沉浸于其中,而且一再重复,以为这样做就能有助于宇宙秩序的维持。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古人所理解的自然秩序是作为他意识中的东西而存在的。莱奥·弗罗贝尼乌斯(Leo Frobenius)从这种“自然现象的演出”中引申出更为重要的结论,认为正是在这里所有社会获得了它的原始政体的形式。国王就是太阳,王权就是太阳运行路线的形象化。[70]在弗罗贝尼乌斯看来,在祭礼仪式中,游戏完全要服务于宇宙事件的再现,并且这也是游戏因素之所以能够出现的原因;而在赫伊津哈看来,恰恰相反,祭礼仪式整个重点在于游戏,祭礼仪式中的游戏因素和儿童游戏以及动物游戏并无本质的区别。
有人认为,在原始民族的重大宗教节日里,人们相互祝贺就足以证明他们并非处于一种幻觉之中,而只是处于一种“非现实”的心态之中。他们的仪式演出总会具有一种隐蔽的严肃性。[71]在列维—斯特劳斯看来,“游戏与仪式之间也存在着同一种类型关系。……我们很容易举新几内亚人的‘加虎库’游戏(Gahuku-Gama)这个例子来说明。……这就是说把游戏当作仪式来对待。弗克思印第安人在举行接纳(adoption)仪式时所做的游戏也是这种性质,他们的目的是用一个活人来替换一个已死的亲戚,这样才容许死者的灵魂永别人世。”[72]
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原始民族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舞蹈总是构成了宗教仪式的中心:“对土著来说,舞蹈既是一种娱乐,又是一种仪式。”[73]在仪式性舞蹈中,同一种动作总是被不断地重复,这是有原因的:不断地重复可以减少传递思想时的暧昧不明。有节奏地重复同一动作是多数仪式的特征。原始人类的艺术主要也是在仪式中发展的。信号越简单就越不会发生错误,建造一个回应信号的接受者也越容易。“假若没有传统的仪式和风俗,人类决不可能形成一个大于原始家庭团体的社会单位。……没有一个人,甚至最伟大的天才,能够独自发明一套社会标准和仪式的系统,以便代替文化传统。”[74]
仪式的存在是全球性的,它和戏剧的相似性曾为许多学者所注意。南非社会人类学家马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1930年后在南非纳塔尔省(Natal)从事对祖鲁人(Zulus)的研究工作。他把祖鲁人的仪式看作为一种“社会戏剧”,认为仪式“并不仅仅是凝聚力和社会价值及社会情绪的简单表现,就像E.涂尔干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理论所论证的那样,仪式确立了群体对被夸大了的社会冲突的蔑视”[75]。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是最早研究中非恩登布人(Ndembu)的人类学家。他深受马克斯·格拉克曼把仪式看作为一种“社会戏剧”的影响,认为:“恩登布人所赖以维系的最广泛的社会结合体,其作用主要依赖于世代相传的仪式系统。”[76]仪式在恩登布人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恩登布人来说,狩猎仅限于男人的活动,并被高度仪式化了。仪式的主持者组织了狩猎仪式,但他并不是固定村落的酋长,而是那些居无定所的人。他到处流浪,也到处演出,这样,他的表演就会比仅仅是地方村落的共同体成员具有更为广泛的代表性,也能引起更大的兴趣。
许多原始民族的艺术形式完全是仪式的产物。在祭礼仪式的歌唱和舞蹈中,每个参与者都处在一种由韵律和节奏所产生的催眠效果中摆脱了对现实的意识,和现实的分离是以独特的方式进入到潜意识的幻像世界中去的,这种幻像对每个成员都是共同的。正是在这种幻像的内心世界中,他们恢复了去进行新的活动的能力,“仪式中的模仿性诗歌和舞蹈,也就是一种被强烈的巫术所提高了的说话和姿态。在很长的期间内,诗歌和舞蹈依赖于它们共同的起源和作用,变成是不可分离的”[77]。
仪式和游戏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它们之间很难区分谁先谁后的问题:“情感很难成为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仪式的充分的因果解释。这种论证就像许多社会学的论证一样,是一种循环论证——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仪式产生欢腾,欢腾产生信仰,信仰导致仪式的举行。”[78]李安宅先生曾于1935年在美国加州大学进修社会学时,实地考察了祖尼人(Zuni)的生活状况。祖尼人分布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西部,1935年时有2036人;1970年时有7300人。在他对祖尼人舞蹈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宗教性质的舞蹈也仍然具有明显的娱乐性。在祖尼人种类繁多的舞蹈中,有6种最基本的纯宗教性戏剧舞蹈,这6种舞蹈是:特卡奎纳舞(teakwena,有鼓伴奏)、图瓦特卡奎纳舞(towa teakwena,无鼓伴奏)、渥特蒙拉舞(wotemla,有鼓伴奏)、图瓦渥特蒙拉舞(towa wotemla,无鼓伴奏的混合舞)、穆卢克塔卡舞(muluktak'a)以及荷迷西依奎舞(hemiciikwe)。除这些基本形式外,还有从其他部落学来的舞蹈,可分为假面舞和非假面舞两种,后者完全是娱乐性的。“这些舞蹈多多少少都有些严肃性,就跟祖尼人自己的舞蹈一样。非假面舞完全是为了娱乐。”[79]不过,有些原始民族的游戏明显有着巫术的成分。例如“巴芬岛的爱斯基摩人用线绳游戏(jeu de ficelle)阻滞太阳的消失;他们用杯球游戏(bilboquet)催促太阳回归。桑波依尔人(Sanpoil)认为,他们在冬天玩杯球游戏会缩短一年的长度。……人们用猪的脊椎骨玩杯球游戏,以使月亮亏得更快。”[80]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最早出现“游戏”两字的是《史记·周本纪》:“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把农耕的起源看作是种游戏的结果。可见,在太史公看来,游戏是可以成就一番大事业的。借助于考古学的成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已经有了以舞蹈为中心的仪式体系。为什么要说以舞蹈为中心呢?虽然在新石器时代时代,歌唱、打击乐器、吹奏乐器和舞蹈都已经产生,但是,没有乐器和歌唱的舞蹈,仍然是舞蹈,而没有舞蹈的音乐,没有舞蹈的歌唱,几乎就没有意义。因为歌唱和音乐都是为了舞蹈的节奏而存在的,它们服务于舞蹈,从属于舞蹈。《礼记·乐记》:“钟鼓管磬,羽龠干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到了音乐充分发展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乐器都只是“器”,而舞蹈却是“文”。这也就是古人对舞蹈的看法,也可以说是一种舞蹈本体论的看法。
中国古代的艺术,无论是歌唱、音乐还是舞蹈,都和仪式相关。常任侠先生曾根据安阳殷墟出土编磬上的刻文,从文字学的角度,解释了古代的歌唱和舞蹈的起源问题。他说:安阳殷墟曾发现编磬三具,曾经《双剑簃古器物图录》著录,上刻类似殷代的甲骨文字,一为“永启”,一为“永余”,一为“夭余”。“永”后代作“詠”或“咏”,即歌唱,如“歌永言,声依詠,律和声”。“夭”即舞人侧首而舞的姿态,加上口为吴,可以引人娱悦为娱。“夭”字到后来变为轻盈款摆的形容词,用以形容少女的艳丽或花枝的美好,其初皆本于舞蹈的姿态。[81]这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舞蹈中心论的痕迹。磬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可以直接和《尚书》中所说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相印证。最原始的舞蹈大概连最起码的石制打击乐器都没有,全靠舞蹈者的双手来拍出节奏。这就是舞蹈从一开始便能独立于其他艺术形式的原因。
最近,我国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面具,它们都有一些孔可以作佩戴用。在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发现的刻陶假面面具和面饰作品残片较多,完整或基本完整者10余件。在出土的陶片中,面具或面饰陶片约占总数的10%。假面面具的大小与真人面部相同,面饰作品则一般在10厘米左右。平面浅浮雕,单面雕刻,具体技法为阳刻、阴刻、镂空相结合。多用减法刻出凹面与凸面,再用阴刻法勾勒出线条。图案内容有人面、兽面(包括猪、猴、猫科动物)等。艺术风格兼具写实性、象征性和装饰性。据推测,刻陶假面面具可能是祭祀或巫术驱疫时的辅助神器,用来装扮神祇或祖先。这批刻陶面具和面饰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面具。它们的绝对年代为距今8000至7000年间。这些面具的出土不但对我们研究古代的祭祀活动和歌舞艺术提供了实物证据,而且对我们研究戏剧的起源也有极大的价值。[82]
图1 我国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出土的刻陶假面面具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两件面具都有着孔,可以供眼睛观看,可见当时戴着面具的人是可以做各种舞蹈动作的。可以肯定,它们是神话剧上所使用的面具。早在新石器时代,神话剧就已经产生了。这是史书上没有记载的活的历史。由此可见,考古学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去印证史书的记载,而是要去找回那早已被湮灭了的真正存在过的历史。此外,另一件西周时期的兽形青铜面具已在1985年从一批企图走私到国外的文物中找到,它上部留有穿孔,可供佩戴。眼孔稍突出,鼻子部分最为突出,无嘴部,可能是为了便于歌唱和说话。它出土于河南禹县,古称夏邑,相传夏代禹王曾在此建都。[83]这些早期的面具未必和后来的“傩”有什么关系。
戏剧的核心在于演员的出现,演员的本质在于自我的丧失而进入到角色,而第一个戴上面具的人,就意味着演员的诞生。所以,我们的戏剧史应该以新石器时代面具的出现来作为开始。
仪式和艺术之间的联系是毋庸置疑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说过:“如果没有仪式庆典,没有哑剧和舞蹈,以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戏剧,没有舞蹈、歌曲,以及伴随着的器乐,没有社群生活提供图样,打上印记的日常生活的器皿与物件,远古的事件在今天就会湮没无闻了。”[84]仪式是多种多样的,有学者认为,不能随便使用“图腾”的概念。“牛是佤族的图腾似乎是人所共知的定论了……但很多人对佤族剽牛、分食牛肉的习俗又深感困惑……这样疯狂地对待图腾动物、分食图腾动物似乎与崇拜二字相抵触。”[85]又如在独龙族中的剽牛祭天仪式,每年秋收后,祭坛之中,置芭蕉柱墩,直径半米,用毛绳把牛拴于木柱上,巫师奋臂将矛刺入牛的胸膛,牛剧痛狂奔,“三转舞蹈至此,迎头遮阻,又刺一矛。人越喧吼,牛更蹦跳。以为如此便可感通天神。”[86]这些描述都可以在古代遗留下来的青铜器中得到印证。在云南晋宁石寨山曾出土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其中一些就涉及剽牛的习俗。但是,这种“游戏”毕竟对动物太残酷,因此它始终局限于某一地区,并且最终没有被保留下来。把它看作是图腾崇拜的遗迹,则是毫无根据的。
【注释】
[1]R.R.马雷特:《人类学》(Anthropology),纽约和伦敦1911年版,第8、10页。
[2]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人类学理论的兴起》(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哥伦比亚大学1968年版,第142页。
[3]T.K.彭尼曼(T.K.Penniman):《人类学100年》(A Hundred years of Anthropology),伦敦1935年版,第48页。
[4]A.R.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eliffe-Brown):《原始社会结构与功能》,英汉对照本,2007年版,第1卷,导论。
[5]维柯:《新科学》,中译本,上册,1989年版,第178页。
[6]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中译本,2006年版,第2卷,第503页。
[7]达尔文:《贝格尔舰环球航行记》,中译本,1998年版,第538~539页。
[8]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中译本,2006年版,第1卷,第107页。
[9]R.威廉斯:《关键词》(Keywords),纽约1976年版,第77页。
[10]理查德·芒奇(Richard Munch)和尼尔J.斯梅尔策(Neil J.Smelser)编:《文化理论》(Theory of Culture),伯克莱、洛杉矶、牛津1992年版,第43页。
[11]拉尔夫·林顿:《个性的文化背景》(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Personality),纽约1945年版,第XVI页。
[12]安德鲁·兰(Andrew Lang):《安德鲁·兰献给泰勒文集的前言》(Lang's Preface in Essays Presented to Tylor),伦敦1908年版。
[13]埃德蒙·利奇:《论“创始人”》(On the“Founding Father”),载《邂逅》(Encounter)杂志,1966年,第7卷,第561~564页。
[14]约翰·卢伯克:《史前时代:古代残留物和现代野蛮人生活方式及习俗的说明》(Pre-Histonic Times,as Illustrated by Ancient Remains and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Modern Savages),伦敦1865年版,第416页。
[15]B.马林诺夫斯基:《社会科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文化”条目,纽约1931年版,第4卷,第621~646页。
[16]B.马林诺夫斯基:《美拉尼西亚西北部野蛮人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 western Melanesia),伦敦1948年版,序言。
[17]B.马林诺夫斯基:《美拉尼西亚西北部野蛮人的性生活》,伦敦1948年版,第34~35、37页。
[18]M.约翰逊(M.Johnson):《考古学理论导论》,中译本,2005年版,第136页。
[19]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纽约1889年版,第1卷,第427页。
[20]詹姆斯·弗雷泽:《图腾与外婚制》,伦敦1910年版,第1卷,第54页。
[21]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中译本,2006年版,第2卷,第484页。
[22]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遥远的目光》,中译本,2007年版,第28页。
[23]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和罗杰尔·芬克(Roger Finke):《信仰的法则》,中译本,2004年版,第101页。
[24]塞缪尔·贝克:《尼罗河流域的种族》(The Races of the Nile Basin),伦敦1867年版,第231页。
[25]R.R.马雷特:《宗教的开端》(The Threshold of Religion),伦敦1909年版,序言。
[26]阿兰·邓迪斯(Alan Dundes):《西方神话学读本》,中译本,2006年版,第131页。
[27]参见弗雷德里克J.斯特伦(Frederick J.Streng):《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中译本,1991年版,第290~291页。
[28]A.R.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中译本,2005年版,第243、98、78页。
[29]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研究》(Study of Sociology),中译本,2001年版,第88页。
[30]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论人》,中译本,2006年版,第120页。(www.zuozong.com)
[31]玛丽·道格拉斯:《圣洁与危险,对亵渎和禁忌观念的分析》(Purity and danger,An analysis of the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以下简称《圣洁与危险》),伦敦1966年版,第1页。
[32]转引自米尔恰·埃利亚代(Mircea Eliade):《熔炉与坩埚》(The Forge and The Crucible),纽约1962年版,第176页。
[33]参见罗伯特·洛伊(Robert Lowie):《人种学理论史》(The History of Ethnological Theory),纽约1937年版,第24、25页。还有人曾经说过:在白尼罗(White Nile,今属苏丹)的丁卡人(Dinka)、希卢克人(Shilluk)、努埃尔人(Nuehr)、基奇人(Kytch)、博尔人(Bohr)、阿利亚布人(Aliab)和希尔人(Shir)中,除基奇人外,其他原始部族都没有对神灵的信仰,既无偶像崇拜或其他崇拜,也无任何迷信活动。
[34]K.T.普罗伊斯:《宗教和艺术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Religion und Kunst),载《地球仪》(Globus),不伦瑞克1904~1905年版,第LXXXVI卷。
[35]K.T.普罗伊斯:《宗教的发展与退化》(Entwicklung und Ruckschritt in der Religion),载Zeitschriftf Missionskunde und Religionswissenchaft,柏林1932年,第XLVII卷。
[36]卡尔·贝思(Karl Beth):《原始部族中的巫术与宗教》(Religion und Magie bei den Naturvolkern)。
[37]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巫术的理论》(Theorie de la Magie),载H.于贝尔(H.Hubert)编:《社会学的人类学》(Sociologie et Anthropolgie),巴黎,1950年版。
[38]E.E.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中译本,2002年版,第54页。
[39]罗德尼·斯达克和罗杰尔·芬克:《信仰的法则》,中译本,2004年版,第10页。
[40]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讲演集》,中译本,2007年版,第29页。埃德蒙·利奇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一书,整个都是为了批驳列维—布留尔而写的。“该书的基本论点是,如果我们像列维—布留尔那样认为原始人的‘前逻辑’思维和现代人的‘逻辑’思维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历史对立的话,那就错了”。见埃德蒙·利奇:《列维—斯特劳斯》,中译本,1986年版,第100页。
[41]阿道夫·詹森:《原始人中的神话和祭礼》(Myth and cult among primitive peoples),芝加哥大学1963年版,第17、18、3页。
[42]W.冯特:《神话与宗教》,载《民族心理学》,莱比锡1906年版,第2卷,第307~311页。
[43]S.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载《弗洛伊德全集》,伦敦1981年版,第13卷,第27页。
[44]H.S.休斯(H.S.Hughes):《意识与社会》,纽约1958年版,第145页。
[45]阿诺尔德·范·根纳普:《过渡礼仪》(The Rites of Passage),伦敦1960年版,第13页。
[46]E.E.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中译本,2002年版,第46~48页。
[47]罗德尼·斯芬克和罗杰尔·芬克:《信仰的法则》,中译本,2004年版,第10页。
[48]E.E.埃文斯—普里查特:《原始宗教的理论》(Theories of Primitive Religion),牛津1965年版,第15、17页。
[49]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猞猁的故事》,中译本,2006年版,第205页。
[50]玛丽·道格拉斯:《危险与过失》(Risk and Blame),伦敦和纽约1992年版,第3页。
[51]转引自罗伯逊·史密斯(Robertson Smith):《关于闪米特人的宗教的讲演》(Lectures on the Religion of the Semites),爱丁堡1889年版,第20页。
[52]阿诺尔德·范·根纳普:《过渡礼仪》,伦敦1960年版,第14~16页。
[53]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讲演集》,中译本,2007年版,第234页。
[54]F.M.柏格尼渥(F.M.Bergounioux)和约瑟夫·戈茨(Joseph Goetz):《史前时代与原始宗教》,伦敦1965年版,第22页。
[55]G.H.吕凯(G.H.Luquet):《化石人的艺术和宗教》(The art and religion of fossil man),纽黑文和伦敦1930年版,第165~166页。
[56]L.卡皮唐(L.Capitan)和D.佩隆(D.Peyrony):《人类学评论》(Revue anthropologique),第xxxi期,第382~388页。
[57]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神话简史》,中译本,2005年版,第2~3页。
[58]T.D.麦科恩(T.D.McCown):《化石妇女》(Fossil Woman),载《时代》杂志,1937年3月号,第17~18页。
[59]凯伦·阿姆斯特朗:《神话简史》,中译本,2005年版,第36页。
[60]史蒂夫·吉尔伯特(Steve Gilbert)编:《文身的历史》,中译本,2006年版,第126页。
[61]《祖先的声音——非洲神话》,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中译本,2003年版,第45页。
[62]参见A.R.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中译本,2005年版,第55、180页。
[63]米尔恰·埃利亚代:《宇宙创生神话和“神圣的历史”》,载阿兰·邓迪斯:《西方神话学读本》,中译本,2006年版,第177页。
[64]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讲演集》,中译本,2007年版,第245页。
[65]约翰·赫伊津哈:《文化中的游戏因素的研究》(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伦敦、波士顿1980年版,第14、15、167、141页。
[66]约翰·赫伊津哈:《文化中的游戏因素的研究》,伦敦、波士顿1980年版,第15页。
[67]H.-G.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Truth and Method),纽约1989年版,英译本,第104、108~109页。
[68]卡罗伊·凯伦伊:《庆典的本质》(Vom Wesen des Festes),莱比锡1938~1940年版,第1卷,第59~74页。
[69]R.R.马雷特:《宗教的开端》,伦敦1909年版,第48页。
[70]莱奥·弗罗贝尼乌斯:《非洲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 Afrikas),莱比锡1932年版。
[71]阿道夫E.詹森:《原始民族中的割礼和性成熟仪式》(Beschneidung und Reifezeremonien bei Naturvolkern),斯图加特1933年版。
[72]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中译本,2006年版,第36~37页。
[73]A.R.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中译本,2005年版,第91、92页。
[74]参见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攻击的秘密》,中译本,2000年版,第303页。
[75]马克斯·格拉克曼:《东南非洲反叛的仪式》(Rituals of Rebellion in South East Africa),载《非洲部落的秩序和反叛》(Order and Rebellion in Tribal Africa),伦敦1963年版,第18页。
[76]维克托·特纳:《非洲社会中的分裂与连续》(Schism and Continuity in an African Society),纽约1957年版,第292页。
[77]乔治·汤姆森(George Thomson):《希腊悲剧诗人与雅典》(Aeschylus and Athens),1941年版,第63~64页。
[78]E.E.埃文思—普里查德:《努尔人——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中译本,2002年版,第81页。
[79]李安宅:《关于祖尼人的一些观察和探讨》,载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2005年版,第84页。
[80]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神话学:餐桌礼仪的起源》,中译本,2007年版,第164页。
[81]常任侠:《古磬》,载《文物》,1978年第7期。
[82]《2004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5年版,第10~11页。插图采自该书第11页。
[83]飒焱:《从文物走私犯手中夺回珍宝》,载《文物天地》杂志,1987年,第3期。
[84]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中译本,2005年版,第363页。
[85]杨兆麟:《原始物象》,2000年版,第67~69页。
[86]王均:《独龙族的剽牛祭天》,载《民族调查研究》,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1985年第3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