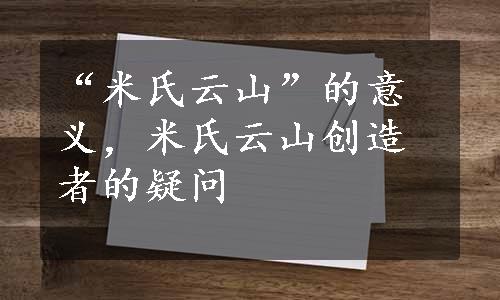
“米氏云山”的意义
提 要:米氏云山是通过简约董、巨山水画风,并结合墨戏的观念,而创造的士夫墨戏山水,这是士大夫开始有意识寻找属于自己山水画语言的开始。这种基于墨戏的山水画简约画法,影响了元明清的山水画格局,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
有关米芾的研究很多,本文只作针对性的讨论。
《宣和画谱》卷十《山水叙论》:“自唐至本朝,以画山水得名者,类非画家者流,而多出于缙绅士大夫。”士大夫对于山水画的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但士大夫开创了山水画的典范,而且完善和系统化了山水画的理论,使画诀上升为画论,并进一步与中国古代哲学精神联系起来。这个情况在有画论之初即产生,即宗炳《画山水序》已明确指出山水画是味道之物,是仁智之乐。系统的山水画论应以今传《笔法记》为代表,其中的“六要”,虽然还有画诀的痕迹,但从其中雅言的内容来看,也很可能出自士大夫画家之手。到了北宋郭熙,其《山水训》始将画诀与仁智之乐联系起来。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画山水序》所强调的味道与仁智之乐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北宋末的韩拙则又结合《笔法记》,对《林泉高致》的理论进一步深入讨论。山水画的理论至此,可谓大备。但我们如果注意到这些理论,虽然意识到“仁智之乐”是山水画追求的最高境界(这表现为隐逸文化的特点),但最终在技法上,还受当时尚理思潮的影响,并没有使技进于道,其所主张的画法与“仁智之乐”并不匹配,这便暗示着将有一种新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意义在于,使山水画技法与仁智之乐的追求统一起来,这便是“米氏云山”。
一 不同的典范
明王世贞说:
张彦远,顾恺之、张僧繇之功臣也;刘道醇、郭若虚,则李成、范宽、关仝之功臣也;米元章、沈括,则董源、巨然之功臣也。道子小损于元章,二李微疵于若虚,虽各尊所知,不无意味。(《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十五《艺苑巵言附录四》)
王世贞的意思可以这样看,即在画史的作者来讲,某一时代具有影响的代表性画家,并没有绝对性,这与画史作者的趣味、选择关系很大。由于趣味的影响,北宋中期,郭若虚等所看到具有典范意义的画家,是李成、关同、范宽这样的人。这有其原因,或者是因为当时风气便是如此,而的确有很多人学他们,这种风气也可能影响画史作者的选择。但是,稍晚的沈括与米元章则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注意到沈括对于绘画的看法有时常与画史不同。这暗示着当时还存在另外一股潜流,即与主流画史不一样的审美追求,这种追求最终导致在比《图画见闻志》稍晚约20年的《画史》中[1],开始确立了另外两种师法的典范,即董源和巨然。
在郭若虚所树立或发现的典范中,以李成、关同、范宽为代表。《图画见闻志》卷一《论三家山水》:“画山水惟营丘李成,长安关同,华原范宽,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跱,百代标程。”郭若虚所以确立这三家典范者,最重要的是他们各自影响了一批人。但其中,除了李成是士大夫之外,关同、范宽似乎都是专业画家。虽然关、范的师承可以上溯到传为业儒的荆浩,但到了他们的确只能作为专业画家来看了。当然,从另外一方面看,这些传承中,专业画家和士大夫画家是混杂的,由李成等人创立的山水画的典范,是人人可学的,并不具有身份和境界追求的针对性。也因为这个原因,习尚三家者,有士流,也有杂流。所以,即便是士夫画家如荆浩、李成,开创了山水的典范,但这种典范最终的影响者,既有画工,也有士夫画家。这种典范尚未与仁智之乐,与脱俗的精神追求匹配起来。而郭若虚树立的三家,一方面具有历史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不是绝对的,也和他的审美取向有关系。
但是,这稍后的一段时间,正是北宋画坛“多事”之秋,正是绘画风尚发生转变的时期。沈括是较早谈论董源、巨然的。《梦溪笔谈》卷十七:
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其后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宛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
可以说,沈括已经注意到董巨与一般所见的山水画(奇峭之笔)不同之处。这除了地理的原因之外,还涉及笔法。但沈括对于董巨,还没有从根本上将他们的地位确立如李成、关同、范宽一样。这个工作,则是由米芾来完成的。
米芾对于董、巨的注意,可能在他居镇江以后,在与沈括这样一类人物交往中形成的。按米芾(1051—1107)《画史》:
1.巨然师董源,今世多有本,岚气清润,布景得天真多。巨然少年时,多作矾头,老年平淡趣高。
刘道士亦江南人,与巨然同师。巨然画则僧在主位,刘画则道士在主位,以此为别。
董源平淡天真多,唐无此品,在毕宏上。近世神品,格高无与比也。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岚色郁苍,枝干劲挺,咸有生意。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片江南也。
2.余家董源雾景,横披全幅,山骨隐显,林梢出没,意趣高古。
3.苏泌家有巨然山水,平淡奇绝。
4.董源峰顶不工,绝涧危径,幽壑荒迥,率多真意。
巨然明润郁葱,最有爽气,矾头太多。
5.颍州公库顾凯之维摩百补,是唐杜牧之摹寄颍守本者。置在斋龛,不携去,精彩照人。前后士大夫家所传无一毫似,盖京西工拙,其屏风上山水林木奇古,坡岸皴如董源,乃知人称江南,盖自顾以来,皆一样。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谢氏亦作此体,余得隋画金陵图于毕相孙,亦同此体。
米芾所说“乃知人称江南,盖自顾以来,皆一样。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谢氏亦作此体”。则知江南画风亦久已存在,并非董巨始有,而此类画风,其于启发米氏应是毫无疑问的。按最后一段,应作于“拔发司”时。按蔡肇为米芾作的墓铭:
初补秘书省校书郎,授含光尉。七迁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县。乞监中岳庙,授涟水军,使除发运司勾当公事,蔡河拨发,入奉常为博士。(《清河书画舫》卷九下)
这个入奉常为博士,实际上是在蔡京为相之后提拔的,也就是在崇宁二年以后的事。蔡肇的墓铭也指出崇宁三年米芾“适官太常”。
从这两则材料来看,米芾注意到董、巨,也是晚年的事。而当时的审美风气,正是江南画风始渐上升到主流的时期。米芾在推崇董、巨之时,也同时指出,董、巨画风,不是这两个人独创的,而是有历史渊源的。这个历史渊源,在他看来,即从顾恺之开始,这种画风便已显现,而且在江南地区,这种画风是流行的。而郭若虚等人所看到的则是北方的山水。所以,如果说郭若虚发现三家,具有历史的客观性,那么也主要是对北方而言。而米芾发现董、巨,对江南而言,也具有历史客观性。这看似是因地域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实际上还暗示着一种更为根本不同的绘画主张。
我们还要注意到米芾对于“文人正规画”的批评。《画史》:
李公麟病右手三年,余始画。以李尝师吴生,终不能去其气。余乃取顾高古,不使一笔入吴生。又李笔神彩不高,余为目睛面文骨木,自是天性,非师而能,以俟识者,唯作古忠贤象也。
这是从人物画的方面来批评李伯时(吴道子)的,因为他们的作品在米芾看来不“高古”,这实际上指出了“文人正规画”的问题:画法与趣味的不统一。士夫画需要一种与之相匹配的画法,而不是借取画工的画法。
这种思想同样表现在山水画方面。而在山水画方面,这个困难仍然存在。《画史》:
余尝与李伯时言分布次第,作子敬书练裙图。图成,乃归权要,竟不复得。余又尝作支许王谢于山水间行,自挂斋室。又以山水古今相师,少有出尘格者,因信笔作之,多烟云掩映,树石不取细,意似便已。知音求者,只作三尺横挂,三尺轴,惟宝晋斋中挂双幅成对,长不过三尺,褾出不及椅所映,人行过肩汗不着,更不作大图,无一笔李成关仝俗气。
按“宝晋斋”,米芾《书史》:
余白首,收晋帖,止得谢安一帖,开元建中御府物,曾入王涯家。右军二帖贞观御府印,子敬一帖有禇遂良题印,又有丞相王铎家印记。及有顾恺之戴逵画净名天女观音,遂以所居命为宝晋斋。
则取此斋名时,已“白首”,应在其晚年。这与上面所说情况一致,即米芾在晚年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可以看到,与“高古”对应的,在山水画方面,米芾要追求“出尘格”,所以便“信笔作之”“意似便已”,这种画法,无疑是从董巨来的。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
1.北苑画杂树,但只露根,而以点叶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此即米画之祖,最为高雅,不在斤斤细巧。
2.董北苑画树,多有不作小树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树,但只远望之似树,其寔凭点缀以成形者,余谓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盖小树最要淋漓约略,简于枝柯,而繁于形影。欲如文君之眉,与黛色相参合,则是高手。
这将米氏云山与董巨的关系讲得很清楚。更重要的,是他在强调“信笔”和“意似便已”,实际上是墨戏的问题了,这同时也将山水画的技法简约化了。元吴师道《礼部集》卷十八《米元晖云山图》:
书法画法,至元章、元晖父子而变,盖其书以放易庄,画以简代密,然于放而得妍,简而不失工,则二子之所长也。
这是颇有见地的总结。
二 米氏云山创造者的疑问
米氏云山是在对董巨的发现、继承和脱化中发展起来的,在米芾,可能已具备其基本的规模。米友仁(1086—1165)至少是米氏云山的完善者。米友仁的意义在于,他将“墨戏”的问题,更加明确化了。但是,从现有文献上看,米氏父子,究竟谁是米氏云山的始作俑者,存在一些疑问。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九下《米芾》引蔡肇《故宋礼部员外郎米海岳先生墓志铭》谓:“其画山水人物,自成一家。尺缣寸楮,人以为玩。”而并没有说米芾何时作画的。按《画继》卷三:
米友仁,元章之子也。幼年山谷赠诗曰,我有元晖古印章,印刓不忍与诸郎。虎儿笔力能扛鼎,教字元晖继阿章。遂字元晖。元章当置画学之初,召为博士,便殿赐对,因上友仁《楚山清晓图》。既退,赐御书画各二轴。友仁宣和中为大名少尹,天机超逸,不事绳墨。其所作山水,点滴烟云,草草而成,而不失天真。其风气肖乃翁也。每自题其画曰:墨戏。
蔡肇墓铭也说:“踰年复召为书画学博士,便殿赐对,询落逮,因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晓图》。”但《宣和书谱》便把这个问题弄混淆了。《宣和书谱》卷十二米芾传谓:“兼喜作画,尝为《楚山清晓图》,曾非俗师所能到也。”这个错误,起于最初编纂之人,还是元初之人想当然地加进去的,不得而知。前面我们指出,意识到董源巨然的重要,在米芾,可能是晚年的事。另外,事实上,由于米芾作画时间,被认为是较晚的,所以,很难说此种画风的出现,在二米之间,究竟谁为先后的。李少龙《关于米芾绘画及其临画乱真问题的辨析》:
考李公麟病右手当在元符三年(1100),是年米氏整50岁,三年后他53岁,距去世仅四年。仅仅用四年短暂时间来从事人物画的学习和创作,显然不会有太高的成就。也只能是“自是天性,非师而能”了。(中略)与上述三家看法不同,在米芾过世几十年后,关于他“临移”书、画均可乱真的记载才大量涌现出来。(《南开学报》1997年第2期)
“上述三家”指米芾之友苏轼、蔡肇、庄绰。又55页注5谓:
从现有资料看,尚没有任何一位与米芾同时期的鉴赏家能够肯定确曾见过米氏的人物画作品。南宋邓椿在评定米芾的人物画创作时,所引证的资料也仅仅是米芾本人的上述记载而已。
也说米芾作画比较晚。以献其子友仁画来看,似乎其子能画在先。邓椿说米友仁画“肖乃翁”,可能指他所见或听说到米氏父子画风相似。而米芾作书画学博士时52岁,即在1102年(崇宁元年)。[2]若按上计,米芾为书画学博士,应在1104年以后(按因为是继他人之后的)。按以此计,距米芾死不过三四年的时间,而米友仁时年十八九岁。
按《画史》自叙计,则也是他才开始学画的时候。正因为他开始作(学)画,而其子友仁时不过十六七岁,已经有多年实践成熟之作,故上其图。米芾作画受其子影响是可能的。而董源、巨然的发现,也不应归功于米芾一人,而应归功于当时与米氏常有交往的士夫团体,从《画史》、《书史》,及其他资料来看,很有可能包括米芾、沈括、章惇、蔡京等人,而其子米友仁在这种氛围里,或早已先于其父而有成功的实践。如《赵氏铁网珊瑚》卷十一引淳熙辛丑(1181)尤袤题:
蔡天启作米襄阳墓志言,元符初,进其子所画万里长江图,时元晖年尚少,其小笔已知名当世矣。方此老无恙时,诸公贵人,求索者日填门,不胜厌苦,往往多令门下士效作,而亲识元晖二字于后。尝自言遇合作处,浑然天成。荐为之,不复相似。
尤袤所题将米芾进米友仁画的事更加推前,(可能是将时间记错了)而且说在那个时候,友仁已知名,是时米芾尚未作画,更说明米友仁作画并产生社会影响,在其父之先,这是完全可能的。
三 米氏云山的传承
尤袤的话透露出,在米友仁门下,有一些人能作米氏云山,这在南宋早期。但米氏云山在南宋产生了多大影响,尚须考察。南宋赵希鹄《洞天清录·米氏画》:
米南宫多游江浙间,每卜居,必择山水明秀处。其初本不能作画,后以目所见,日渐摹仿之,遂得天趣。其作墨戏,不专用笔。或以纸筋,或以蔗滓,或以莲房,皆可为画。纸不用胶矾,不肯于绢上作。今所见米画,或用绢者,后人伪作,米父子不如此。
朱熹《晦庵集》卷八十四《跋米元章下蜀江山图》:
米老下蜀江山,尝见数本,大略相似。当是此老胸中丘壑,最殊胜处,时一吐出,以寄真赏耳。苏丈粹中鉴赏既精,笔语尤胜。顷岁尝获从游,今观遗墨,为之永叹。庆元己未(1199)三月八日,新安朱熹仲晦父。
赵希鹄已经指出,南宋已经出现了米氏画的作伪。朱熹所见也坐实了这个情况。他说“米老下蜀江山,尝见数本”,尤袤谓米友仁自谓“荐为之,不复相似”,即说这类墨戏,重新再画也很难画得一样,所以同一内容能有数本,作伪的可能性很大。当然,这个作伪首先应和米友仁门下之人有关系。从米氏云山在南宋出现伪作或代笔的情况看,米氏云山在南宋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没有疑问的。
在《画继》所列的士夫画家中,尚未见有言师法米氏云山的。《图绘宝鉴》卷四所列南宋士夫画家中亦未见有言师法米氏的。《图绘宝鉴》卷四却记载了一位金朝学米氏云山的士夫画家:
李仲略,字简之,大定进士,官至山东按察使。画山水,尝临米元章楚山图。
金朝人画米氏云山,是否受吴激影响不可得知。[3]
宋末元初的龚开学米氏云山。《图绘宝鉴》卷五:
龚开字圣与(中略)画山水师二米,画人马师曹霸,描法甚粗,尤善作墨鬼钟馗等画,怪怪奇奇,自出一家。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十八《霍元镇规模董北苑、米南宫父子,写山水云物、殊有缥致,见示春江捕鱼图,遂赋此》。元傅与砺《傅与砺诗文集》卷三《方少府云山图》:“岳阳方君嗜山水,妙墨千金不论价。好事林生偶相得,乘兴能为米家画。”元王逢《梧溪集》卷四《赠醉墨生徐贻》:“生也醉墨心醉画,落笔迥夺天人精。首法米南宫,继习北苑董。”元刘仁本《羽庭集》卷二《题米元晖青山白云卷》原注:(www.zuozong.com)
世之图青山白云者,率尚高房山,而又多赝本,殊不知房山盖学米氏父子。慈溪乌性善,出此幅示余,大不盈尺,而有江山无穷意态,聚画史观之,审定为米家物也。今房山不可得矣,况其师者乎。
元代学米最出名者当推高克恭。《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三:
高克恭字彦敬,(中略)画山水初学米氏父子,后乃用李成董源巨然法,造诣精绝。
则以学米氏云山著名的高克恭不但学米氏云山,而且上溯到董、巨,而且也学李成,似乎在探索折中的路子。而倪瓒则应是从这一脉下来的。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
1.倪迂在胜国时,以诗画名世。其自标置,不在黄公望、王叔明间。自云,我此画深得荆关遗意,非王蒙辈所能梦见也。然定其品,当称逸格,盖米襄阳、赵大年一派耳,于黄王真伯仲不虚也。
2.迂翁画在胜国时,可称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之上,历代唯张志和、卢鸿可无愧色。宋人中,米襄阳在蹊径之外,余皆从陶铸而来。元之能者虽多,然承禀宋法,稍加萧散耳。吴仲圭大有神气,黄子久特妙风格,王叔明奄有前规,而三家皆有纵横习气。独云林古淡天然,米痴后一人而已。
又《画禅室随笔》卷二:
山之轮廓先定,然后皴之。今人从碎处积为大山,此最是病。古人运大轴,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虽其中细碎处多,要之取势为主。吾有元人论米、高二家山书,正先得吾意。
又本卷:
米家山谓之士夫画。元人有画论一卷,专辨米海岳、高房山异同,余颇有慨其语。
这正暗示着元代人对于米、高(克恭)的认识已经达到一定的境界。则知元人学董、巨,乃首先在米芾对董、巨的推崇,故南宋学米,而元人上追董、巨。在元代,师法董巨的人增多,如赵雍、黄公望、吴镇、郑禧、王蒙、赵元、张文枢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通过米氏云山去理解董巨、学习董巨的。明张丑《真迹日录》卷一《董玄宰评画》:
子昂尝询钱舜举,曰,如何为士夫画?舜举曰,隶法耳。隶者以异于描,所谓写画须令八法通也。元人以米元章父子,与高房山侍郎为士夫画。然倪元镇又当为米颠配享,虽功力不同,远韵则一。大都元季,皆以董巨为师,如姚彦卿、唐子华,学郭河阳者,不复能与逸品争长矣。
董其昌虽然对隶家的解释不准确,但大体意思是可以理解的,而“逸品”的意义,在董其昌也讲得很清楚,它已不是不合绳墨的意思了,其意义已经是我们今天推崇的有逸气的逸品了。又《画禅室随笔》卷二:
云林山,皆依侧边起势,不用两边合成,此人所不晓。近来俗子点笔,便自称米家山,深可笑也。元晖睥睨千古,不让右丞,可容易凑泊,开后人护短径路耶。
则明人学米,似乎有些滥了。这也似乎说明董其昌只仿不学的原因。王世贞贬低米氏云山,是否也有这个原因,不得而知。
四 董其昌对米氏云山的评价
明代中后期王世贞对于米氏一脉的山水评价不高。《弇州四部稿》巻一百五十五《艺苑巵言附录四》:
张彦远,顾恺之、张僧繇之功臣也。刘道醇、郭若虚,则李成、范宽、关仝之功臣也。米元章、沈括,则董源、巨然之功臣也。道子小损于元章,二李微疵于若虚,虽各尊所知,不无意味。人物自顾陆展郑以至僧繇道玄一变也,山水大小李一变也,荆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李马夏又一变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赵子昂近宋人,人物为胜。沈启南近元人,山水为尤。二子之于古,可谓具体而微。大小米、高彦敬以简略取韵,倪瓒以雅弱取姿,宜登逸品,未是当家。
在他看来,大小米、高、倪均不是当家,即当行的,是行外的画。其实他的说法正与钱选与赵孟頫对话的内容相合。即那段著名的论断:士夫画是戾家画,即是非专业画。只是问题在于,如何认识戾家,即如何认识这不当行的问题。很显然,王世贞看来,不当行即是不入流的。他所说的“宜登逸品”的“逸品”,与唐朱景玄的“逸品”意思是一样的,即将此类画排除在主流之外。
王世贞的看法我们且不作评论。一代宗师,出入诸家,历经多年而后翻然有悟的董其昌,却持有与王世贞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说:
米元章作画,一正画家谬习。观其高自标置,谓无一点吴生习气。又云,王维之迹,殆如刻画,真可一笑。盖唐人画法,至宋乃畅。至米又一变耳。余雅不学米画,恐流入率易,兹一戏仿之,犹不敢失董巨意。善学下惠,颇不能当也。(《画禅室随笔》卷二《仿米画题》)
“一正画家谬习”是一个极高也极准确的评价。引申言之,这正道出了士大夫画在如何对待画工画,或者在不成熟的表现方式中寻求适合于己的画法的长期努力中,终于在米氏云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而这个方式不是凭空而来的,它也根基于一个来自江南的强大传统,即近可以上推至董、巨,上而甚至可以推到传说中的顾恺之。而米氏云山将这一传统与墨戏风尚结合起来,又形成了一个更加简约而又风格突出的典范,使米氏云山成为山水画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画禅室随笔》卷二:
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大家,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遥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李大将军之派,非吾曹易学也。
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要之摩诘所谓云峰石迹,迥出天机,笔意纵横,参乎造化者。东坡赞吴道子王维画壁,亦云,吾于维也无间然。知言哉。[4]
董其昌将米家父子放在山水之变中的重要位置,其眼光是卓越的。另外,他还肯定了米氏云山“墨戏”的意义。《画禅室随笔》卷二:
云山不始于米元章,盖自唐时王洽泼墨,便已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烟景,烟云变没,即米画也。余于米芾《潇湘白云图》悟墨戏三昧,故以写楚山。(《烟江叠嶂图》)
米氏云山给董其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绘画思想。《画禅室随笔》卷四:
1.米元晖作潇湘白云图,自题夜雨初霁,晓烟欲出,其状若此。此卷予从项晦伯购之,携以自随。至洞庭湖,舟次斜阳,篷底一望空阔,长天云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戏也。自此每将暮,辄卷帘看画卷,觉所携米卷为剩物矣。
2.湘江上奇云大似郭河阳雪山,其平展沙脚,与墨渖淋漓,乃是米家父子耳。古人谓郭熙画石如云,不虚也。
3.米元晖又作海岳庵图,谓于潇湘得画景,其次则京口诸山,与湘山差类。今海岳图,亦在余行笈中。元晖未尝以洞庭北固之江山为独胜,而以其云物为胜,所谓天闲万马,皆吾师也。但不知云物何心,独于两地可入画。或以江上诸山,所凭空阔,四天无遮,得穷其朝朝暮暮之变态耳。此非静者,何由深解。故论书者曰,一须人品高,岂非以品高,则闲静无他好萦故耶。
4.米元晖《楚山清晓图》,谓楚中宜取湖天空阔之境。余行洞庭良然。然以简书刻促,翰墨都废,未尝成一图也。
他的以境之奇怪论,则画决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决不如画,或正是从此而来的。按前引:
米元章作画,一正画家谬习。(中略)余雅不学米画,恐流入率易,兹一戏仿之,犹不敢失董巨意。
董其昌说:“雅不学米画,恐流入率易,兹一戏仿之。”实际上同时也指出了米画的不足。但这个问题,不是按王世贞他们的理解可以解决的。董其昌虽然不学米画,但对米画的意义是相当肯定的。他是以“仿”来通过米画而上推至董、巨,实际上通过此来达到与古人的精神沟通,《画禅室随笔》卷二《仿米家云山题》: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流云气,有吐吞变灭之势。米氏父子宗董巨法,稍删其繁复,独画云,仍用李将军钩笔,如伯驹、伯骕辈,欲自成一家,不得随人弃取故也。因为此图及之。
又本卷《孤烟远村图》:
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非右丞工于画道,不能得此语。米元晖犹谓右丞画如刻画,故余以米家山写其诗。
又本卷《题自画小景》:
赵令穰、伯驹、承旨三家合并,虽妍而不甜,董源、巨然、米芾、高克恭四家合并,虽纵而有法。两家法门,如鸟双翼,吾将老焉。
而实际上,正是董其昌通过画禅的实践对二米又有了进一步的突破,这是后话。
小 结
南宋初张元干《芦川归来集》卷九《跋米元晖山水》说:
士人胸次洒落,寓物发兴。江山云气,草木风烟,往往意到时为之。聊复写怀,是谓游戏水墨三昧,不可与画史同科也。
这是对于米氏云山很准确的总结。关于米氏云山的意义,我想强调几点:
首先,米氏云山,是北宋后期画坛审美风尚发生转变的产物,是士大夫开始有意识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山水画语言的开始,也是山水画中“文人正规画”向“文人墨戏”有意识转变的开始。
其次,米氏云山不但在技法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在绘画思想上,刺激了南北宗论和画禅说。
最后,从技法上看,米氏点法正预示了山水画的皴法有被消解的可能,这个在实践上,为近代的黄宾虹所实现。
[1]按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第150页:
是书乃陆续随记,据其自序二言“功名皆一戏”乃崇宁四年(1105)为言官弹劾而贬知淮阳军之心声,为其首生疡之前所毕事,即崇宁五年(1106)成稿。殆其绝笔之作,故体例不如《书史》较为整齐。
又149页谓其生卒年:
然今日辞书著录其生于皇祐三年,未注意及生于十二月,换算公元纪年应是1052年(辛卯十一月二十六日即公元纪年1051年12月31日)。
[2]按《宋史·徽宗本纪》:“崇宁三年六月,置书、画、算学。”又南宋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十二《元丰算学、崇宁四学、大观小学》:“崇宁三年六月壬子(十一日),建算学,书画学(都省上书画学勅令格式)。”南宋董更《书录》卷上《徽宗皇帝》:
长编云,崇宁三年六月壬子,都省言,窃以书学之用于世久矣,今欲依先王置学设官之制,考选拣拔,使人人自奋,至于今日,所有图画之技,与书一体,令附书学,为之校试,约束谨成书画学敕令格式一部,冠以崇宁国子监为名,并乞施行从之。
则书画学的创建,应在崇宁三年(1104)。而蔡京为相,按《宋史》本传,则应在崇宁二年正月。
[3]按《金史》列传三十四李仲略传:
仲略,字简之。聪敏力学,登大定十九年(1179)词赋进士第。(第2127页)
《金史》列传六十三:
吴激字彦高,建州人。父拭,宋进士,官终朝奉郎、知苏州。激,米芾之婿也。工诗能文,字画俊逸得芾笔意。尤精乐府,造语清婉,哀而不伤。将宋命至金,以知名留不遣,命为翰林待制。皇统二年(1142),出知深州,到官三日卒。诏赐其子钱百万、粟三百斛、田三顷以周其家。有《东山集》十卷行于世。“东山”,其自号也。(《金史》第2718页,中华书局,1975年7月)
吴激是米芾的女婿。
[4]董其昌所说的王维,也并非毫无根据,但可能是宋代所造出来的王维。王维被纳入文人南宗中,这和北宋后期对于王维的改造有关。因为这些改造造就了王维的江南形象,所以明人在推其源流时,自然会以为始祖,所以不能片面批评董其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