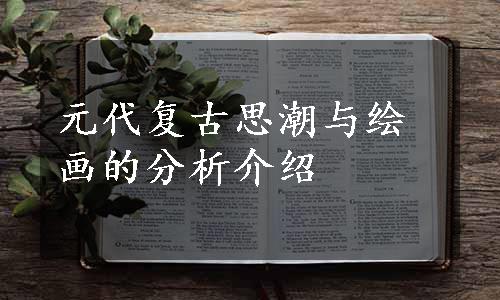
元代复古思潮与绘画
提 要:南宋社会风气渐入萎靡,与科举学校不无关系。表现在士风上,则是士的堕落,表现在文风上,则是矜奇好怪。此风流于元初,乃因而有复古思潮以对治之,于士风则讲理学之道德修养,于文风则讲探求古意,然皆以道德为指归。斯风所至,亦及于绘画,于是绘画之古意说出,强调质胜于文。然而理学在求道德实践之先天依据,而实难所得,则遭遇元末乱世,复古从宗唐转而推求平淡,于是与隐逸文化合一。
《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宪问》:“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又《阳货》:“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好古自孔子始,克己复礼,是以为仁。复古之风,曰复其制,曰复其意,而以复其意为复古之核心。古人之意,古制之意,曰古意。制度易求,古意难知。复古思潮的出现,往往是因时弊而产生的,其于艺术史、绘画史而言,也是如此。
复兴古代真理,应该理解为复古人之意。古意表面的含义,在礼乐制度的方面,指古人礼乐制度后面的哲学追求。作为礼乐思想的“古意”移入音乐理论,是很自然的事。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闻武则曰:尽美矣,未尽善也。作为乐的最高境界“尽善尽美”,大体即是此古意的内涵,它首先包含了道德判断。而文学方面,它更多地指古人的境界:这种境界无疑以道德境界为指归。古意诗体,即可见于《文选》,《全唐诗》犹多,可考。[1]大约在梁代,绘画思想中已经有“古意”之说。姚最《续画品》序:
夫丹青妙极,未易言尽。虽质沿古意,而文变今情。立万象于胸怀,传千祀于毫翰。
姚最之说,即已将“古意”归入绘画作品质的方面,而将形式(文)归入可随时代变化的外在形式。也就是说,绘画作品,它的外在形式是可以变的,但它的质,即其精神内核,是传承古人精神追求的。宋代画论中有关“古意”有比较零星的论述,但很少。如米芾《画史》“武岳学吴有古意”。《画继》卷五:“眉山道士罗胜先,自号云和山长,善山水,有古意。”又南宋楼钥《攻愧集》卷七十五《跋金縢图》:“金縢之说,不明久矣。尝偶得其意,欲著于册而未暇。庐甥祖皋申之,携此图见示,虽出临摹,而古意具在。”在整个两宋画论中,尚未有大张旗鼓地论“古意”的。
一 历史背景
复古思想的产生,往往是社会风气走向浮华褊薄,争奇斗艳,而道德滑坡之时。而历史往往循环往复,所以有以否定旧文化,以适应新时代为主张的,而渐转为以复古为口号,实际上是借复古以解决现实问题,是一种循环往复的革新。宋初诗文,沿袭唐末五代之习,文弱无气,愈极颓敝,柳开、穆修欲变文体、王禹偁欲变诗体,皆不能根本改变当时风气。唯欧阳修崛起为雄,倡为复古,而尹洙能辅佐他改变文体,梅尧臣辅佐他改变诗体,而后则曾巩、苏轼、苏辙、陈师道、黄庭坚等人出。则北宋诗文之盛,与复古思想关系是极密切的。
复古思潮,在南宋中后期亦渐引人注意。如果说北宋文学复古只是针对五代以来文学上的萎靡风气,那么南宋中后期的复古之风,其针对的,不但是这种风气,更重要的是对道德风尚的复古。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二记杨东山所说:
渡江以来,汪、孙、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诗,其碑铭等文,亦只是词科程文手段,终乏古意。近时真景元亦然,但长于作奏疏。魏华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记,虽雄丽典实,大概似一篇好策耳。
杨东山即杨伯子,是杨万里的儿子。在他看来,苏、黄等人的文章便没有欧阳修纯粹。而宋南渡之后,则更是每况愈下,“亦只是词科程文手段”,他直接将这种状况归于科举的负面影响。理宗宝祐元年(1253),姚勉《癸丑廷对》实际上涉及科举、学校等问题,多切中时弊:
古之盛时,自八岁入于小学,其所学则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也,礼乐射御书数之艺也。十有五而入大学,其所学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序也,此古之士所以多全才也。后世以来,所习者词章,所志者利禄。进士可以求仕,则挟书假手者有之矣。学校可以求进,则诡名冒贯者有之矣。世禄之家能学有几,已仕之人,可试尚多,贤良惟僻书奥传之观,而道则不知;词科惟奇文丽藻之习,而道则愈暗。武科则岂真有山西将帅之学,遗逸则不过为终南捷径之求,道之不闻,弊乃至此。无他,上之人求之者以文,则下之士应之者亦惟以文也。(《雪坡集》卷七)
又说:
臣闻求天下之士者,科目也;坏天下之士者,亦科目也。士不务道,惟知工于声病之文,用不适时,惟知习于套括之学。其未仕也,用力惟在于此,其既仕也,从政曷知其方。失在于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非科目坏之乎。大抵科举之取士,惟在于文,不在于道。故天下之士,不习乎道,惟习乎文。每至三年谓之大比,群众以考其艺,誊录以观其文,不求之乡评,不本之宿望,惟其文足以惑有司足矣。初不必素行之可以服乎乡里也,惟能窃用先儒之言,而谓之明理学足矣,初不必用力真在乎义理也。词赋不本于理致,日以雕镌经义,不求其指归,日以穿凿。至于论策之作,欲观其通达之才,而乃俪叶骈花,抽黄对白,竞为纤巧之制,无复浑厚之文,世变如斯,可为太息。然此犹自能之者也。固有平时不稔于文声,一旦忽腾于榜帖,由私径以鬻举,挟厚赀以倩人,公道益亡,科举遂陋。
臣观有唐取士,乡贡以荐而充,虽或间有私情,不敢大废公论。有如武陵之托杜牧一赋,韩愈之荐侯喜数人,允为得才,今岂能及。故唐之世,虽曰私而犹有公议,今之世,虽曰公而实用私情。
(中略)
臣闻学校者,最近民而易以化民者也。今之天下莫不有学,而学校以养士,科目以取人,两不相关,学遂虚设。于其艺而不于其行,考其暂而不考其常,能为发策决科之文,则曰能事已毕。问其根本当然之事,则茫然不知。气习一浮,风俗遂薄。内则有燕安废学之失,外则有挑达在阙之愆。逐利惟竞于锥刀,养指遂失其肩背。失在于所养非所教,所教非所养也。太学四方所聚,实系观瞻。而乃诡冒成风,遂成奸弊之薮,祈恩趋利,尤开侥幸之门。太学尚然,况乎天下。(《雪坡集》卷七)
《癸丑廷对》是姚勉抡魁之作。姚勉主张以道取人,而不以文取人,则正是因为当时科举以文取人有如此多的流弊。从另一方面看,他对于理学的推崇,反映了理学在南宋时被推尊,也正是救时弊的需要。但是追根溯源,这个现象的发生,未尝不可以追溯到以王安石变法为标志的北宋中后期江南文化的崛起,其所主张的“革新”往往成为“尚异”,而在南渡之后,因为地域的关系,俨然成为文化的主流,其表现于士风,则是道德堕落,其表现于文风,则是重文轻质,用现代的话来讲,就是重形式创造,轻视文化(道德)内涵。这个对于画界亦不无影响。
南宋以来科举、学校之弊,大抵在元初还有流行。元前期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国学议》:
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学,唇腐舌弊止于四书之注,故凡刑狱薄书金谷户口靡密出入皆以为俗吏,而争鄙弃,清谈危坐,卒至国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学校,教法止于四书,髫龀诸生,相师成风。字义精熟,蔑有遗忘。一有诘难,则茫然不能以对,又近于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学之不能通也,于是大言以盖之,议礼止于诚敬,言乐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谓自汉而下皆霸道;其不能词章也,谓之玩物丧志。又以昔之大臣,见于行事者,皆本于节用而爱人之一语,功业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达之深者,必悉天下之利害,灌膏养根,非终于六经之格言不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学干戈,秋冬学羽籥,若射御书数皆得谓之学,非若今所谓四书而止。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尝以儒诟诮,由国学而化成于天下,将见儒者之用不可胜尽,儒何能以病于世。
元代初期虽然取消了科举,但学校还有,宋代学校的流弊依然存在。士风萎靡的情况,可能延伸到元早期。元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二十《士辨》:
士失其道也久矣。失其道则失其性,失其身,所失非一而已。其失也始于为学之差,不惟学者之差,而传道授业,为父兄师友,当陶铸甄别,作养摩励之任者,从而为之差。内则父兄,外则师友,下则乡里,上则大臣,教士取士,既为之差,承讹习缪,其差愈深,莫之能救差者,何也,盖所学所取者,士道之土苴,文章之糟粕,衣冠语言之糠秕,影响威仪动作之文饰奸伪,求其志守身治家,事君之节行才能,则无有也。
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今之为士者志在富贵声色而已耳。伊尹之志,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被其泽,若已推而纳之沟中。又曰,天之生斯民,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伊尹之志,岂止于成身而已乎。
孟子曰,守孰为大,守身为大,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今之守身者权势所在,奔走趋向,阿媚迎合,取容求悦,胁肩谄笑,不以为耻,立志守身,凡下若此,则责以居官事君之节,责之者误也。
舍节行取文才而以为士,然则仪、秦、商鞅、李斯、孔光、张禹、柳子厚、刘禹锡、王荆公、吕惠卿,文辞之雄,照耀古今,才术之优,足以遂奸当时,后世置之奸邪小人之流,不齿清议,然则不以文才取人也亦明矣。而况今日之以文辞自负者,剽窃补缀,陈烂冗长,著述数十万言,而无一新语施之于时政,迂阔执滞而不可行,施之于名教则不足以垂训,施之于金石不足以取信后世,其视刘禹锡、柳子厚辈若萤火之视列星,欲为文章糟粕土苴而不可得。
所学一差,豪杰莫起,遂今若辈自以为贤俊,知治体识时务,又能藻饰皇猷,品章庶物,欺世盗名,蒙昧聊相,以取高位。言不顾行,行不顾言,一日临事,手足俱露,使上之人疑而莫信,曰:某人也,世以为贤,举而用之,则事迹若此;某人也,世以为材,举而用之,则言行若是。贤者材者若是,不贤不才,年未高学未至不为人所称道者,其可用欤。吁,吾道之不幸以至于此,虽善为辞说者莫能文也。
岂知取士之差,取其末不取其本,见其文而信其实,以文艺之小人,而为君子大贤之流品,以灭裂剽贼无用之浮辞,当致主泽民之重任,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古人之用人,先求其性行,次择其材能,学者之应用养其气识,修其天爵,尊德性道问学。今之用人,与学者之应用能如是乎。
这是讲士风的。至于文风,至正四年(1344)奉元路儒学教授张冲谨序萧贞敏《勤斋集》云:
以近代言之,宋末金前,理昏而气衰,或病乎繁文而委靡不振,或溺于骈俪而破碎支离。体裁既失,萧散不存,古意无余矣。
张氏序言将宋末元初文坛情况及元初复古的情况讲得很概括。张养浩《归田类稿》卷十《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某官谥文敏元公神道碑铭》说:
夫古文自唐韩柳,后继者无闻焉。至宋欧阳公出,始起其衰而振之。曾苏诸公,相与左右,然距韩柳犹有间。金源氏以来,则荡然无复古意矣。
这是从金朝那边的情况来讲的。而对于南宋,赵孟頫也有同样的认识。《松雪斋集》卷六《第一山人文集序》:
宋以科举取士,士之欲见用于世者,不得不繇科举进。故父之诏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长,非程文不习,凡以求合于有司而巳。宋之末年,文体大坏,治经者不以背于经旨为非,而以立说奇险为工。作赋者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缉新巧为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应程文之变,至此尽矣。狃于科举之习者,则曰,钜公如欧苏,大儒如程朱,皆以是显,士舍此将焉学。是不然。欧苏程朱,其进以是矣,其名世传后,岂在是哉。
“治经者不以背于经旨为非,而以立说奇险为工。作赋者不以破碎纤靡为异,而以缀缉新巧为得。”文坛(或者整个社会的)这种风气无疑渗透到其他艺术门类。理宗淳祐间释道璨《柳塘外集》卷三《赠开图书翁生序》:
然时不好古,士不师古,以风帆阵马为痛快,以插花舞女为姿媚,翁学虽古,孰肯过而问哉。
此序作于淳祐己酉,1249年,是讲书法的。而《松雪斋集》卷六《印史序》:
余尝观近世士大夫图书印章,壹是以新奇相矜。鼎彛壶爵之制,迁就对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鸟之象,盖不遗余巧也。其异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无二三焉。一日,过程仪父,示余宝章集古二编,则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纸,可信不诬。因假以归,采其尤古雅者,凡模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汉魏而下,典刑质朴之意,可髣髴而见之矣。谂于好古之士,固应当于其心,使好奇者见之,其亦有改弦以求音,易辙以由道者乎。
这种以新奇相矜、不遗余巧、媚俗于世的风气所弥漫的,不止是文坛、书坛、印坛,画界也无逃此种情况。清厉鹗辑《南宋院画录》卷一引都穆《铁网珊瑚》:
近世画手绝无。南渡初尚有赵千里、萧照、李唐、李迪、李安忠、栗起、吴泽数手,今名画工绝,惟写形象,惜无精神。
这应是讲南宋后期画坛情况的。从现有的资料看,南宋画家多世家,且地域亦多限于杭州一带。这些画家大都子不逮父,却世袭垄断“画院”职位,形成利益集团。利益驱使下的所谓绘画“创作”,只能以媚俗为本领,这也可能是刺激赵孟頫绘画古意说的原因之一。
二 古意论
元之统一,使北方文化占据优势,此时则与江南文化存在冲突。然而北方文化之占据优势,与理学的兴盛相为呼应。元初因为这些崇尚理学的人多居要职,他们利用政治优势,也欲对南宋以来士风萎靡作一大整顿,而在文化上,则对于重文轻质浮薄之风的纠正,于是成为理势之必然。而此种整顿,实是对王安石变法以来所形成士风与文化上流弊的清理。
张养浩《归田类稿》卷十《故翰林学士资善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赠某官谥文敏元公神道碑铭》:
天开皇元,由无科举,士多专心古文,而牧庵姚公倡之,骎骎乎与韩柳抗衡矣。其踵牧庵而奋者,惟君一人。
在他看来,取消科举,却是一件有益士风与文风的事。元初取消科举,在客观上对于纠正南宋以来因科举而形成的萎靡之风,有直接的意义,也直接推动了元代前期的复古之风。
(一)赵孟 文学古意论
文学古意论
赵孟頫(1254—1322)绘画“古意论”来自其文论与诗论的影响。赵氏是这个复古思潮中的一个环节,但却并不是一个风气的开创者。《松雪斋集》有关绘画的“古意”说未见一条,却有几处以“古意”论诗的文字。赵孟頫诗歌古意论的思想,可能直接受仇远、戴表元这些人影响。
仇远(仁近)《金渊集》今尚存。仇远于宋咸淳年间已有诗名,他论诗有“近体吾主于唐,古体吾主于《选》”的主张,与赵孟頫是朋友。《金渊集》四库提要谓:
远在宋末已与白珽齐名,号曰仇白。厥后张翥张羽以诗鸣于元代者,皆出其门。他所与唱和者,周密,赵孟頫,吾邱衍,鲜于枢,方回,黄溍,马臻,皆一时名士。故其诗格高雅,往往颉顽古人,无宋末粗犷之习。方凤序述远之言曰,近体吾主唐,古体吾主选。
戴表元也有复古的思想,在其《剡源文集》卷二《学古斋记》提出求古意于内之“学古”:
余闻仲实之子安恬悃悫,言真而志俭,既过他人远甚,抑学古实难,子之道将何先。今且由子之学于是斋者,言之子早起而盥沐巾栉,焚香而振册,则冠服鼎彝简编字画非古也;饥食而渴饮,寒裘而暑葛,与夫宾客祭祀之交接,其礼文器物制度非古也;广而推之,出而与宗族姻戚朋友言,入而仰以燕其亲,俯以帅其妻孥藏获,一举足一出口,而步趋唯诺之节非古也;益广而推之,事之非古者何限,而子何以安之。虽然,若此之类,犹欲以古其外必不可已,则又当古其中乎,故曰学古实难。
赵孟頫文学上复古的主张,大抵受这些人影响。赵孟頫明确地对尚奇的文风表示批评。《松雪斋集》卷六《刘孟质文集序》:
文者所以明理也。自六经以来,何莫不然。其正者自正,奇者自奇,皆随其所发而合于理,非故为是平易险怪之别也。后世作文者,不是之思,始夸诩以为富,剽疾以为快,诙诡以为戏,刻画以为工,而于理始远矣。故尝谓学为文者,皆当以六经为师,舍六经无师矣。
《赵氏铁网珊瑚》卷五引赵孟頫《跋李仲渊所为刘简州墓铭后》:
余读仲渊之文,知刘简州之为人,有用世之才,因刘简州之行事,见仲渊叙事,有稽古之学,盖古之为文者,实而不谲,简而不奥,理而不诩,若仲渊之文,真古文也哉。若刘简州者,真可于古人中求之也哉。
其复古的主张,可以看作是对谲奥新奇文风的纠正中提出来的。而《松雪斋集》卷二《酬滕野云》:“赋诗多秀句,往往含古意”;又本卷《送文子方调选云南》:“我友文子方,其人美如玉。高谈动卿相,惠利厚风俗。文章多古意,清切绿水曲。”都涉及文学上的“古意”。另外,《松雪斋集》卷六《左丞郝公注唐诗鼓吹序》:“嗟夫,唐人之于诗美矣,非遗山不能尽去取之工。遗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发比兴之蕴。世之学诗者,于是而之绎之,厌之饫之,则其为诗将见隐如宫商,铿如金石,进而为诗中之韶濩矣。”又本卷《南山樵吟序》:“吴君年盛资敏,不以家事废学,故其为诗,清新华婉,有唐人之余风。此予所以深嗟累叹,爱之不能巳也。”则明显表现出以唐人为宗的师古倾向。
(二)赵孟 绘画古意论
绘画古意论
赵孟頫有关绘画古意论的文字,多见于它处,却并不见于《松雪斋集》。《松雪斋集》在赵氏生前即已辑成[2],里面没有直接谈绘画“古意”的问题,这意味着赵孟頫当时并没有认为这是值得一提的事,或者当时至少没有明确的意识。至于赵氏绘画上的古意说,在当时有多大影响,而汤垕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影响,都是有待研究的。
赵孟頫明确地提出绘画古意说的,可能是在《松雪斋集》集成之后(大德戊戌,即1298年戴表元序)。而其最著名的说法,则是1301年的。《清河书画舫》有较详细的记载。《清河书画舫》卷十下引赵孟頫自跋画卷:
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大德五年(1301)三月十日赵孟頫跋。
“用笔纤细,傅色浓艳”即应是南宋画界遗风。1317年,他在题王居正《纺车图》时,评说其画“命意高古”。张丑《真迹日录》卷二《宋王居正纺车图》引:(www.zuozong.com)
按王拙河东人也。大中祥符间,父子以画驰名海内。延祐四年(1317)予客燕都,有持此卷相示者,因以五十金购之,乃贾师相故物也。图虽尺许,而气韵雄壮,命意高古,精采飞动,真可谓神品者矣。是岁中秋日,松雪道人赵孟頫识。
另外,1320年,题其1304年所作的罗汉像时,自评“粗有古意”。按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十下:
赵松雪画罗汉像,大德八年(1304)暮春之初,吴兴赵孟頫子昂画。
余尝见卢楞伽罗汉像,最得西域人情态,故优入圣域。盖唐时京师多有西域人,耳目所接,语言相通故也。至五代王齐翰辈,虽画,要与汉僧何异。余仕京师久,颇尝与天竺僧游,故于罗汉像,自谓有得。此卷余十七年前所作,粗有古意,未知观者何如也。庚申岁(1320)四月一日孟頫书。
又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十六录严氏藏赵魏公《幼舆丘壑图》并题卷:
予自少小爱画,得寸缣尺楮,未尝不命笔摸写,此图是初傅色时所作,虽笔力未至,而粗有古意。迩来须发尽白,画乃加进,然百事皆懒,欲如昔者作一二图,亦不可得。右之要余再跋,故重书以识之。孟頫。
所以,绘画古意说可能是赵孟頫在13世纪末始萌发,并贯穿其此后生命历程中的画学主张。当然,此前他诗论中古意主张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从时间上看,赵孟頫主张古意说,在文学领域早于绘画领域,可以认为其绘画古意说是受文学中古意说影响的。
另外,他的宗唐说也存在同样情况。赵孟頫绘画宗唐的主张,是其古意说的具体表现,在其绘画作品中可看到,这是一种模仿唐人画风的画风复古,用今天的创新观念来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他绘画的宗唐思想,从文献上目前可考的,只是《佩文斋书画谱》卷十六《元赵孟頫自论画》:
宋人画人物不及唐人远甚。予刻意学唐人,殆欲尽去宋人笔墨。
吾自少好画水仙,日数十纸,皆不能臻其极。盖业有专工,而吾意所寓,辄欲写其似。若水仙树石,以至人物牛马,虫鱼肖翘之类,欲尽得其妙,岂可得哉。(《铁网珊瑚》)
这里标明是引自《铁网珊瑚》的,而在《佩文斋画谱》卷八十四《宋赵孟坚水墨双钩水仙长卷》又引:
吾自少好画水仙,日数十纸,皆不能臻其极。盖业有专工,而吾意所寓,辄欲写其似。若水仙树石,以至人物马牛,虫鱼肖翘之类,欲尽得其妙,岂可得哉。今观吾宗子固所作墨花,于纷披侧塞中,各就条理,亦一难也。虽我亦自谓不能过之。子昂(珊瑚网)
则谓出自《珊瑚网》,但今查,止有画水仙一段,在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卷七、明汪砢玉《珊瑚网》卷三十有引文,均与卷八十四所引同。独“予刻意学唐人”一语,不知所出,亦止此一条书证。倘若这是真的,不妨将其看作受诗论中宗唐意识影响的。
(三)汤垕等人的古意论
赵孟頫并非元代最早提倡绘画古意论的。王恽《秋涧集》卷七十一《跋甫田图后》:
近与李野斋读岷隐先生诗说,冲冲然殊有所得。及观是图,其经国备物之制,伤今怀古之思,令人想见三代忠厚气象,如在乎其间,亲承其事。至于禽鱼草木车服豆笾之盛,一一视之,皆具古意。又有可观可兴者,抚卷三叹,不觉慨然。孰谓丹青形容,起予至于斯邪。至元戊寅入夏五日题。
至元戊寅有两个时间,一是1278年,一是1338年。按《元史》列传五十四,王恽大德八年卒。则此至元戊寅,应是1278年,而非1338年。所以从可考的时间上看,在元代,以古意论画者,至少王恽要早于赵孟頫。
又元黄庚《月屋漫稿》[3]《题三月梅花卷》:
纷纷姚魏家,颜色竞妩媚。人方眩春华,东皇出古意。[4]
此说提出时间也有可能比赵孟頫早。
又汤垕《画鉴·唐画》:
曹霸画人马,笔墨沉着,神采生动。余平生凡四见真迹。一奚官试马图在申屠侍御家。一调马图在李士弘家,并宋高宗题印。其一下槽马图,一黑一骝色,圉人背立见须眉髣髴奇甚。其一余所藏人马图,红衣美髯,奚官牵玉面骍,绿衣阉官牵照夜白,笔意神采,与前三画同。赵集贤子昂尝题云,唐人善画马者甚众,而曹韩为之最。盖其命意高古,不求形似,所以出众工之右耳。此卷曹笔无疑。圉人太仆,自有一种气象,非世俗所能知也。集贤当代赏识,岂欺我哉。
赵孟頫之为集贤直学士,按本传(至元)“二十七(1290)年,迁集贤直学士”(《元史》第4020页)。又谓“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讲学士,迁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三年(1316),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4022页)。则至少在1290—1316年间,皆可以集贤称之。仅从这段文字看,汤氏有关“古”的思想,可能受赵氏影响的。[5]《画鉴》多处以“古意”评画,如:
《画鉴·唐画·李思训》:
宋宗室伯驹字千里,复仿效为之。妩媚无古意。
《画鉴·唐画》:
戴嵩专画牛,为韩晋公滉幕客,专师法于韩,而青出于蓝者也。(中略)古人云,牛畜非文房清玩,若其笔意清润,开卷古意勃然,有田家原野气象,余于嵩有取焉。
《画鉴》:
郝澄画马甚俗。尝见人马图,不过一工人所为,殊无古意,上有宣和题印。又曾见滚尘马图,后有篆文曰,金陵郝澄,极妙,知是两手。
《画鉴·宋画》:
裴文晛工画牛,有声,然形似有之,古意不足。
有些学者认为汤氏的古意说是从赵孟頫来的。但如果汤的活动时间较早,那么很难断定一定就是这样,至少在赵孟頫之前已经有人讲过绘画古意的问题了。这也许是在当时士人圈中的一种流行看法。
三 从宗唐到尚陶:与隐逸文化的合流
从总体上看,元初好古之风,是以道德标准对于俗文化的反思、批判。到了元代中后期,基本上表现为对道德标准的怀疑和对隐逸文化的认同,这主要和世变有关。李祁《云阳集》卷六《阆山樵隐记》:
婺源治之东,有阆山。其山自五龙来,磅礴崒嵂,委蛇百折而后至,其源之来也远,其气之积也厚,而其数若将有所待者,于是汪君士章始营之,以为隐居事母之所。士章故婺源大姓,父祖以上,率为承平时显官。至士章,幼失所怙,母年甫三十,誓自守,以抚其孤。鞠养训掖,备极艰苦。士章既长且冠,乃慨然念曰,吾闻君子之道,莫大乎事亲,事亲之道,莫大乎禄养。以禄为养者,人子事亲之荣也。吾不幸不得养吾父,而吾母独存,吾又幸有世禄可阶,吾曷敢不勉。由是以祖荫得佐浙东帅府幕事。
未几,而世变歘兴,所在强暴,奋挺崛起为乱。乡人士咸弗宁于厥居,士章复喟然叹曰,此非君子可仕之时也,吾不得遂吾禄养之志矣。乃退而筑室于是山,奉其母以居,且题之曰,阆山樵隐,而属予文以记。(中略)
盖尝观古人之事其亲,心虽无穷,而时则有异。故当其时之可为,则推其道以扬于王庭,析圭儋爵以娱其亲。若其时之不可为也,则退焉而深藏歠菽,饮水亦足以遂其志。时有不同,则事亲之道岂必同哉。今士章遭时艰险,虽不获禄养以为亲荣,而犹能择高明显敞之地,取足甘旨,以尽其欢。徘徊山阿,以乐其道,是非独于古人事亲之际为无忝,而进退出处之机,舒卷行藏之义,盖亦深得夫古人之用心矣。予尝备官婺源,素知士章家世为详,又颇知其山水之胜,故乐为记之。
李祁是元统元年(1333)进士,元末天下乱,隐于永新山中,元亡后自称不二心老人,年七十余卒。这篇文章,记叙了一个官僚如何经世变而选择隐居的心理历程。他认为,这种选择是合于古之道的。同样地,在李祁《云阳集》卷六《松萝旧隐记》:
休宁多佳山水,其县治百里,有村曰溪西。俞君公济世居焉。丙申变故,兴家悉毁,遂辟地里之山中,去家十里余,沿溪而入,外阻中廓,泉石竹树,清洁丛茂,髣髴若古之桃源者。(中略)
呜呼,世变时移,陵谷易处,而公济于斯时也,乃能得胜地而居之,有山水之娱,有花木之美,有奉亲之乐,有宾友亲戚之往来熙熙焉,无异于太平之时,公济之得此,亦何幸哉。
予尝闻古桃源故事,想其人于桃花流水间,谓与蓬莱神仙同一归趣,然犹以为此特避世隐居者之为,非太平盛事,不足深慕。及乱离十五六年之间,东西奔窜,迄未有宁日,然后知向之居桃源者,真神仙流,未可以为荒唐而莫之信也。噫,桃源不可得而见矣,安得复有如松萝谷者,以遂吾志哉,慨焉兴怀,书以为记。
则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在这则故事里,李祁引用了桃花源的典故。事实上,在元代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地以桃花源、陶渊明等隐逸题材为内容的绘画。这既是一种怀古,也是一种古为今用的价值选择。
汪克宽《环谷集》卷四《和溪渔隐图诗序》:
古之贤者未达,而隐居以求志,莫不有所托而自晦焉。是以卜式隐于牧,朱买臣隐于樵,郑子贞隐于耕,吕尚庄光张志和之徒隐于钓,初非以樵牧耕钓为可乐,特藏济时之器,而托迹于是耳。苟不知幼之所学者为何道,壮之所行者为何事,而济世之无具,猥曰隐焉,奚隐之云乎。
汪克宽泰定丙寅(1326)举于乡,元亡不仕,明初征修《元史》,以老病辞归,洪武五年卒于家。此序也表达了当时很多人隐居求志的情况。但是,这只是对于隐逸的一种解释。我认为还有一种更为深刻的对于隐逸的理解,这和宗教、隐逸文化有关。在元代中后期,当以推崇陶潜、服膺米芾的倪瓒为代表。
倪瓒亦处于元末乱世,当时的文坛,按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十一《潇湘集序》:
兵兴来,词人又一变,往往务工于语言,而古意寖失,语弥工,意弥陋,诗之去古弥远。吾不意得潇湘集于四十年后,尚有古诗人意也。
这个序作于1366年,距元亡仅两三年。杨维祯对元末的文风心存贬意。杨维祯所说的元末文风“古意寖失,语弥工,意弥陋”,这个情况与南宋末习是类似的。
明英宗天顺四年,即1460年,钱溥《清閟阁全集》原序云:
东吴当元季割据之时,智者献其谋,勇者效其力,学者售其能,惟恐其或后。而有甘抱清贞绝俗之态,卒閟其用,全其身,而不失其所守者,非笃于自信不能也,锡山倪云林先生是焉。
钱溥谓倪瓒“攻词翰,皆极古意”。“予谓其清新典雅,迥无一点尘俗气,固已类其为人。然置之陶韦岑刘间,又孰古而孰今也邪。”这则是由元初宗唐的“古”向宗陶的“古”转化。倪瓒追求的这种陶渊明式的隐逸境界,即是其心志不为物迁,主张一个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均能恪守自己道德操守的。
在对社会现象的反思上,隐逸文化与复古文化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于现世的否定。在某种意义上,隐逸文化的理论无不是从古人的理论中延伸开来的,是古人的价值观在现世的具体实现。所以,它也不妨看作是复古思潮中的一种情况。在元代后期,这种现象有它的特殊性。即对复古思潮而言,以复古人之精神(古意)为核心的复古,在元代中期以前更多地指恢复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道德追求。而元中后期,一方面因为世变动荡,一方面因为道德实践先天依据并无理性之根据,所以它转而向古人的隐逸或庄子,或宗教的境界探询,这也是一种古意的探询。
总之,复古思潮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复古之制,一是复古之意。而复古思潮的核心即是复古之意,或者说,古意论凝缩了复古思潮的主要内容。
就绘画思想而言,古意论是自南宋晚期以来,由文论中的古意论,渗透到画论中的一股思潮。这种思潮在南宋表现得还不是非常明显。至元初始因赵孟頫等人强调绘画“古意”为人注意,大致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就是宋末元初形成文坛尤其是诗坛的复古风气。由于相应的诗论出现了强调“古意”的风气,这个思想自然地被移入绘画思想之中。其次可能是自南宋以来因利益而垄断形成的裙带关系弥漫画坛,并拒斥外地画家,因此在画坛上形成一种创造力低下、追求新奇,而实际上是名利之争所致的风气,这种风气,是赵孟頫欲以古意说来纠正之的前提。在绘画思想上,古意说的提倡实际上是对绘画追求形式(文)革新、忽视意境(质)的否定,它肯定士夫画是尚质轻文的,以意境为先,反对绘画中的俗气,主张绘画中应有道德的,进而是宗教的审美追求,而不是以形式革新为务的。从文化的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是自南宋以来理学思潮对于王安石变法以来“尚异”风尚反思的结果。在元中期以前,这种古意的追求基本上以孔孟的伦理道德境界为核心,但是,由于道德实践的先天依据,是理学无法回答的问题,所以,在元中后期,随着社会动荡,复古思想则转向与隐逸文化合流。
[1]唐(日)释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
古意者,非若其古意,当何有今意;言其效古人意,斯盖未当拟古。(续修四库全书本,第77页)
[2]《松雪斋集》四库提 要:“集前有戴表元序,见剡源文集中。末题大德戊戌岁,盖孟頫自汾州知州谒告归里时,裒集所作,请表元序之者。”
[3]四库提 要:“《月屋漫稿》一卷,元黄庚撰。庚字星甫,天台人,生於宋末,入元不仕。后来选诗者,以其为宋遗民,并载入宋诗中。然观其集首自序,乃泰定丁卯所作。时元统一海内,已五十七年,不得仍系之宋人,今故仍题作元人。”
[4]张观光《屏岩小稿·题三月梅花卷》内容雷同。
[5]关于汤氏的生平及《画鉴》成书时间,可参见周永昭《元代汤垕生平之考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5期)、周永昭《汤垕〈画鉴〉版本之流传及汤垕著作之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6期)。《画鉴》的写作时间如果早于1298年,则说明赵氏绘画古意的思想产生地更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