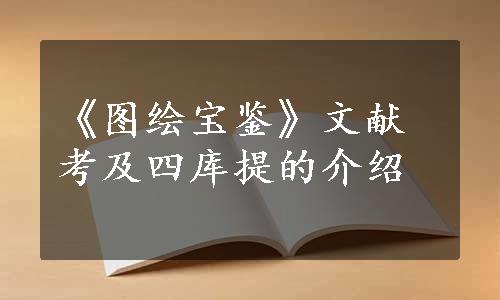
《图绘宝鉴》文献考
提 要:《图绘宝鉴》可能是在元代画家传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画史著作。其扩充以《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画继》等书为底本,以《宣和画谱》等为参考。由于扩充的部分过于仓促,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历来著录都指出,其编次往往倒置体例。这是本书最明显的问题。除此之外,《图绘宝鉴》还有剽袭之嫌,这个前人已经注意到。在画家传中,由于剽袭仓促,则对于画家的重要信息丢失较多,画家的选取有时过滥,同时又遗漏了很多应该录入的画家。作为现存仅有的一本元代画史著作,《图绘宝鉴》的参考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但它也并非所谓“在画史之中,最为详赡”的,也不足以当“征考家数源流”之说。
《图绘宝鉴》四库提 要:
文彦字士良,其先吴兴人,居于松江,嗜古,精绘事,为杨维桢所称。其家多藏古迹,又于见闻所及广搜博访,采辑古今能画者,录其姓氏,加以品藻,作为是编。自轩辕以迄元代,旁及外国,得一千五百余人,中间如封膜之类,尚沿旧讹,未能纠正。又每代所列,不以时为区别,往往先后倒置,难于检寻,体例亦未为尽善。然其搜罗广博,几于苞括无遗,洵亦画史中之最详赡者。郎瑛《七修类稿》尝谓《图绘宝鉴》,但纪历代善画名人,及所师某人而已。当再添言所以,方尽其意。如董源则曰山是麻皮皴之类,马远则曰山是大斧劈兼丁头鼠尾之类,如是则二人之规矩,已寓目前,而后之观其画者亦易,云云。其意若以是书为未备,而欲为补之,不知文彦所纪,主于征考家数源流,与笔法赋等书之详论画诀者不同,固未可执是说,而辄嫌其疏漏也。[1]
今人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第264页谓《图绘宝鉴》:
《书画书录解题》指出:“六法三品、三病、制作楷模、古今优劣四条,剽自郭氏《图画见闻志》。陶南村《辍耕录》称其论画三品,盖扩前人所未发,未免失考。粉本、赏鉴、装褫书画定式三条,则剽自汤君载《画论》。六要、六长两条,则剽自刘道醇《圣朝名画评》,而去其识画之诀四字,遂似言作画之诀。又截为两则,致与原意不符(后来论画之书多征引六要六长,误为作画之诀。且多以为出于士良,尤为粗疏可笑)。以上俱未注所出。独《叙历代能画人名》一篇,注明出《历代名画记》,遂似前所列诸条悉为己说,故为暴而出之。”经复核,文字与郭、汤、刘三氏之书稍有不同。不注明出处,虽为古书之通病,但不免被后人讥为“剽袭”。
以上诸书,将《图绘宝鉴》有关问题讲得很清楚。其卷一、卷二的有关问题,可参见本书卷六《画学文献的剽袭与言公问题》一文。本文主要集中在其卷三、卷四、卷五的宋元部分,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2]
一 编次混乱举证
是书编次混乱的问题,向为目录家所诟病。这以卷四南宋画家传最为突出。现举例子如下:
《图绘宝鉴》卷四编次问题统计表略
这些排列只是指具体人物而言,是不完全统计。另外就体例而言,如《画继》之体例,即可提供借鉴,而与之颇不合。另如马公显、世荣排在其父前,马远排在其兄马逵前,都不妥。而且越往后靠的人距应并列的人距离越大,这表明很可能是添加于后,而未能及时整理的。
二 人物重出,选取过滥
何庆先《〈四库全书〉载〈图绘宝鉴〉底本考原》:
《宝鉴》夏氏原著有正文5卷,卷一辑录前代画论,为本书理论部分;卷二至卷五为历代画史人物传记资料;卷二为上古至五代,卷三为北宋,卷四为南宋(包括辽、金),卷五为元(附“外国”)。正文后附录补遗一卷,续补一卷。《宝鉴》共辑入画史人物1489人,去其重出者11人,实有1478人,是中国古代最为赡博的画史专著,向为艺林珍重,后世论画者多喜征引之。
……
震于《宝鉴》之盛名,翻刻、续作者皆欲附骥尾以传其书。明正德十四年(1519)锦衣卫都指挥苗增因旧本漫漶,遂发起重刊《宝鉴》,请吴麒手录夏氏原著并续纂明代画史人物。吴又请友人钦天监副韩昂执笔续编成卷,辑入明代136人,合夏氏原著重刊为六卷,是为正德本,或称苗本。明末毛晋依正德本刻入《津逮秘书》,使《宝鉴》广为流传。明末清初毛大伦、冯仙湜等增补卷六,续编卷七清代、卷八女史,清康熙十二年(1673)刊印合刻八卷借绿草堂本(后印本称武林传经堂本),增补明代107人,续编清代516人及女史97人,共辑有古代画史人物2334人,是《宝鉴》主要通行本的最后版本。[3]
所谓重出11人,未详是何人。但卷四可见者如杨安道,按《宝鉴》卷三:
杨安道,九江人,学范宽山水,用焦墨太重耳。
《宝鉴》卷四:
杨安道,九江人,人物山水师范宽,笔法有江湖气韵。
应是一人,而卷三、卷四均录之。又如《宝鉴》卷四毛文昌,疑是将北宋之毛文昌弄到南宋来。此人可见《宋朝名画评》《图画见闻志》及《宝鉴》卷三。
另外,选取标准太滥。该选的不选,不该选的乱选。如《图绘宝鉴》卷四:
李东,不知何许人,理宗时尝于御街鬻其所画村田乐,常酣图之类,仅可娱俗眼耳。
《图绘宝鉴》卷四:
周白平之曾祖工山水。
类似这样画品低俗,或者连名字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画家,是不应入选的。这表明《图绘宝鉴》对于画家的选择并无明确的标准,选取画家过滥。同时又遗漏了应该选入的画家。(夏文彦紧后作补遗,即可知他已意识到这个问题)。
三 遗漏两宋画家举例
而最重要的是,此书遗漏颇多,并非所谓“最为详赡”。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六十八《清明上河图别本》跋:
按择端在宣政间,不甚著。陶九畴纂《图绘宝鉴》,搜括殆尽,而亦不载其人。[4]
另外如著名的画家任仁发也在被遗忘的行列。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第264页谓《图绘宝鉴》:
卷二,记载吴、晋、(刘)宋、梁、陈、隋、唐、五代诸画家。卷三为北宋、卷四为南宋,此两卷几占全书之半。卷五为元朝,并附外国,有日本、高昌、夏国、西蕃、高丽,其中高昌、高丽两条,显系取汤垕之书。以上四卷所记画家,凡一千五百余人。搜收可谓较以往画史为多,但遗漏亦不少。故高士奇《江村消夏录》说其不知何澄、祝次仲,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指其漏录宋伯仁。夏氏亦自知“而尚遗虑者不少”,故初版后,又作补遗,收(刘)宋一人,齐五人,梁二人,后魏一人,唐三十六人,五代四人,宋八十一人,辽四人,元三人,凡补一百三十七人,又继为续补,五代一人,宋五人,金一人。
以下按两宋别集所统计,为《图绘宝鉴》所未录入的画家列表:
《图绘宝鉴》遗漏两宋画家表略
以上只是部分未被《图绘宝鉴》(或者其他两宋画史)录入而为两宋(金)别集所载的画家。其中刘敏叔名讷,字敏叔。按《佩文斋书画谱》卷五十一《刘讷》:
刘讷,字敏叔。杨万里题三老图,序云,刘讷敏叔秀才写乘成先生、平园相国,及余,为三老。因署其后云,刘君写照妙通神,三老图成又一新。只道老韩同传好,被人指点也愁人。(诚斋集)
又《佩谱》卷五十三《刘敏叔》:
刘敏叔工写貌,虞集云,刘敏叔画故端明潜斋王公于梅雪之间,其高风胜韵如在。(道园学古录)
应是误为两人而重出者。
四 遗漏元代画家举例
以下面列表按元代别集不完全的统计,为《图绘宝鉴》所遗漏的画家:
《图绘宝鉴》按元代别集统计遗漏画家表略(www.zuozong.com)
以上仅以元代别集为标准,画家不一定是元代的,是不完全统计。
何庆先《<四库全书>载<图绘宝鉴>底本考原》:
四库本《宝鉴》的底本是孔府本,因无法对孔府本进行直接研究,只能通过四库本与同宗的借绿草堂本的若干共同点推测其内容特点。考证过程相当繁琐,本文略去论证,仅用结论勾画出孔府本的大致轮廓。
孔府本是嘉靖本或毛大伦本,而毛大伦本又是借绿草堂本的底本,其版本源流如下:
四库本与借绿草堂本直接或间接地出自嘉靖本,嘉靖本又出自正德本;四库本与借绿草堂本在内容上的若干共同特点,应能反映嘉靖本与正德本的版本差异。通过四库本、借绿草堂本与正德本的校勘,可以发现嘉靖本的底本是正德本的一个残本:
底本卷二原脱末叶,故缺杜韬、赵弘2条;
底本卷三原脱第六、第四十五叶,故缺刘寀、董源、李成、范宽、张谅、张戬、傅逸、王晟、卢道宁、丁晞颜等10条;
底本卷四原脱末叶,故缺僧玄悟、僧归义、龙门公、隐秀君等4条;
底本原脱续补一卷(一叶),故缺钱侒、李交、任源、朱象先、苏晋卿、徐明、杨邦基等7条;
底本续编(卷六)原脱王孟仁1条。
以上24条借绿草堂本与四库本皆缺。因董源、李成、范宽为古代画史上的大宗师,不可或缺,故借绿草堂本根据其他资料重新编写辑入,内容与其他各本皆不相同;而四库本则一仍其旧,保留了底本的原貌,体现了只删改不增补的原则。同样,正德本原有的一些脱误,两本的处理也不尽相同。如卷三道宏条“晚年似有所遇”,年字误作季,卷四刘夫人条“画上用奉华堂印”,奉字误作春,两本皆未订正;而卷五张衡条“书学张长史”,脱史字,借绿草堂本已补,而四库本则仍旧。四库本又脱卷二王弘、卷三李皓、卷四何青年及马永忠等条,他本不缺,当非底本问题,或为四库抄录时脱漏。
而以上所说因底本脱叶造成的脱漏并未计入表内。所以总体上看,此书也并非所谓“详赡”的。
五 《图绘宝鉴》的写作过程
《图绘宝鉴》疑是先写作元代部分,其他后来仓促补上的,因为元代部分编次混乱的情况比较少见,编次混乱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卷四、卷三、卷二。而卷二自唐以后画家传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编次混乱问题。
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第264页:
《书画书录解题》亦有评议,云:“而其最疏失者,即仅分朝代而不按画人时代重为编次。盖先就一书所载依次抄录,然后更及他书。其原书体例如何,绝不顾虑。如《宣和画谱》本以道释、人物、宫室、番族等类分编,各类中仍按时代列入。邓公寿《画继》分类又不同,亦各按时代为次,具有条理。此书则先取《宣和画谱》,不问其分类如何,仅依朝代顺次移录。录毕,复取《画继》依样顺次录之。其他各书亦复如是。所录之书愈多,则其间分类愈复,则时代错杂愈甚。故编中每一朝代道人、释子、王侯、闺阁纷杂其间,无复伦次。此但求省事,苟且成书之弊也。”复核余先生所言“盖先就一书所载,依次抄录,然后更及他书……此书则先取《宣和画谱》……”一节,查《四库全书》本《宣和画谱》,卷一道释门,首为顾恺之,次为陆探微、张僧繇……;而《图绘宝鉴》卷二,其次:吴曹弗兴、晋卫协、顾恺之、史道硕、谢稚,宋陆探微、梁张僧繇……。两者比较,可见并不“先取《宣和画谱》”,亦不先取《历代名画记》,而有所排比。可见所评未据事实,而非的言。至于“编中每一朝代道人、释子、王侯、闺阁纷杂其间”,诚是。总之,是书确存在每朝人物不以时代为次之疏失;但此病非此书独有,以寓目之画史书而言,可说几乎皆有,不过多少之不同。
谢氏显然在对《图绘宝鉴》著述草率的问题有意回护。但这种对古人盲目的辩护是不妥当的。余绍宋对于是书成书过程的说法是依据《宣和画谱》为底本,依次抄录,然后依其他画史填充,在这样的过程中,未必一定要机械地按《宣和画谱》所规定的次序来填充的。我们只能从大体的趋势来作判断。而谢氏则以曹弗兴为例便断然否定余氏的猜测,是不足取的,因为曹的时代在吴,将其人略调至首位是很容易的事。余绍宋对于是书成书过程的说法实际上是有根据的,陕西省图书馆《图绘宝鉴》怡堂藏版(以借绿草堂本参校):
夏士良先生序
仆性鄙僻,六艺之外,他无所好,独尝嗜画,遇所适,辄终日谛玩,殆忘寝食,然犹病其不博,稍取历代画史,考论其世,与夫得失优劣之差,以广未至,而卷帙浩繁,不能编举,欲辑为一书,未暇也。自卜居泗上,人事稀阔,间以《宣和画谱》,附之他书,益以南渡辽金国朝人品,刊其丛脞,补其阙略,汇而成编,分为五卷,名曰《图绘宝鉴》,顾所摭虽详,而尚虑遗者不少,益其未备,竭其精诚,俾千载之下,莫逃乎赏鉴,岂无博雅君子,与我同志欤。至正乙已秋七月甲子吴兴夏文彦士良书于宝墨斋。
可见余绍宋应是据此夏士良序讲的。但此序与陶宗仪的说法不一致,因为是书写成时,是托陶宗仪向杨维桢求序的,所以此序的可靠性是有疑问的(或者有两序)。有关是书成书问题的情况,我们要注意陶宗仪的说法。
陶宗仪《辍耕录》卷十八《叙画》对于是书的编纂过程是这样描述的:
因取《名画记》、《图画见闻志》、《画继》、《续画记》为本,加以《宣和画谱》、《南渡七朝画史》、齐梁魏陈唐宋以来诸家画录,及传记杂说,百氏之书,搜潜剔秘,纲罗无遗。
也就是说,《宣和画谱》其实并没有作为编纂的底本。这个说法也被四库提要所引用。大概在当时,《宣和画谱》就已经被看作是有问题的。可以看到,夏文彦所选取的底本是《名画记》、《图画见闻志》、《画继》、《续画记》,《续画记》是什么样的书已无法可考,但《名画记》、《图画见闻志》、《画继》这三本书今天看来,也是最佳的底本,夏文彦确实是有眼光的。只可惜《续画记》这本书已无法可考,估计是续《画继》的。而《宣和画谱》和今已无法可考的《南渡七朝画史》只是作为旁补资料而已。其实,陶宗仪已经将这个过程描述得很清楚了。这当然是一种最理想的写作方法。
我们注意到,在《名画记》、《图画见闻志》、《画继》这三本书中,前两书都是按时代先后编排画家,但《图画见闻志》却同时对人物身份作了分类,《画继》又继承了这种分类的方式。两种不同的分类方式存在于两本著述中,这可能是导致《图绘宝鉴》出现混乱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这些问题以南宋为最集中。
而且,为了进一步解释元代画家传这种情况不明显的原因,我再提出一种可能,即此书是先作元代画家传,而后大体依陶宗仪所说的方式进行编纂的。
另外,四库全书未录杨维桢、夏文彦序,不知何故。或者此两序的真伪在当时已受到怀疑的。(如果夏文彦序是假的,那么夏文彦是否为此书的作者,也应成为问题。王世贞说此书是陶宗仪的,或许并非毛奇龄所说,是疏漏的原因。)
总之,《图绘宝鉴》的写作过程,四库总目提要已经说得比较清楚。大抵是取当时被认为可靠(可能如此)的几本重要的画史如《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等为底本,汇集而来的。《宣和画谱》似并非其首选。而以卷四中编次错乱最为突出,而元代这个问题并不严重。这有一种可能,即元代部分是作者首先开始写的,其时并未准备写其他内容。其他内容是后来匆忙加入的。加上南宋资料不完备,随写随改,可能匆忙出版,(从后一年匆匆续上补编的情况来看,判定它属于匆忙出版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因此留下很多问题不容回避。作为现存元代唯一的画史著作,它虽然被评为“固无所禆于问学”(毛奇龄),但其卷四、卷五关于南宋与元代画家的记载,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绘画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它关于元代画家的记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人对元代画坛的印象。另外,由于南宋《画继》(还有《声画集》)之后,有关于对南宋画坛的历史记录尚无留存(清人所辑的《南宋画院录》不计,《南渡七朝画史》等未知是何书),则《宝鉴》卷四对于南宋画坛的记录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总体来讲,它并非是“详瞻”的,其写作也是比较草率的。
[1]清毛奇龄《西河集》卷六十一《书图绘宝鉴后》:
《图绘宝鉴》合四卷,元吴兴夏文彦著。文彦字士良,即云间义门夏氏,盖其先吴兴人也。其书谱列代能画名,自前古迄元,固无所禆于问学,而说者备焉。昔王弇州撰陶九仍传云,又籍古之善书画者,而纪之曰《书史会要》、曰《图绘宝鉴》,尝疑是书固陶九仍著者。然考孙作所撰南村先生本传,有云,其所著书时,所传《说郛》一百卷,《辍畊录》三十卷,《书史会要》九卷,《四书备遗》二卷,曾无《图绘宝鉴》之目,盖尝简是书所叙,则杨君维桢叙也。叙云,吴兴夏氏,集是书成,介其友天台陶君九仍,持之示余。则是书固夏氏所作,而曾介九仍以乞杨为一叙之。弇州不识是书与九仍展转,而不考夏氏,遂为九仍所著书也。事不深考,诬所从来,乃无作者久矣。且夫为人传,抑不可以无实录。丁未书。
明赵琦美编《赵氏铁网珊瑚》卷十四《墨菜铭》引夏文彦:
气含风露满深秋,真味由来胜庶羞。若使东坡曾见此,品题当不到元修。
[2]《天禄琳琅书目》卷九:
《图绘宝鉴》(一函四册)
元夏文彦著,五卷,补遗一卷,前元杨维桢序,文彦自序。
考栗祁《湖州志》云,夏文彦吴兴人,后居云间,精图画,著有《图绘宝鉴》五卷行世,但称五卷,不云有补遗一卷。今按文彦自序,作于至正乙巳,自谓汇而成编,分为五卷,其补遗后别行,又标至正丙午新刊,则补遗之作,在文彦自序中,且未之及,故栗祁作志,亦从其略,不知乙巳、丙午,仅越一年,自是一时并刊,非为后出。栗志之疏,固不足辨。又按杨维桢序中称,云间义门夏氏士良,又称士良,名文彦,云云,栗志仅详其名,而不及其字,则其未经深考,可知也。士良本至明时版已漫漶,正德中有锦衣卫都指挥苗增字益之,取家藏本缮写重刊,又汇次当代善画者,续编为六卷,刻于正德己卯,司经局,洗马滕霄为序,是本仍止五卷,及补遗并无重刊,序跋系欲伪充原椠者,然选纸坚致,古香黟然,亦佳本也。杨维桢字廉夫,浙江会稽人,元泰定中进士。
[3]《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4年第6期,转自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
[4]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六十八《清明上河图别本》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有真赝本,余俱获寓目。真本人物舟车桥道宫室,皆细于发,而绝老劲有力。初落墨相家,寻籍入天府,为穆庙所爱,饰以丹青。
则今所传《清明上河图》并非饰以丹青,未知孰是。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