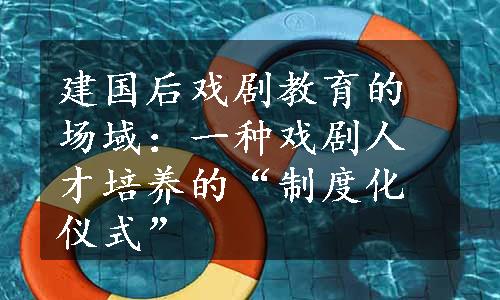
舞台精英:建国后戏剧教育的场域[1]——一种戏剧人才培养的“制度化仪式”
作者简介:
胡志毅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影视艺术与新闻媒体系主任,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话剧理论与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副主编)、《现代传播艺术——一种日常生活的仪式》、《神话与仪式:戏剧的原型阐释》、《20世纪中国文学典藏·戏剧编》(主编)、《神秘·象征·仪式:戏剧论文集》、《世界艺术史·建筑编》、《国家的仪式:中国革命戏剧的文化透视》、《中国话剧艺术通史》三卷本(与田本相教授合编)。在《文学评论》、《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戏剧》、《戏剧艺术》等刊物发表论文90余篇。
摘 要
按照布尔迪厄的观点,名牌大学是培养国家精英的场域,国家精英是“造就分离”的“神圣人群”,这种“教学活动”就是“准备占据霸权位置”的“神化行动”。“国家的仪式”,在戏剧教育中,是通过“制度化的仪式”来完成的。
法国著名学者布尔迪厄在《国家精英》中提出名牌大学是培养国家精英的场域,他说,“所谓‘精英学校’,就是负责对那些被召唤进入权力场域的人(其中大多数都出生于这个场域)进行培养,并且对他们加以神化的机构”。他解释说,“以准备占据霸权位置为目的的任何一项教学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项以造就分离的神圣人群为目的的神化行动,或者说一项制度化的仪式。甚至在教学活动最具技术性的方面也是如此”[2]。也就是说,国家精英是“造就分离”的“神圣人群”,这种“教学活动”就是“准备占据霸权位置”的“神化行动”。戏剧教育也是如此,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以及云南艺术学院等院校就是这样的培养“准备占据”舞台“霸权位置”的“神圣人群”的场域,这种培养是一种培养舞台精英的“制度化的仪式”,是“国家的仪式”[3]的组成部分,其中校庆就是“制度化仪式”中最能体现戏剧艺术院校传统的一种。
一
“国家的仪式”,在戏剧教育中,是通过“制度化的仪式”来完成的。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是南京的前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和上海的前上海市立戏剧实验学校的延续,但是这种延续是一种断裂的延续。如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校长余上沅,只是在上海戏剧学院担任教授,没有继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是由欧阳予倩担任的;而熊佛西则在上海戏剧实验学校延续担任院长职务。
建国后的戏剧教育,是从建立中央戏剧学院和华东分院(后改为上海戏剧学院)开始的。同时各个地方的艺术院校,也开始了戏剧人才的培养。后来的舞台精英,大都是从这些戏剧院校培养出来的,如山东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等70多所学院(包括一大批艺术职业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1950年4月2日在北京成立,由原华北大学文学院、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东北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组等单位人员联合组建,由欧阳予倩任院长,曹禺、张庚任副院长,光未然任教务长。设普通科、本科学制与研究部,并有歌剧、话剧、舞蹈等剧团。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改组为专业的话剧学院。欧阳予倩任院长,沙可夫、李伯钊任副院长。学院设本科表演系、导演系、舞台美术系和戏剧文学系[4]。
上海戏剧学院是在1952年建立,这个学院由熊佛西任院长,朱端钧任副院长。前身是上海市市立实验戏剧学校,1945年12月1日由著名教育家顾毓琇与著名戏剧家李健吾、顾仲彝、黄佐临等创立,熊佛西先生为首任院长。1949年10月,由上海戏剧实验学校改名为上海戏剧专科学校。1952年,山东大学艺术系戏剧科、上海行知艺术学校戏剧组并入,组成学院,当时称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1956年正式更名为上海戏剧学院,仍由熊佛西任院长,系科设置与中央戏剧学院完全相同。这些系科组成了话剧舞台艺术所需要的完整的体系。
中国的戏剧教育除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之外,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和云南艺术学院等多所学院。其中云南艺术学院在戏剧教育上有显著的成就,其院长吴卫民(吴戈)教授本人就是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培养出来的硕士和博士。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成立于1960年6月,戏剧系是其主要的系科。吉林艺术学院原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1958年改建吉林艺术专科学校,设有话剧舞蹈系,戏剧系创建于1960年。山东艺术学院创建于1958年。云南艺术学院戏剧学院的前身是戏剧系,创建于1960年,主要有表演和导演专业,是西南地区唯一的一所培养戏剧艺术专门人才的教学科研单位。专业设置和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一样,影视艺术教育以及播音主持人专业是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设置的新的专业。
布尔迪厄说:“‘精英学校’一直履行着神化的职能,它们在教育的过程中完成的那些技术性活动其实与制度化仪式的各个时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教育体系的存在或许就足以让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选拔就是‘当选’,考试就是‘考验’,训练就是‘苦行’,离群索居就是接受奥义传授时的避静,技能就是奇理斯玛资格。换言之,在‘精英学校’通过分离和聚合这样的神奇活动完成的转化过程倾向于产生被神化的精英群体。”[5]在这里,有必要作出解释,在中国大学的“技术性活动和制度化仪式”这两种教育体系也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西方的制度化仪式中的“神化”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奥义”的话,那么,在建国以后则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戏剧学院和普通高校一样,学生的“选拔”,就是“当选”。在中国是要强调“出身”的,即工农子弟优先。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还是强调“成分”的。考试就是“考验”,在中国考试是一直作为一种入学的方式存在的。在“文革”时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考验”,如张铁生考试时交白卷;在电影《决裂》中,只要有一双长满了老茧的手,就可以读工农兵大学。训练就是“苦行”,在中国的大学中,在毛泽东著名的“五七”指示号召下,往往还要学工、学农、学军。“离群索居”就是“接受奥义传授时的避静”,读书时需要个人单独思考,这种思考往往会成为一个人一生中的觉悟的时刻。技能就是奇理斯玛资格。“奇理斯玛”,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的中心。进入大学学习技能、技术,获得奇理斯玛的资格。
在这里,布尔迪厄制度化的仪式(rites d'institution)和特纳的“入门仪式”(rite de passage)有区别,他认为,“正如大多数的入门礼仪建构了所有普通的人,学业礼仪建构所有持有称号的人,作为制度化礼仪之一的学业神化过程建构了神圣群体”[6]。 “入门仪式”又可以译为“通过仪式”或者“生命仪式”。 这种仪式表明人类可以通过仪式得到一种成长,因此也可以理解为成长的仪式。
戏剧教育的“制度化仪式”,和一般大学教育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不过是包括新生入学典礼、考试、毕业典礼。
布尔迪厄说:“新生入学典礼只不过是在预备班和名牌大学本身完成的许多制度化的仪式中最明显的、最容易观察到的一种,也是人们灌输这些传统的时机之一。”[7]
熊佛西在剧校创建之初就谈到培养人才的目标:“培养人才的目标,我以为,首先应该注重人格的陶铸,使每个戏剧青年都有健全的人格,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爱民族,爱国家,辨是非,有志操的‘人’。然后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所以本校的训练体系,不仅是授予学生的专门知识与技能,更重要的还是训练他们如何做人。”[8]
但是在戏剧学院和其他大学不一样,因为这和舞台艺术的本质是相关的。除了戏剧文学系和综合性大学的汉语言文学系的学习有点类似,导演、表演和舞台美术就很有很大差异。导演、表演要做小品,现在则推行工作室。舞台美术则是要写生和节能型舞台装置的训练。
在戏剧学院“制度化的仪式”,最重要的不是毕业典礼,而是毕业“大戏”。
田华在回忆1955的表演干部训练班的时候说:
“表训班共录取了24名学员和部分旁听生。1955年初正式开课,一、二学期完成了《联共党史》,本来还要学《政治经济》,时间紧迫未能完成……表演、台词、声乐、形体(代表作),名著贯穿始终。一切从零开始,交流、适应、想象……
“从自我出发的单人无言到双人、多人有言小品,从塑造人物形象的片段到排大戏,这些大戏基本上都是从片段中形成的。
“《小市民》中,我演女佣人波丽雅,戏不太多,专家说:‘你成功地演出了“谢达依捷卡”(中国小姑娘白毛女),看看你能不能演成功莎翁笔下的朱丽叶。’于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就选定了我。专家还为方掬芬选了苏联儿童剧《玛申卡》……为了展示所有学员和旁听生的才华,《暴风骤雨》诞生了。
“我们用幕前幕后的小品形式做案头工作,每个人还在舞台边上布置了自己(人物)的小环境。中戏美术系苏联专家雷克夫为我们设计的服装和布景,外国戏由专家排练,中国戏大部分是演员自己走台排练,那一段时间简直是忙得不可开交,直到1956年6月,才正式在当时的中戏小经厂剧场与观众见面!四台大戏打响了!轰动了!”[9]
上海戏剧学院计划从2009年开始,到2014年连续5年开办国际导演大师班,聘请美国、英国、俄罗斯、德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国顶级国际导演大师亲自授课,并开设导演工作室。这种培养,就是一种舞台精英教育的方法,它较之于20世纪50年代聘请苏联专家来传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还要具有国际性。
二
在具体的培养模式中,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在建国初期都是按照苏联的教学模式进行的,尤其是传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表演体系。这是话剧国家化、正规化的一种“制度化仪式”。
1956年1月1日,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举行毕业公演,剧目是由列斯里指导排练的苏联话剧《柳鲍夫·雅洛娃娅》。8月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干部训练班举行结业公演,演出高尔基的《小市民》和苏联当代戏剧阿费诺盖诺夫的《玛申卡》。1957年10月上海戏剧学院表演师资进修班在上海举行毕业公演苏联作家拉甫列尼约夫的《决裂》,表现苏联十月革命中阿芙乐尔巡洋舰起义的故事。
在戏剧学院,往往是通过演出经典戏剧来明确“制度化的仪式”的权威性。P.布尔迪厄说:“古代经典作品是令人敬仰的,是神圣的,而对于现在却完全没有用处;然而在各种各样的历史背景中,它们却是最宽阔的文化舞台的重要支撑。”[10]在戏剧学院,演出的不仅有古典经典作品,还有现代的经典作品。
中央戏剧学院作为中国戏剧界的最高学府,他们以演现代的名剧为主,如:欧阳予倩的《桃花扇》,郭沫若的《屈原》、《孔雀胆》,田汉的《关汉卿》,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等。1961年中央戏剧学院实验话剧院在北京上演的多幕话剧《黑奴恨》,由欧阳予倩根据美国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编,孙维世导演,田成仁、金振武、李丁、张家声、石维坚、雷恪生、游本昌出演。同时他们还演出当代的优秀剧作:《战斗里成长》、《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刘胡兰》、《党的女儿》、《红色风暴》、《洞箫横吹》、《远方青年》、《霓虹灯下的哨兵》、《年轻的一代》等。另外他们也演出外国的经典剧作,如哥尔多尼的《一仆二主》、《女店主》,莫里哀的《伪君子》,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暴风雨》,席勒的《阴谋与爱情》,奥斯特罗斯基的《大雷雨》、《无辜的罪人》,小仲马的《茶花女》,维迦的《羊泉村》,巴尔扎克的《做纸花的姑娘》,高尔基的《小市民》,等等。
1991年中央戏剧学院校园狂欢节,演出了一系列的先锋戏剧: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品特的《风景》、《升降机》,未来主义风格的《黄与黑》,还有《飞毛腿或无处藏身》以及《等待戈多》等。孟京辉说:“1991年中下段的任何一个晚上,只要你走进北京中央戏剧学院,都会看到一场不同寻常的演出。在那里,每天都像过节一样。十几个戏剧狂热分子组成的创作集体用自信、狂想、冒险、激情,用耐心、苦干、理性、献身使我们和观众在一种戏剧气氛中得到陶醉,受到震动。”[11]
2005年4月2日我曾经在北京观看中央戏剧学院表演、导演班毕业十年以后相约排演和上演的爱尔兰剧作家约翰·沁孤的剧作《圣泉》。这个戏表现的是一对非常恩爱的瞎眼老人,在一位圣徒用圣泉来为他们治疗后,得以再次睁开眼睛,但是当他们重见光明的时候,看到的是对方的丑陋,于是互相讽刺、挖苦,以至于他们宁愿回到原来的盲目状态。这也是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期望表现的精神力量的一种象征。
上海戏剧学院排演了许多剧作,如熊佛西的《上海滩的春天》,田汉的《关汉卿》、《文成公主》,曹禺的《家》、《北京人》,老舍的《方珍珠》、《龙须沟》、《全家福》,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心防》、《法西斯细菌》,陈白尘的《升官图》,等等。他们上演了当代优秀剧作《红旗歌》、《在新事物面前》、《甲午海战》、《战斗里成长》、《第二个春天》、《槐树庄》、《李双双》、《年轻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等。另外还上演了世界名剧如莫里哀的《吝啬鬼》、莎士比亚的《无事生非》、席勒的《阴谋与爱情》、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契诃夫的《樱桃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以及苏联话剧《曙光照耀莫斯科》、《以革命的名义》等。1961年1月18日,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在上海上演多幕话剧《战斗的青春》,由陈加林、苏堃根据雪克的长篇小说改编,朱端钧、关尔佳导演。
2007年10月14日至21日上海戏剧学院举办了第四届国际小剧场戏剧节,上演了八部戏剧:《清明上河图》、《青凤与婴宁》、《哈姆雷特:那是一个问题》、《狂人教育》、《两个老柴玩游戏》、《股票反弹》、《狂人教育》、《圆明园》、《爱与恨》等。
2009年11月,上海戏剧学院1959届毕业的学生演出了一台非同寻常的话剧《钦差大臣》。由陈明正导演,焦晃、张先衡、顾永菲、卢若萍、王家驹等主演,焦晃饰演赫列斯塔夫。这个戏曾经是上海戏剧学院上演的重要剧目,到今天再来演出具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它见证了一代戏剧人的理想。
云南艺术学院的剧目,从1989年开始记录的有《魔方》,宋之的的《群猴》,曹禺的《雷雨》,吴雪的《抓壮丁》,孟冰的《绿荫里的红塑料桶》,乐美勤的《留守女士》,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过士行的《坏话一条街》,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水上勉的《文那,从树上下来吧》,莎士比亚的《奥赛罗》,奥尼尔的《悲悼》,萨特的《死无葬身之地》,苏童的《妇女生活》,蹇河沿的《黑白祭》,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安东尼奥·布埃罗·巴耶豪的《楼梯的故事》,郑天纬的《阮玲玉》,弗·奥宗的《八个女人》,阿瑟·米勒的《萨勒姆的女巫》,万比洛夫的《打野鸭》,萧红、田沁鑫的《生死场》,迪伦马特的《贵妇还乡》,巴金原著、曹禺改编的《家》,张爱玲《倾城之恋》,等等。
2004年9月3日至15日,云南艺术学院主办了第五届华文戏剧节,上演了八台戏剧,其中有《青春禁忌游戏》、《死亡与少女》、《白门柳》、《金池塘》、《蛇,我寂寞》,澳门的短剧《小神仙初到凡间》、新加坡FUN的《恋人物语》、云南艺术学院的《黑白祭》等。
云南艺术学院影视艺术学院导演班的毕业大戏《倾城之恋》上演之时,正值学院50周年庆典,在指导老师余力民、张芃的指导下,在简朴的舞台背景中展示上海、香港的“双城记”,表现了云艺的整体实力。两位主要演员的表演初现明星风采,其他演员配合非常默契而自然,而群舞和音乐则显示了戏剧的氛围和节奏,基本表现出张爱玲小说的原意,给人一种时尚的感觉,但苍凉感略有不足。
三
布尔迪厄说,学校的精英群体就是集体信仰为特殊的命运选定的人物;从模态命运(destinède modales)的标准来看,或者说,从最普通、最平凡、最正常的命运来看,这个群体的建立所产生的效应就是建构了最杰出的命运,而杰出的命运的征象就是最崇高、最难企及的人生轨迹[12]。而从这两所学院毕业的学生,就是通过这样“最杰出的命运”,来征象“最崇高、最难企及的人生轨迹”。
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有欧阳予倩的头像(在北京有欧阳予倩故居);进入上海戏剧学院则有熊佛西的头像,并且有以熊佛西命名的楼——佛西楼和以朱端钧,命名的端钧剧院(上海戏剧学院还设立了余秋雨大师工作室,尽管这个命名引发了诸多异议)。
必须指出的是,一流的院校,首先要有一流的师资。仅仅是戏剧史论方面,中央戏剧学院有周贻白、廖可兑、孙家秀、祝肇年、谭霈生、晏学等。上海戏剧学院则有顾仲彝、朱端钧、赵明彝、陈多、吴光耀、胡妙胜、余秋雨、叶长海、荣广润、丁罗男、孙惠柱等。
在导演方面,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徐晓钟教授导演的《培尔·金特》、《桑树坪纪事》、《奥赛罗》,成为舞台的经典。
戏剧学院的制度化仪式,不仅体现在本科学位的授予,还体现在硕士、博士学位的授予。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设立了戏剧戏曲学重点学科。另外,吉林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和云南艺术学院都相继设立了硕士点。2009年云南艺术学院设立了戏剧戏曲学博士培养点。这些戏剧艺术院校在更高的层次上培养着戏剧人才。
在高层次戏剧人才的培养方面,尤其是戏剧理论人才的培养方面,除了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之外,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传媒大学都设有戏剧戏曲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话剧所是研究中国话剧的国家性的研究所。话剧所的第一任所长葛一虹,主编了《中国话剧通史》。第二任所长田本相教授,最早从北京广播学院调到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又从中央戏剧学院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在他的主持下,主编出版了《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新时期戏剧述论》、《中国话剧艺术通史》等。南京大学的戏剧影视研究所是话剧研究的重镇,陈白尘、董健教授等主编有《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当代戏剧史稿》等著作。
北京大学也设立了林兆华戏剧工作室,并且开始在艺术学院招收戏剧艺术的研究生。
舞台精英大都是从戏剧学院产生的,也就是说,要成为戏剧舞台艺术工作者,必须进入戏剧学院或者相关的艺术院校。这种教育资源是国家垄断性的,布尔迪厄说:“垄断一旦得到认同,就会转化为精英。这种效应会越来越得到肯定和强化,原因在于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除了具有集体拥有的凝聚在称号(titre)里的象征资本之外,还在这种神奇的参股(partcipation magique)逻辑中具有了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以个人的名义拥有的象征资本。”[13](www.zuozong.com)
在这种“象征资本”的感召下,中央戏剧学院从1953年到1966年共培养了3 000多名各类毕业生[14]。而到现在已经培养出10 000多名学生。
导演系有李保田、鲍国安、曹其敬、陈薪伊、熊源伟、张子扬、查明哲、王晓鹰、吴晓江、娄乃鸣、古榕、徐松子、任鸣、阎建钢、李六乙、张扬、孟京辉、田沁鑫、马俪文等。
表演系有田华、于蓝、雷恪生、王铁成、严顺开、林连昆、林兆华、陈宝国、赵奎娥、陈道明、姜文、丛珊、吕丽萍、巩俐、史可、徐帆、陈晓艺、陶虹、李亚鹏、王学兵、陶红、夏雨、章子怡、袁泉、秦海璐、胡军、刘烨、陈好等。
戏剧文学系有何冀平、黄维若、范元、谢丽虹、成浩、朱小平、肖复兴、陆星儿、乔雪竹、杨立民、张仁捷、张一白等[15]。
在这中间有人取得了错位的成就,如导演专业毕业的李保田、鲍国安等成为表演艺术家;而表演专业毕业的林兆华成为著名的导演,他导演的剧作有《绝对信号》、《车站》、《野人》、《狗儿爷涅槃》、《鸟人》、《哈姆雷特》、《罗慕路斯大帝》、《浮士德》、《理查三世》、《三姊妹·等待戈多》、《大建筑师》、《故事新编》、《风月无边》、《阮玲玉》、《北京人》、《茶馆》、《古玩》、《赵氏孤儿》等。
陈薪伊导演了《女人的一生》、《奥赛罗》、《商鞅》等话剧,获得了国家舞台精品工程奖,查明哲导演了《纪念碑》、《青春禁忌游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SORRY》等,王晓鹰导演了《萨勒姆的女巫》、《死亡与少女》等,孟京辉导演了《思凡》、《恋爱的犀牛》等剧作,这些剧作成为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的舞台精品。
进入戏剧学院是一个艺术家成长的转折点,或者说这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现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著名导演任鸣就回忆说:
“记得1982年入学时,我流了泪。5年后,1987年我走出校门时,我又流下了泪水。5年的中戏生活,使我从一个社会上的待业青年成为北京人艺的职业导演。在很多场合我都说过:‘我是人艺的儿子。’那么中央戏剧学院我的母校,就是我的乳娘,是她给了我初始艺术生命的养料,是她给了我影响一生的品格。”[16]
在表演人才中,有所谓横跨戏剧电影或电视的两栖型、三栖型演员。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林连昆、林兆华、杨立新、徐帆、陈小艺等,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上靠演出或导演出名的(其中杨立新、徐帆、陈小艺等是属于三栖型演员)。雷恪生也是三栖型演员,他出名主要是在影视中,但是他在舞台上也演了几十年的话剧,在晚年参加了上海第二届国际艺术节的明星版《雷雨》的演出,他对话剧舞台的魅力感慨道:
“当首场演出结束的大幕徐徐合上时,观众席里顿时响起暴风骤雨般的掌声。谢幕、谢幕、再谢幕,长达十几分钟。有的观众还高喊着演员的名字……不少观众在剧场门口等着与我们合影留念……
“我演了几十年话剧,这种令人激动的场面,在我的记忆中还从未出现过。”[17]
上海戏剧学院从1952年到1965年培养了1 200多名各类毕业生,通过60年的发展,也已经培养了上万名戏剧人才。
这些人才都是被以国家冠名的,如国家一级导演、国家一级演员、国家一级舞美等,成为国家的舞台精英。
导演有胡伟民、陈明正、徐企平、张应湘、杜冶秋、熊源伟、苏乐慈、汪遵熹、张仲年、郭小男、谷亦安、卢昂等。
表演有魏启民、严丽秋、陈奇、严翔、胡庆树、游本昌、娄际成、张先衡、赵有亮、焦晃、李志舆、祝希娟、杨在葆、李家耀、刘子枫、魏宗万、陈裕德、孙飞虎、郑毓之、潘虹、奚美娟、郭达、李媛媛、吕凉、宋忆宁、李幼斌、刘威、丁嘉丽、张秋歌、宋佳、龚雪、尹铸胜、王洛勇、陈红、田水、徐峥、田海蓉、任泉、陆毅、李冰冰、郝平、佟大为等。
编剧有陈恭敏、杨履方、陈耘、沙叶新、耿可贵、乐美勤、赵耀民、李容、李婴宁、孙慧柱、徐频莉、曹路生、陆军等。
舞台美术有崔可迪、金长烈、周本义、蔡国强、吕振环、陈箴、丁加生、李汝兰、胡成美、徐家桦、韩生、伊天夫、潘健华等。[18]
这些人物构成了一个舞台精英群体的长廊。
在导演人才中胡伟民在20世纪80年代非常著名,导演代表作有话剧《秦王李世民》,可惜英年早逝。陈明正导演过话剧《哈姆雷特》、《海鸥》、《黑骏马》、《白娘娘》等,徐企平导演过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物理学家》、《罗慕路斯大帝》等,熊源伟导演的话剧有《奥尔菲》、《仲夏夜之梦》、《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泥巴人》、《歌星与猩猩》、《金大班的最后一夜》、《4:48精神崩溃》、《兄弟》、《弘一法师》等,谷亦安导演了《屋里的猫头鹰》、《艺术》、《谁杀了国王》等,郭晓男导演过话剧《魂归何处》、《秀才与刽子手》等。
在编剧人才方面,陈恭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创作过《共产主义凯歌》,杨履方创作了《布谷鸟又叫了》,陈耘创作了《年轻的一代》,沙叶新则主要活跃在新时期,他创作的《假如我是真的》受到了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的影响,后来他创作了《陈毅市长》、《寻找男子汉》、《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等一系列剧作。乐美勤创作了《留守女士》,赵耀明则创作了《良辰美景》、《长恨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孙慧柱有《挂在墙上的老B》、《中国梦》等,徐频莉著名的有《芸香》,曹路生则在改编方面非常成功,如《庄周戏妻》、《谁杀了国王》、《九三年》等。
在舞台美术方面,应该说非常有成就。就凭现在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都是舞台美术出身就可见端倪。
曹禺在为中央戏剧学院三十周年庆而作的《贺词》上说:
“1950年建院时,我才四十岁,除欧阳予倩老院长外很多同志都很年轻。三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头上生出了白发,他们为学院的成长献出了青春;应该说,他们的青春在学生们身上再生了。多少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人,在祖国各地的戏剧舞台上焕发着光彩。
“我要祝贺这些可敬的老师和优秀的学生,我要祝贺学院的干部和工作人员。
“过去,道路并不平坦;今后也会有艰难曲折。世界上历史最长的戏剧学院是英国‘皇家戏剧学院’,它于1904年成立,到今年已有七十六年了。我们戏剧学院也会有七十六年,还会有一百年。到了一百周年纪念的日子,尽管我是不在了,但我相信中央戏剧学院事业会更加兴旺,更加壮丽的。
“它的历史是我国日后的伟大艺术家在那里发育,成长为党,为人民攀登戏剧艺术高峰的历史。”[19]
我们现在可以说,2009年云南艺术学院建院50周年,2010年中央戏剧学院建院60年,2012年上海戏剧学院建院60周年,这些艺术院校应该步入了戏剧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因为无论从办学经费、学校建设到招生人数都是历史上空前的。我们应该像曹禺那样“相信”这些戏剧艺术院校能培养出“攀登戏剧艺术高峰”的“伟大的艺术家”,培养出真正的舞台精英。
【注释】
[1]本文所涉“建国后”专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编者注。
[2]P.布尔迪厄:《国家的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5页。
[3]胡志毅:《国家的仪式:中国革命戏剧的文化透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贾冀川:《20世纪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
[5]P.布尔迪厄:《国家的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70页。“奇理斯玛”(charisma)这个词原是早期基督教的语汇,最早由马克斯·韦伯在论述各种权威时将它加以引申并赋予新义,用它来指有创新精神的人物的某些非凡品质。后来,爱德华·希尔斯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奇理斯玛”现象的更为综合的观点。他指出,社会上的奇理斯玛不一定来自有“奇理斯玛”的个人的创造,“它是赋予人们行为、作用、制度、符号以及物质客体的一种品质,因为它们被认为与‘终极的’、‘根本的’、‘主宰一切的’产生秩序的权力有联系”。他还说:“‘奇理斯玛’倾向是社会需要秩序的结果。”“社会有一个中心,社会结构有一个中心带……而这个中心或中心带是价值和信仰领域的一种现象。‘奇理斯玛’是符号秩序中心,是信仰和价值中心,它统治着社会。它所以是中心,因为它是终极的,不能化约的;很多人虽不能明确说出这点,但却感到有这样一个不能化约的中心。中心带是具有神圣性质的……中心价值体系的存在,根本上取决于人类需要结合能超越平凡的具体个人存在(并使其改观)的某种东西。人们需要与大于自己身体范围的和在终极的实在结构中比自己的日常生活更为接近核心的一个秩序的一些符号相接触”(参见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6]P.布尔迪厄:《国家的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05页。
[7]P.布尔迪厄:《国家的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0页。
[8]熊佛西:《校庆抒感怀》,见《熊佛西戏剧文集》(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961页。
[9]田华:《中戏“表训班”》,见《戏剧殿堂》,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10]P.布尔迪厄:《国家的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0页。
[11]孟京辉:《先锋戏剧档案》,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358页。
[12]P.布尔迪厄:《国家的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9页。
[13]P.布尔迪厄:《国家的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9页。
[14]贾冀川:《20世纪中国现代戏剧教育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页。
[15]参见中央戏剧学院网站教育教学栏,http://www.zhongxi.cn;http://www.chntheatre.edu.cn,名单略有出入。
[16]任鸣:《感恩母校》,见《戏剧殿堂》,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17]雷恪生:《发挥余热——写在话剧﹤雷雨﹥演出之后》,见《戏剧殿堂》,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18]丁罗南主编:《上海话剧百年史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名单略有出入。
[19]曹禺:《贺词——为纪念中央戏剧学院三十周年而作》,载《曹禺全集》第六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