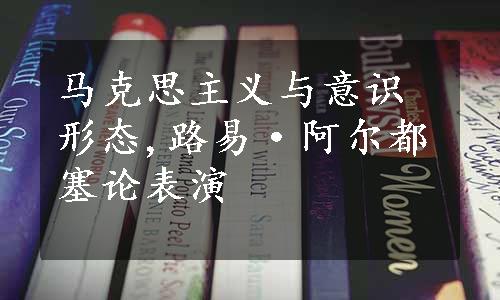
邱红霞
路易·阿尔都塞(1918—1990),法国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家。他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之后在阿尔及尔和法国接受教育。1939年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录取,后因二战时期服兵役而中断学业。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时期,阿尔都塞被关进了德国的战俘集中营,直到战争结束。他获释之后,才继续自己的研究事业。1948年,他完成了一篇关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硕士论文,随后通过了哲学资格认证,并留校任教。
阿尔都塞在他人生的前三十年中是一位见习天主教徒,并在此期间表现出了对天主教修道生活及天主教传统的强烈兴趣。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阿尔都塞加入法国共产党,并终其一生保持党员身份。在1968年5月的巴黎罢工时期,他因患抑郁症在疗养院中疗养,他一生中都在与这种疾病抗争。与一些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同,他支持法国共产党否认学生运动的革命性,尽管他后来颠覆了这一观点。
1980年阿尔都塞杀死他的妻子,但因为不适合受审,只是被收容,于1983年获释。他后来住在巴黎附近,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1990年死于心脏病。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他写了两个不同版本的自传,这两本自传都在他1992年死后才得以发表(都收录在1995年版的《来日方长》中)。
阿尔都塞之所以重要,在于在他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方式。这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与20世纪60年代的知识分子流行思想形成共鸣,其中包括了结构主义思想。阿尔都塞的作品有时被称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后现代马克思主义”。不管标签如何,他重读马克思旨在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从苏联以及人文主义的解释中释放出来,这种重读意味着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得以复兴,并把他们重新应用于革命目的。
阿尔都塞的众多著作中,其中有三本特别有影响力:《保卫马克思》(1965年在法国出版),《阅读〈资本论〉》(1968年在法国出版),以及经常被引用的长篇论文《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写于1969年,被收进《〈列宁与哲学〉及其他文章》中)。阿尔都塞对不同领域都有所涉猎,如文化研究、电影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尽管他在表演研究领域中并未达到同等高度。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评定,其中包括拒绝一些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核心设想。例如他反对决定论的说法,而这种说法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构想中可以找到。经济基础指的是特定的经济“生产方式”在一定的社会中运行。不同的社会由不同的经济系统(生产方式)组织——例如农业的、资本主义的或计划的。上层建筑是指政治的、社会的、宗教的,以及一个社会的其他非经济方面,包括一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方面,例如政府的、教育的、宗教的和其他制度结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上层建筑——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由经济模式或经济基础决定并受其制约。而阿尔都塞更倾向于谈论关于社会形态(也就是社会)包括三种实践的观点,即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看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并给予上层建筑相当大的自治权,但最后,他不得不承认经济基础起决定性作用,即使它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不占主导地位。
“实践”这一术语对阿尔都塞有特定的意义,他指明了变革的过程:“关于实践,我们一般指的是通过一定的人力劳动,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把一定的原料加工为一定产品的过程。”经济实践涉及运用人力劳动和其他生产方式来实现从(自然)原材料到(社会)成品的转换。政治实践用革命来实现社会关系的转换,意识形态实践用意识形态来改变现实社会关系,即一种与主体相关的现存的生存条件。理论通常被视为与实践相反,但对阿尔都塞来说,理论恰恰是一种实践。
意识形态这个词是阿尔都塞的理论议程的核心。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里,阿尔都塞融合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精神分析思想,以发展他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它与主体性的关系。阿尔都塞在这篇文章中主要关心的是,在现存的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复制生产模式的问题,以及它们与人的关系问题。根据马克思主义思想,实际上他们心甘情愿地受统治阶级的统治,为什么人们会支持这种过程?通过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及传唤的概念阿尔都塞明确地表达了他的答案。
资本主义社会的复制过程发生在两个层面:压制性层面以及意识形态层面。一方面,社会控制可以通过运用镇压力量来进行强制,通过那些制度体系,如政治、军队、法庭和监狱——阿尔都塞称之为“压制性国家机器(RSAs)”。这些体系制度压制不满,维持社会秩序,如统治阶级所预期的那样。但是,应用压制力量不是保障、维护资本主义的唯一方式。除了“压制性国家机器”,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也必须用来维护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阿尔都塞把这些意识形态的控制模式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s)”——教育、家庭、宗教、运动、电视、报纸和其他媒介——所有这些都复制了资本主义的价值、标准和设想。由“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s)”产生的意识形态的话语作用于个人主体,通过这样的方式,自身和他人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并受制于此,乐于受制于统治力量,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总之,意识形态强加于我们,实际上,我们在有所行动的同时,作为意识形态议程的心甘情愿的行为者。
马克思早期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错误的意识,与之不同,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理解为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尽管是在资本主义剥削已经被基本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意识形态)是为人类主体提供身份认同。对于阿尔都塞来说,“意识形态代表了对人类真实生存条件的虚构的个体关系”。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掩饰了一个易接近的、透明的真实的世界,但是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差别使得阿尔都塞与其相反。与把意识形态当成一种歪曲或者错误意识这种观念相反,阿尔都塞则把其看作一种借以理解我们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叙事或故事。实际上,客观世界对我们来说不可获得,只能(通过意识形态)表现出来。
意识形态对于每一个个体都有显著的作用。阿尔都塞通过传唤这一概念来理解这种作用。用一种特殊的论述,意识形态“招呼”和“定位(传唤)”个体,换一种说法,即意识形态给了我们主体定位。正如阿尔都塞所提出的,意识形态“起作用”或者“发挥功能”的方式是把个体“改造”成了主体。假定我们被传唤的地位认同已经接受了社会意义,并把自身置于这些意义当中,实施自己的目标,并假使我们有首先作出决定的自由。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概念是反人文主义的,因为他在此过程中对自主的能够自由选择的个体的核心性进行了质疑。相反,这一主体服从于统治意识形态,他把意识形态的传唤误认为是个体的自由选择行为。值得注意的是,阿尔都塞用一个戏剧性的隐喻描述了主体嵌入意识形态的这种介入。他对社会复制模式的工作的论述如下:
戏剧的舞台指导(场面调度)模式会受到剧本的制约,在这种戏剧中,同时拥有自己的舞台、剧本、演员;而且只有在他们首先被迫成为演员的时候,他们才能不时地成为真正的观众,另外,他们不能成为其作者,因为从本质上说,这是一场无作者的戏剧。(www.zuozong.com)
阿尔都塞提供了一个在活动中传唤的例子,他说,假如一个人在路上被一个警察叫住(传唤),警察说:“嗨,叫你呢!”这个人就转过身来面向这个警察。阿尔都塞说,仅仅做了180度的转身,他就变成了一个主体,为什么呢?就因为他已经承认那个呼唤“正”是冲着他的,“被呼唤的正是他”(而不是别人)。正如例子中显示的那样,传唤是一种行为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体通过对社会提示回应而变成主体,意识形态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在这方面,阿尔都塞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与皮埃尔·布迪厄、朱迪斯·巴特勒和欧文·戈夫曼等人一样,也认为主体是通过表演生成的。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主体意志同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相吻合,如同法律,以及那些形成及维护意识形态的体系。意识形态就将我们转换成主体,(我们就成了)用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思考和行为的主体。
根据阿尔都塞的理论,尽管意识形态被理解为个体旨在满足统治阶级意志,但并不是说意识形态是不可改变的。相反,意识形态中包含着非常明显的矛盾以及合理的悖论。这就意味着被传唤的主体在意识形态中至少有撤销或者动摇的空间,(这个时候)改变或者变革可能发生。
阿尔都塞在《“皮科罗剧场”: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了表演的政治性。他对意大利导演乔尔焦·斯特雷勒1962年的作品进行了评论,在他看来,乔尔焦·斯特雷勒的作品与德国剧作家、导演布莱希特的唯物主义戏剧实践的原则相一致。穆罕默德·卡萨尔在读《“皮科罗剧场”: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时指出,正是阿尔都塞对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分析进行重新组合,才使得我们得以窥探社会批判对被传唤的主体保持开放是如何可能的。
戏剧表演,作为一种艺术活动,(如果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领域层面上看,因此成为了上层建筑)不能认为能够带来绝对变化。但是,上层建筑活动,包括戏剧实践和政治哲学,可以很好地展示改变状况和致力于鼓动改革的前锋派。阿尔都塞一贯主张上层建筑与结构或者基础之间的组织原则有更大的决定作用。
卡萨尔进一步表明,阿尔都塞认为唯物主义戏剧的批判性不是戏剧本身揭露矛盾,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而是表演与观众之间的互动
观众“在部分意识的一般情况下,参与到演员、导演、剧作家当中”。这就是为什么阿尔都塞维护“剧本本身就是观众的意识”;观众与表演享受同样的限定认知,竭力从唯物主义意识向辩证思维转换……从两种幻觉的意识(观众与表演的对抗)的冲突中,批判地定向地进行对方所缺乏的补充……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身份诞生了——借艺术性活动通过参与到认识论的研究中来为自身辩解,反之亦然。
蒂莫西·穆雷运用阿尔都塞的《“皮科罗剧场”: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这篇文章来界定那些先锋主义者,如理查德·福尔曼、马布·迈因斯等人的表演的政治价值。穆雷认为虽然这些作品退回到正面描述,但并未退回到程式化的地步,它只是退回到电影以及执行认识论研究任务的表演。这些表演给观众提供了一种对唯物主义的直观看法,基于这种看法,它们得以发展,也受到支配。然而,赫伯特·布劳读了同样的文章,但对于阿尔都塞的唯物主义戏剧有能力使观众直观意识形态机器这一说法,并不像穆雷这样乐观。布劳在阿尔都塞另外的社会批判表演实践的可能性的可靠断言中发现了一股悲观主义的暗流,因为阿尔都塞曾经说过:
剧本本身是观众的意识”……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采取的标准的问题,采用何种标准来衡量虚构……使观众事先与剧本结合不一定能保证一种批评的清醒性,也不一定能保证这种统一的过程被感知。
最终很可能仅仅是简单地思考,使统一的意识形态的假设具体化,而不是为挑战他们创造条件。
(邱红霞: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硕士)
【注释】
[1]原文参见Philip Auslander,Theory for Performance Studies:A Student's Guid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p.33-38.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