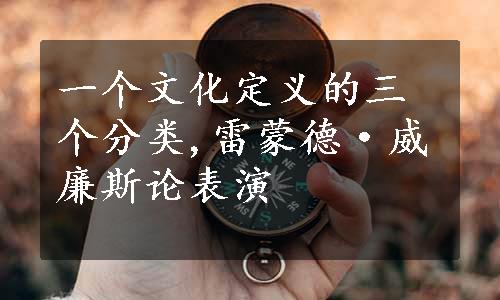
杨楚晗
雷蒙德·威廉斯,英国文学理论家、小说家、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文化研究的创建者之一。他出生于威尔士,在一个工人阶级家庭里长大。1939年,威廉斯凭着一笔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修习文学,其间加入了“剑桥大学社会主义俱乐部”。1942年他被征召入伍,在二战中担任一名坦克指挥官,学业由此中断。战争过后,威廉斯重回剑桥大学完成了学业。
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在牛津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工作了十五年,其间写就了《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 and Society)和《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这两部重要著作。1961年他进入剑桥大学担任讲师,教授英文和戏剧,此后一直在剑桥工作,直到去世。和这本书里介绍的大部分理论家不同,威廉斯在作为学者和时事评论家的双重生涯中,将戏剧作为他的主要研究课题。在他最早的著作《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Drama from Ibsen to Eliot)和《表演的戏剧》(Drama in Performance)里,他将涉及表演的文学性戏剧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实践进行审视。他20世纪60年代的重要著作包括《现代悲剧》(Modern Tragedy)和《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1975年,他成为剑桥大学首位戏剧学教授。
威廉斯从一个跨学科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来切入文学。他发现,在文学中表现社会阶级划分的方式通常是对上层阶级有利的。他也对交流模式与社会物质条件之间的关联方式感兴趣。他的理论,尤其是关于文化的理论,深深影响了诸如新历史主义等其他思潮,并时常让人联想到海登·怀特的“元史学”概念以及后者对“历史编纂”的关注。在怀特看来,考虑到社会权力的问题,历史编纂作为一种阐释性的叙事模式永远不可能是客观公正的。
威廉斯关于文化的观点给现在为人所知的文化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在他第二本重要理论著作《漫长的革命》一书中,他探讨了与“文化”这一术语相关联的概念性议题。他区分了“大写的文化(Culture)”与“小写的文化(culture)”。“大写的文化”是一个道德和美学意义上的术语,最初是由一些英语作家如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与人文主义者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以及现代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F.R.Leavis)所提出的。在他们的话语中,大写的文化意味着“高雅文化”,即文明中最伟大的道德和美学成就的总和。显然,“大写的文化”这一概念并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它主张和维护社会阶级——“高雅文化”和“高级”是同义词。与这种观点相反,威廉斯从社会角度出发提出了“小写的文化”这一概念。在这里,文化不再只包含那些被视为文明制高点的观念和成就,而是涵盖了人类活动的全部产物,包括语言、社会、政治、宗教观念和机构以及其他概念的和物质的表现。换言之,这种意义上的文化包含了人类为使自身存在有意义而创设的一切事物。
“文化”这一概念正是威廉斯文学-文化研究的焦点。威廉斯认为文化的概念被简化成精英阶层的产物,于是他开创了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文化研究(威廉斯有时称之为“文化科学”,以强调它同社会学的联系)——考察非精英群体的日常生活。
作为社会性的文化这一观念是威廉斯“文化定义的三个分类”中的一个。“文化定义的三个分类”,即理想的、文献的和社会的文化。“理想的文化(ideal culture)”是指把文化视为以绝对或普适标准来衡量的“人类自我完善的状态或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分析“实质上是对生活或作品中那些被认为构成了一种永恒秩序或与普遍人类状况有永久关联的价值的揭示和描述”。“文献的文化(Documentary culture)”将文化当作一种文献记录、一座仓库,使其装着诸如文学、艺术、哲学这些文化成就的人工制品。在这里,“文化即知性和想象性作品的主体部分,这些作品详尽地记录了人类各种各样的思想和经验”。最后是“社会的文化(social culture)”,如前所述,“社会的文化”对文化的关注并非简单地依据高级精英文化产品和成就,而是依据整体上人们构想和践行生活的多种方式。因此,文化包含着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和流行的文化,以及其他各种生活在这世界上的人们的思想和实践模式。对威廉斯来说,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种过程,它一方面维护自身并作用于我们,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被人类所生产和改变。文化的过程是既流向我们又从我们流出的。作为社会的文化这一概念就是要表达这种动态。
威廉斯平等的非精英主义文化观的副产品之一就是他为流行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因为对文化分析而言,一切人类产品和实践都是有价值的、可利用的,如今被我们称为流行文化的那些形式——电视、电影、流行音乐或摇滚乐、体育、博客等——和高雅文化产品一样都在揭示文化的本质。所有文化产品都是文化。威廉斯对流行文化的研究明确地反映在他后期作品中,如《电视:技术和文化形式》(Television∶Technology and Culture Form)。
威廉斯提出,文化的这三种类型或定义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并且要考虑到这三种文化要素之间的互动和关系。他说:“无论实践起来有多难,我们也必须将这个过程视为整体,并把我们特定的研究同这个实际的复杂机制联系起来。”所以,威廉斯将所有戏剧性的表征,不论是舞台上的、银幕上的、广播中的还是电视里的表征,都视为同一套文化冲动的表现,而不是把它们作为单独的美学和文化形式隔离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表演中的戏剧》一书最后对一部电影进行了分析,这本书关注的是文学性的戏剧以及它们上演的条件。威廉斯把戏剧和一切文化形式都看作一个既定社会其他实践特征的延续。例如,他在《现代悲剧》一书中指出,“悲剧”一词严格的文学性意味不应该优先于日常使用中的通俗含义,因为这一切表现的都是生活于一定时空中的人们对它们生活的理解。威廉斯从未放弃作为一个批评家对区分作品好坏的兴趣,但他坚持认为作品质量不能同它的文化定位画等号,因为“你能在国家大剧院看到粗劣之作,也能在警察剧里发现极富独创性的剧本”。
一些评论家如艾伦·奥康纳(Alan O'Connor)和香农·杰克逊(Shannon Jockson)认为,人们可以从威廉斯与戏剧相关的作品中探寻他的思想从文学导向到文化导向的转变:他从主要依赖文本关系的思考转向对文化的思考,并把文化视为一种像表演一样行动化和具体化的东西。通过“双重视角,即既看到舞台与文本,又看到在它们内部活跃并发挥着作用的社会”,威廉斯觉得他能够像“理解社会本身一样理解我们构建起来的既定惯例”。在对文化的考察中,威廉斯对他称为“感觉结构(the structure of feeling)”的概念给予了极大关注,这一概念也最早出现在他的戏剧论著中。威廉斯认为,“感觉结构”就是一种共同的文化感觉所具有的特征和品质。尽管这个术语的确切含义在威廉斯作品中随时间发生了改变,但它最主要还是指在特定文化语境下的一个民族或一代人鲜活的经验。鲜活的经验包括“官方文化”——法律、宗教教义以及文化中其他规范形式——和人们在他们文化语境下的生活方式之间的互动。感觉结构为一个民族注入了一种特定的“生命意识”和社群经验。它包含了一套特定的文化共性,这套文化共性普遍存在于一种文化中,即使文化中的个体存在差异也不例外。威廉斯指出,社群经验不一定被一种文化广泛共享,相反它最有可能是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群体的感觉。这种文化感觉通常不会由任何书面的理性的话语模式来表达,尽管它经常存在于文学性的文本中,仅仅被间接地揭示出来。对感觉结构的文化分析目的在于发现这些共同的感觉和价值是如何运作并帮助人们理解他们的生活的,以及感觉结构在不同的情况下是怎样出现的。
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一书中,威廉斯考察了历史编纂的问题,他认为文化研究者们必须意识到历史语境中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并要注意避免偏袒其中那些主导性的权力话语。换言之,威廉斯没有将历史视为一段可命名的文化时期的连续进程——其中每一个时期都决定了接下来的另一个时期——而是要通过文化斗争和抵抗的视角来看待历史。为此,他提出了三个概念,“它们不仅承认‘阶段’和‘变异’,还认识到任何实际过程中内部动态化的关联”。这三个概念是指历史时期中的“主导的”“残余的”和“新兴的”方面。(www.zuozong.com)
一个历史时期“主导的”方面是指那些主宰或试图主宰人们所想所为的思想与实践体系,即主导性的价值、道德以及意义的主张。对威廉斯来说,主导性这一概念与霸权相关。主导性同时也意味着霸权性,它严格地推动着当权者的利益,却压制了其他人的利益。但是主导文化并非无可匹敌。威廉斯提醒我们,在任何一个文化语境中,“有效的主导文化”总是处在非主流的辅助的价值、意义及实践的围攻之下。这些主导文化的替代者和反对者可在“残余”和“新兴”的形式中被发现。
一个历史时期“残余的”方面是指过去的文化形态。这些陈旧的价值和意义可能一度具有支配性,但如今却被当前的主导权力代替。这些更老的文化形式现在可能依然活跃,对主导的文化形式施加着压力,即使它们通常是从属于主导文化的。简言之,残余文化既可以被收编到主导文化中来,同时也内含着反对或代替主导文化的因素。
一个历史时期“新兴的”方面是指那些新生的价值、意义以及实践,它们预示着未来的文化走向并对现存的主导文化造成压力。文化形态永远不会被主导文化所冻结。主导文化也因这些威胁要取而代之的新兴文化而永远面临阻力。
威廉斯把这三种文化过程的关联视为一个领域,在这里,摆脱压制的努力以及对霸权的抵抗都在发生。更进一步来说,这种历史进程的三重视角要求我们将文化视为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还要留心文化运动与变革中这三个方面的交叉与相互渗透。下面关于戏剧的陈述总结了他的观点。
任何时期,包括我们这个时期的戏剧,都是一套错综复杂的实践,其中有些是被收编了的——残余但依然活跃的系统中那些已知的节奏和运动——有些是探索性的——新兴的表征、重塑、新身份中难懂的节奏和运动。在真实的压力之下,这些截然不同的种类经常杂乱且强有力地融合在一起;难以找到一个单纯的旧戏剧或新戏剧的实例。
威廉斯关于文化和历史的概念对戏剧和表演研究贡献巨大,尤其是他说文化分析意味着任何既定的文化形态或话语都要放在与其他文化的联系中而不是孤立地去看待,这种观点贡献更大。比如说,那些排除了百老汇音乐剧及其他流行形态的戏剧史符合精英主义的利益,而并未提供任何意义上的复杂的方式,即不同类型的戏剧相互关联并且同既定时期内文化表达的其他形态相关联。他对高雅文化与流行文化之间壁垒的摧毁表明了一种非正统的观念,由此,要想理解任何特定文化元素的复杂性,需要考查文化图景中的一切方面。最重要的是,威廉斯的观点是一种唯物主义观,它强调总是要把文化话语和经济与社会力量联系起来看,这并不是基于经济和社会决定文化这样的假设,而是出于对它们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感觉结构的理解。这种感觉结构表明,人们体验日常生活的方式正如他们体验表现性文化的方式一样丰富。
(杨楚晗: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硕士)
【注释】
[1]原文参见Philip Auslander,Theory for Performance Studies:A Student's Guid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8,pp.159-16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