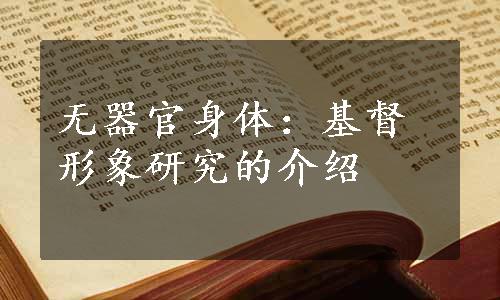
王 蕾
摘 要:东正教圣像画的缺失和文艺复兴绘画的缺失,程度是相同的:或者只想画出不可见的基督,或者只想画出可见的基督,无论是只强调神性还是只强调人性,都不是耶稣的真实形象。真实的耶稣,必然同时包含着双重性,他不是场景里的道具,而是一具“无器官身体”。基督的形象就处于这样的夹缝里,不断地进行着一场充满悖论的叙事:“辖域化——解辖域化”“肉身——道”“死亡——复活”,进行着一场永无休止的争执。
关键词:无器官身体 基督形象
20世纪伟大的德语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一生保持着自身的孤独状态。孤独,并非因他缺乏对话者,而是他要用更多的时间和他的上帝撕扯。
里尔克曾说:“我所有的书中只有少数的几种是不可或缺的,有两部甚至无论我在何处都在我的物品中。此刻它们也在我的身边:《圣经》和丹麦伟大诗人茵斯·彼得·雅各布森的书籍。”
《圣经》作为精神源泉,给了里尔克无尽的灵感。他写下众多关于基督教题材的作品,比如以圣母玛利亚为题材的诗集《玛利亚生平》,众多以《圣经》人物为题材的诗歌如《上帝的故事》《基督幻想》《定时祈祷文》,以及惊世之作《杜伊诺哀歌》。
里尔克的一些诗虽然没有明显的《圣经》出处,却也隐现出相关的宗教思想痕迹,譬如《严重的时刻》[2],其内容如下: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在世上哭,
在哭我。
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
无缘无故在夜间笑,
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
望着我。
这版译文是九叶派诗人陈敬容所翻译,诗题被译成“严重的时刻”,抑或“沉重的时刻”。一个隐去了名字的神秘时刻,引发了后世永无休止的揣测,众说纷纭。
假如将此时刻和“基督受难”联系起来,未尝不是一种贴近里尔克精神世界的有效阐释。毕竟,里尔克曾耗尽生命,试图探索和重建与基督的关联。
“哭、笑、走、死”,这是四种沉重的情感状态与生存状态,它们预示着某个严重事件的发生,令人感到既悲伤又欣慰,隐含着一种深深的宿命感和必死论。而这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却是源于“无缘无故”,这个重复出现的词语一次又一次印证了必死的宿命。
死是什么?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是什么?望着我,是什么?
某个改变人类命运的重大事件: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作为上帝唯一的独子,耶稣的道成肉身命定了献祭自身的结局,他别无选择,抑或说,他主动选择了死亡。没有任何人必须去死,哪怕是为了赎世人的罪。所有的发生都无法追溯任何缘故,都仅仅因为耶稣是基督,是上帝之子,是道成肉身,这就是无缘无故。就像你就是你自己一样被命定了。
“望着我”——一个眼睛的动作,十分坚定,情绪饱满——是里尔克极为情感化的处理方式,在拯救者与被拯救者之间注入了情感的关系。耶稣基督无缘无故被钉死在十字架的严峻时刻,没有因痛楚而哀嚎,没有关注自身的困厄处境,而是在“望着我”。我,既是诗人的自况,也是世人的类比。死去的那一刻,耶稣望着世人。
不如说,那个严重的时刻,那个无缘无故被处死的时刻,基督耶稣透过一个凝视的眼神,表达了他对所有人,甚至谋杀者的谅解。有些人也许在等待被谋杀者的复活,并拥抱残暴的凶手。
那么,为什么这个宗教事件一次次地重演,在格吕内瓦尔德[3]、霍尔拜因[4]、弗朗西斯·培根等伟大画家的笔下不厌其烦地描绘耶稣之死?
耶稣之死这一历史事件的严重性在于,它改变了人类历史和整体命运。濒死的时刻,仿佛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里尔克眼里的基督无辜而绝望,却并没有抛弃和世人的关联,“他望着我”,无论那个瞬间有多么紧迫。
献祭肉身是他的宿命。《新约》里的基督耶稣不像《旧约》里的上帝,他具有双重性:神性——人性,无限性——有限性。
选择被处死,献祭自身,这个行为恰恰是耶稣身处双重语境、濒临边缘时刻的一次重大的争执。作为肉身的耶稣,依然被搅碎了,扭曲了,变形了,他的灵魂仿佛立即就被肉身的搅拌机甩出去。可是,他还没有彻底逃脱肉身的撕扯,必须承受鞭刑的苦痛和枪戟的折磨,从而进入了一个濒死的漩涡。
这个状态就是“歇斯底里”[5]。
痴迷于“基督受难”这一暴力事件的画家弗朗西斯·培根,在二战后期创作了众多相关作品。1945年战争阴霾还未消退,人们就被弗朗西斯·培根画于1944年的三联画《以基督受难为题的三张习作》(图1)震惊了。
图1 《以基督受难为题材的三张习作》
注:该画创作于1944年,现收藏于英国伦敦泰特美术馆。
画面里三个怪诞的、可怖的、痉挛状的怪兽形象,绝望地嘶吼着,它们似乎被囚禁在密闭的狭小空间里,被无望的压迫感催生出歇斯底里的状态。这件作品令饱尝战争灾难的英国人感到战栗不安。那三个怪物的歇斯底里,就是弗朗西斯·培根所认定的“耶稣受难”。
图2 《三联画,十字架刑》
注:该画作创作于1965年,现藏于美国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
1965年,他又创作了《三联画,十字架刑》(图2)。此画里面诡异的怪物形象变成了血腥的场面:中间联,一个带着纳粹袖章的裸体屠夫正在屠宰另一个几乎只剩一摊血肉的人,旁边有两个身着黑衣的审判者;左联,一团血肉模糊的人瘫在一张床上,他也带着纳粹袖章,另一个血肉模糊的人从旁边观望着;右联,像是一只被屠宰剥皮后的动物,血淋淋地被悬挂起来。
这些过于残暴血腥的场面,让观众惊惧不安,不忍卒睹。画家弗朗西斯·培根在和大卫·西尔维斯特的《访谈录》里解释道:“有关屠宰场与肉的场面,完全符合‘基督受难’的整个事件……动物屠宰前的死亡气息弥漫着整个画面,这是您无法想象的。那些动物,其实早已意识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它们千方百计想要逃避。所有这些……预示的东西与基督受难已极为接近。”[6]
我们发现弗朗西斯·培根作品中有一种非常独特且明显的内部结构,就是基督受难事件与屠宰场事件的紧密交叠。他将耶稣受难的意义拉向了对人类残暴本性的反思:战火、屠杀、集中营、监控器的世界里,人类暴露出的丑陋狰狞面目。
每一次杀戮、每一个人的死去、每一只动物的屠宰,都是在忍受着如同“耶稣受难”这般的绝望情绪。这意味着,弗朗西斯·培根把“耶稣受难”这一宗教历史事件的意义扩大到了人类生存处境的层面。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人类历经的所有苦难都变成了一个隐喻,一个互文。那个看似放荡不羁的画家弗朗西斯·培根在《访谈录》里严肃地说道:“假如你路过那些不可思议的屠宰场和肉铺店,就像沿着一排排死亡的走廊,看到那些肉、鱼、鸟……所有的一切都被悬挂起来,奔赴死亡。”[7]
死亡最深刻的意义就是从“耶稣之死”开始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物的死亡,都是对耶稣之死的模拟。死亡出现一次,耶稣就再死一次。
德国宗教改革时期,画家格吕内瓦尔德创作了著名的《艾森海姆祭坛画》(图3),他在这幅画里也把耶稣拉入了真实可感的困厄处境。
这幅祭坛画里,他描绘了《耶稣磔刑》《耶稣复活》《受胎告知》等几个《圣经》里提到的场面。其中《耶稣磔刑》是关于“耶稣受难”的悲剧场面,画面弥漫着悲伤凄惨、阴森可怖的气息。
图3 《艾森海姆祭坛画》
注:该画现藏于法国的安特林登博物館。
画中,搭成十字架刑具的两块原木重大粗粝,令人恐惧不安。被钉在上面的耶稣,遍体鳞伤,鲜血淋漓,肌肤腐烂,手脚抽搐。周身皮肤幽绿,像患了麻风病一般,流着脓血。他面孔扭曲,嘴巴下垂,忍受着濒死的巨大痛楚,奄奄一息。那种难以忍受的绝望与惨痛,让观众感同身受,如同置身于古罗马残暴的大屠杀中。
格吕内瓦尔德的基督介于尸体与垂危之间的病危状态。基督不是拥有大能的唯一的神的独生子吗?这是不是画家有意识地丑化耶稣的形象?
画家想要给世人一个当下处境里真实的基督。身处困境的人们所需要的拯救者,绝非抽象的、遥远的、坐在宝座上戴着金冠的王。
原来,这幅祭坛画是为当地麻风病院所画。所有的麻风病人都会对着它祈祷。将耶稣的形象塑造成一个濒死的患者,就会让病人们相信基督与他们同在。
格吕内瓦尔德世界里的耶稣形象,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旧约》里的上帝,而是身处人间困厄的受难者。这时,耶稣就同时具有受难者与拯救者的双重身份,他的使命就具有了双重维度。
1521年,德国画家汉斯·霍尔拜因创作的一幅木板画《墓中的基督尸体》(图4),更赋予基督带有伤痕与疼痛感觉的身体性经验形象。
画面展现出墓穴的内部,棺椁里有一具受磔刑之后的耶稣。他受尽了非人的残酷折磨,已经被从十字架上撤了下来,人们任其腐烂。这是近乎一具干瘪的尸体,那浮肿的脸上血迹斑斑,满是伤痕,瞳孔凝固了。
图4 《墓中的基督尸体》
注:该画创作于1521年,现藏于瑞士巴塞尔艺术博物馆。本图中附有局部细节图。
耶稣已经骨瘦嶙峋,右侧胸肋、手掌、脚掌三处的伤口显然在入殓时被人擦拭过,留下斑驳干涸的血迹。鼻翼、手指、脚趾处,一股铁青色逐渐蔓延开来,让人感到死神正在吞噬他的躯体。
这幅杰作彻底征服了俄罗斯19世纪以沉重深刻著称的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8]。1867年8月2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亲眼目睹《墓中的基督尸体》这一传世之作,携新婚夫人安娜·斯尼特金娜专程赶往巴塞尔艺术博物馆。结果,汉斯·霍尔拜因令他震惊无比,并启发他创作了小说《白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夫人安娜·斯尼特金娜在1867年8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画中的基督酷似现实中的一具尸体,画得那么逼真,以致我不愿意和它呆在一个房间里。也许,这是一种惊人的真实,但是它决不是一种美,它使我产生的只是厌恶和恐惧。可费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称)对这幅画评价极高。他想凑近细细观赏,便站到了椅子上……”
后来,安娜·斯尼特金娜在《回忆录》中又写道:“这幅画给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压倒一切的凄惨印象,他站在画前,似乎惊呆了。这幅画我实在继续看不下去:印象太沉闷了,对于我那敏感的神经来说,尤其受不了。因此我便到别的展厅去。过了十五——二十分钟,我回来后,发现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画前,好像钉在那里似的。在他激动的脸上有一种吓人的表情,那是我在他癫痫发作之前曾不止一次见到过的。……所幸,病并没有发作: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终于悄悄平静下来,在离开博物馆时还坚持再一次进去看看那幅使他如此震惊的画。”
究竟这幅画里有什么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受到如此强烈的刺激,甚至几近癫痫?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前辈作家尼古拉·卡拉姆津[9]也曾提到过霍尔拜因的《墓中的基督尸体》。卡拉姆津在《一位俄国旅行者的通信》中写道:“刚刚从十字架上卸下来的基督身上,看不出任何神圣的东西,但作为一个死人,他却被描绘得十分质朴自然……”
据卡拉姆津所言,墓中的基督形象没有了神圣的维度,他被还原成一个有血肉之躯的死人。这是人们必须认识到的真实性的残忍。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白痴》中多次提到《墓中的基督尸体》,他借书中人物之口说,一个人“总得相信什么!总得相信谁!不过霍尔拜因那幅画实在奇怪”,因为它“能使某些人丧失信仰”。
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这幅画会令人丧失信仰?
众多拜占庭时期的圣像画里,基督的形象多少会受到一些美化,因为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是具有“神圣性”和“超越性”的救世主和赎罪者。但凡涉及耶稣的受难题材,无论是“上十字架”“十字架磔刑”,还是“下十字架”,多数画家都会竭力保持耶稣面容的美。这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超验的美,即使在忍受最可怖的磔刑时仍旧如此——“溃烂的伤口”和“痛苦的面容”曾经被作为禁忌,一向被视为渎神的表征。
因此,圣像画家们,抑或以宗教为题材的传统画家们通常用被美化的、体面的“五伤”痕迹来象征基督曾被钉死的事实。譬如15世纪的安德烈亚·曼特尼亚[10]的《耶稣受难图》、16世纪的丁托列托[11]的《钉刑图》、17世纪的保罗·鲁本斯[12]的《升举十字架》、19世纪的马尔顿·雅各兹·凡·汉斯克克的《各各他》等诸多经典作品里正在接受钉刑的耶稣,他的五处伤口被淡化了,面容带着一丝绝美的神情。
然而,小霍尔拜因的《墓中的基督尸体》里耶稣的形象丝毫没有被美化,画家竭力画出他饱尝的无限的苦楚、创伤、刑罚,画出他死去时肉身所承受的难言之痛。这种残酷的真实一般会被教廷视为对耶稣形象“神圣性”的弱化,被视为一种“渎神”,这也许是《墓中的基督尸体》至今无法进入梵蒂冈的缘由所在。
作为上帝之子,作为救世主,他如此孱弱,连死亡的痛苦和恐怖都无法克服,又怎能制服罪恶呢?
既然“基督受难”是耶稣无法选择的天职与命运,既然他可以用坦然又超然的态度接受门徒犹大的背叛、众人的误解唾弃、行刑者的鞭笞,那么行使众多神迹的耶稣为何不能超然绝美地死去?
这就是困扰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仰之惑:“它能使某些人丧失信仰。”
小霍尔拜因的《墓中的基督尸体》里,耶稣形象是一具腐烂的尸体;格吕内瓦尔德的《艾森海姆祭坛画》里,耶稣形象是一个生命垂危的麻风病人;弗朗西斯·培根的《耶稣受难三联画》里,耶稣形象是一摊肉铺店里被屠宰后露着脊柱骨和血管的肉……这种残忍血腥的形象,是否有着一种渎神的危险?
假如让拜占庭时期的圣像画家来回答,他们可能睁大惊惧的眼睛指责:基督的面容怎么可以有死神的影子?
小霍尔拜因、格吕内瓦尔德、弗朗西斯·培根在画基督脸部时,都使用了渎神的颜色:青绿色。而培根在使用青绿色之外,还把耶稣的形象直接画成了一摊肉。
在拜占庭时期的圣像画家的眼里,这简直不可思议。拜占庭时期“东正教”的圣像画中,耶稣的面容和光环都被直接使用金箔或者银箔(金箔更加常见)描绘。金子的物理属性极为稳定,金色本身也是对权力和永恒的象征。耶稣的面容基本上都必须左右对称,五官的位置、距离、大小都必须遵循一个固定的范例。这当然是为了赋予上帝之子一种超验性和绝对性,他们的这种手法正是出于对“神性”的强调。
文艺复兴早期,耶稣形象有了一些改变,可是圣像画里象征永恒的金色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很多画家仍然把耶稣的面容和躯体画成金色。譬如15世纪的洛伦佐·莫纳科(Lorenzo Monaco)[13]的木板油画《基督受难像》、1641年亨利·贝勒丘斯的《十字架上的基督和圣丹尼的殉教》里,基督耶稣的形象色彩构成主要是以金黄色融合出闪亮的接近肤色的肉色,以用金色的闪光类比基督耶稣的神性。
文艺复兴中期,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丁托列托、拉斐尔在描绘“耶稣”形象时,就开始拒绝把他的肌肤画成金色。那种象征着至高无上“神性”的金色逐渐消失了,画面中出现的耶稣也具有了正常人类的肤色。这在16世纪初拉斐尔的《背十字架》、16世纪中期丁托列托的《钉刑图》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圣经》里记载的“基督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的神子,他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拥有可见的肉身与不可见的神性。相关的基督教历史研究证明,耶稣确实在历史上存在过。公元451年,卡尔西顿会议就声明,“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同等完整的,他在神性上与圣父本质相同;他在人性上除了没有罪以外,其他方面都与我们人相同”。[14]
可见,基督教神学并不否认基督的人性。这意味着他不仅仅是一个宗教里的神话,必须同时具有现实性。这就是艺术的处境化。艺术的处境化必然带着不忍直视的惨痛才能揭示现实的黑暗与罪恶。真实的耶稣绝不是遥遥无期的绝对的他者,而是处于危险的边缘,同时具有受难者和拯救者的双重身份。
所以,我们不能漠视尼采对传统基督教那个过于抽象的“神”的指责:“现在他把自己变为某种更为瘦弱和苍白的东西;他变为一个‘理想(ideal)’,他变为‘纯粹精神’、‘绝对者’、‘物自体’、神退化成了:他变成了‘物自体’。”[15]
有些疯癫气质的尼采毫不掩饰他对康德把上帝变成“超验”之物的厌恶。假如把“不可见者”的超验性与经验性对立起来,就等于否认了上帝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连接。
这也是为何尼采在《上帝之死:反基督》里宣告了上帝的死亡,却对耶稣表现出审慎的敬意与赞誉。
尼采在《上帝之死:反基督》里接着写道:
事实上,曾经只有过一个基督徒,而他已经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
这个福音的带来者死了,正如他曾经生活过一样,正如他曾教训过人们一样——他不是去“救赎人类”,而是告诉人们必须怎样去生活。这个实践他给我们人类的遗产:他在裁判者前,在捕役前,在那些控制者以及各种诽谤者和责难者前的行为——他在十字架上的行为。他没有反抗,他没有为他的权利辩护,他没有采取过可能挡开最恶劣结果的步骤;相反的,他反而惹起它。他乞讨他受苦,他爱那些陷害他的人。不反抗、发怒——但是,甚至反抗恶魔——去爱他。
只有在生活实践中,人们才会感到神圣、幸福、福音,才会时时感到为上帝之子。[16]
上帝之子的存在意义恰恰是他没有变为一个与现实隔阂的“理想(ideal)”“纯粹精神”“绝对者”“物自体”。他的处境具有双重性:上帝的理想世界与罪恶的现实世界。
他是一个中介体,身处共同边界、缝隙、褶皱的争执场域里,体验着歇斯底里般的死亡。毋宁说,他是一个“无器官身体”,一个“根茎(Rhizome)”。[17]
只有将身体性赋予耶稣,他才成为基督。而这种身体性需要在法国诗人、剧作家安托南·阿尔托[18]所提出的“无器官身体”的层面里理解。
1948年,安托南·阿尔托将“无器官身体”解释为作为体验的身体的界限,他在一个名为《84》的杂志上写道:“身体是身体/它是独一的/而且不需要器官/身体永远也不是一个有机组织/有机组织是身体的敌人。”[19]
戏剧作为体验的身体,与布莱希特[20]所坚持的“知性戏剧”截然对峙。安托南·阿尔托坚信表演绝不诉诸知性,而是诉诸身体,诉诸体验的无器官的身体。他还有更加大胆的提议:毁掉舞台,消弭演员和观众之间的界限,就像从来没有主角、配角、观众的身份区隔。这些在当时显得狂妄的建议,都是为了消解一切形式的隔阂。
阿尔托理想中的表演,并非隔绝于观众的舞台中央聚光灯下的独角戏。真正的表演者和尼采所渴慕的耶稣一样,是一个在危险边界游走的行动派和实践者。
后来,法国有些偏执狂气质的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拓展了阿尔托“无器官身体”的概念,他写道:“与没有器官的身体相对的,不是器官,而是人们所说的有机组织对器官进行的组织。”[21]他在另一本书中写道:“有机体根本不是身体,不是无器官身体,而是一个在无器官身体之上的层,也即,一种累聚、凝固、沉淀的现象——它强加给无器官身体以形式、功能、束缚、支配性的和等级化的组织,以及被组织的超越性,而这些都是为了从中获取一种有效的功用。层就是束缚,就是钳制。”[22]
假如在阿尔托和德勒兹所阐释的“无器官身体”的意义上去理解基督,那么耶稣的使命就更加艰辛和微妙。他需要做到尼采所要求的“去——超验性”,除此之外他还要拒绝把自身辖域化、等级化、组织化。这意味着耶稣不仅仅不能作为一个瘦弱和苍白的“物自体”,更不能作为任何程度上的主角、偶像、霸权者、特权者。
基督的存在就是为了反对阶层区隔,他是一个沿着危险的边缘不断摸索的“游牧者”。
这难道不是格吕内瓦尔德、霍尔拜因、弗朗西斯·培根笔下的耶稣形象吗?
他拒绝作为一个“超验”的偶像,而是和任何面对死亡的生灵一样,承受着真实的疼痛与折磨。
确切地说,耶稣形象是一个处于缝隙里的不确定因素,他永无休止地在反抗确定性。无论是成为确定的“理想”“纯粹精神”“绝对者”“物自体”,还是成为确定的“宗教领袖”“偶像”,任何一种确定性都是对真实性的辖域化。
他必须反抗任何形式的辖域化,这种游牧状态就是“生成(becoming)”[23]。它永恒地处于“正在发生”“还未发生”“已然发生”的模糊边界里,它是某物到某物的过渡,是一个“间性”状态。
莱布尼茨[24]、黑格尔[25]、尼采、海德格尔、德勒兹等诸位哲人都曾对此过渡状态作过阐释。
其中,海德格尔的阐释相对而言比较明晰,他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一文里写道:
“生成”并不意味着万物的某种流变,亦不意味着纯粹的状态变化,亦不指无论何种发展和不确定的展开;“生成”乃是指从某物到某物的过渡,是莱布尼茨在《单子论》(第11章)中称之为changements naturals[自然变化]的那种运动和激动,这种运动和激动完全支配者ens qua ens[存在者作为存在着],也即,ens percipiens et appetens[知觉的和欲望的存在者作为存在着]。[26](www.zuozong.com)
耶稣的复杂性就体现在他的存在正是此种“生成”状态的一个比喻,一个象征,一个类比。
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颇为独特的后现代哲学家吉尔·德勒兹首次将此种“生成”的抽象概念具象化了。他把它比喻成“游牧”的状态,并为处于此种状态里的“游牧者”起了另外一个名字——“根茎”。类似于田地里马铃薯的根茎,既作为根部,又作为茎部,没有任何中心和部分的差异,根须从任何一点蔓延开来。
他还给它找到一个恰当的附身之物:游牧者,类似于弗朗西斯·培根笔下扭曲变形的形象。
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理解,游牧者的形象成为耶稣形象的一个隐喻,他和弗朗西斯·培根画布上扭曲变形的形象一样,处于双重性的场域边缘。
这是一个充满了风险的边缘,因为有双重方向的辖域化的力量在撕扯着形象:“肉”的辖域化与“灵”的辖域化。前者拉扯着形象进入一种有着严密组织和等级制度的现实世界,譬如耶稣作为宗教领袖与偶像的身份;后者拉扯着形象进入一种彻底抽象和超验的理想世界,譬如耶稣作为绝对神圣的救世主和上帝之子,变成一种不可知的“物自体”。
形象需要随时抵抗双重的诱惑,既不能堕入现实的确定性,也不能坠入超验的确定性。两者之间有一个极为危险的缝隙,一种临界点和共同区域。形象就在这条细若游丝的线上保持着平衡。
培根所画的面孔,处于兽性和人性之间;霍尔拜因所画的墓中的基督,处于尸腐和气若游丝之间;格吕内瓦尔德所画的受刑基督,处于垂危与伤愈之间,这些形象都在一个危险的临界点进行着抵抗与冒险。
这些形象的在场就是一种有着强度的真实:作为基督,他同时具有“神性——人性”,他本身就是游离于边界的无器官身体。
那么,岛子[27]是如何处理耶稣形象的?
那个严重的时刻充满了无助与悲伤,就仿佛上帝开了一个无缘无故的玩笑。
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代世界中的艺术家,岛子很少直接对《圣经》所记载的事件进行场景的图解,甚至是有意地避免,也许这是他为尽量保持艺术独立性的一种坚持。
但作为基督徒,岛子的精神源泉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圣经》,可以说《圣经》成为了他精神世界的支点。他早期的作品虽然只有少数的几幅,但也涉及了“耶稣受难”题材。
最早的一件“基督受难”题材的作品是他2007年所画的《宝血挽回祭》(图5)。后来,他似乎主动放弃了对这个严峻时刻的描绘。
画面里,一团焦墨粗粝地扫过耶稣的面容,甚至摧毁了那张总是带着超验美的面孔。耶稣的躯体和四肢也被同样沉重焦灼的黑色侵蚀,没有丝毫的精雕细琢。一扫而过的粗暴感,几乎让人想起某种残忍的暴力。
假如这个粗暴的形象没有被悬于一个残损的十字架之上,我们几乎不可想象他竟然就是上帝之子耶稣。十字架的形象更加残破不堪,布满斑驳的破洞和烧痕。《圣经》所载,观看“基督受难”的所有旁观者——耶稣的门徒、圣母玛利亚、行刑者和两个强盗——都被抹去了,没有出现在画面中。令人感到更为诡谲的是,原本齐整的宣纸边缘明显被刻意撕扯成残损的状态,仅余两条蜿蜒破碎的断线,并且布满了烧痕。岛子强调他创作此画时忽然受到某种启示,这鞭策他把葡萄酒洒向画中的耶稣形象,于火上炙烤画作,直至出现烧痕。
如此,整个事件都被粗暴地改变了。无论事件的发生场景、参与者,还是形象的塑造,毋庸置疑都一同指向“在场感”,在场感是一种有着强度的真实。
避免细腻入微的美化,而故意使用一种粗粝的手法,难道不是更接近“受难”时耶稣身体所承受的残暴?
那些斑驳的烧痕似乎带着疼痛感,从耶稣的四肢和胸肋处蔓延开来,随之发生了疼痛的共情:伤痕累累的十字架和空无一物却布满烧痕的场域,同样在承受着非人的折磨。刀枪剑戟的鞭笞和众人的指责谩骂,透过撕裂和火燎的痕迹,重现了难以承受的莫大痛苦。
图5 《宝血挽回祭》
一种带有强度的真实感完全被身体化了,耶稣受难所包含的一切意义都透过这种具体可感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个破碎的基督形象,他所承受的疼痛完全被粗粝残暴的痕迹隐喻而出。烧痕,就是酷刑的视觉隐喻。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献祭”自身的时候,难道他不能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去感受鞭笞的痛苦,感受死亡的威胁吗?
耶稣形象不再是完美无瑕的、超验的、抽象的、纯粹的、绝美的化身,相反,他带着肉身的残损与缺陷,被痛苦所裹挟,成为一个现实世界的受难者。
曾发生于历史上的暴行——鞭笞、刺杀、分裂、焚烧——倘若无法被重现为一种“感觉”,那么世人要如何体会“死亡”逼近时作为受难者的歇斯底里
身体性就是一种迫近、一种感觉的类比和共情,也就是更深层意义上的“通感”。
所谓“深层意义上的通感”,根据现象学的解释,每种色彩、味道、触觉、气味、声音、重量之间,皆有一种存在意义上的交流——这就是通感,穿透可见性界域的感觉的共情时刻。
这是一种更加深层、更加潜在的类比。它处于“肉身——精神”“可见——不可见”“无形无象——形象”的缝隙里,弥散出感觉的某种原始统一性[28]:水墨之黑白、烧痕之气味、葡萄酒之苦涩,三者将视觉、嗅觉、味觉凝聚起来,使得原本只能被眼睛看到的色彩跳脱出可视范畴,绵延至可嗅、可品的感觉的原始而综合的层面。绘画对于色彩的限制性规定在此处被消解,黑白、烧痕、葡萄酒皆可入画。这甚至类似于一种通灵术,其间的泼墨、焚烧、滴酒皆可作为一种祭奠仪式的痕迹。
《宝血挽回祭》里所有的形象,不论是耶稣、十字架,还是被隐去事件参与者的场面,都成为基督正在受刑的身体,都通过通感这一通灵术体验到了“受难”感觉的原始同一性。
所有的存在物都同时感受着烈日炙烤的苦楚、刺穿肋骨的疼痛、皮肤碎裂的折磨。所有的在场都成为耶稣具有感觉的体验性的身体。如此,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惨绝人寰和历史无法抹杀的罪恶,全部昭然若揭。
两年后,岛子创作了一幅“基督受难”的主题作品,名为《蔚蓝》(图6)。
画面弥散出一股紧迫窒息的感觉。
带着原木质感的硕大的十字架伫立于天地之间,在其映衬之下,耶稣显得孱弱单薄。他无助地耷垂着头颅,眼睛凝视着画外某处,让人想起里尔克《严重的时刻》里面的受难者:“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耶稣周身发青,右肋一股血迹凶猛地涌出,他的头顶没有金色的光芒,取而代之的是一摊朦胧的灰暗的水迹。大地和天空阴霾密布,全然遮蔽了光线,世界似乎陷入了黑暗的深渊。耶稣左侧,汹涌的荆棘丛似乎瞬即就要将他吞噬。
《蔚蓝》里的耶稣仍然是一个单独的形象,充满了苦楚和疼痛。这种撕扯人心的“十字架苦像”相比拜占庭时期抽象的“圣像画”更加真实。
图6 《蔚蓝》
可见,岛子处理耶稣形象的时候,完全没有把这位上帝之子当作绝对的、超验的“纯粹精神”和“物自体”,而是视其为有血有肉的受难者。所以画面没有出现东正教“圣像画”那样金色的面孔,也没有出现像丁托列托或者拉斐尔那样用透视法的观看原则画出的面孔。
《蔚蓝》里的基督形象难道不是更接近格吕内瓦尔德、霍尔拜因、弗朗西斯·培根笔下的悲惨形象吗?他们被同样的惊惧和伤痛所裹挟,无力挣扎。《蔚蓝》里的基督形象极为晦暗,被水墨调和藏青而成的青绿色所充满。这种幽暗的青绿色同样出现在格吕内瓦尔德和霍尔拜因的耶稣的面容上。
中世纪拜占庭时期,画家使用青绿色来描绘基督曾被视为一种渎神行为。传统基督教艺术范式中,青绿色只能用于渲染魔鬼撒旦或者堕落天使的恐怖。倘若将此种可怖的颜色用于耶稣,则会受到驱逐或审判。
在使用青绿色的冒险之外,还有着面孔的冒险。《蔚蓝》里耶稣的面孔模糊不清,让人难以分辨。可见,画家对写实主义没有丝毫的兴趣,他拒绝按照表象的模仿规则去调度色彩,而是选择了一种“意象化”的方式:氤氲模糊的墨迹,晕染出十字架苦像的模糊轮廓,而不去精雕细琢。
同样的冒险难道没有在格吕内瓦尔德、霍尔拜因、弗朗西斯·培根的世界里出现?
那些几乎陷入渎神困境的形象,不过是为了凸显耶稣受难所暗含的现实存在意义。
耶稣被钉十字架,不仅仅是一个悲惨的“事件”、一个被处死的“场景”,而是一个充满了强度的“事实”。这种事实,既和耶稣的个人命运相关,又和人类的整体命运相关;既和耶稣的个人选择相关,又和上帝的命定相关。抑或说,“耶稣受难”是一个具有双重性的事实。
如何将不免有些悲剧色彩的事实重现出来?
这里并不需要重现场景,而是需要突出在场感。这需要一个有着多重隐喻的文本,它既要和历史中的耶稣相关,又要和现实中的苦难相关。这就是“处境化”的潜在性的类比:从《圣经》故事的场景再现,转换为现实中正在发生着的“不可争辩的事实”。
这种“不可争辩的事实”不妨透过基督悲戚的面容和孱弱的身体表现出来。如此,无助的形象在身体的疼痛与精神的救赎之间,便建立起一个共同区域,一条缝隙,一个褶皱——沿着这个危险的边缘,基督的“神性——人性”“无限性——有限性”“理想——现实”进行着永无休止的撕扯。
我们的现实处境并不单单需要历史里的宗教领袖复活,还需要他即便复活也要在当下的困厄处境里复活。当我们遭遇苦难时,我们的基督并非遥远超然的“神”,而是与我们同在和与我们共同承受着一切的受难者。
这就是语境的漂浮。宗教语境、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三者交织,形成一个褶皱。如此,那个曾经发生于骷髅地的残暴“事件”,未尝没有发生在别处,它甚至是随时随地都正在发生的“事实”。这意味着,耶稣的死不仅仅在宗教历史中产生过难以估量的意义,他的死也构成了一个隐喻:他死去了,之后便永远在隐喻里活着。抑或说,耶稣并没有死去,现实中每一个受难者的牺牲都变成一个重现仪式,一次次的受难就是一次次地丰满那个残忍“事实”的维度。
如此,骷髅地的惨案就不再是一个历史事件,不再是对《圣经》的一种宗教性图解,它本身就构成了“献祭”这个词语的在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吕内瓦尔德、霍尔拜因、弗朗西斯·培根、岛子所画的“基督受难”题材的作品,就不是关于“场景”的艺术,而是德勒兹在《感觉的逻辑》里提出的“感觉”的艺术。
德勒兹认为“场景”与“感觉”有着根本区别[29],场景作为可见性的力量有着“辖域化”的功能,就像《福音书》所记载的骷髅地作为场景,上演着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历史事件。
这个场景中的事件被一代又一代的画家逼真地再现出来:一个叫做骷髅地的地方,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上有一个牌子,写着“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他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强盗同时被处死,旁观者有他的门徒、圣母玛利亚、抹大拉的马利亚、雅各和约西的母亲,以及四个拈阄的兵丁。
《新约》四福音书对“耶稣受难”事件的时间、地点、参与者,均有详细交代。
在他头以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马太福音27∶37-38》)
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经历的事,就极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她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事他的。内里有抹大拉的马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马利亚,并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马太福音27∶54》)
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巳初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马可福音15∶25》)
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还有些妇女远远地观看,内里有抹大拉的马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马利亚,并有撒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事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们在那里观看。(《马可福音15∶39—40》)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路加福音23∶33》)
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注:有古卷在此有“用希腊、罗马、希伯来的文字”)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路加福音23∶38》)
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锤着胸回去了。还有一切与耶稣熟识的人和从加利利跟着他来的妇女们,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路加福音23∶47-49》)
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彼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约翰福音19∶18-19》)
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还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姊妹,并革罗罢的妻子马利亚和抹大拉的马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约翰福音19∶25-26》)
通过对比四福音书的文字记载,我们将“基督受难”这一事件分解为一些因素:发生地名为“骷髅地”,时间为“巳初的时候”,一同被钉死的还有两个强盗,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耶稣在两者中间。十字架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行刑时,观看者众多,福音书中出现的人有:两个强盗、刽子手、百夫长、圣母马利亚、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马利亚、抹大拉的马利亚、耶稣门徒,以及很多信众。
这种再现就是把“耶稣受难”的核心当作一场可供模仿的场景,却忽略了更深层的东西——作为耶稣正在受难的身体,它有着自身的感觉。
受难的耶稣是一具有着感觉的身体,就像格吕内瓦尔德、霍尔拜因、弗朗西斯·培根、岛子笔下的死亡形象,承受着一切:苦痛、死亡、惊惧、战栗、无助。即便这类感觉可能出于“肉身”的有限性,即便这类感觉可能被扣上“渎神”的帽子,它仍然保有着身体经验的真实性。
毋庸置疑,德勒兹所谓的感觉性等同于身体性,对于形象而言,身体就是一切。《圣经》记载,基督就是道成肉身。这意味着一直被尼采所诟病的看不见、摸不着的“纯粹精神”终于拥有了可见的身体。当抽象的“物自体”有了身体,它才能被世人看见、触摸,它才能和世人对话、交谈。只有透过身体,世人才能感知、触摸、思辨、判断,身体规定了可能性的边界。
身体,是基督不可拒绝的维度。
但是,这一“身体”并不等同于“肉身”,而是“道成肉身”。所谓的“道成肉身”,在德勒兹的世界里预示着一种确切的真实。它具有双重性:可见性——不可见性、神性——人性。它处于两者的共同边界,处于褶皱的缝隙里,就像一具“无器官身体”,像一块“根茎”。
耶稣的形象就处于这样的夹缝里,不断地进行着一场充满悖论的叙事:“辖域化——解辖域化”“肉身——道”“死亡——复活”,进行着一场永无休止的争执。
所以,东正教圣像画的缺失和文艺复兴绘画的缺失,程度是相同的:或者只想画出不可见的基督,或者只想画出可见的基督。无论是只强调神性还是只强调人性,都不是耶稣的真实形象。真实的耶稣,必然同时包含着双重性,他不是场景里的道具,而是一具“无器官身体”。
这也是为何我们在格吕内瓦尔德、霍尔拜因、弗朗西斯·培根、岛子的作品里看不到场景,却对耶稣承受的多重痛苦犹如感同身受,就好像我们亲身饱尝了鞭笞的暴力的原因。
这也是为何对场景的叙事与图解就像一堵墙,它只允许看,只允许旁观者存在,却阻隔了参与者,阻隔了身体感觉的传递的原因。感觉的力量,未尝不是在场感的另一重身份,它无法抗拒经验性的、身体性的表达。
一切皆因基督身体的悖论:他必然死去,而后才能复活。受难基督,他的身体处于一个困境,一个共同边界。他的身体正朝着无器官身体慢慢靠拢。复活后的基督,才真正获得了一个纯粹的没有器官的身体。
这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
(王蕾: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
【注释】
[1]“无器官身体(Corp sans organes)”是德勒兹从阿尔托那里借来的词语,是德勒兹相当重要的一个概念,在《普鲁斯特与符号》《重要的逻辑》《反俄狄浦斯》《千座高原》里都有反复深入的论述。它是一种“生成”的介质,而不是生理学和物理学上的“身体——肉体”概念,正如尼采所论述过的“身体想象”和麦克卢汉所说的“感觉比率”。无器官身体濒临“有机体”解体界线上的“纯粹肉体”,等同于一个“非有机系统”,可以指称所有的存在物。德勒兹认为绘画作品中存在着两种身体:“器官身体”与“无器官身体”,前者的整体性、中心性、等级性导致绘画的精神性被“叙事性”与“具象”所辖域,这在西方传统基督教艺术中表现最为明显。究其原因,一则,基督教绘画的母题往往出于对《圣经》故事的图解,这样绘画就作为附属的“图解性”插图地位而被排除其自由表达的可能性;一则,基督教绘画受传统教义的制约,难以自由地传达其纯粹精神。“器官”是一种组织化、辖域化的力量表征,正是由于器官遵从于组织功能的界定与分工,器官才具有相应的功能化事实。但是这只是一种可见的表层幻象,它要求画家“有机具象”的机械写实。潜在的真实在于打破组织与辖域化力量的差异化事实,抵达“无器官身体”的去组织化的事实。所谓的“去组织化”,否定了一切既定的程式道路,要求绘画自身不断地“生成”。
[2]〔法〕波德莱尔、〔奥〕里尔克著,陈敬容译:《图像与花朵》,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17页。
[3]格吕内瓦尔德·马蒂亚斯·戈特哈尔德·尼多哈尔(约1455-1528),16世纪专擅祭坛画的画家,德国文艺复兴绘画中最不可思议的画家之一。代表作是艾森海姆市(Isenheim)修道院附属医院礼拜堂画的祭坛画。这巨大的多翼式祭坛有两套翼板,描绘耶稣磔刑、耶稣复活、受胎告知等主题。这些场景的透视法技巧非常娴熟,意象却大致遵循末期哥特式风格。这件祭坛画最动人的特点是作者强烈的情绪和耶稣扭曲的肢体,是一幅以“基督受难”为题材、呈现前所未见的肉体折磨惨状景象的画作。
[4]汉斯·霍尔拜因(1497-1545),16世纪德国最后一位著名的画家,出生于奥格斯堡,父亲汉斯·霍尔拜因也是一位画家,因此他被称为小霍尔拜因。
[5]“歇斯底里”是德勒兹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这种状态处于危险的边界,悖论的压迫下生成“无器官身体”。德勒兹认为真正的绘画就是歇斯底里,他说:“绘画是歇斯底里,或者说,绘画改变了歇斯底里,因为它使得在场感直接成为可以被看到的东西。”
[6]David Sylvester,Interviews with Francis Bacon,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75.
[7]同上。
[8]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19世纪俄国的伟大小说家之一。他与列夫·托尔斯泰分别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和“广度”。
[9]尼古拉·米哈伊诺维奇·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作家、诗人、历史学者和文学评论家,其《可怜的丽莎》等作品开创了俄国伤感主义文学的潮流,他在历史学上的代表作是十二卷的《俄罗斯国家史》。
[10]安德烈亚·曼特尼亚(1431-150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画家。他作于1480年的《哀悼基督》为了突出画面深度,采用从基督的脚向头看去的角度进行透视缩减,成为传世之作。
[11]丁托列托(1518-1594),原名雅各布·罗布斯蒂,16世纪意大利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受业于提香门下,是提香最杰出的学生与继承者。他继承了提香传统,同时发展了独特的自我风格。
[12]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斯画家,巴洛克画派早期的代表人物。
[13]洛伦佐·莫纳科(约1370-1425),也叫唐·洛伦佐,意大利画家,最早发展了哥特风格的佛罗伦萨画家之一。
[14]卓新平主编:《中国基督教基础知识》,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15]〔德〕尼采著,刘崎译:《上帝之死:反基督》,志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82页。
[16]〔德〕尼采著,刘崎译:《上帝之死:反基督》,志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108、113、118页。
[17]“根茎”,德勒兹的重要概念之一,是一种“解辖域”结构的隐喻和类比,譬如地下的马铃薯和红薯的根部。“茎块”和现代主义“树状”的整体性、层级化、组织化的结构隐喻形成对峙。“根茎”表征一种解辖域的力量。
[18]安托南·阿尔托(1896-1948),法国演员、诗人、戏剧理论家。20世纪20年代曾着迷于超现实主义戏剧,后受象征主义和东方戏剧中非语言成分的影响,发展出“残忍戏剧”的理论。他主张把戏剧比作瘟疫,经受它的残忍之后,观众得以超越它。此理论对热内、尤奈斯库等人的荒诞派戏剧产生了重大影响。
[19]〔法〕吉尔·徳勒兹著,董强译:《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20]贝尔托·布莱希特(1898-1956),著名的德国戏剧家和诗人。布莱希特戏剧常被视为象征主义,是20世纪德国戏剧的一个重要学派,注重“间离效果”,强调表演诉诸知性与思考。
[21]〔法〕吉尔·徳勒兹著,董强译:《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22]〔法〕徳勒兹、〔法〕加塔利著,姜宇辉译:《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221页。此书里,德勒兹指出直接束缚我们的三种“层”:“有机体”“意义”“主体化”。
[23]“生成”是德勒兹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描述的是作为“生命”之实质的“时间”之本然状态。他认为,在宇宙论层面,“生命”等同于“时间”,是一道无穷无尽、无始无终的强力的绵延,即为“生成”。
[24]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德意志哲学家、数学家,历史上少见的通才,被誉为17世纪的亚里士多德。
[25]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
[26]〔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上海世纪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页。
[27]岛子(1956-),山东青岛人,先锋诗人,当代艺术家,他的“圣水墨”作品为中国当代基督教艺术的代表,影响颇广。
[28]〔法〕吉尔·徳勒兹著,董强译:《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29]〔法〕吉尔·徳勒兹著,董强译:《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4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