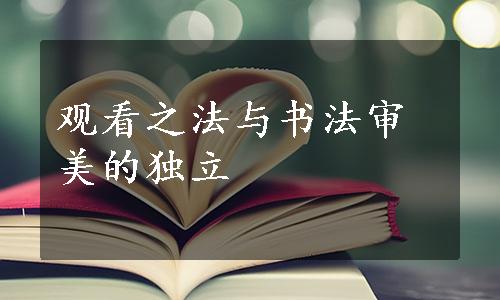
王韶华
摘 要:中国书法审美的独立是伴随着书家观看书字之法的演进而实现的。远观、近察,作为古人观看书字的两种方法,看似只是观书距离不同,但却内涵着书家完全不同的审美意趣。汉代重远观,远观书法的生命之美,书法的审美受到了限制。魏晋并重远观与近察,远观书法整体生命之境,近察书法笔画结字之美,书法艺术之美得以完整呈现,书法审美得以独立。
关键词:书法 观看之法 审美 远观 近察
中国书字的生命美在汉代就已获发现,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示。汉字自创始至秦代小篆,虽然字形逐步简化,但始终在像物之形的轨道上演进着,对物象之形的描摹痕迹非常明确。隶书的创制,其初衷是使文书的书写方便,结果却为汉字的飞跃发展和书法艺术的审美独立创造了契机。隶书作为有汉一代的书写工具,以横平竖直取代了篆书婉转委曲的同时,也以抽象的字形取代了篆书的象形会意。以“简”为原则对篆书的改造产生了重大意义。一方面,这使汉字摆脱了对象形汉字一笔一画的描绘,从而解放了书家,激活了书家的个体情感。在书写过程中,书家的生命热情寄寓于书字的形式中,使书字散发出了主体的生命活力。另一方面,汉字在以象形原则进行创造的时候,对物象的简化抽象中,保留了物象之生命气韵。而在隶书对篆书象形的再次抽象中,篆书所呈现的物象气韵已经无法依赖字形与物象的“相似”展现,于是物象生命自然内化于抽象笔画的运行中,成为内在之“势”。书家的主体性情与书字的抽象线条相结合,使得运笔结构的书“势”得到了书家的关注,如崔瑗的《草书势》、蔡邕的《篆势》《隶势》《九势》等,并将其演绎为书法创作的原则。内在于笔画线条的如“势”,就是对书字本身所蕴含物象生命的关注和提炼,在这种关注中,书字的生命美为汉代书家所发现,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阐发。
在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上,书法审美正是伴随着对于书字生命美感的充分认识而确立的。这个过程与古人观看书字的两种方式息息相关,即远观与近察。两种方式看似只是观书距离的不同,但却内涵着书家完全不同的审美意趣。
汉人观书,惯于远观,即“远而视之”,且远观到的是一个个书字之像,书法的笔画结构之美被淹没了。同时,如赵壹的《非草书》担心时人学草书“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宏道兴世也”。在汉代书法实用性的约束下,对书字生命美的欣赏与阐发是有限的,书法的审美价值并没有得到完整的发现。魏晋以降,书家观书时,近察与远观并重,不仅继承汉代传统,看到了书字篇章的生命之美,更看到了笔画结字之美。书字笔画、结构的美感以及书字整体释放出的生命活力成为这一时期书法美学关注的焦点,书法审美随之独立。
一、书字形式美的发现——近察
汉代书家已注意到了“远而望之”“迫而视之”两种书法观审方式,但更侧重于“远而望之”,着重于远观书字浑然化一的整体气韵,很难在其中分离出对笔画、形体的单独审美,故谓“观其法象”[1],“思字体之俯仰”[2]。虽然汉代书家也近察书字,即“迫而视之”“就而察之”,但并没有将视线置于书字本身,而是对书字整体进行笼统的评价,如蔡邕谓“近而迫之,端际不可得见,指伪不可胜原。研桑不能数其诘屈,离娄不能睹其隙间”。[3]崔瑗谓:“就而察之,一画不可够。机微要妙,临时从宜。”[4]与汉代不同,魏晋书家重视近距离的观看,正是在“迫而视之”的近察中发现了书法的形式之美。
1.近察书字的整体形势与趣味
晋代书家卫恒在其书论中为“就而察之”注入了功力。他在自作的两篇书势《古文书势》《隶书势》中,对古文书势、隶书势的描述不仅关注远观的气势,更关注近察的细节,使远观与近察的关系得到了平衡。“故远而望之,若翔凤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远而望之,若飞龙在天;近而察之,心乱目眩,奇姿谲诡,不可胜原”。远观与近察不仅在文字表述上趋于均衡,更重要的是,近察时真正将视线投射到书字本身上,即书字“有若自然”“奇姿谲诡”。作为著名的书法家,卫恒将远观所感受到的书字整体气势之美用于近察,在近察中发现书字整体的气势特征。只是与远观所得飞龙翔凤生动活泼之像不同,近察所得在整体书字的气势。远观之像乃是由感受而得的自由无拘的想象,而近察对于书字整体气势的概括感受显然已经受到了书字本身的约束。如“有若自然”,既是笼统的概述,又一定是基于书字整体结字的评价,“奇姿谲诡”则明显地已包孕着对隶书笔画的审美感受。也正是这种对于整体气势的近察之功,延伸出了对笔画结字等形式细节的进一步观审。故卫恒近察古文、篆、隶、草等四体书势,发现并生动地描绘了书字的形式之美:《古文书势》中,古文笔画“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结构“矫然特出”者“若龙腾于川”;“森尔下 ”者,“若雨坠于天,”跌宕起伏。《隶书势》中,隶书“纤波浓点,错落其间”。由此可见,卫恒熟练地使用了近察之法。
”者,“若雨坠于天,”跌宕起伏。《隶书势》中,隶书“纤波浓点,错落其间”。由此可见,卫恒熟练地使用了近察之法。
晋代成公绥使用了近察之法,形成了其对于书法趣味与理想的判断,而这一趣味、理想与书字形式细节息息相关。成公绥的《隶书势》中看到,隶书之形体结构的审美效果既不是篆书的单一,也不是汉人草藁书一笔一画模仿前人的做作、呆板、迟缓,而是充满了丰富灵动的审美趣味。这种审美趣味源于笔画形体共同组合而成的书字浑然一体之美,《隶书势》就是针对隶书的这一审美特征而发论的。成公绥确立了隶书“工巧”的审美理想。其所谓“工巧难得,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有意晓”,实际又是对法则的超越,“工”乃深谙法则的结果,“手”乃书字创作的外显途径。在成公绥的论说中,工必须妙而至于巧,手必须隐而应于心。因此,由心意传递于书字形体、结构的“巧”必是超越形式之上,渗透着主体精神的生命态势。因此对书势,成公绥更多感受到的是隶书用笔、布局等书写过程中生成的生命之势,强调的是主体创作过程中强烈的生命动感。《隶书势》形容隶书形体构造间运笔挥毫为“灿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锦绣之有章”。形容书字的黑白布局、篇章构造为“或若虬龙盘游,蜿蜒轩翥,鸾凤翱翔,矫翼欲去;或若鸷鸟将击,并体抑怒,良马腾骧,奔放各路。仰而望之,郁若霄雾朝升,游烟连云;俯而察之,漂若清风历水,漪澜成文”。形容创作状态为“彤管电流,雨下电散……一何壮观”!书家创作就是在主体性情的释放中创造书字的生命与趣味。
2.近察书字的笔画
近察的结果是书字笔画、结构之美得以充分显现,这在卫恒之女——卫铄的书论中得到了彰显。卫铄的《笔阵图》[5]所论以书法用笔为核心:“夫三端之妙,莫先于用笔;六艺之奥,莫若于银钩。”将书法笔画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观审笔画的生命与意趣,这是前人未曾发论之处,是《笔阵图》对于中国书法美学的贡献。
《笔阵图》指明了各种笔画的审美特征和各种用笔的审美特征,真正凸显了书字字形、结体、笔画的美。“一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丶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有绷也。丿陆断犀象。百钧怒发。丨万岁枯藤。崩浪雷奔。乚劲弩筋节。”作为字形构成的基本单位,笔画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使用价值,但在魏晋书家的眼中却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卫夫人用生动的形象,显现了笔画所有的这种审美特点。显然,卫夫人所言的笔画之美是专指魏晋流行的成熟的正书笔画。笔画以自然景观、战争景观为喻,其共同的特点是气势宏大、力量雄强,且具有无限的幻觉延伸性。“千里阵云”,以辽阔的空间与变化莫测的阵云构筑了奇特的幻觉空间。“高峰坠石”,以无限的高度赋予山石的强大力量和高峰的不可名状构筑的是一个充满了强烈动感的幻觉空间。“万岁枯藤”,以无限的时间与枯藤的生命构筑的是一个苍古的内蕴无限的生命空间。“崩浪雷奔”,以力度和速度共同构筑笔画的生命形象。而“百钧怒发”“劲弩筋节”,则在无以差比的力量基础上,创造飞动的虚灵时间和突兀的虚灵空间。一笔一画之美呈现的是虚幻灵动的空间形象。卫夫人所谓的“多力丰筋”,在对笔画审美的过程中,成为了该审美意蕴中最本质、最基础的特点,并由这种筋力生成了虚灵的生命空间之美。卫夫人对于笔画的观照确实已进入了审美的自由之境、超越之境。况且,这诸多笔画在卫夫人眼中可以“一一从其消息而用之”。它们可以因人而异、因笔法而异,本身就充满了无数的变化之态。
在近察笔画之美的基础上,卫夫人对六种用笔方法(六种书体)进行了审美观照:结构圆备如篆法,飘扬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特立如鹤头,郁拔纵横如古隶。不同的用笔方式产生了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字体有不同的构字结体的方式,由此不同生成的审美特征也各不相同。魏晋时期各种书体均已产生,各种书势类的论著也层出不穷,对各种书体的历史溯源、书体特点、用笔结构等的总结也日渐丰富,而书法创作实践经验和书法的传承学习更为这种总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力。《笔阵图》是书法授课讲义,因此关注创作的具体方式方法。从全文看,用笔方法本身并不是书法初学者的目的,品鉴书体之美是卫夫人传授书法更上一路的要求。也就是说,如论笔法、笔画如何使用,须以各种不同书体的风格之美为更高的追求。
3.近察书字的笔力
近察之法还使得书法笔力得到了关注。卫夫人的《笔阵图》看到了书法之美在于骨力,而骨力之有无在于创作时主体付诸笔画的精力、气力。李斯见到周穆王书,评价:“七日兴叹,患其无骨。”[6]蔡邕观鸿都观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7]所叹所嗟都是书字的笔画筋骨气力,这是一种具有刚健之美的书字感受。“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魏晋书家随着纸上作书经验的日渐丰富,将“多力丰筋”确立为书法创作的审美标准,并且将笔力的具体运用与多力丰筋的审美标准相结合,对书法进行观审,使用笔成为书法创作之本。因此,善笔力也便是“多骨”的创作之本,由“多骨”生成的就是可谓之“圣”的筋书,否则就是墨猪。这种由具体的创作用笔为始到生成审美效果为终的论述,确为前人未发之论。这种论说使书法艺术的审美真正落到了书体构造的各个具体元素中,即“下笔点墨画芟波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创作主体以全身之力传递于手腕,并进而传递于纸墨,书字自是以筋骨为胜。当然,卫夫人所谓的一身之力并不仅仅是一种生理之力的全倾而出,而更关注的是这种生理之力如何形成。《笔阵图》并未具体论说这一问题,但其言“若学书,先大书,不得从小”“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实际上已经透露了“一身之力”须源于精神的专一。专一的精神需要的是主客的浑一,稍有分离就可能造成身体之力的分解。这种主客浑一的创作状态在《笔阵图》中被演绎为具体可行的实践方式。在其所列的七种执笔之法中,都是将主体内心之意与执笔落墨的具体状态结合起来进行归纳总结的。真正精妙的书法作品是“执笔远而急”的作品,是“意前笔后”的作品,而失败的书法则心手不齐,或心急而执笔缓,或心缓而执笔急,或执笔近而不紧,或意后笔前。七种执笔状况传递的信息是:创作过程中主体要专一于书意,以意为书法创作的统帅;创作过程中纯熟的用笔技巧能使用笔与主体心意保持始终的一致。与汉代蔡邕笼统地强调“随意所适”(《九势》)相比较,卫夫人的《笔阵图》更着意于强调笔如何适应意,且详尽地考察了实践中心与手、意与笔之间的种种关系。由书字的审美趣味——筋骨,阐发书字创作中该审美趣味的生成,进而阐发执笔方法,卫夫人的《笔阵图》关注的焦点着实在于其所谓书法之妙的“莫先乎用笔”“莫若乎银钩”。
4.近察书字审美的生成过程
沿着卫恒、卫夫人由于近察而开辟的书法形式审美之路,王羲之继续探索书字笔画结构的审美特征,他将近察的注意力放在了书字审美的生成过程中。《题卫夫人〈笔阵图〉后》[8]提出:“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在“意”的统摄下,汉字的书写不是点画的组合,而是艺术的创造。如果书写笔画“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但得其点画尔”。显然王羲之将书定义为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而不以实用价值为主。汉字的上下齐平、大小统一在王羲之的草书创作论中是不合美的规则的。他所追求的美的书写规则是“字体形势,状等龙蛇,相钩连不断,仍须棱侧起伏”。就具体的点画而言,须从空中掷笔而作。其目的仍然是创造如卫夫人《笔阵图》所谓“高峰坠石”的审美感受,但王羲之更注重于这种审美效果的生成过程,这正是一个著名的书家亲身的创作体会。各体书法的创作具体使用的笔法不同,但最终目的是要使书字能够感发人的意志,能够传达内在的意思。若写正书(当时称正为隶),要“先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先发”。若写草书,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若急作,意思浅薄而笔即直过”。
王羲之的《书论》更为详尽地对书写过程进行了审美品评。“凡作一字……先构筋力,然后装束……每作一点,必须悬手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后曳。每作一字,须用数种意……作一字,横竖相向;作一行,明媚相成……若作一纸之书,须字字意别,勿使相同。”从笔画到具体的结字,从行的布局,再到书字篇章的整体构造,王羲之层层观审,进行了细致的分辨。其中就作字而言,使用了各种形象的比喻,如水中蝌蚪、壮士佩剑、妇女纤丽等。这些书字的美感基础仍然是笔画,各种笔画,或似八分,或如篆籀,或如深林乔木,或如钢钩,或如枯干,或如针芒,或如飞鸟空坠,或如流水激来,共同组合成了书字整体的美。与卫夫人相比较,王羲之的比喻更为具体,更适用于具体的创作实践。如果说卫夫人强调的是笔画的气势与力度,王羲之则更重视笔画的形象本身,这正是对书法形式美的进一步发掘。因此,当卫夫人以“多力丰筋”作为书法审美标准的时候,王羲之提出“欲书先构筋力,然后装束”的更高要求。装束是王羲之的发明,也恰恰是书法形式审美化的进一步明证,而与此相伴的是王羲之对于具体创作方法的关注。王羲之的《笔势论》共有十二章,分别论述创作的总体特点、创作过程中各种笔画的特点及使用方法、各种结体构字的特点与方法等,非常详细。具体的点画结体,创造的是书法的书字形式。对点画结体的详尽关注,就是对书法形式美的集中观照。王羲之的《用笔赋》对书字的形式审美特点进行了集中概括,并赋予书字的形式笔画以内在的韵味:“方圆穷金石之丽,纤粗尽凝脂之密。藏骨抱筋,含文包质。”方圆纤粗的点画展现着金石一般的光彩、凝脂一般的细密。书法之美恰是在点画形式中矗立着骨气筋力,在点画结构中体现着内在意蕴和外在形式的完美结合。文质彬彬的审美特点在被文学借用作为文学艺术的审美追求后,再次被引入书法领域,使书法的审美理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奠定了以后中国书法美学的思想基础。
二、书字生命美的发展——远观
汉代书家重视远观书字,远观所得在于书字的生命之势。魏晋继承汉代,并进一步发展,将汉代的远观宇宙生命发展为远观自然生命,将汉代的远观书字物象发展为远观书字的整体之境,并放眼于整个书法的发展历史上,远观书法书体的源流变迁。魏晋的远观书字使书法的使命从哲学的承载演化为艺术美的传达,书法的审美由此独立。
1.远观书字的生命:从宇宙生命到自然生命
正如汉代蔡邕所言:“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立,形势出矣。”(蔡邕《九势》)中国古代书家秉承着先秦哲学思想,将书法看作超越于笔画形式的生命体,该生命承载着、体现着宇宙本体的道,承载着阴阳乾坤的根本。因此,由书字中流衍出的不是视觉意义上的书字,而是具有生命意义与生命活力的书字。书字在创作主体的默思静观、任情恣性中与宇宙本体的道相契合,进而具有了生命的气韵与生命的意义。这种书字内涵着的宇宙生命观在魏晋时期得以继承,并得到了进一步的演化,逐渐呈现出由宇宙本体生命向活跃着的自然生命转化的趋向。
魏晋早期的书家钟繇所谓“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或“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即是对书法生命的哲学观照。按照前一种说法,用笔之理归于天,由用笔创造出的书字之美则归于地,该书字的美与自然界的万物之美一样,是宇宙自然本体的物化形式。这种美的形式虽然属于个体形式,但内蕴着天道自然的本体,因此,所谓的“流美”既是主体创造的个体美,更洋溢着宇宙本体的生命活力。后一种说法则突出了书法创造的特点,书法是由笔画线条勾画出的形式,该形式因为由主体创造而具有了美感。书法因为人的参与而显现出美的特质。因此,书法自然体现着人的情感、学养和精神人格,书法的美感中渗透着主体生命的内在活力。而这种生命的活力外显为笔画所形成的形式中,该形式也是主体在对自然物象进行抽象而形成的形式。因此,这种形式既是主体生命的显现,也是宇宙万物生命的显现。无论何种说法,都可以从中看出钟繇书论对于书字生命,尤其是内蕴的宇宙生命的关注。(www.zuozong.com)
卫夫人的《笔阵图》借鉴了汉书家蔡邕“为书之体,须入其形”“纵横有可象,方得谓之书”的思想。她认为,“书道”是“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她视创作中由抽象书字转化为现实之象的做法为书法之道,实际上把书法创作、书法欣赏从字形中解放出来,转为观其象,因为美感恰恰深藏于“象”的光辉中。所以卫夫人又言“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书法不是一种技艺,而是一种生命灵动之性,还是又能传递生命灵动之性的个体生命。它既通于创作主体的生命,又通于现实客观世界的生命。书法承载的不仅仅是书家的情感,还有宇宙中的客观自然生命,书道正是以书家主体之生命的灵性感通宇宙中自然生命之灵动,创作出“各象其形”的书字,而不师古不能成就此道,孤陋寡闻、学识浅薄也不能成就此道。显然卫夫人注意到了这种书字的美感源于创作时对书字形象化的感发,由此创作的书字便具有了宇宙中自然生命灵动、鲜活的气质。
这种对生命的关注在魏晋书势类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张扬,在书势类著作中,书字的生命之美逐渐走下了哲学的圣境,走进了自然社会形形色色的生命美境中。
2.远观书字的生命之境
晋代书家索靖的《叙草书势》是专门论述草书体势的书学文章,他在书中以自己的创作体会描述草书之为状“宛若银钩,漂若惊鸾”,又若“虫蛇虬蟉,或往或还”,这种描述与汉代书家以及晋代成公绥的书势描述大体相似。尽管书势之作早已有之,但都将书势描述为一个又一个独立的、零散的审美意象,书家们并不在意于书势整体之境的勾画,但索靖对草书“举而察之”后的审美感受却发前人所未发。索靖的《叙草书势》不仅深切地感受到了书字带来的生命形象的美感,更发现了书字创造的境美。在对草书状简要的描述后,索靖描述了“举而察之”的感受,即“又似乎和风吹林,偃草扇树,枝条顺气,转相比附,窈娆廉苫,随体散布。纷扰扰以猗靡,中持疑而犹豫。螭狡兽嬉其间,腾猿飞鼺相奔趣。凌鱼奋尾,蛟龙反据,投空自窜,张设牙距”。这种对书势的感受与形容由孤立的象到整体的境的转换,不是简单的象的相加与组合,而是书字审美的一大进步。索靖对于充满了众多生命体和审美意象的完整画面的描述源于其对于书字之势的深切“感思”。中国汉字创始于对客观物象外形的摹写,象形文字的创造、书写追求的是与自然物象的相似,要得物象之真。这种摹写客观物象的方法一方面创造了中国早期的文字,一方面在古代书家的心中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当隶书取代篆书,使汉字从具象的形式中解放出来而不再以摹写客观物象为目的的时候,书家心中以自然为依据的烙印并没有完全消去。所以汉代崔瑗言草书创作“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此虽并非直言草书创作要摹写自然中具体特定的物象,但却认为是在对自然万物观察、体会、感悟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生动形象性的书字。蔡邕以“书肇于自然”的哲学高度阐释书道,使书写站在了体现自然之道的立场上,由此摆脱了具体客观的物象之形的约束,而要求由书法创造形象的生动之势,唯有此才可以称之为书,即“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纵横可有象者,方得谓之书”。蔡邕所谓的“其形”“有象”并不是自然之象,而是一种由书写创造出的鲜活的生命感受。在这种生命感受中,书字生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形象,美也正产生于这种形象在主体心理的生成过程中。谓之纵横有象,谓之入其体,实际上是主体进入审美状态的一种具象化解释,是一种主体心理创造的生命体,正如“大象无形”。该生命体体现着自然宇宙本体的律动,体现着自然宇宙的本体生命,创造着宇宙万象,操纵着无限时空中的生命运动。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蔡邕何以能言“纵横”二字,何以能进入抽象线条组合成的书法之“形”中。因此,蔡邕的书道本身就是要创造宇宙生命。晋代索靖的书势之论延续了蔡邕的纵横有象论,使书字审美时生成的各种意象和谐相处,统一安排于“大象”之中,使之形成一幅交织着各种形象的、活跃着各种生命的、充满着和谐美感的美丽的图画。蔡邕对书道自然本体意识的强调,虽然建构了统一于宇宙生命的书法意象,但各种意象之间不是共时共存的,而是孤立的。索靖则描述了同一个时空中各种不同的审美意象,这些意象独立地展示着各自的生命色彩,相互之间又共同构筑着自然生命和谐并存的整体气象。由象至境的发展,既是索靖将无形的大象生命具象化、落实化的过程,将书法的哲学思考转化为审美感受的过程,也是他将书字单字、片断的审美转化为书字篇章整体审美的过程。正如索靖在《叙草书势》中所言:“去繁存微,大象未乱,上理开元,下周谨案。”当书法不再随时深切地履行自己肩负的体现宇宙自然的书道重任时,当书法欣赏摆脱了具体书字、片断特征的约束时,主体对于书法的欣赏由此进入了自由无累的精神境界,书法审美在这种对书境的创造中实现了其自身的价值,书法艺术由此进入新的阶段。
3.远观书字源流与书体形象生命的创造
魏晋远观不仅在一篇书字作品本身,还在远观整个书法艺术的源流,远观书字形象生命的创造。
魏晋书法四体已经稳定,书写方式也已经稳定。随着创作黄金时期的到来,书法也开始进入理论的总结时期。卫恒的《四体书传并书势》共四篇书论,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书法理论著作,四篇书论正是对于四种书体的总结。卫恒首先梳理了各种书体的源流,为各种书体作传,然后描述各种书体的书势。每一篇书论,都包括书传与书势两个部分。其中各种书体的书传部分以及古文、隶书的书势部分为卫恒所撰写,篆书势、草书势是汉代蔡邕、崔瑗所作。
卫恒的《四体书传并书势》开创了为书法溯源流的风气。尽管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就中国文字的起源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但许慎是对文字而言,并不涉论作为艺术的书法。卫恒对四体源流的追溯,显然已经超越了文字的认知功能本身,是对于文字视觉形式的关注。当视觉形式脱离了文字的内涵而成为被关注的对象时,文字潜在的审美意味被挖掘了出来。因此,作为晋代著名的书法家,卫恒为四体书字立传的思想基础是美学,而不是文字学。正如《古文》篇所言,卫恒称自己喜欢古文,并竭尽自己的思绪称颂古文之美,“愧不足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无别名,谓之字势云”。卫恒的目的是保存古人书字之象,这种象被称之为“势”,这也正是卫恒创作《四体书传并书势》的原因。显然,卫恒将抽象的书字视为可以感知的象,这种象又不是文字字形本身仿效自然事物而成的象形之象、客观之象,它是具有活力的生命体。以“势”取代“象”的意义正在于此。文中的“因声会意,类物有方”在卫恒的观念中已不同于汉人所谓仓颉造字时的“依类象形”[9],而是把握了宇宙万物的运动规律与结构规则之后在心中生成的新的形象,并以此形象为基础进行文字的创造。如“日处君而盈其度,月执臣而亏其旁,云委蛇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卉苯 以垂颖,山岳嵯峨而连冈,虫跂跂其若动,鸟似飞而未扬”。卫恒在文字的创造中关注的是创造事物生命活力的内在运动特性,如此造字显然超越了客观形象的局限,生成了书字的生命活力。因此,卫恒格外强调书写中的“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势”作为书字生命的内蓄力量,成为书体创作的最重要指标。创作的重心由形象形式的书写转化为形象生命的书写。既如此,卫恒在对书字整体生命运动特性关注的同时,将视线放置于形象生命的创造中。“如弓”“如弦”“龙腾于川”“雨坠于天”“鸿鹄高飞”“流苏悬羽”等,本来抽象的笔画与结构,在卫恒的眼中具有了生命的形象与力量。笔画形象与结构形象显然是欣赏主体在想象中自我创造的形象,这些形象生成于对书字美的体验中。如卫恒自己所言:“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宜。”无论书家的创作还是欣赏者的欣赏,最终都在思致的引导下进行并完成。思致在书法创作与欣赏中的存在为联想与想象插上了起飞的翅膀,书字的创作与欣赏由此进入了自由的空间,并依据每一个主体的不同而进入了富有个性的创造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书字潜在的艺术意味显现了,书字的美学品格树立了,书字作为美的艺术的自由创造性实现了。正因为如此,卫恒才会将“近察”后的古文书字特点总结为“有若自然”。“异体同势”(隶书),以审美的精神看待隶体书法时,卫恒强调的依然是书势,是隶书笔画结构的生命活力。
以垂颖,山岳嵯峨而连冈,虫跂跂其若动,鸟似飞而未扬”。卫恒在文字的创造中关注的是创造事物生命活力的内在运动特性,如此造字显然超越了客观形象的局限,生成了书字的生命活力。因此,卫恒格外强调书写中的“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势”作为书字生命的内蓄力量,成为书体创作的最重要指标。创作的重心由形象形式的书写转化为形象生命的书写。既如此,卫恒在对书字整体生命运动特性关注的同时,将视线放置于形象生命的创造中。“如弓”“如弦”“龙腾于川”“雨坠于天”“鸿鹄高飞”“流苏悬羽”等,本来抽象的笔画与结构,在卫恒的眼中具有了生命的形象与力量。笔画形象与结构形象显然是欣赏主体在想象中自我创造的形象,这些形象生成于对书字美的体验中。如卫恒自己所言:“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宜。”无论书家的创作还是欣赏者的欣赏,最终都在思致的引导下进行并完成。思致在书法创作与欣赏中的存在为联想与想象插上了起飞的翅膀,书字的创作与欣赏由此进入了自由的空间,并依据每一个主体的不同而进入了富有个性的创造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书字潜在的艺术意味显现了,书字的美学品格树立了,书字作为美的艺术的自由创造性实现了。正因为如此,卫恒才会将“近察”后的古文书字特点总结为“有若自然”。“异体同势”(隶书),以审美的精神看待隶体书法时,卫恒强调的依然是书势,是隶书笔画结构的生命活力。
其后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笔势论》《用笔赋》、王珉的《行书状》、刘劭的《飞白书势》、杨泉的《草书赋》等都十分强调书字之势,都在形象生命的创造与展示中阐释书字作为艺术具有的美学品格。卫恒则对书法发展的这一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其《四体书传并书势》有言,“故竭余思以赞其美,愧不厕前贤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无别名,谓之字势云”,[10]这道出了书法之美与书法之势的关系。“势”接近于“气”,但与“气”不同的是,“气”是虚物,而“势”则是由实向虚或由虚向实的一种物的动态,不纯然属于内在的精神,也不纯然属于外在的物形。它包含着一个完整的物象,一个活跃着的富有生命力的物象。无疑“势”的品评为抽象的书法艺术复原了艺术的形象性,在形象的感受中领悟中国象形文字的本源,艺术的魅力也由此而生。故索靖在《叙草书势》中称书法“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滋生”。
结语:比喻之品——书法审美之确立
由近察而得书字的笔画形式之生命美,由远观而得书字的整体结字篇章之生命美。书法艺术的审美空间在魏晋南北朝得到了向细节与向整体的双向拓展,在抽象线条与形象的自由想象中,审美空间得以充分地拓展,书法生命之美得以完整地呈现。从此,书法以鲜活的生命体的形式入驻艺术之林。也正因此,形成了书法接受中的一道风景:比喻式品评。梁代袁昂的《古今书评》是这一方法的实践者,该书全篇品评25位书家,其中21位都用形象生动的比喻进行言说。但与前代不同的是,袁昂更多的是把不同类型的人当作喻体。比如,品羊欣的书法,“如大家婢为夫人,虽处其位,而举止羞涩,终不似真”。品阮研书法,“如贵胄失品次,丛悴不复排突英贤”。品梁鹄的书法,“如太祖忘情,观之丧目”。品袁崧书法,“如深山道士,见人便欲退缩”。与前代的比喻品评相比,由于袁昂对人物神态的格外关注,使书法品评更加凸显了书家书体的精神气貌,凸显了书家的审美风格,使读者对书家书体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在书法品评中别具一格,在比喻品评中也独树一帜。《古今书评》虽然抓住了书家书体的最主要的风格特征,在书法风格的品评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却丝毫不涉笔墨、结构等书法语言。而庾肩吾的《书品》在品评张芝、钟繇、王羲之等书家时即采用了折中两全的方法,既有形象的感受,又将这种感受付诸具体的点画结构中,如“分行纸上,类出茧之蛾;结画篇中,似闻琴之鹤……抽丝散水,定于笔下;倚刀较尺,验于字中……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华落纸将动,风采带字欲飞”,这正是远观与近察相结合的结果。
(王韶华: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注释】
[1]崔瑗:《草书势》,见王伯敏、任道斌、胡小伟主编:《书学集成》(汉—宋卷),河北美术出版社版,2002年版,第2页。
[2]蔡邕:《篆势》,见王伯敏、任道斌、胡小伟主编:《书学集成》(汉—宋卷),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3]同上,第7页。
[4]崔瑗:《草书势》,见王伯敏、任道斌、胡小伟主编:《书学集成》(汉—宋卷),河北美术出版社版,2002年版,第2页。
[5]《笔阵图》旧题为卫夫人撰,后众说纷纭,或疑为王羲之撰,或疑为南朝人伪托。因《晋书》未载,而未曾参战的卫夫人以作战体会言论书法似乎不大可能。但从《笔阵图》文字看,且据孙过庭《书谱》记载,《笔阵图》原附有图示,且有关于造纸、制笔、取研、制墨、执笔的文字,《笔阵图》属于授课讲义之类的文章,其中的文字很可能是卫夫人的弟子(王羲之曾师从卫夫人)根据听课记录编辑而成。其中所表述的书写要旨、书法理论是卫夫人的观点。
[6]卫铄:《卫夫人笔阵图》,见王伯敏、任道斌、胡小伟主编:《书学集成》(汉—宋卷),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7]同上,第23页。
[8]《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疑为后学者转录王羲之的言论而成。参见陈方既、雷志雄:《书法美学思想史》,河南美术出版术1994年版,第127-128页。
[9]许慎《说文解字序》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10]卫恒:《四体书传并书势》,见王伯敏、任道斌、胡小伟主编:《书学集成》(汉—宋卷),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