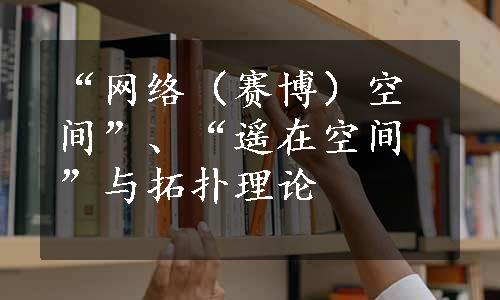
“网络空间”及其相关的“赛博空间”、“遥在空间”等空间术语与“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仅仅是计算机运算和传输数据信息的方式和抽象的空间概念。此“空间”只是人们对数字传输方式的称谓,并不是真实具体“场”的表现。它通过一系列数字科技软、硬件设备的支持,最终将信息数据呈现为动态影像画面,或通过三维立体打印机打印出三维真实模型。在数字公共艺术“场所”混合空间中,数字动态影像成为重要的空间表达形式,因此才出现了以“空间”称谓的“网络空间艺术”、“赛博空间艺术”、“遥在空间艺术”等空间艺术的术语。然而,网络空间的出现与拓扑理论有着一定的联系。例如,至19世纪中期,对于空间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研究方法,科学家们运用数学分析中的拓扑学方法,去研究几何图形在连续改变形状时的不变性质。拓扑学属于几何学的一个分支,到了20世纪迅速发展,其研究对象已成为现代数学普遍研究的内容。尤为重要的是拓扑学虽从图形研究演变而来,但它已从实体抽象成与之无关的点、线、面,并将此三者之间的关系运用到数字网络空间中,网络被拓扑为一个完整的信息结构体系,从而使之成为庞大的数字公共艺术通信空间。
以上对于数字公共艺术“场”有关的空间问题的研究,无论是德谟克利特的“虚空”论,还是牛顿的绝对时间、绝对空间论,其基本观点大多是从空间、时间与物质相分离的立场出发;或是把空间理解为可填满物质的“大箱子”,空间和时间只是结构与框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形式”,物质则是“内容”,是装进“形式”和“框架”中的“东西”。此类古典空间理论无论以哪一种学术流派出现,时间与空间的基本结构是不变的,它规定着每一事物与每一事件的时间和地点,决定着宇宙间万事万物永恒不变的时间和空间的特性。换言之,数字公共艺术的“场”性混合空间现象并没有脱离这类理论规律的指导,相反,隐藏在不同混合空间现象背后的数字公共艺术及其“场”性表征,都能找到与自己相符的理论依据。进一步说,空间和时间只是一切事物、事件的表演舞台,而事物、事件只是充当表演者,视时空为背景或表演场所,演员可变但舞台不可变,演员与舞台始终是一个相互独立的关系。不过,古典空间理论所能解决的场所空间现象仅局限于传统的时空领域,而不能解决数字公共艺术及其“场”性的所有问题。只有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现之后,人们关于时间与空间的观点才开始发生革命性的转变。爱因斯坦彻底否定了牛顿的时空观,并建立了“狭义相对论”。他认为:当运动物体的速度接近光速时,运动物体的长度会变短,时间会膨胀,故此,空间与时间的关系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物体的存在方式不但是三维的,而且是四维的。除此之外,为证实狭义相对论中引力问题和非惯性问题,爱因斯坦又提出了广义相对论。他认为:引力场客观上是一个弯曲的时空,其原因在于物质的存在可导致空间的时间发生弯曲。虽然相对论与数字公共艺术“场”的混合空间性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其本质在于打破了人们千古不变的时空观,并为空间、时间与物质的划分提供了方法论。爱因斯坦认为:“空间和时间内部都可以做详细的划分,空间和时间可以是并质的,即可以各自划分为不同的特性,也就是说,空间也好,时间也好,都不是连续的、均衡的。”[20]这就为数字公共艺术在同一个场所同一个空间中所出现的异质混合空间提供了依据。“为什么不是呢?因为世界上所发生事件的关系是多种类的。爱因斯坦认为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没有真实地描述世界宇宙状态,因为空间、时间、物质或事件是在时空背景下发生的,而要说,并不存在这样被割裂了的背景,所谓空间和时间可以被置换成事物或事件之间各种性质不同的关系,换句话说,物理事物各个部分之间的邻接关系,或者说,事物或事件之间的次序关系是多种多样的。”[21]这就表明了数字公共艺术在同一个场所空间中,完全可存在着多维度混合空间。科学进步告诉人们,真理具有相对性,随着科技的发展,绝对的真理在不同的空间、不同的维度、不同的层面上进行讨论往往会变成谬论。过去,在传统公共艺术“场所”中谈论混合空间问题并不成立,但到了数字时代,这一问题却成为事物发展的必然。爱因斯坦的贡献不仅在于相对论,而且还在于告诉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应从构成事物要素的层次和不同的维度去思考。就空间结构而言,空间的不同层次是由其构成要素的数量决定的。例如,在相对论出现之前,人们认为构成空间的秩序是点—线—面—体(三维)的关系,三维产生立体空间。相对论出现之后,由于把时间因素考虑进去,在特定的情况下空间才被证实是四维的。无论是三维空间还是四维空间,考虑其正确与否应从相同的层次、相同的语境、相同的时代和相同的空间去考虑。一旦违背了这样的原则,人们便会与新生事物相对抗。凡·高作为后期印象派的代表人物,其作品的形式与内涵已超出了19世纪人们对于绘画的理解和欣赏,是绘画的形式、风格跨越时代,具有超前意识并且不能被当时人所接受的例证。毕加索早期的代表作《亚威农少女》,是典型的立体主义绘画作品,其绘画理念旨在用二维平面去表现四维空间,作品采用的是类似矩形条块分明的小块空间组合。一方面,其形式与黎曼回环矩阵和黎曼曲面空间[22]在数学原理上似乎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表明不同类似矩形条块之间的连接方式和组合关系,另一方面,又与爱因斯坦的空间理论有着某种维度上的联系。作品中的人物不仅可以看到其正面、侧面、顶面,还可以用条块分割的方式将人体背面的形态,用跨越空间的方式并列表现出来,这就是四维立体。用这种多维度的方式去研究和表现绘画,体现了立体派绘画的多维空间时代特征。可是,像这样一件旷世杰作在当时并不能被人理解。然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证明并打破了这一规律。“物质、事件是由它们的形状、形式以及物质和事件构成要素之间不同的连接、排列关系及连接顺序决定的。”“在不同历史时代,人类可能是在不同的空间维度思考问题,人们很难从较低维度空间想象较高维度空间科学……”[23]这就为本研究引出所要探索的数字公共艺术“场”的混合空间性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实际上,这一问题本身就是指在同一个场所空间里,同时存在着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空间现象;存在着不同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现象;存在着虚拟与现实等不同的混合图像知觉。如果从时空、图像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的话,那么同一个“场”中,不同的“层次与维度”问题才能够被真正理解。(www.zuozong.com)
从上述对以哲学为命题而引发的对于数字公共艺术“场所”空间理论的探索、回顾与梳理得知:人类经过数千年的不懈努力,从哲学与数理角度出发,获取了大量抽象的演绎和以现实验证为依据的普遍真理。这些以数理研究为出发点的多视角的空间理论,具有普适性的指导意义,也回答了关于空间的本源问题,空间、时间、运动问题,以及空间与物质关系的问题等,其中绝大部分依然适用于对数字公共艺术“场所”的建构,以及对某些具体特殊空间概念的认识和理解。然而,数字公共艺术“场”的混合空间性非同于传统意义上公共艺术所具有的全部特征。由于数字化手段介入空间,致使数字公共艺术“场”的混合空间性拥有自己鲜明的异质空间的特性,如真实现实空间、虚拟现实空间等。不可否认,数字公共艺术混合空间特性的形成,在许多情况下,用传统媒介营造空间依旧主导着公共艺术,混合空间特性仍然包含这类空间的存在方式,但其形式和特性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空间原理上,传统空间理论也大多能与日常具体的“场所”内容直接发生关系。不过,在现实呈现上,某些抽象的空间形式并非通过感官可直接知觉之,因此,要回答诸如数字公共艺术“场所”、“空间”问题,在立足于具体空间理论的同时,还必须从多种类数字艺术介入“场所”、“空间”出发,将“现实场空间”、“虚拟场空间”、“音响空间”等与人发生直接关系的“场”性要素综合加以考虑,如此,才是认识数字公共艺术“场所”、“空间”的关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