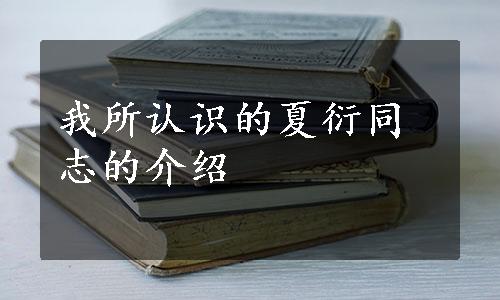
一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夏衍同志从四川回到上海,我才第一次见到他。和许多老同志比较,我认识夏公是比较晚的,但是距今也整整40年了。在这40年之中,我接触夏公的机会并不多,除了谈工作或听他作报告,很少个人交往。但40年以来,有三件事我一直不能忘记。
第一件事是1950年夏天,那时我还在私营文华影片公司工作,我编导了一部影片叫《太平春》,由石挥、上官云珠、沈扬主演。内容是揭露美帝国主义轰炸我国沿海城市,残杀我们劳动人民的罪行,为推销中央人民政府发行的“胜利折实公债”作宣传的。那时候我们刚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一种强烈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愿望。但由于我第一次接触这种现实题材,影片在艺术上还很不成熟。当时有一位同志在报上发表了严厉的批评文章。不久,我收到柯灵同志写给我和黄佐临同志的一封信(那时佐临是文华公司的艺委会主任),柯灵的信大意是说,他听到夏衍同志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提到影片《太平春》,认为某同志对这个影片的批评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公正的。夏衍同志说,《太平春》在广大市民中起了很好的教育作用,而且这个片子比桑弧过去的作品有进步,也是私营公司所拍摄的一部较严肃的作品,应该予以表扬。柯灵同志在信中同时指出,我们要看到夏衍同志的热情赞扬含有鼓励的意味,从思想内容来说,他对私营公司出品的影片的衡量,尺度比较宽。我收到这封信之后,心情非常激动。过去我长期在上海工作,应该说,思想觉悟是比较低的。在解放之初,抱着满腔热情去拍摄反映现实斗争题材的影片,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夏公的这一番鼓励,使我特别感到温暖,也坚定了我走革命文艺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件事是1953年初,我正在筹备拍摄袁雪芬、范瑞娟主演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本来准备拍黑白片,后来看到美影厂拍摄的彩色木偶片《小小英雄》,是我们技术厂自己冲洗的,效果还不错,我们就打报告,建议《梁祝》改拍彩色片。这件事得到夏衍同志和上影厂领导的大力支持。当时物质条件非常困难,《梁祝》所使用的底片早已过期,而且是日光片,色温比较高;而上影厂只有少量的炭精灯,又缺少发电设备。经过夏衍同志向上海市长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同志呼吁,陈老总热情地答应把防空部队用的发电车借给我们使用。于是,解放军每天上午把发电车开到上影厂,拍完戏又开回去作晚间防空值班之用。这样连续半年,才把戏拍完。影片完成之后,夏衍同志看了,对这第一部彩色舞台艺术片给予充分肯定。他还邀请周总理、邓颖超同志和陈毅市长来观看样片,对我们作了很多鼓励。夏公那种积极支持新生事物,并且亲自奔走,帮助解决具体困难的精神,使摄制组全体同志十分感动。
第三件事是1956年,那一年我导演了夏公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祝福》。本来这个片子是上影厂的剧目,正巧汪洋同志率领北影厂的一部分同志从苏联学习回来,准备拍摄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在征得夏公和上影厂的同意后,这部片子就改由北影厂拍摄,我和白杨、魏鹤龄也就被借到北影厂去工作。这个片子预定要在10月19日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日上映,摄制它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这一年南方的黄梅季节特别长,摄制组在杭州、绍兴拍外景,遇上连续的阴雨。从5月初到6月底将近两个月,几乎下了50天的雨,拍摄进度受到很大的影响,拍下的镜头数,只占全片工作量十分之一左右。眼看完成任务有危险,我们不得不下决心返回北京拍内景,并把一部分外景搬到玉泉山和十三陵附近拍摄,由美工师池宁同志加工成江南农村的风光。夏衍同志对影片很重视,他几次找我谈了他的改编设想,以及他对分镜头剧本的意见。他还建议请刘如曾同志作曲,并坚持用民族乐队。他好几次来看阶段样片,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他经常鼓励我们。这个片子从7月初到9月上旬停机器,在北京花了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完成了十分之九的工作量。由于赶时间,拍得很匆忙,不免有点粗糙。而更主要的是我在导演的艺术处理上,还显得比较幼稚。例如影片中卫老二和祥林嫂的婆婆商量要把祥林嫂卖给猎户贺老六的戏,卫老二说价钱已经谈好了,贺老六肯出80吊钱,先付40吊,另外一半等花轿上了门再付。婆婆不满意,要求一次付清。卫老二说:“贺老六一下子凑不出那么多钱,他还在想办法借呢!”下面一个镜头,就是从贺老六的中近景拉出,他正在向一个地主借钱,在借据上盖手印。又如另一场戏,祥林嫂在舂米,贺老六背着一捆柴回家,他发现祥林嫂像要呕吐的样子,意识到妻子可能怀孕了。接下来一个镜头,就是婴儿在摇篮里啼哭。像上面所列举的那种呼之即来的“叫板”式镜头,我当时还自鸣得意,以为镜头衔接很紧凑,其实显得矫揉造作。时隔二十多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许多“文革”以前拍摄的影片拿出来复映。1978年我又看了一次《祝福》,当我看到上面这种镜头时,感觉特别不舒服。这种手法比较浅薄,既不符合鲁迅小说的风格,也不符合夏衍文学剧本的风格。记得我拍《祝福》的那一年正好40岁,虽然说不上年少气盛,确实还有点“矜才使气”的味道。影片中当然还有其他不足之处,但是我每次遇到夏衍同志,他从来没有责备我。他那种对待后辈的宽厚的胸襟,一直使我感到不 安。
二
上面我讲了自己难忘的三件事。下面,我想谈谈夏公在文艺理论特别在电影创作方面的一些主张。他的这些主张,长期对我产生影响,而且我至今认为它们是正确的。我想谈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他的群众观点。欧阳予倩同志在给夏衍同志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他着重谈了写剧本的群众观点。他主张首先必须要群众看得懂,再就要让群众高兴看。看不懂固然不行,看得懂而群众不喜闻乐见,那也就无从起教育作用,收宣传效果。为着更好地把作品普及到群众中去,剧作者必须从自我欣赏的小圈子解放出来,深入群众,千方百计为群众写出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结合的剧本。”夏衍同志自己在书中说:“每一个从事电影工作的人,都要把群众性牢牢地记住,永远不要忘记电影的群众性,以及电影对群众所起的思想上、感情上的影响。”他又说:“……即使是从名著改编的电影,也先要设想观众根本没有看过原作。也许你会说,鲁迅的《祝福》谁不知道?《祥林嫂》也演过无数次,谁还不知道?作为一个电影剧本作者,我劝你不要这样想。电影有上千万观众,其中有许多人可能就根本不知道《祝福》这篇小说。而且电影是‘一次过’的,它不像小说可以翻回头再看一遍。所以你必须设想观众没有看过这篇小说,没有看过这个戏。所以,我讲改编名著也必须作一番大众化的工作。”与此相关联,夏衍同志在很多场合,强调一部影片第一本的重要性。他说,在第一本里,有很多东西都要从头告诉观众,假如开演了十分钟,头绪还搞不清楚,那以后就很难搞清楚了。一部影片第一本的好坏,关系很大,它影响整个影片的质量。夏衍同志又认为,从小说改编为电影,对话要特别下功夫。小说看不懂还可以再看一遍,电影是“一次过”的,观众听不懂就既不能达意,又不能感人了。再说,语言不好,演员念词儿也有困难,搞创作的同志也要为演员着想。所以,让演员容易“上口”,使观众易于“入耳”,这是写对话最基本的两条。以上一些见解,都反映出夏衍同志一贯坚持的群众观点。
夏公一方面主张编剧和导演要有群众观点,要使作品为观众所容易看懂,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影片的“直、露、多、粗”。这两者似乎有矛盾,其实是辩证的统一。作品让群众看得懂并不就是“直”和“露”,一看就懂决不等于“一览无余”。反过来,晦涩难懂也决不等于含蓄。我们应该努力做到既能使观众一看就懂,又要耐人寻味。有些作品缺乏群众观点,剧中人爱讲一些所谓有哲理性的语言,观众不懂,作者不怪自己,却怪观众水平太低,这是没有道理的。有的作者甚至说他的作品不是为今天的观众服务的,而是要过若干年才能为观众所接受。这里我想摘引刘海粟老人回忆郁达夫的一篇文章中的几句话:“世界上很少关起门来为后代写作的艺术家,作品往往都是起作用于当时,从而在历史上获得位置。失去了当时,永久并不存在。”我想,刘老的这几句话也许对那些准备把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作者,有一点参考作用。以优秀影片《红衣少女》为例,这部影片中的人物并不讲那些所谓哲理性的语言,讲的都是日常生活里的话,但是观众感到这部影片是富有哲理性的。柯灵同志有一次接受记者的采访,在谈到艺术表现上的创新追求时,柯灵说:作为电影、戏剧,艺术家当然应该有勇气作各种创新的尝试,但又无论如何不能忘却争取观众对自己的了解。创新是为了增加吸引力,而不是增加隔膜。在这种场合,不存在“光荣的孤立”。我认为柯灵同志讲得很好,说到底,创新不能没有群众观 点。(www.zuozong.com)
第二个方面,我想谈谈夏衍同志对改编工作的高度重视。他自己身体力行,积极从事改编工作。1933年,他把茅盾的《春蚕》改编为电影剧本;1943年,他把托尔斯泰的《复活》改编为话剧。解放以后,他先后把三四部小说和一部回忆录改编为电影,那就是《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和《烈火中永生》。
夏衍同志认为,改编不是创作,但改编也得付出创造性的劳动。有人把改编看得很容易,认为原作已经有了很好的主题、情节、性格和结构,改编只不过用电影手法把它改写一遍而已。有人则相反,把改编看得很困难,特别是改编那些已有定评的名著,认为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夏公说,他虽然没有“讨好”的念头,但“吃力”是亲身体会到了。当有人问他,是不是小说、戏曲都有可能改编为电影,或者问得更具体些,哪一种作品比较适宜于改编时,他说,一般来说不论是小说、戏剧、传记文学、叙事诗歌,凡是故事性或者说戏剧性比较强,人物性格比较鲜明,头绪不太繁复的,就比较容易改编。反之,困难就比较多。我认为这是他从实践中得来的经验之谈。我至今认为,戏剧性比较强,人物性格比较鲜明,头绪不太繁复这三条,反映了一种艺术规律,也是切合中国电影观众的实际情况的。这个规律并没有过时。
夏衍同志还在好多场合建议培养一支掌握改编技巧的队伍。他要求各故事片厂分管剧本的厂长重视这个工作。他说,如果各厂都拥有一支有经验的、工作效率高的改编队伍,可改编的作品应该说是很多的,这样,制片厂的日子就好过了。
他这一段话还是二十多年前讲的,我认为目前更具有针对性。近几年来,全国故事片的产量有了很大增长,剧本荒的问题很突出。而全国每年都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短篇、中篇和长篇小说,可供改编者选择。事实上,这几年有不少得奖的影片是从小说改编的,例如《高山下的花环》、《红衣少女》、《人到中年》、《城南旧事》、《骆驼祥子》、《天云山传奇》等,可是数量还不算多,同时各制片厂也没有建立一支比较有经验的专职改编队伍。夏衍同志关于培养这么一支专职队伍的建议,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设想,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他所说的有经验的改编队伍,他们在包括选择题材、用多少堂布景、多少主要演员、几处外景、有没有季节性限制、影片多少长度、摄制周期的估计,以及如何节约成本等方面,都要能够比较准确地做出判断,有严格的职业基本功。当然,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培养出一大批这样全面的人才,但是高标准、严要求还是应该的。我们知道,夏公要求自己很严格,他所改编的剧本,比较考虑制片生产规律,也比较符合拍摄要求。他过去有着长期的办报和编刊物的经验,有时候版面上有一块空白需要填补,他问一下大致缺多少字,就让排字工人等在身边,他从容挥笔,缺多少就写多少,立等可取。他这种扎实的职业基本功是很值得学习的。
我们集会纪念夏衍同志从事革命文艺工作55周年,我们对他为开拓中国进步电影事业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对他半个多世纪以来培育了几代电影工作者所耗费的心血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还要学习他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态度和“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工作作风。让我们继承和发扬他的高尚品德,团结一致,奋发努力,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1]原载《论夏衍》,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