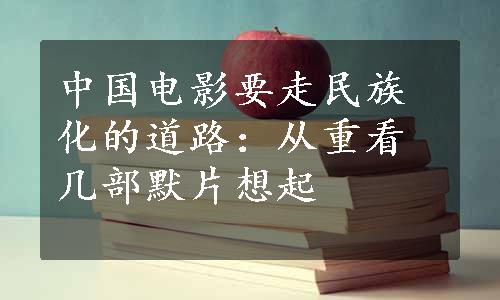
最近有机会重看了20世纪30年代的几部无声电影,那是孙瑜同志编导的《大路》、《小玩意》和吴永刚同志编导的《神女》。大家都认为它们是好影片,不但内容是健康的,革命的,在艺术上也很有感染力;同时能增进我们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认识和剖析能力。
这使我想起半年前在意大利都灵、米兰、罗马三个城市先后举行的“中国电影回顾展”的情景。在这个回顾展上,一共放映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130多部影片,跨越年代之长和影片数量之多都是空前的。回顾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各国专家和广大海外侨胞的热烈欢迎,并引起了强烈的连锁反应。继意大利之后,法国、西德、加拿大、南斯拉夫、瑞士等国都准备举办中国电影回顾展。在国际影坛上,中国电影正在引起愈益广泛而浓厚的兴趣。应邀去意大利参加回顾展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多位电影史学家和评论家,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所摄制的一些优秀影片,给予很高的评价。如日本著名电影学者佐藤忠男说,“这次看的电影中,有不少是描写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因为我了解历史,所以我看了这些镜头,觉得是真实的。作为一个日本人,我感到可耻”。
意大利最有影响的电影评论家卡西拉奇,在《团结报》上发表了《新现实主义最早出现在上海》的文章,赞美《大路》、《马路天使》、《桃李劫》、《乌鸦与麻雀》、《我这一辈子》、《林家铺子》、《早春二月》、《天云山传奇》等影片,对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道路给予充分的肯定。
我认为,一些优秀的国产片之所以受到外国专家们的赞赏,主要是由于这些影片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中国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表现了我国人民的优秀品质和高尚情操;其次是这些影片的内容和艺术形式富有民族特色。外国人看中国电影,总希望看到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影片中所看不到的人和事。因此,愈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影片,愈是能够为外国观众所接受。电影的民族化与国际性不应该是对立的。一部影片,要是能受到亿万中国人民的喜爱,它也往往能冲出中国,走向世界。
要回答中国电影如何走民族化道路的问题,不是这篇文章所能胜任的。这是一个值得从多方面加以探讨的课题。但是,从我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优秀影片受到欢迎中可以得到启发,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宣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例如,影片《喜盈门》受到国外观众的热烈欢迎,就因为影片中反映的新的伦理道德观念对资本主义国家也具有针砭时弊的教育意义。
我还感到,一些优秀的国产影片,它们在表现形式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使观众一看就懂。因为电影是一种“一次过”的艺术,银幕上的画面转瞬即逝。如果在放映过程中,稍有令观众不懂或费解的地方,他们很容易散神或“出戏”,这样势必影响后面的戏的感受。以《神女》为例,从头到尾没有一个镜头是观众所不懂的,导演手法晓畅流利,加上阮玲玉的杰出表演,观众看了影片,感到是很大的艺术享受。
“一看就懂”决不等于“一览无余”。那种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或者观众早已明白而剧中人还在那儿喋喋不休的影片,是缺乏艺术感染力的。一方面要让观众一看就懂,同时又不要一览无余,要讲求含蓄和回味,这是我们所追求的境界。白居易的诗,老妪都能明白;李商隐的诗用典太多,比较隐晦难懂。他们都是伟大的诗人。不过,读一首诗,可以反复吟咏,玩味其中的含意,而看电影却不可能有这么从容的时间。因此,在电影创作上,我们应以白居易为师,而不要去学李商隐。(www.zuozong.com)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他讲的是国家大事,我看对文艺创作也是适用的。中国电影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拍摄了不少好的和较好的影片;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电影事业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电影只有走民族化道路,才能不断前进,立足于世界之林。实践也证明,中国电影五十多年来所形成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也是需要好好总结经验,予以继承和发扬的。
当然,我们强调民族化的同时,并不否定吸收外来的有益营养。凡是外国的进步的好的东西,一定要本着“洋为中用”的精神,坚定地借鉴,坚定地学习,这一点也是不能含糊的。
1982年9月28日
【注释】
[1]原载《解放日报》社编:《朝花精粹1956—1996》,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