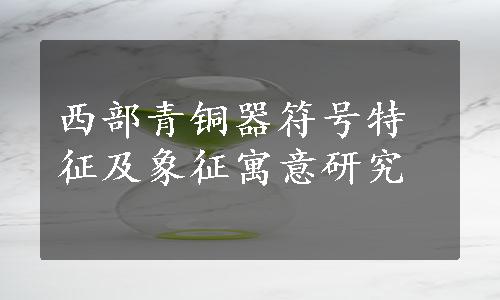
(一)“犬戏牛”铜鸠杖首
1.“犬戏牛”铜鸠杖首简介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件沉睡在河湟谷地长达3000多年的青铜时代珍贵文物“犬戏牛”铜鸠杖首在考古工作者的手铲下再现出它昔日的风采。它出土于青海省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87号墓中(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这件文物总体造型非常奇特,采用青铜材质多个范具合铸而成。利用鸠鸟头与颈部造型为创意骨架,在鸠鸟头顶托起犬戏牛的生活写照,塑铸出精彩的整体圆雕造型。在鸠首部铸出硕大的圆形眼睛,眼外一周采用联珠纹样做衬托,钩状鸠喙向前伸出。利用鸠鸟颈部铸出圆筒形銎,銎下部一侧留有一圆形小孔,为固定杖柄而设。在鸠首顶端塑铸一对牦牛母子圆雕,其小牛犊正在母亲的腹下仰头吃奶,神态安然。一条硕大的牧犬站在钩状鸠喙尖端,仰头张嘴,蹬腿翘尾,朝着牦牛狂吼。母牦牛则俯首瞪眼,耸肩纵背,弓蹄翘尾与牧犬准备搏杀。这件青铜器构思巧妙独特,造型写实逼真,是卡约文化青铜器中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
当中原奴隶制国家进入鼎盛阶段时,河湟谷地的卡约人仍处于氏族部落的联盟时期。这时勤劳聪慧的羌族先民已进入了畜牧业的文明,他们蓄养的牲畜主要是牛、羊、马和狗,这可从河湟地区不同类型的卡约文化墓葬动物骨骼陪葬中得到印证。卡约人对狗的畜养则有特殊的含意,将它作为人类与牲畜的保护神而进行驯化。从“犬戏牛”铜鸠杖首上牧犬的形象特征以及它与牦牛之间体量比例的观察,该犬比牦牛的体量小,但比小牛犊的体量又大得多,从而推测,此犬很可能就是今天藏獒犬的先祖。
2.“犬戏牛”铜鸠杖首各元素解析
下面将这件文物中的藏獒犬、牦牛、鸠鸟动物组合造型分别进行研读。
(1)犬造型解读
“犬”的形象在青海文物中所占的比重不算小。1974年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卡约文化墓地出土一件狗纹彩陶罐。在器物的肩部用紫红色矿物颜料绘制一周正在奔跑的群犬形象,其狗的特征突出,线条简练抽象。如果将此图案展开观赏,则会形成八条犬似列队一排奔跑的图像。器高8厘米、口径10厘米。在同一文化墓地528号墓中出土一件铜铸狗圆雕,高3厘米、长5.7厘米(青海省文物处青海省考古研究所编著《青海文物》199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这件铜狗锈蚀严重,整体造型作行走状。其头大身小,比例失调,前后双腿之间有铜条相连,怀疑是某种物品上的装饰部件。
1978年在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核桃庄辛店文化墓地11号墓中出土一件狗纹彩陶瓮。在其瓮的肩部用黑色矿物颜料描绘一条较为写实的犬的形象,高34.2厘米、口径15.8厘米(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民和核桃庄》200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此犬总体形象憨厚淳朴,三足稍稍抬起,似向前奔走状,动态十足,惹人喜爱。
青海彩陶文化学会提供一件青铜时代唐汪式狗纹三彩陶瓶,高21厘米、口径10厘米、腹径18厘米(张建青《青海彩陶收藏与鉴赏》2007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此器施红色陶衣,在颈肩、肩及下腹部以白瓷土涂抹三道白彩,白彩上下用黑色矿物颜料勾线。在其肩部用黑彩描绘5条长耳细身犬(似牧羊犬)形象,如同一字队形跳跃奔跑,极富动感。
1985—1988年,在青海省岩画调查中发现有关狗的图像:画面一,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得乡野牛沟发现距今3200年的犬图像岩画。画面上4条狗方阵布局。其中西侧竖向排列的两条狗采用垂直打击法制成,为早期作品;东侧两条狗形则采用磨划法制成,为晚期作品。画面二,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江河乡卢山发现距今2000年的图像岩画。两条竖向排列面部向东站立的狗,采取垂直打击法制成。画面三,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怀头他拉乡哈其布切沟发现距今1200年的犬图像岩画。画面上磨划有两条狗和太阳图形,采用磨划法制成。画面四,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巴音乡巴厘河滩发现犬图像岩画。画面上反映两个故事内容,其中上部分是一人与一狗,下部分是一日与一狗。画面五,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切吉乡然呼曲村和里木发现犬图像岩画。一条面东而立的狗,采取磨划法制成,属晚期作品(汤慧生、张文华《青海岩画: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2001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20世纪90年代末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征集到唐代的一只银质牧羊犬和一只鎏金狼狗饰件。其中银质牧羊犬高5.7厘米、长7.2厘米、宽3.8厘米。犬呈卧姿焊接在长方形底座之上,器身采取先锤揲出两半、后组合焊接成器的技法。犬首平伸向前,与前肢基本对齐,头颈部以极细的线条刻出一桃形忍冬花结。犬两耳下垂、目视前方,在嘴角两侧对称钻孔,可能原件上配有饰物。背部捶出竖向的卷毛结7个,在结两侧,各有7对鬃毛纹横向展开。犬尾向右侧上方翻卷,四肢伸向前方,犬身錾有三瓣小花作为装饰。鎏金狼狗高2.5厘米、长4厘米、宽2.1厘米。犬呈卧姿、犬首上昂,两耳竖立。犬身采用细线刻画出鬃毛,四肢前伸,尾巴下垂于地面,平伸于后方,尾端呈三瓣花形。器体捶揲而成,无分半焊接痕迹。品种高贵,造型富丽(许新国《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2006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在《新唐书·吐蕃传》和《突厥传》中有两段是关于吐蕃人与犬的关系的记载:“吐蕃人拜必手据地而犬号,再揖身上。”“吐蕃犬出也,唐与之婚。”此外,《册府元龟》称吐蕃人为“犬戎”,大概也能间接反映吐蕃人与犬的关系。就这些材料看,也许吐蕃人的某些部落是来自以狗为号的部落。现今居住在青海省化隆县黄河岸边的藏族人普遍敬奉“狗头神”,每家都设一个供奉“狗头神”的龛位。这种风俗在湟水流域的汉族人中间也很盛行,但不见于草原藏区。
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中有一段关于狗的故事:“止贡赞普年幼之时,为罗阿木达孜所害,其尸骸置于有盖能启的铜匣之中,抛于藏布大江之中央……后哈牙木胡西库和那囊氏赞雄甲二人将宇宙大神之神犬温苏牙扎、江之苏则马江及温古等毛上涂以毒物,越过险峻高岩,无草荒山,下往谷里相看觇之,吉,于是将狗引至娘若香波山之侧畔,将毛上涂有毒物的神犬遣放至罗阿木达孜之近旁。达孜一见好犬,大喜,以手抚摩犬毛,连呼:‘好犬!好犬!’犬毛上之毒遂浸染达孜之手上,罗阿木达孜乃毙命,得以报仇雪恨。”(王尧等《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1992年民族出版社出版175页)犬作为人类的忠实朋友,能替人报仇,但作为具有特殊能力的动物,也可觇吉凶。
一般来看,狗被藏族人视为忠实朋友,有些地方甚至认为狗拥有某种特殊的能力,因此被用于祭典仪式,但并没有被作为一种崇拜物进行宗教崇拜。王文泸先生在《獒之惑》一文中对藏獒犬的描述极为精准:那个时代的人尚不知道“藏獒”这个概念。那是一只真正的獒犬无疑。硕大而浑圆的头颅被蓬松的鬣( )毛围裹,集中了整个躯体最强烈的攻击信息。短鼻、阔嘴,上吻两侧柔软的唇肉覆盖着下颚(“犬戏牛”铜鸠杖首上犬的特征)。眼睛上方是两砣(
)毛围裹,集中了整个躯体最强烈的攻击信息。短鼻、阔嘴,上吻两侧柔软的唇肉覆盖着下颚(“犬戏牛”铜鸠杖首上犬的特征)。眼睛上方是两砣( )醒目的黄斑(俗称“四只眼”)。粗壮的四肢迸发着钢筋似的力度和弹性。倒卷着的尾巴紧贴后尻(
)醒目的黄斑(俗称“四只眼”)。粗壮的四肢迸发着钢筋似的力度和弹性。倒卷着的尾巴紧贴后尻( ),像古建筑屋脊上的装饰物“吻兽”。它的毛色黑如煤炭,唯有四肢内测、下颚、腹部和爪子呈焦黄色。这正是藏獒中的典型“铁包金”。
),像古建筑屋脊上的装饰物“吻兽”。它的毛色黑如煤炭,唯有四肢内测、下颚、腹部和爪子呈焦黄色。这正是藏獒中的典型“铁包金”。
它身上有一种王者之气,黑藏獒的叫声低沉、结实、浑厚,仿佛有着某种金属的质感。发出的每一个音节都可直接撕开空气,将声音传向非常遥远的地方,随后又被高原上的群山依次反弹,因此有时候哪怕只有一只藏獒在叫,也仿佛有无数只獒犬在吼叫。
(2)牛造型解读
根据“犬戏牛”铜鸠杖首上牛的造型,我们可以看出这头牛当属雪域特有的牦牛种类。《西羌传》载:“或为牦牛种,越隽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也就是说“牦牛”“参狼”“白马”等动物都曾经是古羌族人崇拜的图腾,再根据藏族史料的记载,“古牦牛羌族”是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这些史料,我们可以推断这件“犬戏牛”铜鸠杖首很有可能是越隽羌人的杰出作品之一。这件青铜器中牛的造型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牛在西部地区的青铜器时期有着很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牛这一造型符号在其他青铜器中的表现来得以证实。
1959年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诺木洪塔里他里哈青铜时代诺木洪文化遗址中出土一件陶塑牦牛,长8.8厘米、宽4厘米、高6.3厘米,两角及尾部略残,头部两侧不对称,背部隆起呈波浪状,长毛及地,故显得短矮茁壮、憨态可掬。据分析,野牦牛在当时的青海高原诺木洪地区可能是家畜之一。1985—1988年,在青海省岩画调查中发现有关牦牛的图像: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格尔木市郭勒木得乡野牛沟发现牦牛图像岩画共22幅,牦牛单体100头(距今3200年);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江河乡卢山发现牦牛图像岩画共9幅,牦牛单体36头(距今2000年);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怀头他拉乡哈其布切沟发现牦牛图像岩画共1幅,牦牛单体5头(距今1200年);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蓄集乡察汗台没台发现牦牛图像岩画共1幅,牦牛单体2头(距今1200年);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切吉乡然呼曲村和里木发现牦牛图像岩画共6幅,牦牛单体30头;切吉乡中布滩发现牦牛图像岩画共1幅,牦牛单体5头;切吉乡卢阿龙河当山发现牦牛图像岩画共1幅,牦牛单体1头;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泉吉乡立新大队舍布齐沟发现牦牛图像岩画共2幅,牦牛单体12头;刚察县吉尔孟乡哈龙沟发现牦牛图像岩画共1幅,牦牛单体6头。
在藏传佛教中,牛的形象大多是作为“护法神”出现的,这一点很可能是藏传佛教深受印度教影响的原因。在印度教中,牛是非常神圣的形象,它是湿婆的坐骑,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这一点随着印度文化流入西藏地区逐渐被藏传佛教所接受。然而,在岩画中,牛这一形象却出现得十分频繁。静态的牛、群体的牛、单独的牛、动态的牛,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中刻画的野牛,到新石器时代欧亚大陆各地区岩画的各种图画牛,从岩画壁画到青铜器,牛这一形象始终有着重要的地位。1960年在青海省西宁市南滩出土一套汉代木质牛车。车体双轮双辕,车厢采用四块木板组合而成,全长48厘米。牛的形象憨厚呆板,四肢齐全。
1998年,在青海省海东地区平安县古城乡7号墓内出土两件东汉早期的木雕牛文物。其中1件为牛形独角兽,牛头顶部安装一支分叉的独角,双耳竖立,双目突出,牛舌外吐。牛的耳、舌、眼及独角均涂红色(也许是镇墓兽)。这件文物整体采用圆木雕刻而成,残长30厘米、宽9.6厘米。牛体已残,无四肢,故无法判断牛的姿态。另1件牛整体同样采用圆木雕刻而成。制作粗糙,前窄后宽,牛头上部两侧钻双孔以示双眼,无四肢。牛腹部四角位置凿有四个孔,推测可能是为镶嵌牛四肢而设。
20世纪90年代末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征集4件唐代银质卧牛饰件。其中3件均有底座。银牛卧在长方形底座之上,长9厘米、宽3.8厘米、高6.2厘米,昂首嘶鸣,牛角内弯,怒目圆睁。银牛的目、鼻、口及颈下部均以折线纹表现,牛头及身体部位均以极细的线刻技法攒出卷草纹样,其纹样在目前所知的唐代金银器中前所未见。牛尾上卷,银牛的角、耳、尾各部件分别制作,然后组合焊接在一起形成银牛的整体造型。牛体采取先捶出两个半件,然后再焊合成一体的技法。整个工艺制作复杂而细密(许新国《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2006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两件银质卧牛饰件从外观造型以及牛体纹样上看完全一样,但经仔细观察,发现在牛的后腿部的纹饰略有不同,其中一牛有卷毛饰,而一牛则无。也许这种细微的区别另有含意,或者是区分牛的性别标志。
青藏高原自古就有对牦牛崇拜的习俗,对牦牛的有关记载比比皆是,藏族史料中对牦牛记载是这样的:部分藏族部落就源自“古牦牛羌族”。古代的羌人“……为牦牛种,越隽(juan)羌是也……”。这说明牦牛曾是古代羌族的图腾崇拜物。关于牦牛图腾的由来,在藏族创世纪神话《万物起源》中写道:“牛眼变成了日月、牛肠变成了江河湖泊、牛毛变成了森林、牛骨变成了山川……”
苯教是藏族地区的本土宗教,在西藏苯教的宗教活动中,到处都展现着人类对高原牦牛的尊崇之情。例如,苯教信徒在跳神以及各种祭祀活动中,都会将黑色的高原牦牛作为神圣、威严、力量、正义、权威的象征,而将白色高原牦牛作为平安、吉祥、善良、美好的标志。在全世界很多地区,都曾将牛角作为防御和攻击敌人的锋利武器,因此在西藏地区,牦牛角被视为汇聚神灵神力的力量源泉,也是战胜所有邪恶势力的无上法宝。西藏苯教中举行庆祝战争获胜以及修建寺院仪式时,首领会选择一头非常雄壮的雄性牦牛作为标杆,然后用神龙降妖箭将其射杀,用清油熬煮牦牛骨,再用青稞酒将牛骨冲洗干净,并在未干的牦牛头骨上面刻写经文、咒语、符号。紧接着,教长要对刻画经文的头骨诵读经典,将牛头骨、牛尾和利刃器械一起深埋在特定的方位,这就是藏族所称的“驱邪镇山三宝”。
在我国除藏族对牦牛崇拜外,不同民族对不同品种的牛也有崇拜的习俗。如佤族就是以水牛为图腾的民族,水牛在佤族人心中是神圣、高贵、吉祥、庄严的象征。在佤族创世史诗《司岗里》以及古代《大惹嘎木》神话中,都记述了有关牛是人类始祖的传说。当地还流传着牛是佤族救命恩人的传说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一对佤族青年男女到公明山上放牛,男名艾那,女名叶布勒。正当他们打算赶牛回家时,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洪水很快泛滥高涨到公明山上。除了站在公明山最高点的艾那、叶布勒和所骑的那头水牛外,其他一切生灵均遭劫难。洪水汹涌了三天三夜之后才慢慢退去,艾那和叶布勒得救了,可水牛却因长时间驮着二人而累死了。后来,艾那和叶布勒结婚并生育了很多子女,这才有了今天的佤族。”(王勇等《中国世界图腾文化》2007年时事出版社出版)因此,水牛就成为佤族的救命恩人,每逢年节,佤族人都要祭拜水牛。佤族人在祭祀自己的祖先时,还要进行剽( )牛活动。这天,佤族女人随着音乐的节奏开始起舞,男人则把水牛牵进剽牛场,随着祭祀的鼓乐大震,标枪手走到水牛跟前,高举梭镖猛地刺进水牛的心脏。水牛经过痛苦挣扎后倒地身亡。然后,人们砍下牛头,用来祭祀祖先。水牛曾是佤族人的图腾崇拜物。
)牛活动。这天,佤族女人随着音乐的节奏开始起舞,男人则把水牛牵进剽牛场,随着祭祀的鼓乐大震,标枪手走到水牛跟前,高举梭镖猛地刺进水牛的心脏。水牛经过痛苦挣扎后倒地身亡。然后,人们砍下牛头,用来祭祀祖先。水牛曾是佤族人的图腾崇拜物。
《农业考古》研究表明,“牛是指两种不同属的黄牛和水牛。黄牛既可用于肉食又可用于耕田,水牛主要用于南方水田耕作。它们分别是从不同的野生祖先驯化而来的。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地层里,都发现有现今黄牛和水牛祖先的化石,为原牛或原始牛。所以,在中国黄牛和水牛是独立起源的。河北的武安县磁山遗址,河南新郑县裴李岗遗址和巩义县瓦窑嘴遗址及午阳贾湖遗址、山东滕州市北辛遗址、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等,都出土过牛骨。虽不能确定都是家养的牛,但也不能否定当时已有驯养野牛的尝试。”“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牛骨大为增加,至少在新石器时代后期,牛已在原始畜牧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商周时期养牛业有很大发展。除了肉食、交通外,牛还被大量用于祭祀。”“春秋战国时期,耕牛已经推广,在农业生产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中国文物报社编《大考古》济南出版社2004年出版)。可见,耕牛的出现和牛耕的生产方式很早就出现在北方广阔的生产领域中。有学者认为黄牛出自北方,而水牛则出自南方。
2010年,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香加乡哈日塞沟M4号墓中各出土一具彩绘木棺,经过复原临摹,在棺侧板西边隐约可以看出绘有“牛耕图”的耕作场景图像,画面残损严重。这组“牛耕图”画面,东面画有一着红衣的人侧转身牵牛向东而行,中间一头红色耕牛挽犁,后面跟一人扶犁耕作。而扶犁人的形象只画有一部分。由此分析,这幅棺椁彩画起始程序可能是从右边开始起笔向左边延伸绘画,待画到扶犁人时,已到棺板边缘无法全面表现。因此可看出,古代画家在绘画时并没有全方位地考虑到总体布局与构图,可能只是根据自己对传统的理解,将墓主人生前的事迹按连环画的形式一步一步地画在棺板之上。这是青海海西地区首次发现农耕图像。
“叔均”也作“始均”,《山海经》说是神农的孙女,也有史书说是黄帝的孙女。重要的是这个名字的内涵。按《山海经》的说法,“叔均”是“稷”的孙女。“稷”发明了农业,而他的孙女“叔均”却发明了牛耕的生产方式。按《山海经》提供殷商的“叔均”始作牛耕的说法,牛耕传入中原至少也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
关于神牛的由来,在纳西族《东巴经·创世纪》中有这样的记载:神牛是大海中的巨卵所孵,牛角能顶破天,四蹄能踏破地,因此造成天摇地动。为了保护世界,纳西族的始祖开天七兄弟和开地七姊妹联合起来将它杀死,并用牛头祭天、牛皮祭地、牛肉祭泥土、牛骨祭石头、牛肋祭山岳、牛血祭江河、牛肺祭太阳、牛肝祭月亮、牛肠祭道路、牛尾祭树木、牛毛祭花草。这才有了明亮的天空和万物生长的清静世界。从此,牛作为世界的起源,被纳西族世代供奉着。
我们很难考证中国的十二生肖起源于何时,但历史上最早记载十二生肖的是东汉的王充所著的《论衡》,《论衡·物势》中记载:“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午,马也。子,鼠也。酉,鸡也。卯,兔也……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巳,蛇也。申,猴也。”在上述引文中,只有十一个生肖,没有龙,然而在该书《言毒篇》中又说:“辰为龙,巳为蛇,辰、巳之位在东南。”两篇内容叠加之后十二生肖便齐全了。十二生肖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而这一历史遗产产生并流传至今与人类早期对人类起源的认识不科学有很大的关系。关于“我从哪里来”是古代人类孜孜不倦求解的问题,在远古时期,人们认为自然界中的动物和植物与自身有血缘关系,比如草原民族认为他们是狼的子孙,有些部落认为自己是鹰的子孙,并将此作为自己部落的图腾。而十二生肖也是不同部落的崇拜物,除了这十二个崇拜物,还有很多,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有这些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
牛是早期农业生产社会必不可少的,牛有着任劳任怨的品格,在我国很多民族中牛这一形象都非常受欢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很多形式的牛崇拜,关于这些崇拜的起源也有着不同的说法。在不同民族中,牛的诞生之日有很多,因此也有着不同的生日。比较典型的有粤北的客家人世代相传的农历四月初八作为牛王生日,在当地人中被称为“牛王诞”;闽西人历史中,牛的生日是农历三月三日;而瑶族人民则是将十月初一作为牛的生日。除此之外,壮族、纳西族以及苗族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也有着过牛节的风俗习惯。
除了国内各民族对牛的崇拜以外,“牛”几乎可称为世界范围内的崇拜主题。比如,在印度教教义中,峰牛象征着繁殖和兴旺发达,而印度教中崇拜的湿婆大神就是以一头威武高大的神牛——南提作为他的坐骑。印度教教徒将峰牛看作是神的化身,称为“神牛”,因此在印度教中,峰牛在牛类中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中母峰牛则是峰牛中最为神圣的,按照印度教教义,婆罗门和“神牛”是造物主在同一天中创造出来的,因此“神牛”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印度教教徒顶礼膜拜的神物。
据学者考证,印度教徒对牛的崇拜与他们的祖先雅利安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历史上,对过着游牧生活的雅利安人而言,牛是最宝贵的,包括它身上所有的一切。印度人有句话:娘生我,牛养我。圣雄甘地曾说:“牛是印度千百万人的母亲。古代的圣贤,不论是谁,都来自牛。”(王勇等《中国世界图腾文化》2007年时事出版社出版282页)的确,牛能帮助人类耕耘、驮运,牛奶又是人的重要食物,连干牛粪都可以作燃料,湿牛粪可以用来涂地抹墙,具有防虫蛀的功效。
尼泊尔人把牛视为神的象征,他们忌食牛肉、禁止使用牛皮,有的地区甚至不允许用牛来耕地。尼泊尔人在每年的8月都要过“牛节”,整个节日要持续8天。在尼泊尔,牛还是他们的国兽,在他们的国徽上就有喜马拉雅山、太阳和星月、河谷及国花杜鹃花、国兽白牛和国鸟绿雉(王勇等《中国世界图腾文化》2007年时事出版社出版276页)。
古岳先生在《谁为人类忏悔》一书中对牛的描写十分精彩:当上千头乃至几千头一群的野牦牛从那亘古莽原上走过时,天地都会为之动容(古岳《谁为人类忏悔》2008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它们像一股势不可当的洪流,在江河源头奔腾呼啸,它们似一道划空的闪电,在雪域深处漫步而过……草原为之沸腾。牦牛原产亚洲中部山地,现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等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由于它常年生活在雪山草地、冰滩陡岭中,常常有剧烈奔跑的习惯和能力,所以它有极强的耐力和适应性。现今人们称牦牛为“高原之舟”“人间之宝”。它即为“旌( )牛”“髦牛”,因叫声似猪,又称为“猪声牛”。因它身矮体健,全身披有黑色、深褐色或黑白花斑的长毛,故能抵御严寒雪雨,睡卧冰滩雪地。它那宽阔的肩膀、飘逸的裙毛、威武的身躯令人肃然起敬。
)牛”“髦牛”,因叫声似猪,又称为“猪声牛”。因它身矮体健,全身披有黑色、深褐色或黑白花斑的长毛,故能抵御严寒雪雨,睡卧冰滩雪地。它那宽阔的肩膀、飘逸的裙毛、威武的身躯令人肃然起敬。
它的飞奔速度往往使骏马也黯然失色。赛牦牛是赛牛者骑在牛背上,比谁的牛奔跑的速度快,其竞赛场面极为壮观、激烈、扣人心弦。一头头赛牛怒目仰首,一窝蜂似的向前疾驰。前后拥挤的赛牛翘起奋力的尾巴,浩浩荡荡直冲前方,狂奔的飞蹄震撼着大地,摇曳着人心,好似一道滚滚的山洪,在辽阔的草原上奔腾、呼啸……(www.zuozong.com)
(3)鸟类造型解析
鸟类的图形符号是世界很多民族中共存的。在西北地区同许多崇鸟民族一样,鸟也是古代羌族最早的崇拜图腾之一。这种以鸟为主题纹饰和造型的艺术品,在青海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宗日文化,青铜时代的辛店文化、卡约文化以及汉唐时期相关遗址均有大量实物出土。学界大都认为,鸟是太阳的象征。何新先生的解释是:“一谓太阳本身就是鸟,一谓日中有乌或三足乌。”
关于鸟图像或造型的文物在青海地区比比皆是,下面仅就个别与鸟相关的文物造型做简要介绍:青海省海东地区乐都县高庙镇柳湾墓地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墓葬中出土2件鸮面罐。器形整体模仿禽鸟——鸮的形象烧制。在同一墓地的齐家文化墓葬中也出土了10件鸮面罐,其造型与上略同。在器物口沿部分半封隆起的半圆面,鸮首五官就在这半圆面上表现。其中在半圆面的中部钻两个小圆孔以示双眼,有的在器物颈部粘贴一圈附加堆纹与身体相隔,有的利用附加堆纹在半圆面上贴出鸮面形状。这种制作手法不仅将鸮的特征表现突出,而且显得十分传神,真是远古时代一件经典之作。
1985年,在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黄家寨墓地卡约文化M16出土铜鸟形杖首,范铸合成,鸟体中空,内有圆形石丸1粒,系铃舌,摇之有声。铜鸟整体呈立式,挺胸昂首,双目圆睁,喙呈钩状,张嘴鸣叫,头顶齿状立式冠,身体饱满圆润,尾部展开呈欲飞状。鸟身两侧镂空成六个弧形长条孔,以示鸟翅,双腿以镂空的圆管表示,此鸟饰应是插在某一物件上的装饰部件(崔兆年陈荣《大通黄家寨墓地》任晓燕《再现文明:青海省基本建设考古重要发现》2013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3年在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大华中庄征集1件卡约文化的鸟形铜杖首,其鸟头两侧铸一凸起的圆形大眼,圆形眼球内凹,层次格外分明。鸟喙前伸下弯,喙上铸有鼻孔。鸟颈上窄下宽与圆润身体对接,背部以浮雕技法铸出羽翼,腹部一周竖向镂空八片叶形纹,体内设一圆形弹丸,摇之有声。鸟体下部铸一圆筒形銎,銎底一侧铸一方形孔。
1985年在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拦隆口征集1件卡约文化的鸟形铜铃。其鸟头部较小,头两侧雕有三角形双眼,钩状鸟喙向下弯曲,细长脖颈与身体自然衔接,从脖颈中部至身体尾部竖向镂空九道长叶纹,体内置一铃锤,摇之有声。体下腿部铸一长方形中穿小圆孔的铜片,这个小圆孔一定有它实用的含义,也许是绑缚在某种物品之上起到装饰作用的。
1978年在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乙M3号中出土1件东汉时期的青铜神鸟冠(单独阐述,此不赘言)。同墓还出土1件鸟形铜带钩,钩首模仿鸟头形状铸造,钩身模仿鸟的双翅,总体造型极为精彩。在同一墓地乙M5号出土1件东汉晚期的鸟首铜削,轮廓曲线简练传神。2004年在青海省西宁市山陕台墓地(乙区)M20出土2件东汉时期的鸟形铜带钩。其总体造型优美古朴,与上述同类器物略同。据不完全统计,青海地区发现的犬、牛、鸟图像及圆雕造型文物数量很大,其中发现犬形28条,在3件陶器上绘制有14条,在岩壁上凿绘有5幅11条,铜铸圆雕有1条,金银锤揲有2条;发现牛形311头。其中在都兰诺木洪发现1头陶塑牦牛,在岩壁上凿绘有44幅305头,木雕牛3头,银质锤揲牛2头;发现鸟形有20只。其中陶塑器物造型12只,铜鸟杖首2只,鸟铃1只,鸟冠1只,鸟带钩3只,鸟铜削1只。
其中,“犬戏牛”铜鸠杖首中的鸠鸟还有另外一层文化寓意。《周礼》载:“罗氏献鸠养老,汉无罗氏,故作鸠杖以扶老。”说的是到了汉代以后,以专门捕鸠献给老人为职业的罗氏没有了,就只能取鸠鸟长寿吉祥之意,在手杖的首端铸鸠鸟的造型,以此代表鸠送给老人了。据史料载,以鸠杖赠老人的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就已产生。春秋时通行大夫70岁退休的制度,如果因国家需要而不能退休,国君就赐给他鸠杖,并派专人服侍他的出行。汉代继承了这种敬老美德。从此,鸠杖也淡化了它“以鸠其民”的王权特征,走进了寻常百姓人家。《后汉书·礼仪志》载:“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脯之糜粥。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王杖九尺,端以鸠鸟为饰。”因为,在诸多的食物中,以肉食为最珍贵。在原始采集和狩猎时代,肉食是先民们拼着性命猎来的。当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发展起来后,肉食仍极为宝贵。孟子构想的理想生活,就以70岁能吃上肉为重要标准,弟子拜师的礼物也不过是两束肉干,可见肉食的难得。
看到远古先民们的一件件优秀作品,勾起我们多少幽幽怀古之情,那些经典作品记载着多少辉煌的往事。早在3000多年前,雄踞在青海高原上的古代羌人以鸠鸟的形象告诫人们尊老的风尚,并以此作为部落首领权力的象征和代表王者之威严。今天的藏族人民还仍然将鸠鸟崇为至高无上的神鸟,这种鸠鸟崇拜习俗在青海高原一直流传至今。
(二)文房佳作——青铜玄武砚滴(汉晋)
玄武是中国古代“四神”中指代北方的瑞兽。在我国古代神话系统中,它的地位颇高,是天文二十八宿中的北方神,又是传说中的水神、海神兼冥王。在道教中它被称为真武大帝,因此成为道教中的四大天王之一。
如此宝贵的以古代玄武神形象为造型的文物,在青海地区也有发现,其中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青海省海东地区互助土族自治县高寨乡东庄村出土1件魏晋时期的青铜玄武砚滴最具特色,高5厘米,长14.7厘米,龟形,背上盘踞一条饰有鱼仔纹的蛇,蛇首伏在龟的左肩上。龟首高昂,口衔小碗,腹空,背部饰回纹,背中心处设一筒状添水口,龟甲边缘呈莲瓣状,龟尾低垂。这件文物构造设计合理,做工考究,形象逼真,洋溢着动态的美感。
而玄武作为水神,最初是起源于上古时期理水之官——水正。在《吕氏春秋·孟冬记》中记载:“水神玄冥”,而在《左传》中也有着“水正曰玄冥”的记载。而水正正是我们所熟悉的以治水而闻名的大禹的父亲,后来在治水的过程中以身殉职,除水正这个名字外,他还有个更为后人所知的名字——鲧( )。
)。
根据上古传说,水正以身殉职的地方是羽山,羽山在传说中是极北之山,在《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掩洪水,不得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山。”而在《山海经·海内经》中又有记载:“在北极之阴,不见日”,在《淮南子·地形训》也有关于极北之地的记载,因此玄武便成为北方之神,也是北方七宿的方位星神。
冥、昧古音相同,读若“晦”,而其音义又与海相通。所以玄冥由水神再变为海神,遂与原来的海神禺强混而为一。《山海经·海外北经》郭璞注:“禺强字玄冥。”
传说中的北方是长年不见日的黑暗王国,即“幽都”。而禺强在传说中又是主管刑杀的“不周风”之神,这样一来,玄冥便成为冥王,即“北方黑帝”,也就是中国神话系统中的死神之一。
宋高似孙《纬略》云:“龟水族也,水属北,其色黑,故曰玄;龟有甲能捍御,故曰武。”玄武一名再变即为真武。真古音读填,与玄为叠韵音转。真武,勇武也。此语义汇于玄冥神话系统中,真武大帝便被塑造成一位仗宝剑,着黑衣,脚踏龟蛇的武士形象。
另外《左传》记载:“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修及熙为玄冥。”这段史料极为重要。这里所说的“熙”就是“鲧”的近音通假字。而修正是鲧的夫人和大禹的母亲女修。《竹书纪年》载:“帝禹夏后氏,母曰修巳。”巳通姒,是夏族的族氏。巳与蛇在古代是同字。故修巳实际上就是修蛇。而熙则是鳖,鳖与龟为同类。由此我们便可理解玄武神以龟蛇合体的形象出现,正是熙(鳖)与修(蛇)夫妇的象征性变型。《文选》注:“龟与蛇交曰玄武。”原来龟与蛇组合的“玄武”神的形象,实际上就是大禹父母交配的姿态。这种组合形象是否又包含着神秘的古代性崇拜因素呢?
通过以上材料的对比与分析,对玄武神的来龙去脉有了基本的了解。然而“青铜玄武砚滴”的出土,充分表明中原汉文化中的“四神”崇拜,已在魏晋时期的青海高原地区落脚。《饮流斋说瓷》云:“蟾滴、龟滴,由来已久。古者以铜,后世以瓷。凡作物形而贮水不多则名曰滴。”龟形砚滴在我国晋代比较多见,它是古代文人墨客文房中的儒雅用具。
古代先民通过千百年对自然环境的观察,利用四种动物形象将四方划分,这种划分法,是先民们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古代科技成就,是认识、了解和顺应自然的体现。在人类生产力尚不发达的昨天,顺应自然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三)古代照明用具——青铜卧羊灯
羊生性温和,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家畜之一,让原始人类不再以打猎和采集为主要生存手段,尤其是在青藏高原这个畜牧业占重要地位的地区,羊对这些地方的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因此羊符号的崇拜也顺理成章。在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黄家寨地区,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征集到了一件非常典型的以羊为主要造型的青铜器——青铜卧羊灯,它是古代的照明工具,现收藏在青海省博物馆。这件青铜器产生于汉代,通身长共12.5厘米、宽7.0厘米、高12.5厘米,重340克。此灯具是模仿一只卧羊姿态塑铸而成,其羊首昂起,双角向下弯曲贴至颊部,羊目仰望天空,唇下羊须与颈部相连,肌肉发达的前后四肢弯跪,臀部肥硕圆润,短尾。形态憨然,纯朴古雅,设计巧妙,手法写实。羊腹中空,用来储放灯油。羊的背部和身躯分为两部分,羊首后部装有活钮,臀部装小提钮,使得羊背可以向上翻开,形成一椭圆形凹弧灯盘平架在羊首之上。羊背灯盘设有小流嘴,以便放置灯捻,当熄灯时,灯盘内剩余的灯油可顺小流嘴倒回腹腔库,羊背灯盘扣回身躯,即恢复为卧羊姿态。这件青铜器做工精美,而且相比其他出土的青铜器,实用性更强,因此可以说这件青铜灯具是古人将审美和实用结合在一起的产物。
采光对于人类的生活至关重要,小到蜡烛灯具,大到建筑门窗设计,这些都体现了采光对人类生活的重要影响。而灯作为照明工具,在古代,只要有燃料和灯捻,以及盛放燃料的盘形物体,点燃之后就能实现灯最原始的照明功能。早期的灯具,类似陶质的盛食器具“豆”。“瓦豆谓之登(镫)”,上盘下座,中间以柱相连,虽然形制比较简单,却奠定了中国油灯的基本造型。自此之后,铸造技术提高,青铜文化大放异彩,而灯具经历着变革的洗礼,除了其实用性以外,在造型上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更加具有艺术性,为中国油灯艺术奠定了基础。而这件青铜卧羊灯便是其中的翘楚。
这件结构巧妙、制作精细的卧羊灯具,正是汉代崇羊观念与儒家思想在文物上的具体表现。我国是世界上较早驯养羊的国家之一,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有了原始的畜牧业。《诗经》中就有“尔羊来思”的诗句。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羊已是人类主要的肉食来源之一。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河南省新郑市裴李岗、陕西省西安市半坡、临潼县姜寨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出土过羊骨和陶质羊形器物,说明中国北方养羊的历史有可能早到六七千年以前。《卜辞》记载,在当时祭祀活动时用羊数量多达数百只,甚至上千只。《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每群羊的数量达到三百只,可见商周时期养羊业甚为发达。春秋战国时期,养羊业更加甚之。“今之人生也……又蓄牛羊”。(《荀子·荣辱篇》)秦汉时期,西北地区“水草丰美,土宜产牧”,出现“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兴旺景象(《后汉书·西羌传》)。各地汉墓中常用陶羊和陶羊圈等冥器陪葬。魏晋南北朝时期,饲养羊已成为农民的重要副业。因此,《齐民要术》专立一篇《养羊》,总结当时劳动人民的养羊经验。羔羊跪乳虽然是羊的一种天性,但人类往往喜欢“以己度物”,在这种原始思维的推动下,人们便将这种现象赋予人的道德属性,用来表达知报母恩的美好品德。在谯周《法训》中有记载:“羊有跪乳之礼,鸡有识时之候,雁有庠序之仪,人取法焉。”
随着对羊的知报母恩的推崇,很多动物不再是豺狼虎豹般威严狰狞和霸道专横,而是变得可爱可亲,充满了祥瑞之气。而人们对“羊大为美”的观念,已经不再只是贪图温饱,也不仅仅将羊视为入口的食物,而是寄托了更多人们所推崇的精神追求。《西安文物精粹·金银器》一书中写道:“这种性质的铜灯在汉代只有诸侯王一级的官员才能使用。”可见青铜卧羊灯不仅仅是艺术性和实用性的结晶,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这件文物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县黄家寨附近,这个地区与汉代的长宁县非常接近,也是汉代墓葬分布比较集中的地区。然而经过文献检阅发现,在青海地区,汉代并没有埋葬诸侯王一级的汉族官员,所以我们无法得知这件铜质卧羊灯具到底是什么人的墓葬陪葬品。有可能汉代时期有被分封为“王”的少数民族首领,然而这一点至今没有定论,这也是考古史上的谜团,有待考古人员今后进一步探索。
动物形象从古至今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热门的刻画主体。比如古代的图腾,建筑物装饰,如今各类活动吉祥物,甚至一国国旗。而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很多陶器上就已用羊的形象来进行装饰,象征着人们对吉祥如意的向往。而除了青藏高原以外,在商代青铜器中,羊为造型的器物还有很多,比如著名的四羊方尊,它以四只羊的造型朝着四方挺立,共同用背部托起浑厚的方形尊口,呈现出强烈的立体感,被誉为青铜器“十大国宝之一”。
在甲骨文中,羊通“祥”,古铭文的“吉祥”即吉羊。“三阳开泰”源出《周易》,用三只羊来表示,其中一只为母羊,另两只为小羊,一只在嚼春草,另一只跪在母羊腹下吮乳。“羊”与“阳”同音,“三羊”者“三阳”也,表示春回大地、万物滋生、欣欣向荣、光明通泰。在中国汉字中,有许多字与羊有关,如“美”字由羊、大两字组成,“羊大为美”。《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美与善同意。”其“美”字的本意是羊肉味美、好吃,故善字也从羊。
青海原始动物形象中,羊的种类很多,就岩画而言,有羚羊、黄羊、山羊、绵羊等。20世纪末,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本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切吉乡发现两处距今2000年前的动物岩画,一处为羚羊形象共两只,采用磨划法,右侧那只半通体磨划,其风格写实,造型准确。另一处为黄羊形象,共两只,磨划法,羊作奔跑状,形象生动有神,洋溢着美的旋律。
居住在青藏高原以游牧部落为主的先民无论是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都与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藏族由诸羌发展而来,之所以称之为“羌”,正是从游牧的特征对草原民族加以描绘的。“羌”字在甲骨文中为“ ”,金文中为“
”,金文中为“ ”。《说文解字》释为:“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常用古文字字典》更进一步解释道:“像一个头戴羊角的人。”换言之,“羌”字可分解或理解成“羊人”。《新唐书·吐蕃传》则清楚地告诉我们,吐蕃“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为大神”。“羱羝”是一种大角野公羊。羊在吐蕃人的观念中,可能是作为年神而加以崇拜。
”。《说文解字》释为:“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常用古文字字典》更进一步解释道:“像一个头戴羊角的人。”换言之,“羌”字可分解或理解成“羊人”。《新唐书·吐蕃传》则清楚地告诉我们,吐蕃“其俗重鬼右巫,事羱羝为大神”。“羱羝”是一种大角野公羊。羊在吐蕃人的观念中,可能是作为年神而加以崇拜。
关于用羊的宗教仪轨也很丰富,如治病盟誓,祭祀祖先或山神等,但一般说来,羊则多用于殡葬仪轨,在苯教教义中,羊能引导亡灵前往“福乐之国”和“死神之地”,死者在那里幸福地生活。如青海卡约文化墓葬中大都殉以羊骨,同时也有绘制羊纹图案的彩陶器与以羊为主题的青铜器为随葬品。20世纪末期,青海省海东地区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阿哈特拉山出土2件卡约文化羊纹彩陶罐,1件在器腹部饰羊纹图案,羊的形态纯朴、活泼丰满。1件在腹部饰变形羊角纹,线条奔放流畅,结构严谨。青海省海东地区乐都县双二东坪出土1件辛店文化彩陶片,饰有山羊形象,此羊造型古朴写实、圆劲有力。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良教乡出土1件卡约文化的青铜戈,在銎侧铸一盘羊造型圆雕,此羊双角环绕,角尖微翅,两耳卷曲向前,张口瞠目,四腿略弯曲站立在銎上,造型生动逼真。
汉唐时期,青海地区以羊作造型或以羊为图案的随葬品仍然很盛行。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乡吐谷浑·吐蕃墓葬中出土1件唐代对羊织锦,为四方连续图案。双羊相对举首奋翼作奔跑状,布局新颖规范,色彩古朴艳丽,显示了古代艺术家的纯熟技艺和精湛的工艺水平。与其他祭祀中的动物不同,用于殡葬仪轨的羊具有一定的神性。在现代羌人中,举行殡葬仪式时杀羊以引导亡灵的风俗还在延续。
青铜器中的图形符号种类非常多,有些符号不仅仅在青铜器中有所体现,在其他载体中也多有出现。在青铜器后期,人们对金属冶炼和铸造技术的提升,也引出了其他金属器的装饰造型。而这其中最为普遍也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金银器。在中国古代,便专门设置有打造金银器的政府部门。这些部门中工匠技术精湛,打造的图形符号也更加精美,艺术性和装饰性更加突出。比如唐朝时期有专门设置的善金局,聘用了西域多国和唐朝国内的工匠,为皇帝专门设计打造金银器。这一时期,很多西域国家的图形符号传入了唐朝,与当时的符号相结合,诞生了很多融合多国元素的图形符号。因此金属器物的图形符号是图形符号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