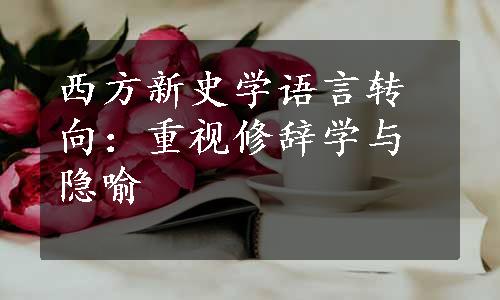
西方新史学在打破宏大叙事独尊而使史学多元化的同时,也不能不在语言风格上有所变化。实际上,承认史学创作中可以融合文学性,就不可能不在语言风格上发生变化。在人文的诸多领域,似乎都可以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在这里,语言转向与人文学科的关系,例如,与这里所谈的史学的关系,乃是处于互动而相互影响的状态。这种语言的变化,并非像以往所说的那样,归结为内容决定形式,把语言简单归结为只是形式。相反,语言不仅是形式,而且本身就是内容,甚至是内容的灵魂。一个思想文化新世界的出现,最终乃是由语言所创造和显现出来的。当然,语言转向不允许任意和随意,它是与思想文化转型一体的自然过程,并且是文化转型的先声和最终成就者。就此而言,著名德国思想家和史学家布克哈特早在19世纪末已经天才地猜测到了语言转向的问题。他在《世界历史沉思录》中最看重的历史内容,乃是诗歌和艺术,并视之为历史的核心内涵。不难理解,诗歌、艺术的语言与规定性的叙述、论说的语言相比,显然具有本质的不同。象征和隐喻乃是诗歌和艺术语言的突出特点。以这种具有不确定性的象征和隐喻语言所创造的作品,流光溢彩,具有唤起人们自由联想的无穷魅力。因此,当布克哈特说“人的精神一旦意识到它自己以后,它就会以自己为中心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时,那么,这个思想的新世界,最终也只能由与之相应的语言创造和显示出来。事实说明,任何作为新纪元的标志的思想文化新世界,总有新的语言来催生和最终成就她。
当代最负盛名的新史学家海登·怀特正是悟到语言转向的重要性,才提出史学研究必须重视“修辞学”问题,倡言史学研究也需要“隐喻”,他还特别强调“隐喻”的重大意义。为此,怀特批判了康德对于“隐喻”的片面理解以至全盘否定“隐喻”的错误观点。在他看来,语言自始就带着“隐喻”来到这个世界上。或者说,语言在本质上都具有“隐喻”性。而这种“隐喻”绝不是只有消极的负面意义,例如,由于人们从邪念和恶念出发,借助它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种种荒谬。相反,“隐喻”还具有不可忽视的非常积极的正面意义。在这个问题上,怀特并不否定“隐喻”可能导致荒谬的消极一面。但是他认为,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此,他在引出康德在其逻辑学中所说的“一切错误的起源是隐喻”之后,接着就指出,“隐喻或许是一切错误的源泉,但它也是一切真理的源泉”。这一看法真是绝妙,大有深意,并显示出怀特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就是说,在逻辑的概念思维之外,人们经常倘佯在诗意联想的“象思维”之中。“象思维”中象征和隐喻的诗意语言,能使人的思想波澜起伏、想入非非。实际上,正是这种波澜起伏的思绪,能打破传统思想惯性的僵化,能开辟人们创新的思想天地。这也说明,原创性思想往往不是从逻辑概念出发所能生发的,相反,只能是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之“象思维”中才能生发。(www.zuozong.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