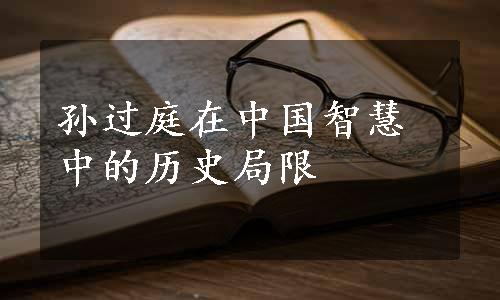
在玉涛看来,虽然孙过庭提出了书法美学的“妙谛”或纲领,但是他却没有纲举目张,或者说,在具体说明人物和品评作品时,不能把写意思想贯彻到底。玉涛的“反中和论”,主要是批评孙过庭对王羲之书法作品评价的不彻底性。玉涛认为,孙过庭不仅在对羲之书的评价上存在偏颇,而且对献之书的评价也不公正。如他所指出的:“‘思虑通审,志气和平’者,乃是对右军‘末年’整个心境的概括;‘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者,乃是对右军末年书风的评价,就好像以‘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否定整个的献之书一样。”就是说,在玉涛看来,孙过庭这里对王羲之的肯定和对王献之的否定,都不正确。在对《兰亭序》的辨析中,玉涛首先指出,以往的误解在于都没有弄清其主题。实际上,《兰亭序》的主题,乃是在文章临近结尾处,在那里充分表现出王羲之对于人生意义的深切感悟。所谓:“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在这里,王羲之表现出他那种特别重视人生价值的积极心态。玉涛通过对《兰亭序》内容的辨析,进而又对《兰亭序》现存摹写本加以批判。他说:“我曾把《神龙兰亭》反复展玩,近看、远看、平看、竖看,认为它没有神采,没有精神。好像残花败柳、死了的美人;又如看美人照片,眼无神气。冯承素等只能临出面貌,不能临出风神……这是毫无办法的:冯承素等生在初唐,又没有右军的身世和修养,怎能临出神采呢?于是,现在的神龙本,又如朽骨一般了。”就是说,即使就《兰亭序》而言,无论从文之主题内容,还是从书体风骨应有的原貌,都不能说羲之书是所谓“不激不厉”或“志气和平”。至于谈到王羲之晚年真正的代表作,玉涛认为,应当是他在家事国事不断遭遇惨祸的岁月中所写的“杂帖”,其中尤其以《丧乱帖》为代表。玉涛说:“右军是有极品的。这就是《丧乱帖》……虽然也是钩摹,但与《兰亭序》不同,那呼天抢地、披头散发的风烈,那又雄强又惨淡的风神,基本上保存下来了。区区八行,由行入草,正说明感情变化的激遽。这才是书道,这才是抒情,这才是真性情的流露。右军有此一帖,足以不朽。此帖离所谓‘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标准,风马牛不相及,相去是何等辽远啊!但,这才是真面。”
实际上,正是王羲之晚年国事家事连绵不断的惨剧、悲剧,使得他在痛苦难耐的磨砺中,赤子的真情和壮士的情怀得到一次辉煌的大爆发,而他的那些杂帖特别是玉涛赞叹不已的《丧乱帖》,就是这种赤子和壮士之情大爆发的产物。在这些帖中,赤子之心、壮士风骨的人格魅力与书法艺术的高标熔为一炉,放射出不朽的灿烂光辉。历史事实证明,具体的人物和艺术作品,都是时代的特殊环境所玉成。因此,只有深入透视历史时代底蕴之人,才能对具体历史人物和艺术品作出把握其本真的领会。可以说,玉涛能破除传统的俗见,别具洞天地发掘出王羲之其人其作品的本真底蕴,并指出孙过庭的局限,正是由于他能透过种种现象而洞悉晋唐时代的精神底蕴。(www.zuozong.com)
在“反自然论”中,玉涛经过详细辨析孙过庭所提出的“自然”与“妙有”,指出两者都是具有“道”与“玄”这种本体意义的范畴。“自然”与“妙有”的这种意义,对于中国美学发展的重要性不可轻视。但是他接着强调指出:“中国艺术、中国美学的生命力,全在风骨,不在自然,不在中和。”玉涛的这个观点表明,他并不是不要自然,而是说就推动中国艺术和美学发展的内在动力而言,不是自然论,而是风骨论。显然,这个观点与他把写意看做中国美学之魂是相一致的。写意就是抒情言志,就是“取会风骚之意”,就是诗心诗意盎然。既然书法艺术乃至一切中国艺术,都以此为魂魄,那么这里所说的风骨,就不过是写意、诗意的另一种表现而已。同时,玉涛对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的看法,也表明他在艺术观和美学上始终坚持以人或主体为主导,坚持充满诗意灵气的能动创造论。实际上,谈到艺术的创造,这种人的主体能动的创造论,作为真正艺术和美学之魂,古今中外都是大同小异的。就以宗白华先生所说的世界艺术三绝来说,有哪一种不是人的主体能动的创造结果呢?不过,在理论形态上,中国的写意美学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并且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玉涛说:“中国艺术对自然的表现,根本不是‘模写’……中国艺术以它全面鼎盛的时代——汉唐为代表,对自然的表现,有什么特色呢?这就是驾御自然,征服自然,蹴踏自然,‘欲与天公试比高’。那结果,是‘天雨栗,夜鬼哭’,自然黯然失色了。它确实从自然来,但它战胜了自然,蹴踏了自然,这是何等魄力?”就是说,中国的写意艺术,特别是书法艺术的创造,不仅不是自然的“模写”,也不是“人化自然”,而是借助自然而又超越自然所创造的“这一个”。“这一个”,世界独一无二的“这一个”,乃是人的诗心诗意的凝结,乃是人的风骨神韵的凝结,乃是与宇宙大道相通之生命魂魄的凝结。显然这种艺术品不是一般人所能创造出来的,也不是从事艺术的人都能创造出来的,每一时代只有极少数天才能创造出来。所以,每一时代所留下的这种艺术珍品,都为数不多。由上述可知,玉涛从“反自然论”,就必然要导出“天才论”之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