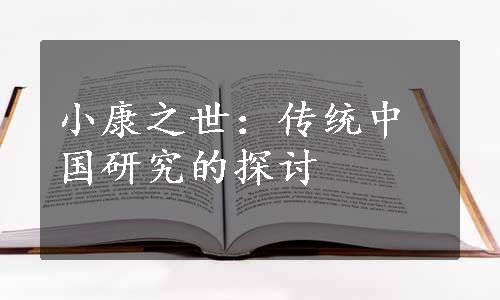
大同之世既非老庄所认为的浑浑噩噩,也不是现代学者所认为的乌托邦,而是儒家礼制的最高理想,即不需要制礼,人们也按照礼的要求去生活。基于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后文的“小康之世”。不过“小康之世”的文本情况会更复杂一些。这一段里也确实有错简的可能,因而使文本的解读变得更加困难。
人们通常的理解,是认为从“今大道既隐”到“是谓小康”都是在说小康之世,这就似乎更接近老庄的历史观,即认为礼乐的兴起伴随着历史的退化。但杨朝明已经发现,这一段里并非每一句话都在说同一种状态,而我们也认为,这里其实包括了两种状态。第一种,是从“今大道既隐”到“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说的并不是小康之世,而是大道既隐之后民风的普遍状况。此后才是在讲小康之世,并不是三代的整个时期,而只是“三代之英”,即“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在位的时期。我们需要清楚的是,不可强行按照现代社会发展史的理论来理解《礼运》的历史观,小康并不是大同之后的一个时代。大同,是最高的礼制理想,被投射到了五帝时期,在现实历史中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小康,是现实历史中可以达到的礼宜乐和的最高境界。而所谓“今”,不仅不是狭义的现在、当今,而且应该泛指整个现实历史时期,既包括三代最好的时候,也包括夏桀、商纣、周之幽厉,以及孔子当时,民风都是大致如此的。
大道既隐之后,人们已经不再像原来那么淳朴,没有教化与约束就不可能自然向善。现代学者常常把“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与“天下为家”连在一起读,似乎是在说家庭的出现。但这里说的是两件事,虽然两者有关系。天下为家,指的是天子传位于其子,也就是后文“大人世及以为礼”。郑注:“大人,诸侯也。”郑氏之所以在这里作注,就是强调“大人”并非后文所说的“六君子”,这些掌权者由于无法做到天下为公,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私心,所以他们是实行家天下的。张横渠说:“大人世及以为礼,由古以来固亦有传世,但道隐之后,虽有子如均、朱,有臣如伊、周者,亦不能举行尧、舜之事,故以世及为定礼。”[49]其关键并不在禅让制与世袭制的差别,而在于贤能是否最高的标准。如以贤能为第一标准,在子为商均、丹朱,而臣有舜、禹之时,就会禅让给贤臣,而不会传位给不肖之子,但在大道既隐之后,却宁传不肖子,也不传贤大臣,于是,“亲亲为大”之仁与“尊贤为大”之义被混为一谈,门内之治及闸外之治的区别也因此而模糊。世及成为确定下来的制度,此时制礼,必须依此而制。在《孔子家语》本,此句作“大人世及以为常”,这就更清楚了,此处强调的,并不是圣人制定了“大人世及”之礼,而是这种制度成为常法。这句话与“城郭沟池以为固”并列,讲的都是掌权者对私天下的。
随后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是连在一起说的,郑注解为“俗狭啬”,即风俗变得自私而吝啬,人们更愿意照顾自己的亲人,而不肯照顾别人的亲人,照顾自己的子女,而不再照顾别人的子女,财货和力气都不愿意与别人分享。“货力为己”,《家语》本作“货则为己,力则为人”。杨朝明认为,《孔子家语》本文义更顺畅。其实,这是两个版本系统性的差异。因为在大同部分时,《礼记》本的“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家语》本就作“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为人”。对勘文本,更像是《家语》本修改《礼记》本所致。我们且不管两个版本的先后,但从义理上,两个版本讲的都是从无私变成了狭啬。
正是因为民风变得狭啬,人们不再能很自然地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还有可能做到孝亲慈子这些最基本的道德。孔疏:“君以天位为家,故四海各亲亲而子子也。”无论在上位的“大人”,还是在下位的百姓,都陷入了私心之中,这是两者之间的关联,却并不是指家庭制度的起源。张横渠说:“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亦不害于不独亲、不独子,止是各亲各子者恩差狭,至于顺达之后,则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50]此语颇中肯綮。“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并不是说将亲人视同路人,因而两个阶段的差别并不是有没有家庭,而是爱敬之情是否只局限于家庭之中。由于爱敬之情局限于自己的亲人,无法推展到家庭之外,所以对于家庭之外的人,就相互为敌,彼此防范。这并不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是家庭变得狭隘,私有制变得刻薄,国家的外在制度与暴力得到了强化。按照《礼运》的逻辑,这个时期的实质问题是,人心浇薄,文巧俗弊。执掌政权的大人们更要防范其他人群的伤害,所以有必要建立城郭,挖掘沟池。阴谋与战争,就必然会出现了。但这个地方的文本有些混乱。如果按照《礼记》本,“城郭沟池以为固”之后接的是“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好像是说因为建立城郭,随后制礼,又因为制礼而有了阴谋和战争,虽经郑注孔疏百般缘饰,逻辑还是很奇怪。所以任铭善怀疑此处有错简,试图将“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移到“货力为己”之后[51],这是一个解决方案,任先生应该是考虑到“大人世及以为礼”之“礼”即“礼义”之礼。而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礼”只是制度的意思,所以笔者以为,这10个字移到“礼义以为纪”之前,应该会更顺畅些。[52]而在《家语》本,从“礼义以为纪”到“而兵由此起”都是没有的,则更加清楚,当然也略显单薄,应该是《家语》的整理者已经感到此处有些混乱,所以删掉了这些内容,而不是像杨朝明认为的那样,这段话完全是后人所加。但不论哪种处理方式,这里都是在说两个情况,一个是大道既隐之后,民风狭啬浇薄,导致了争斗与战争的状况;另一个,就是通过制礼以改变这种状况。这里对历史的理解,与《论衡》中所引的那段很相似:因为民风变得浇薄了,所以人们已经不能自然而然地按照爱敬之情来做事,那就必须通过外在的礼制来约束甚至强迫。但《庄子》中的逻辑是:因为礼制的制订,才导致民风浇薄。这一段显然也不是道家的逻辑。
礼以时为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有特定的礼制,于是才有小康之世的出现。孔疏:“康,安也。行礼自卫,乃得不去执位,及不为众所殃,而比大道为劣。故曰小安也。”“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是“由此其选也”,前文还被称为“三代之英”。郑注:“英,俊选之尤者。”夏、商、周三代并非都是小康之世,只有这六位“俊选之尤者”在位之时,才算小康。如果这里确实有错简的话,则“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都是他们制礼作乐的情况。其中“以功为己”有些不可解,或为窜入之文。这一段与“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文义相连,应该都是六君子制礼作乐之迹。这些均为《孔子家语》本所无,所以《孔子家语》本对六君子的叙述过于简略,疑有脱漏,而不是《礼记》本为后人所补。(www.zuozong.com)
最后几句,两个版本差别也比较大,《礼记》本作“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郑注:“执,执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犹祸恶也。”孔疏:“若为君而不用上‘谨于礼’以下五事者,虽在富贵执位,而众人必以为祸恶,共以罪黜退之。”按照这种理解,此处说的仍然是六君子治国后的效果,因为“刑仁讲让,示民有常”,所以那些在位的“大人”,若有违礼之事,就会被加罪,众人也认为他是祸患。但《家语》本作“礼之所兴,与天地并,如有不由礼而在位者,则以为殃”。虽然有些字句相同,但含义差别很大,变成了对上述一段的概括总结,已经不再是对六君子功业的描述了。
之所以在后半段出现这么大的差别,不一定是因为《孔子家语》本更早更近真,而很可能是因为孔、戴二人共同面对的来源在这里就有些混乱,所以两个编辑者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删改整理,形成了非常不同的两种理解。孔安国删去的内容更多,虽然文本更精简,但显得意犹未尽,小戴保留的更多,也可能自己添加了一些字句,文字就更混乱一些,描述却也更详尽。但两个版本在这里的文字差别并未影响到整体结构,上述大道既隐的乱世里,因制礼作乐而成小康的逻辑,对于两者都是成立的。因而《礼记》本所概括的“小康”,放在这里并不显得突兀,即使不是原本所有的,也是一个恰当的概括。
由上所述,大同之世是礼制的最高境界,即不必制礼,而人人皆以礼行事,五帝之时被认为是这样,而在通常的历史进程中,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小康之世是三代圣王治下的状况,是现实历史中,通过制礼作乐约束教化人民,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形态,即船山所谓:“小康者,民不能康而上康之。”这就是《礼运》首章所描述的历史演进。其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对五帝、三代这两个历史时代的具体理解,而是对礼与人性、民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正如船山所说:“盖其术之不同,繇世之升降,而非帝王之有隆污也。”儒家和道家一样,也认为最自然的状况是最好的,但他们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很不一样,不认为《庄子》中描述的那种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的状态是最自然的,而是认为不需要强制、人们的爱亲敬长之情最充分地流露出来,才是最自然的状态。因而,《庄子》认为礼制的兴起是对自然人性的扼杀与戕害,《礼运》却认为礼制是对自然人性的维护、成全与回归。
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在《礼运》的后文中,为什么没有再谈大同之世,因为那只是一个理想状态的设定,而现实生活中礼制的作用,是要以小康之世为参照的。孔子说:“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这当然是针对小康之世说的,因为在大同之世,大道(就是天道)就行于人间,礼就在民情当中,不需要王者来治理,是在大道隐去、人情浇薄之后,才需要先王以礼为治民之器。
在下文,孔子又谈到了礼制起源的另外一个说法:“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在《孔子家语》中,这一段被编入《问礼》)这是对礼制起源一种更现实主义的描述,谈的是各种制度的起源,与《系辞传》《孟子》等书中对各种具体礼制起源的描述相互呼应。对礼制起源的这两种描述并行不悖。首章所谈,是在理论上,根据民风的演变和治道的变化,谈礼的本质与意义;此处所言,是就具体礼制和礼器,描述其逐渐演进的过程。两种起源都在强调礼与自然天道的关系,也都在谈礼在治道中的功能,以及圣王的制礼作乐。归根到底,礼制与礼器都是为了服务于礼义。我们只要读读《礼运》全篇就可以明白,此处就不赘述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