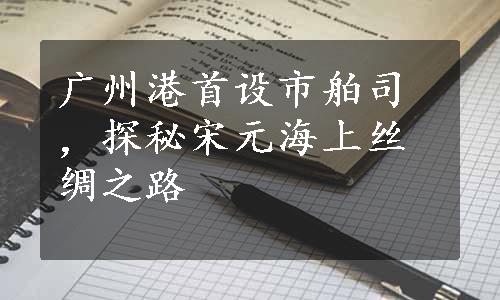
开宝四年(971年)二月,宋朝灭南汉取得广州统治权,时隔四个月,就在广州设置市舶司,经营管理这里的海外贸易。[1]以如此之快的速度设置市舶司,在宋代岭南制度建设进程中是相当领先的。此时,岭南大量州县的县令、录事参军、主簿、县尉等基层官员尚未安排就位。[2]从全国范围看也是如此。宋辽边界的互市管理机构直到太宗初年才设置。[3]从后来同属沿海地区,外贸也比较发达的两浙路和福建路设置市舶司的进程看,宋朝对广州的关注不寻常。广州外贸及其所带来的海外商品,显然受到宋朝的高度关注。
(一)优越的自然禀赋
广州拥有发展航海贸易的许多良好条件,各种条件结合在一起,使广州成为得天独厚的海外贸易港。
第一,广州港海外交通条件优越。帆船时代利用自然力航行,受海流、季候风等因素制约,港口之间的距离是个关键。中国古代外贸对象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中外航海贸易,以南部沿海地区为佳,港口距上述地区比较近。中国南部各海港中,广州与主要贸易对象不但距离比较近,而且海上交通便利。
古代中外海上交通史上,有个重要时间节点,就是吴晋南朝。过去东南亚及其以西国家地区远洋商船来华,大多沿海岸航行进入中国。所以船舶到达今天的越南南部以后,多沿中南半岛海岸东侧北行,到达越南北部后,沿海岸走势向东航行,经过北部湾、雷州半岛,最后抵达位于珠江三角洲北部的广州港。早期远洋船舶沿着大陆边缘海岸,迂回缓慢航行;海岸线附近多礁石险滩,颇为艰险。大约到了吴晋南朝时期,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远洋船舶开始做跨越南海的离岸航行。船舶到达今天的越南南部后,开始远离海岸,向广州方向航行,经过海南岛东部,进而抵达广州。船舶东来如此,西去亦然。至此,广州在中外航海交通上的地位更加稳固,更为优越,中外航海交通贸易也更为便捷畅快。
第二,中国南部各港中,广州港内陆交通条件比较好。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部顶点,东西北三江在此汇流入海。由于水网密织、四通八达,形成特别利于航运的条件。[4]横亘东西的南岭山脉,是岭南僻居中国南端的巨大屏障。但在绵延起伏的崇山峻岭之中,古人早就找到和开拓了多条沟通南北的道路。其中有三处相对便利,比较有名。一处是大庾岭,沟通今天的广东与江西。大庾岭这个地处北江和长江支流之间的分水关,在航海贸易的重要性日渐突出的唐代,翻山越岭的路段经过一再修整,过往条件已经得到很大改善。第二处是骑田岭,沟通今天的广东广西与湖南,山间也有需要徒步陆行的路段。第三处是越城岭,沟通今天的广西与湖南。越城岭较为平坦,早在秦朝已经修筑灵渠。广州经由这一线北上虽然道途迂远,但有全程水路无需陆行的便利。所以广州港国内交通虽然不算便利,但也不是太差,没有太大的困难。
古代广州大部分时间,进出口商品的消费和产地主要坐落在位于南岭以北的京师、江南等富裕发达地带,进出口商品的运输,主要依靠上述几条通道。
第三,这是一个较为安全的港口。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北部顶点,连接南海却不直面海洋。船舶进入珠江口后,要经过曲折绵长的河流才能抵达广州港,因此它在抵御风浪、防范海盗、保护船舶安全等方面有较大优势。海洋中常见的狂风恶浪,在进入广州港附近时,能量和破坏性已大为消减;在外洋劫掠船舶的海盗,到达广州港前,会遇到海防官兵的一再拦阻。因此,两千多年以来这里一直是相对安全的天然良港。
第四,广州港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土地松软、水源充沛、气候温暖,这是个鱼米之乡和资源丰富、宜人居住之地。广州的手工业也在很早以前就已发展起来,海外贸易需要的船舶建造和维修能在此地解决。广州港很早就能提供大量人口衣食住行的需要。
上述保障广州外贸长期繁荣的条件,在秦汉时代已经大体具备,吴晋南朝时期更上一层楼。因此,广州作为中国海外贸易第一大港的地位并不始于宋代,不始于唐宋,而是始于秦汉时代。
(二)历史悠久的外贸大港
优越的自然禀赋使广州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的海外贸易大港,历时两千多年。自秦汉时代开始,广州就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大港。[5]隋唐时期,广州港超越当时还在中国版图里的越南北部港口,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港口。随着中外陆路交通地位为航海交通所取代,广州成为中国与海外各国交通贸易的重心所在。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南汉国定都番禺、统治岭南,广州外贸更为繁茂,为北宋外贸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代十国时期,香药在全国各地大行其道。南汉国是海外香药的聚集之地,数量最大。小王国对大王国的供奉,常包含各种类型的香药。贡献香药最多的小王国是南汉国,以及闽国、吴越国、南唐国等。南汉国的香药,主要来自与海外国家的贸易;闽国香药直接来自海外国家的比重也大,但不排除其中有些是从广州转口的可能性。我们通过对现存资料的综合分析认为,吴越、南唐等国的海外香药主要是从南汉国转口而来。
首先,南汉国在唐末五代时期社会较为安定,社会稳定发展,外贸未受改朝换代、两军对抗争夺政权的打击。唐朝末年,各地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岭南刘谦因邀击黄巢有功,被唐朝任命为封州刺史。刘谦死后,儿子刘隐于昭宗乾宁三年(896年),出兵袭肇庆、广州,成为两广地区最大的割据势力,被封为静海、清海节度使。刘隐重用岭南士人,为后来独立建国、治理岭南,打下了基础。乾化元年(911年),刘隐被后梁封南海王,不久病逝于广州。几年后,其同父异母兄弟刘称帝,国号汉,史称为南汉国。
僻处唐帝国南疆的岭南地区,此时相对安定。“唐末南海最后乱。僖宗以后,大臣出镇者天下皆乱无所之,惟除南海而已。”[6]于是中原士人官员大批来到岭南,“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辟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王定保、倪曙、刘浚、李衡、周杰、杨洞潜、赵光裔等人都受到刘䶮的重用,被辟置幕府,待以宾客,委以重任。王定保是容管巡官曙唐太学博士浚崇望之子。倪曙为唐太学博士。刘浚,刘崇望之子。李衡,李德裕之孙唐右补阙,因奉命出使而到达岭南。杨洞潜早先是邕管巡官,任满客居南海。刘隐曾师事杨洞潜,后任命他为节度副使。[7]中原士人南来,对南汉国社会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第二,南汉国定都在广州这个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港,海外商品充盈其间且为致富之源。南汉统治者大肆挥霍海外珍宝。开国之君刘䶮“好奢侈”,把聚拢而来的海外珍宝做成“玉堂珠殿”;[8]又“悉聚南海珍宝翠羽,以餙宫室。建殿阁秀华诸宫,务极瑰丽”。到了晚年,他“作南熏殿,柱皆通透刻镂础石,各置炉燃香,有气无形”[9];召集南来商贾参观他的宫殿,炫耀珠玉,夸示富有。[10]南汉国丰富的东南亚产品来路不一,海外贸易、海外国家贡献、海上抢掠皆有。
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小王朝多向中原王朝称臣献贡,贡品中包含不少香药等海外产品。他们自知国力不强,不敌中原王朝,希望通过称臣纳贡维持互不侵扰、相安无事的国家关系。后梁时,乾化元年(911年),已经实际掌控岭南的刘隐去世,传位给胞弟刘䶮。次年,刘䶮向后梁进贡海外产品,数额不菲,“遣使贡金银、犀角、象牙、杂宝货、名香等于梁,价凡数十万”。[11]其他南方王朝也向后梁称臣纳贡。例如,越南北部的安南,当时还在中国境内。安南两使留后曲美进献筒中蕉五百匹,龙脑、郁金各五瓶等,以及金器,银器,一些奇巧珍贵的纺织品等。广州贡献的海外产品特别多,超过了也是东南亚外贸船舶惯常的出入之地安南。福建小王朝进献的是用葛纤维作原料制成的布:“福建进户部所支榷课葛三万五千匹。”[12]福建也有外贸船舶出入,但贡献中原王朝的不是典型的海外产品,原因何在,有待研究。
第三,吴越、南唐等国的东南亚产品主要来自南汉国。
东部地区的小王朝吴越、南唐等国也向中原王朝进献香药等东南亚产品。限于当时的航海技术,两国跟东南亚国家交通不便,直接交往不多,东南亚产品从中国南部沿海转口而来,比较便捷。外贸发达的南汉国就有大量海外产品可供转口贸易。
在吴越国,钱氏统治七十余年,“多掠得岭南商贾宝货,当五代时常贡奉中国不绝”。[13]岭南商贾的宝货,应该包括来自东南亚等国的商品。吴越国供奉给中原王朝的海外珍宝数量可观,仅仅依靠抢掠应该不够。当时经营广州和中国沿海各地转口贸易的商人应该不在少数。
南唐国也有类似情况。史书记载:在南唐国,“南海常贡奇物,有蔷薇水、龙脑浆,上实宝之,以龙脑调酒服,香气连日,亦以赐近臣”。[14]广州曾是南海郡的治所,人们往往将“南海”作为广州的同义词。五代十国时期,小王朝自知兵力不强,希望与力量稍强的国家保持良好的国家关系,经常向其朝贡称臣。南汉国的贡品主要是海外商品。贡道相通,商道自然也相通。南唐国与南汉国之间存在商业贸易,当无可疑义。
前面谈过,当时的安南和福建也都有远洋商船到岸。但是,广州是中国最有吸引力的海外贸易港,海外交通便捷,聚拢而来的远洋商船多,海外产品也多。其次,两处与中国的内陆交通都不如广州方便。在当时,内陆运输最好能利用江河。广州与内地的联系,有珠江、长江和湘江可以利用,最常用的交通线从南而北依次为:水路北上,经由北江到大庾岭脚下;翻过大庾岭进入长江支流,继续循水路北上或西向东去。但安南、福建港口与吴越、南唐之间,没有如此便利的江河可资利用。受港口条件和内地交通条件制约,安南和闽国的海外贸易不能与南汉国相比。
在宋军兵临城下之际,广州城内的官员就认为宋朝对海外珍宝兴趣很大。宋军攻入广州的前一天,南汉主的几位宠臣说:“北军之来,利吾国中珍宝尔。今尽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驻,当自还也。”于是他们“纵火焚府库、宫殿,一夕皆尽”。[15]南汉臣僚的讲法和做法,显示出他们的无知和苟安侥幸心态。海外珍奇对任何统治者都具有诱惑力,占据岭南这方宝地,汇聚其间的中外商品便是统治者的囊中之物。宋朝不仅有雄心也有实力占领这里。但无论如何,聚集广州的海外珍宝令宋朝统治者垂涎,南汉君臣以及其他当代人都看得分明。(www.zuozong.com)
南汉国的经济贸易状况,史籍直接记载不多,但种种迹象显示出南越国外贸繁荣,国家富盛。五代十国时期各国珍爱的产自东南亚、南亚、西亚的香药宝货,多数经南汉国而来。
(三)市舶管理制度最早建立的地方
开宝四年(971年)宋朝在广州设置了第一个市舶司,开启了中国古代市舶贸易的新时代。这个时代是唐朝创立的市舶使和市舶贸易制度的延伸。
在唐中期以前,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使已在广州出现。唐代有市舶使,始见于安南和广州。开元二年(714年)为市舶使最早见于史籍的年份。这年,岭南市舶司周庆立和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进献朝廷。[16]周庆立出任市舶使的地点在安南。开元十年(722年),韦姓宦官在广州出任市舶使。从这时起,见诸史籍明确记载的市舶使共有六位,都在广州。[17]周庆立在安南,韦姓宦官在广州任市舶使,都未必是首任,因此市舶使的设置,在安南可能早于开元二年,在广州可能早于开元十年。
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分布着无数港口。在唐代,现今中国境内的港口除了广州,还有扬州和泉州,但中央王朝只在广州设置市舶使。这是为什么?简单地说,这与朝廷希望该机构达到的目的有关。市舶机构是为中央管理外贸,特别是集中外贸利权服务的,所以设在外贸最发达的港口,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控制外贸和获取收益的效率。
派宦官出任市舶使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宦官是皇帝的私人代表,由他们出任市舶使,皇帝可以直接掌控外贸及其收益。唐朝出现的市舶贸易制度,使长期由地方官掌管的外贸直接控制权发生了向朝廷方面转移的明显趋势。唐中期以后,宦官出任市舶使的事例有所增加,有学者认为成了“惯例”。[18]宦官市舶使的权势很大,有时还凌驾于节度使之上。[19]
唐代海外贸易制度的变化被宋朝接过来,并充分利用。宋军攻取广州之后,市舶司很快成为中央政府掌握海外珍奇、控制外贸利权得心应手的工具。
北宋初年,面对海外珍奇持续和大量地涌入,赵匡胤及其臣僚加强中央直接控制的愿望陡然升温,并且针对广州的外贸优势和制度资源,制定了相关的政策法规。
(四)宋朝快速设置广州市舶司的用意
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宋朝设置市舶司是让其掌管从海路进口中国的东南亚及其以西国家的商品,“市舶司掌市舶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20]“市舶”二字一般指物体,即船舶,主要是大型海船。在这里还指行为,即贸易,市舶司是管理海路贸易的机构。南蕃是当时常用的方位和地理概念,专指中国国界以南的国家和地区,即东南亚、南亚和西亚。因此我们知道,宋朝最初设置市舶司的目的,主要只是让市舶司在中国对东南亚及其以西国家贸易中发挥作用,东亚国家尚不在考虑之列。这是宋朝攻取广州初期所制定的政策。
《宋史》说: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21]市舶司掌外国商品和海舶的征榷、贸易。当时还没有开征船舶税,所以“蕃货海舶”的位置应该对调,改为“海舶蕃货”。这里提到了征榷,即征税和专卖,补充了上一个定义的缺漏。但“以来远人,通远物”基本上是虚话。招徕远人与“征榷”之间存在冲突关系,不是市舶司的主要职责。
其实,宋初朝廷设置市舶司的目的,不止于贸易和征榷进口商货。宋太祖在打下岭南以后,迅速在广州设置市舶司的动因,目前未见到明确的记载。此时朝廷已经设置内库,名为“封桩库”,储存财物以备收复西北之用。中央财政已经开始对内库有所依赖。[22]因此,宋太祖有意为该库填充财宝。进口商品物轻价重,储藏价值高。广州这个全国最大的港口设置市舶司后,聚集在当地的海外珍奇便首先通过市舶司,接着经由官办运输系统,送达朝廷。为朝廷积聚财富是宋初朝廷在广州设置市舶司更为深层的目的。
综上所述,宋朝快速设置广州市舶司的最初目的,是通过广州市舶司将当时中国最大的外贸港口广州港和最主要的贸易对象东南亚及其以西国家的对华贸易迅速控制起来,并向京师源源不断地输送市舶司通过征税和专卖等途径获得的外贸收益。
(五)宋代广南东路的市舶机构存在情况
广州市舶机构始于开宝四年(971年)六月,到德祐元年(1275年)五月,“罢市舶分司,令通判任舶事”为止,存在时间长达三百余年。这期间,广州市舶机构遇到过一两次险情,但都安然度过。
神宗熙宁年间曾经有过撤销广州市舶司的动议,但有惊无险。广州市舶司一直健在并运作良好。
南宋高宗建炎年间,市舶机构存废状况史书记载不一,广州市舶机构是否曾被裁撤,是个问题。笔者通过研究,认为建炎间广南市舶司并未被裁撤。
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建炎以来朝野来记》中,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都认为广南市舶司曾同浙闽市舶司一道被裁撤,直至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才恢复,恢复时间晚于浙闽市舶司。而《宋会要稿·职官》与熊克《中兴小纪》提到建炎元年(1127年)浙闽市舶司并归转运司,却都没有提及广南。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则明确指出“建炎诏两浙、福建市舶归转运司,而广南如故”。笔者认为李心传与马端临的记载有误。南宋初期,设在广州港的市舶司从未被撤废。
李心传认为广南市舶司自建炎元年被撤废。但事实上,广南市舶司从一开始就不属于撤并对象。建炎间精省机构的动议是宰相李纲提出的。他提出了若干应该省并的机构,但把广南市舶司明确排除在外,“提举香盐茶矾司并归提举常平司,提举市舶除广南外,余路并归转运司”[23]。那就是说,南宋初在关闭浙闽市舶司时,广南市舶司依然存在。
李心传认为广南市舶司到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才恢复。但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广南东路存在市舶司:“建炎二年七月八日,诏两浙路提举市舶司以降指挥减省冗费,每遇海商住舶,依旧例支送酒食,罢每年燕犒。其上供细色物货,并遵旧制,团纲起发,罢步担雇人。广南、福建路市舶司准此。”[24]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二十六日,尚书省根据广南路提举市舶司的奏状,说“广州市舶库逐日收支宝货钱物浩瀚”。[25]对照李心传的记载,这是广南东路的市舶司刚刚恢复的年月。广州外贸如此繁荣,撤销市舶司的意义何在?宋朝废罢市舶司的动机一般是外贸不景气,没必要继续让市舶司消耗官帑。广南东路市舶司看来一直在运作,不曾中断。
三百余年间,广州市舶机构经历风雨,几次险些被撤并,后来都化险为夷,这不但在宋代是个奇迹,在整个市舶司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