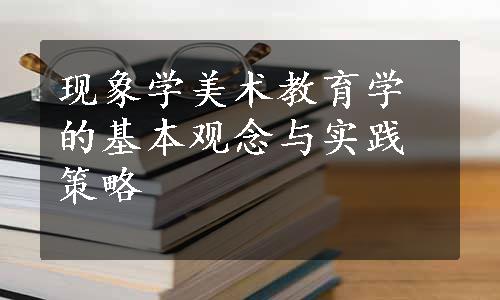
(一)现象
“现象”是现象学的关键词,因此理解现象学的关键在于解读“现象”这一概念。在当下汉语一般语义中,“现象”和“本质”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但现象学语文中的“现象”并不是这样。现象学的特点在于企图消除元对立,有关现象的现象学理解构成了现象学的基础,也是现象学美术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在启蒙运动之前,“现象”首先是一个神学词汇。“现象”一词同时有“显现”的意思,主要是指“奇迹”,是上帝的“显示”。因为“现象”总是神给人的启示,所以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就非常的重要。换句话说,“现象”的背后有更重要的东西,我们必须正确理解神的启示。在这里,“现象”是通向神的启示的重要途径,需要信仰的力量作为支撑。
启蒙运动中受到最大影响的是英国的经验主义学派,即洛克、休谟等。他们不认为信仰可以正确解释现象,同时,他们也不认为人类的理性可以正确解释任何东西。休谟对人类的理性——不管它是否有神的帮助,提出了最根本、最彻底的怀疑。在他们的影响下,传统的形而上学陷入了最深刻的危机。
为了拯救形而上学,德国哲学家康德写了著名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康德指出:对我们人类的理性来说,世界无非就是现象世界。我们的理性具有接受、整理、总结、塑造现象世界的能力。而世界只能通过现象让我们接受、理解,而事物本身,是人类理性不能探及的。在康德哲学中,“现象”和“物自体”是对分的,这种理解的方式对当下的“现象”语义的理解影响很大。在一般理解的汉语语义中,现象有接近“表象”的意思,即事物的外在显现。显然,这种语义暗含了某种形而上学的意思,即事物还存在本质部分的显现。人与世界成了二元世界,事物成了“现象”与“本质”的二分。
但是,现象学的奠基人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显然并不同意这样的设定。他认为“现象”不是事物对人类理性的作用,而是“现象就是事物本身”,“在现象与本质之间不存在一层帷幕”,“现象既是显现场所,又是显现过程,还是显现对象,它们都是在意识中发生的”,从而“意识的活动与事物的显现不再处于主客观两极”。胡塞尔赋予“现象”的特殊含义,是指意识界种种经验类的“本质”,而且这种本质现象是前逻辑的和前因果性的,它是现象学还原法的结果。现象学不是一套内容固定的学说,而是一种通过“直观”描述“事物本身”的研究方法。它所说的现象既不是客观事物的表象,亦非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而是一种不同于任何心理经验的“纯粹意识内的存在”。胡塞尔一生所关心的都是“精神”和“意识”,而现象正是他在研究精神、意识时真正且唯一的对象。此时,现象这个概念被赋予了完全不同于中世纪、不同于启蒙运动、不同于康德的意义,构成了对形而上学与经验科学的同时超越。
它既不能简单地认为没有本质,也不能认为没有表象,而是说“本质”和“表象”是“一起的”,一起构成了“事物本身”。纯粹的本质研究属于形而上学范畴,是无法证实的,其“错误在于在现象之外设定了一个不可直接显现的、自在的领域,但这一领域的存在与性质却要依靠主观思维来设定和推断论证,因而被赋予哲学家们的意图,带有主观随意性”。相反,纯粹的表象研究属于经验科学。“经验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现象的一个方面,因此对现象采取了为我所需的实用态度。它按照一定的标准,根据一定的需要,对现象进行割裂……前提的随意性决定了经验科学不可能达到严格的明证性……只能研究事物的某一方面、某一性质。”现象学在反对形而上学与经验科学之间开辟出了新的道路,为哲学捍卫了研究领地,以事物本身或者现象为研究对象,抛弃一切前提,达到明证性。现象学的诞生构成了哲学的一个转折点。
这种“现象”的现象学观念对于美术及其教育研究而言,无论是对认识论还是方法论,都产生了重大的意义。它让我们回到美术教育现象的现场、回到事物本身,以体验与感悟的姿态生活。现象学以智慧拓宽了我们的美术教育视野与思路,引领我们走向一条超越的道路。
(二)主体间性
与“现象”理解直接相关的是“主体间性”,这也是现象学关键性的观念之一。现象理论与主体间性理论其实是一体的。现象指的是“事物本身”,“主体间性”则构成了“事物本身”的存在方式。
“主体间性”,又称为“交互主体性”,是胡塞尔晚年提出的一个理论。它指的是一种主体之间的互识、共识活动和共存、交往的状态。与传统主客二分的理论不同,主体间性将核心关怀移向主体与主体之间,移向双方之间的相互认知与共存关系上,认为主体之间是交感相遇、相互依存或者水乳交融的关系,彼此互为表里、双向开放。主体间性理论的应用极为广泛。
首先,在哲学上,人与世界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存在。这种认识会影响到人们的世界观与人生观,这和东方哲学结论近似。出于对主体间性的认识,世界不再是人类所认识的对象、征服的对象,而是和人类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这使现象学具有了某种生态哲学的意味。事物本身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存在、一种完整的存在。事物不仅存在斗争性,同时还存在和谐性。星际之间不仅有相互的斥力,还存在万有引力。对于人类的文明史而言,也是这样。如果只讲斗争性,那么人类将降低为野兽的层级。这显然不是人文主义的认识。我们在看到人类矛盾斗争的同时,更应该看到人类的合作与相互理解。正是人类的爱与相互之间的协作,才创造出了人类文明。人类文明的进步主要得益于人类之间的互相学习、文明交换,而不是发起毁灭性的战争。文化融合才是推动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对于人类而言,正是因为还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仇恨,才更需要弘扬爱与和解,这样才能彰显出人的伟大性。这种认识也是人文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可见,现象学的确是一种人文主义。主体间性理论大大地超越了人为划定的主客体界限,以主体之间相互投射与相互对话的关联性消解了主客对立模式中主体的绝对霸权,成就了对主体论的修正和超越。
其次,在美学上,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也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法国哲学家、美学家米·杜夫海纳认为审美过程是主客体共融的过程。“脱离了审美知觉,审美对象就成了一般物;脱离了审美对象,审美主体也就不再是审美主体。”“对于任何一个意识而言它都包含着意向行为和意向对象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正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是不可分离的。”胡塞尔将其称之为“主体间性”的关系。审美的发生需要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的“沟通”。所谓“沟通”,指的是“内在地与世界、身体和他人建立联系,和它们在一起,而不是在它们的旁边”,即建起了巴赫金所说的“沟通的世界”。二者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具有“共在性”的。
再次,在艺术学上,艺术创造也是创造者和世界以及自我的主体间性对话的活动。艺术创造是审美的创造。在创造的过程中,艺术家将“美的规律”、感悟以及艺术理解渗透到艺术作品之中,最后以某种形式的艺术符号凝定下来。苏珊·朗格指出:“艺术是一种有组织的象征,把艺术家对其感觉的认识呈现给我们的知觉。”在艺术创作的过程里,“对话”比单纯的写生显得更为丰富。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时而奋笔挥毫,时而陷入沉思,时而切换观察的角度,时而琢磨塑造的程式。艺术创作需要和艺术形式、生活、美、自我乃至世界“对话”。艺术家将包括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诸多关系的视界投注在艺术作品的创作之中。艺术是世界与人的同在、生命与世界的同构。这是一种高度投入的体验状态。艺术创造体验的过程是审美主体受到激发的过程,是审美经验的唤醒、流动和重组的过程。因为这种情感性的共鸣使审美过程更加深入、更加聚精会神,以至于产生了意味无穷却难以言传的精神战栗。所以,一般认为欣赏体验更接近审美体验的原发性,但创作体验具有表达性,比有意无意地欣赏体验要深切与丰富得多。梅洛·庞蒂针对这种丰富的体验在《知觉现象学》中这样描述道:现象学和艺术创作非常近似,和普鲁斯特、瓦莱里、巴尔扎克或者塞尚等创作的时候一样,都需要辛勤的耕耘:靠着同样的惊讶和同样的关注,靠着同样的思想。艺术创作正是在这样的“对话”中发生与进行的。主体间性对于艺术创作的意义就在于:“使人较充分地发挥其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作用,从而进入一种具有高度统一的意象性世界中。”这种关系正如梅洛·庞蒂的描述:“我不是按照空间的外部形状来看空间的,我在它里面经验到它,我被包围在空间中。总之,世界环绕着我,而不是面对着我。”这无疑告诉我们:我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应该时刻体会到世界与我同在,体会生命的气息,以体验的状态追求本真的生存、唤起生活的意义。
最后,艺术教育其实也存在主体间性的关系。艺术教师与学生在课堂上是双主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主体间性。这就解决了长期以来关于课程主体的争论。其实,问题很简单,教学是“教”与“学”的合成。没有教师的教学,只能成为“自学”;同样,没有学生的教学,只能是教师上课的自我演练。显然,在教学中,学生与教师同样重要:既要发挥教师的主体性作用,也要根据学生的需要制定课程。以前,要么只强调教师的主体作用,成了纯粹的“唯识论”,难免会出现“填鸭式”的教学;要么只强调学生的主体作用,使教师成为被忽略的对象,教师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无法发挥。(www.zuozong.com)
(三)意向性
意向性是一个与“现象”有关的现象学概念。胡塞尔不仅认为现象是事物本身,同时他还认为现象的显现是在意识之中发生的。在胡塞尔看来,“意识,不是精神实体或主观的活动,而是一个揭示真理的过程”。所以,现象学研究既是现象研究,也是意识研究。
意向性是意识活动与意识对象之间必然的、结构性关系的概念。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中世纪哲学典籍之中。后来,德国哲学家布伦塔诺使用这一概念来说明心理学研究对象和物理学研究对象的区别。布伦塔诺认为心理对象的特征是被心灵所意向,它们不必像物理对象那样,不依赖心灵而存在。但胡塞尔则认为“意向性”可以建立包括物理和心理的、外在和内在的对象在内的一切现象。胡塞尔通过对意向活动的分析来确定意识对象,即通过意识的显现过程来说明现象。意向性分析法成了现象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关于意识活动,胡塞尔做了两个重要的区分。第一,任何意识活动都有“性质”与“材料”两个方面。性质是区别活动种类的内在规定性,材料是活动所具有的确定内容。意识活动的性质与材料有着对应的关系,有什么样的活动,就有什么样的意识材料或内容。第二,在意向的结构中,任何意识活动都有“理想的”和“实在的”区别。
胡塞尔建立了一套崭新的知识论。他通过对意向活动的分析,得出结论:真理在于意识与事物的统一,通过意识的意向性结构而获得了统一。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通论》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因为一切体验在某种方式上均参与它……意向性是在严格意义上说明意识特性的东西,而且同时也有理由把整个体验流称作意识流和一个意识统一体。”这是意义、知觉、判断与本质直观的统一。“世界和人生是一回事。”
现象学还原与构造对于美术教育理论基础而言,有着特别的意义。如果要阐发某种美术教育的创见,首先肯定会涉及对美术教育概念的理解。但对于一些基本的概念,比如艺术、美术、教育等观念,又存在着巨大的解释分歧。而我们可以将现象学还原作为工具,将美术教育观念的阐释导入更深层次。以原初的状况,结合人类文化学的方法,来考察我们的美术教育生活,往往会得出很多富有建设意味的观念。所以,在观念解析方面,本书会大量地运用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在现实的美术教育研究过程中,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有前提的事实”。如果没有经过“确定的、无前提的提炼过程”,研究成果往往会比较局限,从而容易产生偏见。现象学还原与构造在现象学美术教育学研究中被广泛地采用着。“回到事物本身——还原构造”是现象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四)生活世界
为了追求“无前提的”哲学标准,胡塞尔于76岁时提出了著名的“生活世界”概念。在现象学还原的研究过程中,胡塞尔的研究逐渐从“纯粹自我”转向了“生活世界”。因为要真正做到无前提,需要悬置的不仅仅是自然态度所认可的客观存在,而且应该包括在历史中形成的理论、概念。在这里,胡塞尔用到了“前科学”这一词汇。他提出回到一个前科学时期,不受任何理论、传统、习惯的影响,直接面对“生活经验”。这样,我们最终会达到一个“生活世界”。这是一个不能再被还原的最后“剩余”,是不可超越的前提。
“生活世界”,在胡塞尔看来,它是直观的、前科学的,是可经验的人的存在领域,是一个有人参与其中,并不断呈现出自身意义与价值的世界。他认为:“生活世界是永远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人们确定它的存在,并不因为某种意图、某个主题,也并不因为某种普遍的目标。一切目标以它为前提,即使那在科学的真理中被认知的普遍目标也以它为前提。
“生活世界”哲学在当下的新课程改革中受到了重视。在钟启泉先生的著作《课程的逻辑》中,他提出课程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构建生活世界的课程。钟启泉认为:“教育是发生在师生之间的真实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活动,生活世界是教育发生的场所,学生的体验和经验构成了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显然,在我们当下的课程中,尤其是小学的语文、数学等课程,基本仍属于“科学世界”的课程,它们严重脱离了儿童的生活经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儿童学习的兴趣,影响了其学习效果。在美术教学中,这一现象虽然不及“主干课程”严重,但这种影响也是广泛存在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美术课程其实也没能和儿童的生活及儿童的需要做到高度的结合,课程过程更是如此。
(五)存在论
胡塞尔曾经说过:“现象学就是海德格尔与我。”海德格尔曾被胡塞尔视为最合适的接班人。海德格尔的哲学常常被归进“存在主义”。但海德格尔本人则始终认为现象学的方法是唯一的科学的哲学方法,他甚至不承认自己的学说是“存在主义”。
“存在物”与“存在”的区分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知识、学习、儿童、教育、生活、人等都是存在的过程、生成的过程和成长的过程。它们的意义居于过程之中,而不在于过程之外。美术教育过于关注艺术品的成品教育成果、学生成长的结果等,就扭曲了有过程才有结果的事实。并且过于关注结果而忽视过程的意义本身就不符合存在是to be的性质,属于一种人类异化的表现。人类具有理性,拥有分割、区分、分类的能力,这是我们做科学研究所必需的,人类也因此获得了许多的科学成果。这种思维可以运用于生活、运用于教育,也可以运用于意识分析。但如果我们以为事实的存在就如同我们分类分析中撕裂式的存在,那就大错特错了。只划分,而不统整;只求结果,而不管过程;只重视智性,而忽视整体;重理论体系,而不重感受。这样,我们的生存就异化成了碎片,失去了感受、关系和自我,也就失去了教育的意义感,乃至失去了生活的意义感。美育不同于德育、智育及体育,它是情感的教育,其教育的方式是陶养。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说:“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作美育……人是感情的动物。感情要好好涵养之,使活泼而得生趣。”美术教育唤醒的正是我们人性的情感,“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可见艺术本来是集人的整体感受性、意义性和审美性于一体的教育,艺术本来是唤醒人格、对抗异化最好的教育。在人的生存异化普遍存在的情况下,美术教育有义务与责任恢复美术原初的生动感受性。在这种特定的情境下,矫枉过正也是必要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排除科技理性的干扰,将美术学科建设成为一种感受型的新教育、一种直观意义感的新教育。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