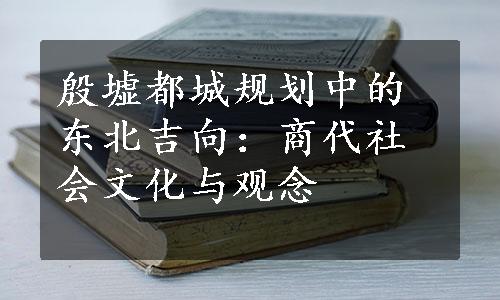
在殷墟都城规划建设过程中,重东北方位的观念表现得最为典型。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进行总结。
(一)殷墟最早遗址在其东北部
按照安阳站考古学家们的分期法,殷墟文化分为一、二、三、四期。第一期早段即是早于武丁时代的盘庚、小辛、小乙时期。而在殷墟范围内发现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极少。30年代考古组在小屯村北发掘的四座贵族墓M232、M333、M388、M331,规模较大,出土青铜器丰富而形制比较特殊[90]。四墓年代有早有晚,但学术界一致认为皆早于大司空村一期而接近二里冈上层的铜礼器形制,应属于殷墟文化一期早段[91]。1964年,安阳市博物馆在殷墟遗址东北方向的三家庄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所出铜礼器与小屯M388等墓出土同类器相似[92]。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为配合基建曾在三家庄一带作过小规模的钻探发掘,清理出8座年代早于殷墟大司空一期的商代墓葬,发掘一批遗址,所出陶、铜器形制属殷墟文化最早期的风格,铜礼器十分接近M388、M331的铜器形制[93]。我们认为,这些为数不多的早期遗迹,当是早于武丁时代的盘庚、小辛、小乙时期的都城文化遗存。推测盘庚初迁殷都时即此地,也就是说殷墟都城的开发建设之始即在于此。此后殷墟都城的发展是向西南方向逐渐扩展的。果然,在1997、1998年的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中,在位于原三家庄遗址附近的花园庄也发现了一处早于大司空一期的殷墟早期大型遗址,面积达150万平方米,村东还发现了一处大型的夯土台基遗址,当是早期都城宫殿建筑的遗留[94]。这为殷墟遗址长期以来没有一期宫殿基址而受到怀疑者否定的局面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队队长唐际根认为,花园庄遗址可能就是盘庚迁殷后的最早遗址[95]。殷墟都城正是从东北角建起,后来逐渐向西南方向的环水南岸小屯一带扩建,东北早而西南晚。这一城建形制当也与商族起源于东北方向的渤海湾地区及其重东北方位的观念有关。
(二)殷墟宫城位于都城东北部
殷墟都城之宫城在小屯村及村北部,也正位于整个都城范围的东北部,宫殿宗庙区也位于宫城(也即内城、王城)的东北部位。宫城是由洹水和濠沟围绕的0.5平方公里范围,抗战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此发掘的五十多座宫殿建筑基址,其北、东两边靠近洹河,正在整个王城的东北角。把宫殿宗庙建筑规划在这个地方,固有其据河守险之意,但此种格局与郑州商城、盘龙城惊人的相似,不能说不是一种传统的观念在起作用。
(三)小屯宫殿区布局以东北为先
3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殷墟都城王城中宫殿区发掘的53座基址,考古学家石璋如先生将其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为寝殿建筑,在最东北部;乙组为宫殿宗庙建筑,在甲组的西南部;丙组为祭坛建筑,又在乙组的西南部。三组的时代也是甲组居早,始建于武丁时期,一直使用到殷末;乙组次之,早到祖甲时建筑,而至文丁及帝乙时改造完成;丙组最晚,建于帝乙帝辛早年[96]。据陈志达先生的研究,也是甲组时代最早,乙组次之,丙组最晚[97]。但郑振香女士根据后来的殷墟发掘,给合对殷墟文化分期研究的结果,认为“这三组基址大概是互有关联,但性质有所不同的建筑群,可能是共存关系,各组基址内部有相对早晚”[98]。这当是近于事实的看法。也就是说,这三组基址是同时经过长时期的修建而形成的,都有早期和晚期的遗存。邹衡先生进一步说:“甲组基址的年代是比较早的。小屯遗址中既然有一批殷墟文化第一期的灰坑和铜器墓,甲组基址中也可能有属于殷墟文化第一期者。”[99]1987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为配合殷墟博物苑的建设,对时代较早的甲组基址进行了重新发掘,在甲四基址东边发现了一座灰坑,坑中“所出的陶器明显早于大司空一期”,即殷墟文化一期偏早阶段。在甲十二基址的上层回填土中所出陶片也与一号灰坑相近,亦属殷墟一期偏早。发掘报告指出,甲四、甲六、甲十二、甲十三修建年代比较接近,而甲十一则早于甲十二[100]。由此可见,甲组基址中属于一期偏早阶段的基址就不下5座。椐杨宝成先生推测,乙组和丙组基址中,也应有相当于此一时期的基址[101]。我们认为,这些属于一期偏早阶段的基址,很可能就是建于盘庚迁殷之后的殷都最早的宗庙宫殿建筑。这就是说,这里作为宫城的宫殿区进行规划时,第一批建筑即建在这个区域的东北部,以后的建筑均以此为准,在其西南方向分布。
图一百〇七 殷墟宫殿区建筑基址平面示意图
(四)宫殿区乙组基址朝向均坐北偏东
乙组基址应是王城之中最重要的、最庞大的建筑群基址,是商王朝宗庙建筑所在。而这群建筑基址中,不管是呈东西向(横向)的主建筑,还是呈南北向(纵向)的辅助建筑,走向都呈一定的倾斜形状,坐东北面向西南,与正南正北方向成一较小的夹角,尤其是乙三、乙四基址以南的大型宗庙建筑,夹角逐渐加大。从乙组基址本身来说是朝向西南的,可我们知道,乙组基址的性质是宗庙,摆放商王先君神主灵位之所。商人(王)入庙祈祷求告时,以人之面向而言,则是朝向东北的。如此安排,就会使得商代时人祭拜祖先时,不仅可以以东北方向面对祖先的灵位,而且也正可以面对东北方向祖先曾经发迹的那块神圣的故土,正得其宜也。不仅乙组如此,甲组、丙组基址群也都呈同一方向的倾斜,而以丙组的朝向偏颇为甚。
(五)乙组基址前祭祀坑位置面向东北
在乙七基址南,发现了南北两组祭祀坑。北组有车马坑5座,在其东、西、南三边共有42座祭祀坑。南组有79座祭祀坑。当然乙七基址也是宗庙建筑,这些祭祀坑是在不止一次的祭祀中埋入的。乙七宗庙基址在祭祀坑的北偏东处。据考古学家推测,乙七基址东部还有十多米被压在乙八基址下。若确如此,则这些祭祀坑就正好在基址的西南方。
(六)殷墟西北冈大墓墓向均为北偏东
墓葬方向一般是指墓葬中死者的头向,受到一定的信仰、观念的影响。一般而言,同一人群墓葬的墓向应该是大体一致的,同时有可能会受到墓地环境、死亡原因甚至性别的影响,甚至同一墓地墓葬的方向在不同阶段也会有所改变[102]。
殷墟遗址自科学发掘以来,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商代晚期墓葬。墓葬都是有方向的,殷墟墓葬墓向较为杂乱,东西南北方位都有,但以墓向朝北的墓葬居多。如以墓葬较为集中的殷墟西区墓地为例,1969年至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这里共发掘了938座中小型墓葬,其中朝向东的墓104座,朝向南的墓328座,朝向西的墓107座,而朝向北的墓达399座[103]。又如,195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大司空村墓地发掘的183座墓葬中,朝向东的墓23座,朝向西的墓40座,朝向南的墓29座,而朝向北的墓达86座[104]。两座墓地所发现的墓葬都是北向的居多。这只是一般的长方竖穴小墓的情况,而那些带墓道的大墓则与此完全不同。据杨锡璋先生的统计:“自殷墟发掘以来,据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资料,共发现了带墓道的大墓三十二座,其中,四条墓道的大墓八座,全集中在西北冈;两条墓道的大墓八座——西北冈三座,后冈四座,大司空村一座;一条墓道的大墓十六座——西北冈两座,大司空村三座,后冈一座,殷墟西区十座。除大司空村有两座一条墓道的墓其墓道是在墓室北侧外,其余全在南侧。即有三十座是北向的。但是,这些墓并不是正北向的,而是北偏东。因此,可以说,殷代王室和高级贵族的墓的方向,绝大多数是北偏东的(辉县琉璃阁的一座两条墓道的大墓M150的墓向也是北向偏东)。”[105]胡厚宣先生也曾统计西北冈大墓,对于大墓的墓向有具体的数据:“其方向大体由北偏东十四度到十六度,而以北偏东十五度为最普通。”[106](www.zuozong.com)
图一百〇八 殷墟西北冈大墓排列与墓向示意图
对于古代墓葬的墓向,美国学者詹姆森认为:“埋葬的方向,在原始人的意识里,有着一定的意义。……现在的后进部族在埋葬死人的方向问题上,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信仰。”即族源地方向、阴冥域界方向和太阳西落方向。其中族源地方向认为人死后,灵魂要回到原来的(或传说中)的老家去,因此,头就朝着老家的那一方向[107]。这在民族学材料中也有不少可以佐证的材料。如台湾泰雅族埋葬死者时头向东方,向着祖先发源地,认为祖先的坟墓就在那里。台湾曹族人在死后,以为灵魂就赴塔山而久留不回。这塔山在阿里山旁,为死灵集中之所。传说为本族始祖发源地,死者是回祖先的老家去了。因此死者埋在屋内,面向正门及塔山方向[108]。如果说殷墟中小墓的墓主身份比较复杂混乱的话,但殷墟带墓道的大墓则是商王墓和殷王室成员墓以及大奴隶主贵族墓。殷墟大墓的墓向为东北方位,说明真正代表商族血统后裔的商代王室及高级贵族把东北方向当做尊位。
(七)西北冈大墓排列位置尊东北方位
安阳殷墟西北冈墓地是商代后期的王陵区所在。这里分布着13座大墓道的大墓,分东西两区。西区大墓排列较有规律,有四排南北向排列的八座墓葬,其中七座为带四条墓道的大墓。这八座墓中,东边的较早,西边的较晚,南边的又晚于北边的。最东一列靠北的一座墓,即这个墓区最东北的一座墓是M1001,它是这一墓区中最早的墓葬。M1001南为M1550,这两座墓都属殷墟文化第二期,在这两座墓以西的墓都属殷墟文化三、四期。关于M1001的时代和墓主,也有争论,或曰武丁[109],或曰盘庚[110]。此墓位于这一墓区的东北角,处在最尊贵的位置。墓葬的排列以先祖在最东北、子孙列于其西南的做法,也当是殷商族人不忘其根本的一种传统习惯。
图一百〇九 殷墟西北冈大墓1001墓向及殉葬坑位置关系示意图
(八)车马坑与大墓位置关系尊东北方位
杨锡璋先生在殷墟西区墓地中找到了这样两个可以说明问题的例子。其一是在殷墟西区第七墓区的西南角,是以M93为主的一组墓葬。M93是一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墓,其西是一座较大的长方形竖穴墓M152。M152西南是车马坑M43。M43和M152以西是车马坑M151和马坑M150。M43和M151是车马坑,两坑内各埋一车二马,车辕都朝向南方。M150是一座马坑,内埋两匹马,马头也都朝南。在这一地区,除了M93和M152以外,没有其他大墓葬,这两座车马坑和一座马坑显然与M93和M152有关。这两座较大的墓葬正好在这三座车马坑的东北处或东偏北处[111]。这种位置关系表明,车马坑的殉葬是为了祭祀在其东北方向的大墓墓主。无独有偶,殷墟西区墓地第六墓区中也有这样的例子。1972年在第六区发现了一座车马坑M7,内有两马一车一人,车辕向东[112]。而早在1959年,在M7东约90米处发掘到四座已遭破坏的车马坑,其车辕一向东、一向北[113]。1983年在M7东约90米之处,发掘到四座一条墓道的大墓,在西北的为两座并排的墓,另两座墓分别在其南和东南。这四座墓的墓道都在墓室南侧,可惜都已遭到严重的破坏损毁[114]。那么,在四座大墓以西和西南的两处车马坑,当是祭祀大墓墓主的殉葬之物。祭祀的方向也是由西南面向东北,正合商族族源的方位。
总之,把东北方位当作吉向尊位,是殷商民族的一个传统观念。在商族建国之后多年仍能坚持以东北方位为吉利方位的做法。这当是他们不忘起源旧地的一种深层次的故土观念,这也为商族起源于东北地区渤海湾一带提供了一个例证。同时,也为今后判断一个考古学遗址的性质是否为商族或以商人为主体的物质文化遗存,提供了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标准。
在学术界,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但是不承认“殷人重东北方位”,而是以测量手段来说明商代墓葬和建筑物在方向上的偏转现象,认为商代墓葬和建筑物多偏向东北这一现象,乃是利用太阳确定方位所致,进而也和遗址所处纬度有一定关系;或者怀疑是技术和方法的原因造成的,指出黄河中游古地磁的走向在古代曾经发生偏移;或者认为商人心目中的四个方位与现在的方位并不一致,而是顺时针偏转了10度左右等等[115]。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因为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在同一纬度地区,不同部族的建筑和墓葬,所呈现的建筑或墓葬方位偏离方向应该是大体一致的。然而并不如此,比如在纬度大致相同的郑、汴、洛地区,这里分布了代表夏商周不同部族、不同时代的都城与宫殿建筑和墓葬遗址,而这些遗址的方向性并不一致。如同时在洛阳地区,作为商代早期城址的偃师商城是北偏东,而作为夏代都城所在的二头里城址则是北偏西,如上所举,周代洛阳成周都城及王城遗址也是北偏西方向。但是作为殷商后裔的宋国都城,近年来被考古勘探出来,所呈方向则是北偏东[116],与属于周族分封诸侯国都城方向正好相反。
如果古代人们是依靠太阳确定方位的,那么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应该大致一样,何以会有一些民族的方位在正方向坐标上向顺时针偏移,而有些民族的方位在正方向坐标上向逆时针偏移呢?因此可以说,不承认不同民族有不同方位观念和不同吉向尊位的观点,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同样,我们也可以举近年发现的鹤壁刘庄先商文化遗址的方位情况来说明问题。刘庄遗址包括了龙山文化豫北类型、二里头文化、先商文化等多重内涵,其中的先商文化遗址中的墓葬方向,绝大多数也是呈北偏东的。而同一遗址的属于其他文化的墓葬方向与此不同[117]。两者的区别划然而判,这说明墓葬方向不是技术和方法的问题,不是测量的问题,而是不同民族不同信仰观念的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殷人重东北方位”是这个民族从来就有的一种方位观念,即殷人不忘其所自从来的最早起源地是在东北方向,所以把东北方位当做吉向尊位,这是不容置疑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