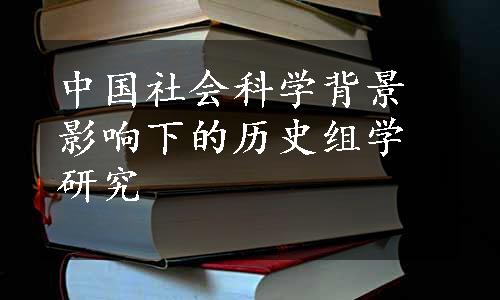
《集刊》是史语所发布学术成果的重要学术平台。截至1949年,《集刊》发表了108位作者的文章、来往书信讨论共447篇,其中涉及25位历史组学人。他们是傅斯年、陈寅恪、余永梁、黎光明、徐中舒、赵邦彦、李光涛、陈槃、劳榦、俞大纲、李晋华、全汉昇、陈述、余逊、周一良、张政烺、傅乐焕、岑仲勉、王崇武、杨志玖、王叔岷、黄彰健、何兹全、严耕望、王明。他们大多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其中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最多,其次为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青年才俊正处在思想活跃、学术风格形塑时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高校历史系课程正处于改革时期,社会科学化是其重要方向。自清末梁启超揭出“新史学”旗号,再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国不断传播,并推动了大学课程改革和新史学的发展。高校历史课程改革社会科学化的发展趋势,推动了青年学子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发展。随着报刊等新兴媒体发展,青年学人思想深受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可以说,高校课程改革和社会科学思潮共同影响了青年学子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历史观的形成。
入史语所前,徐中舒的学术思想有两大渊源即桐城学派和王国维、梁启超的新史学观念及科学治学门径。[1]他说:“我因学桐城派古文,就读了些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社会通译》《群学肄言》这一类的书。因为严复是吴汝纶的弟子,他是用桐城派家法来翻译文章的,因此,我就开始接受了些资产阶级的教育,社会进化论和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理论,从前我接受的封建教育,也就有些动摇了。”[2]因此,徐中舒的治学方法表现出较为浓厚的“理论”特点,[3]即注重运用民族、地理、神话等史料以建设古代社会史。
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劳榦广泛涉猎社会科学论著,形成了系统化的历史认识论。他说:“那时又恰在五四以后的几年,一切思想都在萌芽时代,各杂志及报纸副刊中,有关政治和经济的也不少,就此为阶梯,再看政治和经济的专书仍然非常有用……这种广泛的基础,现在看来仍不是无用。”[4]历史研究不再是纯粹考据之学,而是系统工程。因此,劳榦认为,历史研究虽然离不开考证,但绝不是零碎的,还需要诠释,以形成系统认识。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史论战迅速兴起和发展,激发了青年学子学术报国的热情。钱穆言:“时顾颉刚在燕大办一《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一《食货》,两杂志皆风行一时。”[5]1934年,陶希圣创办《食货》杂志,积极传播其社会史思想,在青年学子中具有广泛影响力。北大时期,何兹全思想激进,积极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因而与陶希圣经常接触,并在后者创办的《食货》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成为陶希圣的“亲兵”。[6]全汉昇在北大时期亦受陶希圣思想的影响,为《食货》杂志的重要作者。在陶希圣影响下,全汉昇的《中国行会制度史》由新生命书局出版。后来,全汉昇很快成为陶希圣的得力助手,陶希圣的《唐代经济史》等著作得到全汉昇的助力。严耕望也因受陶希圣的影响对经济史、政治制度史研究产生浓厚兴趣。[7]
论战的发展改变了治史偏重上古史的学术格局,青年学子多注重研究宋元以后断代史以表达自己史学经世的思想。因此,宋元明清等断代史以及经济史、社会史等专门史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在新史学潮流中,何兹全、全汉昇走上了运用社会科学工具研究历史的学术道路,发表了数篇经济史、社会史、制度史等领域的文章,如何兹全的《北宋的差役与雇役》《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魏晋时期庄园经济的雏形》《三国时代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等。全汉昇大学时期就确定了经济史研究方向,先后发表了《宋代都市的夜生活》《中国庙市的考察》《中国佛教寺院的慈善事业》等论文。何兹全后来创办《教育短波》杂志聚焦乡村教师发展,是青年以学术经世的很好例证。何兹全认为学者融入政治有助于史学研究,他说:“在《教育短波》数年,写社论,接触各方面人物,思路开阔,眼界开阔,也许非书斋中所能学得到的,对研究历史也许更有好处。”[8](www.zuozong.com)
中国制度史也是中国社会史论战时期发展的研究主题。陶希圣先后出版了《秦汉政治制度》《中国政府》《亲属法大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在青年学生中具有很大影响。严耕望在武汉大学师从钱穆,在史学研究领域已有基础,但陶希圣的研究方法还给他以极大启示。严耕望说:“我在大学一二年级时尚无意研究政治制度史,这方面的兴趣是看了陶希圣先生的《秦汉政治制度》那本小书所引发起来的……(这本书)写作方法与《十通》式的传统写法完全不同,可说是运用近代方法写中国政治制度的第一部书。我看了很感兴趣。”[9]入史语所前,严耕望发表了以考证为基础的制度史文章如《两汉郡县属吏考》《秦宰相表》《论秦客卿执政之背景》等,这些文章为其深化制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何兹全、全汉昇、严耕望的社会史、经济史、制度史研究很显然延续和发展了这一风格。
明史研究因与现实有紧密关系,成为青年学子非常感兴趣的另一个研究领域。王崇武在北大学习时期就确定了明史研究方向。据赵俪生回忆:“他(王崇武)在学术定向方面很早熟,在大学期间就写了好多篇与明史有关的文章。那时顾颉刚先生办了个《禹贡》,陶希圣先生办了个《食货》,他们大学高年级学生就在上面投稿。什么宦官制度啦,军屯、商屯制度啦,记得都谈论过。当时虽未形成家数,但苗头已经茁然长出来了。”[10]同一时期,李晋华则在顾颉刚的指导下进入明史研究,顾颉刚回忆说:“去年夏日,李君晋华自粤东来,以从事史学为请。予告之曰,‘北平图书馆之前身为京师图书馆,京师图书馆则出于内阁大库,中多有明代官书,率为他处所不得见者,而此间曾未闻有整理之人,是亦绝学也,子有意乎?’晋华唯唯,日往焉,博考明帝敕撰之书,稿数易而后成,名之曰明代敕撰书考。”[11]王崇武、李晋华等史学青年同时进入明史研究领域,反映了时代主题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南炳文认为,民族危机不断加重推动了明史研究的发展,他说:“明史研究与20世纪以前的传统史学相比面貌大改,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12]
进入史语所前,这批青年学子已经积累了明史研究成果。如王崇武的《明代宦官权势的演变》《明初之屯垦政策与井田说》《明初的屯田制度》《明初施行屯田的社会背景》等,李晋华也先后完成《明代敕撰书考》《三百年前倭祸考》《复社考》《明史纂修考》等文章。李光涛入所前,虽未见发表论文,也已奠定了学术基础,因此才能在同乡徐中舒的推荐下进入史语所从事明史资料整理和研究。可以看出,王崇武、李晋华明史研究主题注重从经济、制度以及与现实相关的视角切入,以抒发青年学子的学术经世思想。
另外,傅乐焕、陈述等在大学时期已经确定了宋史、辽金史研究方向,他们与冯家昇被后学誉为“辽史三家”。傅乐焕在北京大学时期完成了《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陈述在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陈垣治辽金史,相继撰著了《陈范异同》《补南齐书艺文志》《金史氏族表》《蒋心余先生年谱》等论文。傅乐焕、陈述以史料考证见长,但在史料考证背后仍反映了他们的史学经世思想。傅乐焕与全汉昇、何兹全、杨向奎等皆为北大同学,史学经世思想成为他们共同的思想倾向。陈述的辽史研究亦有此情怀,陈寅恪为陈述《辽史补注》写的序文中指出辽史研究的现实意义,陈寅恪说:“况近日营州旧壤、辽陵玉册,已出人间。葬地陶瓶,犹摹革橐。不有如释教信徒迦叶阿难之总持结集,何以免契丹一族千年之往事及其与华夏关系之痛史,不随劫波之火以灰烬。故《辽史补注》之作,尤为今日所不可或缓者。”[13]通过整理辽史资料以延续契丹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之关系,是陈寅恪治史的时代关怀,陈述与陈寅恪这种学术情怀应该是相通的。这批青年学子能够进入史语所历史组,也反映了傅斯年、陈寅恪等大学者对新史学的态度。
陈寅恪虽批判但不否定社会科学理论的价值。时任史语所所长、历史组成员的傅斯年,则表现出对社会科学的积极态度,比如他看重社会科学方法在材料组织、问题阐释等方面的价值。中国社会史论战进行之时,傅斯年提出:“社会科学工具之完备,今日史学界定有长足的进展。”[14]这一认识大体能够说明傅斯年对社会科学的积极评价。另外,他还曾翻译完成人文地理学代表作《英国文明史》[15]前五章,他说:“此种学派,现盛行于法国,称人文地理学派。Buhnes之著作曾解释早年罗马村落生活之现象,彼以为古代人类住居,必临河之高岸上,以地理环境解释文化之发展,对于历史之帮助甚大。”他还曾借鉴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中有关批评该学派的批评,撰写了《地理的史观》之文章。[16]傅斯年对社会科学的态度从他对青年学人的评价中亦可见一斑。1934年,夏鼐完成了《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的田赋问题》,这是一篇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社会问题的社会史论文。傅斯年给予很高的评价道:“取材丰富,组织严谨。”[17]傅斯年所重视的正是夏鼐对历史材料的组织能力。傅斯年对中国社会史论战中涌现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人才也非常欣赏并积极招揽,他说:“希圣前办《食货》,收罗北平各大学毕业生不少,北大犹多,如鞠清远(师大,山东)、傅安华(北大,河北),皆良士也。”[18]傅斯年、陈寅恪对史语所青年学人治学采用社会科学方法不仅不反对,还加以积极引导。全汉昇曾回忆说:“进入史语所后,傅斯年先生即嘱咐我专门研究中国经济史,期盼我能拓垦这尚未有人耕耘的园地。”[19]陈寅恪也曾亲自指导俞大纲从经济视角研究中古史。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