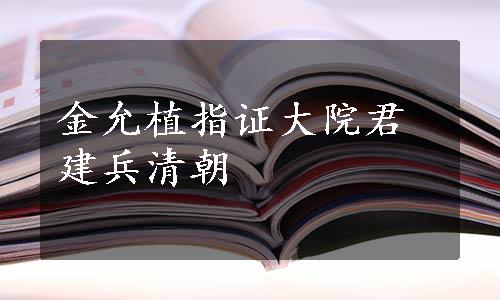
8月4日,在张树声将金允植的笔谈报告总署之后,黎庶昌发来第四封电报,称从日本方面获得消息,朝鲜王宫被袭击,日本出兵系保护应办之事,非意在打仗,中国亦应派兵前往镇压,并责朝鲜惩办凶徒。[23]这是继围馆逐使之后,清朝方面获得的关于兵变的进一步信息。同日,金允植接到了周馥的来信,知道了王宫被击的消息。金允植“心中固已疑虑矣,闻此信息,我国事断可知矣”。[24]黎庶昌的电报证实了金允植最初的担心,王宫果然被乱党袭击。5日,张树声致函总署,认为“朝鲜乱党欲谋不轨,果不出该陪臣金允植等所虑,中国兵船尤不可不速往镇压”,随即派丁汝昌和马建忠前往打探详细情况,鱼允中作为向导与丁汝昌和马建忠同往。[25]
同日,金允植与周馥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谈。笔谈前,金允植先将自己对局势的判断写成了一份详细的报告书。金允植在报告书中首先介绍了李昰应的身份来历,并明确指出大院君一直以来都在“结党蓄谋”,与国为敌,以图东山再起,李载先即是李昰应之子,李载先政变即是李昰应指使。“去年逆党私立三号,一天字号犯宫废立之事也,一地字号芟灭国王信臣及干涉外务之人也,其一蜂字号即逐出日人之事也。因事机先泄,不得遂意,今闻逐使之举,与犯宫同时并作,是其去年余谋,皎然易知,若乱党不即散灭,嗣后事将无所不至矣。”[26]可见,因为黎庶昌所提供的围馆逐使和袭击王宫这两点情报与李载先政变的计划相同,所以金允植推断此次兵变是去年李载先的余党所为,那么背后主谋显然应该是李昰应。这是金允植认定李昰应为祸首的推理过程。同时,金允植又写道,朝鲜国王“自嗣位以来,至诚事大……惟以时局大变,外交难拒,禀天朝之命,成议约之事,实为保宗社,安生民之苦心,而彼乃以斥和为义理,修好为卖国,昌言讨罪,鼓煽众心,酿成今日之变,故三号之目,一则逐邻使也,一则灭干涉外务之臣也”。[27]所以,在金允植看来,此次变乱完全是上一次的重演,而大院君自然会被认为是祸首。
该书信呈给周馥之后,金允植与周馥又进行了笔谈。[28]周馥显然对李昰应的外交立场并不清楚,周馥认为李昰应向与日人关系亲密,担心表面上驱逐日本人,但暗中与日本人勾结,借日本的势力达到自己夺权的目的。该说法立即被金允植否决,金允植认为,“通商修好之举,惟寡君力主……举国愚见,皆以外务为非,故李某借此为啸聚党徒,收拾人心之资”。[29]从大院君之前一直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来看,金允植该说法是合理的。随后,金允植向周馥献计,清兵可“以弹压乱党、镇守王京为辞,先致书于政府,晓谕勿惊,则必不敢动,既入京城,便可围住其第,以康穆王妃命数其罪,而赐之死,则名正言顺”。[30]周馥对此较为谨慎。金允植认为,如果李昰应得权,必定不会与日人谈判讲和,双方恐怕会有小规模冲突,而日本冲突之后的动作就很难预料,也许会借讨乱为名干预国事。所以金允植请中国迅速出兵并希望清朝派熟悉外交之人一并前往相助。[31]
值得注意的是,金允植所著《阴晴史》中所记述的8月5日给周馥的书信以及笔谈的内容较为简略,没有《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所收的版本内容丰富。《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所收书信和谈草是张树声附在自己的报告之后一并转给总署的,其真实性不容置疑。笔者对照两个版本的书信和谈草之后,发现《阴晴史》中没有关于李昰应情况的介绍以及金允植指证李昰应可能为兵变主使的内容,更没有金允植请求清朝处死李昰应的建议,再对照《天津谈草》亦是如此。所以,金允植应是出于忌讳,在记录《阴晴史》和整理《天津谈草》时故意将原始书信和谈草中关于李昰应的部分全部删掉,只保留了请求清朝出兵的内容。张礼恒依据《天津谈草》中周馥和金允植的笔谈,认为金允植为了达到使清政府出兵的目的,故意夸大了日本的威胁。对此,我们可以对照一下《阴晴史》《天津谈草》和《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周馥和金允植笔谈的内容。《阴晴史》和《天津谈草》的内容如下:
玉山(周馥字——引者注)曰:日本兵船,想已到贵国,其间果剿除乱党否,或无干预废置等事否?余曰:窃料乱党得志,初头必无乞和之理,一再交仗,日人必当上岸,便不可复制矣,乱党既已鼠窜,日人之干预国事又未可知,此所以欲中国,速派兵先出,毋在日人之后也,若中国兵出,不至打仗,自有善处之道,他国则不能也。[32]
而《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金允植的说法如下:
若李某得柄,日人之来,必不肯先行乞和,或恐有些少打仗之事,继此以往,日人所为,实难预料。因以上岸直进,借名讨乱,以至干预国事,谁能保其必无耶?所以愿中国速派兵丁,毋在日人之后者也。[33]
对比上述两段史料,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叙述的主体。第二段史料与第一段史料相比,明确用大院君李昰应作为叙述的主语,这就会造成理解上的不同。大院君执政时一直奉行闭关锁国和卫正斥邪的政策,以外交为非,与日本发生冲突是可能的,而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干预朝鲜国政,扶植亲日派上台亦不无可能。所以,金允植有此担心是合情合理的,无过分夸张的成分。
8月7日,总理衙门上折,请求派兵援护朝鲜。总署的奏折中引用了黎庶昌4日及之前的电报与金允植十九日的笔谈,并同意张树声的意见,总署认为,“中国不待朝鲜求助而调拨师船前往援护,既示字小之恩,而日本为中国有约之国,在我属邦受警,亦应一并护持,庶日人居功问罪,两计可以隐伐其谋”。[34]同日,清廷下发上谕道:(www.zuozong.com)
朝鲜乱党突起滋事,既围日本使馆,兼劫朝鲜王宫,其意不但与日本为难。日本现在派兵前往,其情尚难测度。朝鲜久隶藩封,论朝廷字小之义,本应派兵前往保护,日本为中国有约之国,既在朝鲜受警,亦应一并护持,庶师出有名,兼可伐其隐谋。著张树声酌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35]
至此,清朝正式决定出兵。关于金允植在促使清廷出兵的过程中起的作用,张礼恒认为,周馥把与金允植5日的会谈情况汇报给了张树声,张树声结合黎庶昌的电报,致函总署作出了前述中国兵船应速往镇压的建议,所以金允植5日的建议加速了清政府出兵的决策过程。[36]但是,据《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金允植8月5日致周馥的信以及与周馥的笔谈在8月8日才由张树声报送总署,而张树声8月5日致总署的信并未提到金允植当日书信和笔谈的情况,该内容见于张树声8月8日的信函。[37]那么,若张树声在8月5日就已经接到了周馥的报告,他没有理由将此重要情报延后三天上报。所以,张树声5日向总署提出出兵建议之时,并没有看到金允植给周馥的书信及笔谈的内容,而前述总署的奏折所依据的情报只有金允植8月1日和2日的谈草以及黎庶昌的四封电报。从8月1日到5日,尽管金允植一再向清朝表达出兵的请求,但清朝一直没有同意,张树声亦只是决定派遣丁汝昌和马建忠先往朝鲜打探消息。从清朝上谕的表述来看,出兵是因为朝鲜乱党围馆逐使和袭击王宫,日本的情况“尚难测度”,要“伐其隐谋”,这基本是黎庶昌电报的内容,所以,在清朝出兵的决策过程中,黎庶昌的情报起了重要作用。
8日,张树声致函总署,决定在丁汝昌和马建忠打探消息回来后,派遣陆军吴长庆所部前赴朝鲜。张树声做此决定原因有二:第一,若李昰应果为乱首,则单凭朝鲜的力量难以平定乱党;第二,日本已派兵,若无相当军力为后盾,则难与日本谈判,故张树声“综筹统计,是续调陆师,事无可止”。[38]可见,张树声出兵的安排是基于各种情况的综合考量,并非仅据金允植一面之词。
8日下午,黎庶昌电送第五份情报:“高丽乱党杀王妃[39]及闵氏大臣等十三人,王无恙,王父大院厅执政,兵宜速往,为无日人所先,闻美约有不批准之意。”[40]该情报的重点是大院君已重新执政并且朝美条约可能不会被批准,朝鲜的开化政策面临夭折。张树声在接到黎庶昌的电报后认定,“李昰应果为乱首,欲坏通商之局,王虽无恙,势无能为……至此次高丽之乱,悉如在津陪臣金允植所料,该国局势已变,日兵又占我先着,办理犹未易措手……盼至高事定后,一切自应由中国主持,庶镇抚内外,乃能顺手也”。[41]至此,大院君被认定为乱首。仔细梳理大院君被确定为乱首的过程,可以发现其中有很大的推测的成分,但这种推测在当时的情况下又显得合情合理。首先,金允植在获悉朝鲜乱党围馆逐使的消息之后自然联想到了李载先政变,而李载先政变的幕后主使是大院君;随后黎庶昌有关乱党袭击王宫的情报使金允植认为此次变乱就是上一次的重演;而兵变之后国权尽入大院君之手,大院君成为兵变的最大受益者,所以张树声在得到大院君重新执政的情报之后便断定李昰应是乱首。这个过程充满巧合,但将其放入当时的语境下是合理的。同时,因为金允植的推测都被黎庶昌的情报“印证”,所以金允植和鱼允中自然获得了清朝的充分信任。
9日,周馥与金允植进行了笔谈,周馥向金允植通报了大院君上台的消息并询问粮草以及进兵路线等问题。金允植回答,“兴宣一门,断不可贷”,朝鲜国王已无实权,故粮草一事朝鲜无能为力。进兵路线有两条,大路稍平,小路需朝鲜人为向导,仁川港浅,兵船须舶于港外二十里,以小船登岸。对于大院君,金允植认为可“下谕饬兴宣前来军前面问事状,若来则不死,不来则举兵讨灭”。清兵上岸之后,行军之时可四面哨探,然后进军,乱党“一败则不可复振”,故节节进兵,可无他虑。[42]金允植凭借自己对朝鲜政情及地理环境的了解,为清朝进兵提供了详细的建议,但该谈草在《阴晴史》和《天津谈草》中亦未被收录。
13日,张树声面见金允植。金允植认为,“乱党自无远见,藐视他国,若一经炮火,经倒散走,嗣后日人诱以祸福,亦不无阴合之虑,所以欲中国派兵速出,恐失其机也,语日人则曰,弹压乱党,语乱党则曰,调停日人,名正言顺”。[43]对于张树声大军直入会使朝鲜国王处境危险的担心,金允植则献策,可请乱党出城接谈,若其不肯来,可用好言安慰,然后节节进兵,围住四门,乱党既不肯屈服于日人,必来投奔中国。[44]金允植的建议得到了张树声的肯定。
14日,张树声收到了马建忠的调查报告。据随马建忠一同前往调查的鱼允中禀报,此次兵变系大院君“率众倡乱,直入王宫,劫杀王妃”,又囚禁国王,杀戮主张开化的大臣。[45]张礼恒认为,马建忠、张树声据此报告层层上报,最终坐实了李昰应为乱首的罪名,金允植、鱼允中几乎是壬午兵变所有信息的来源。但重新梳理马建忠的报告可以发现,除了鱼允中的调查报告外,日本参赞近藤真锄“亦谓李昰应因兵作乱,往见王妃,进酖以弑,现在大权独揽,极为猖獗”。[46]马建忠结合金允植此前的谈草、鱼允中的报告和近藤真锄的看法,遂认为“李昰应借清君侧之名,翦除国王羽翼,徐以窥伺藩位无疑”。[47]所以,清朝对于大院君乱首的认定亦是各方意见综合得出的,并非仅据金允植和鱼允中的一面之词。另外,据美方史料,在兵变发生之后,美国驻华使馆给美国政府的汇报和美国驻日使馆与日方的交涉文件中均认为大院君是兵变的罪魁祸首。[48]所以,大院君为兵变的主使在当时是各方共识。随后,周馥派人将马建忠的报告送与金允植查阅,金允植由此知悉了兵变的详细情况,并获悉大院君上台后尽废开化新政的消息。[49]16日,金允植作为向导随清军前往朝鲜。最终,清军逮捕大院君送往保定囚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