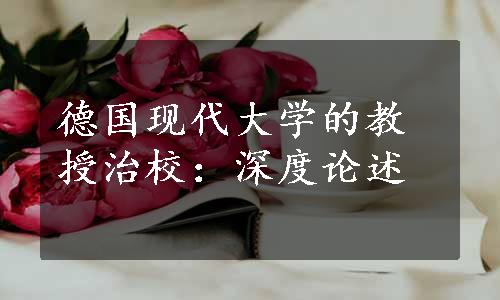
德国大学发源于中世纪末期,但直到19世纪之前都没有取得令德国人特别引以为傲的成绩。然而,从1810年柏林大学创建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这段时间里,德国大学却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声誉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德国大学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成功,不仅因为其独特的办学理念和学术生产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也得益于大学组织管理模式上的创新。
一、德国现代大学的产生和发展
虽然同属中世纪的产物,但与意大利、法国、英格兰等国的大学相比,德国大学要年轻得多。在意大利、法国、英格兰等国家的大学已经存在了两个世纪以后,德国一些雄心勃勃的诸侯才开始创造条件按照邻国的模式建立自己的大学。尽管来得晚一些,但德国早期的大学对中世纪文明同样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相关资料显示,到16世纪初期,德国在校大学生规模已经达到了4200人,与14世纪通常的1200人相比,其增长数量是相当可观的。[21]可惜的是,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没有持续下去。到17—18世纪,与整个欧洲大学一样,德国大学也陷入了危机之中,社会声誉一落千丈,大学的糟糕状态一度受到社会的全面抨击。以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helm Leibniz)为代表的激进派学者甚至认为,大学作为中世纪的产物已落后于时代,应由新的其他形式的机构予以取代。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改革势在必行。
危机中往往孕育着新的生机。到18世纪中叶以后,以理性为基本原则的启蒙运动在德国进入全盛时期,成为一股最具革命性的力量强烈地冲击着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它以雷霆之势向宗教传统和神学权威发出强硬的挑战,从而也为新型大学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社会环境。18世纪德国两所最出色的大学—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就是启蒙思想的产物。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哈勒大学强烈地抨击神学教条主义,宣称大学要成为“自由的殿堂”。哥廷根大学更是把思想宽容和研究自由看作大学的根本原则,取消了神学院自中世纪以来享有的对其他学院的监督权,赋予大学教授“教学的自由和不受检查的权利”[22]。哥廷根大学的创立者明希豪森(Jerlach Adolf von Münchhausen)非常重视教授的学术声誉,不仅不惜重金鼓励教授们争取出版研究成果,还想方设法从其他王国争抢著名教授。这两所大学所实施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改革措施,有效地激发了大学教授们的学术生产力,大学教授在学校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两所大学的声誉也一路攀升。到18世纪末期,德国所有的大学都纷纷仿照这两所大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或重组。
虽然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从整体上看,19世纪之前德国大学的发展还是远离时代的要求,大部分学校仍然身陷困境,而真正引导德国大学走出危机并使德国大学迎来了发展黄金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还是柏林大学的创建。
柏林大学是在德意志民族和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1806年耶拿战争后,普鲁士大败于拿破仑的军队,致使德国一半以上的国土屈辱地被割让出去,且随着国土的丧失还失去了七所大学,其中就包括哈勒大学,整个国家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和灾难之中,但这一变故却“意外地”为柏林大学的创建提供了契机。为了挽救生死攸关的德意志民族,普鲁士包括国王腓德烈·威廉三世在内的一批有识之士,迫切希望通过学术教育上的繁荣和精神上的胜利来洗刷军事上失利带来的国耻。1807年8月,当来自原哈勒大学的教师代表团在法学教授施马尔茨(Schmals H)的率领下,去晋谒腓德烈·威廉三世并请求国王支持他们在柏林重建一所大学时,国王欣然答应,并鼓励说:“国家要用脑力来补偿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23]不出一个月,国王便颁布法令,将原哈勒大学的一切经费全部改为柏林大学的补助费用,并拨出专款供新建大学之用,同时捐赠华丽的王子宫殿作为教学楼,还将一座博物馆归入新大学的版图。在柏林重建大学之所以受到如此待遇,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与特殊历史时期赋予大学身上的特殊期望有关。可见,柏林大学从创建开始,就已经承载了帮助恢复国家尊严、重整民族雄风的时代使命。
柏林大学的最终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洪堡等人的贡献。1808年,身兼德国学者和政治家身份的威廉·冯·洪堡(Friedrich Wilhelm Christian Carl Ferdnant von Humboldt),被任命为当时新建的普鲁士内政部文化司的第一任司长,负责全面改革普鲁士的教育。上任5个月后,他便开始按照其新人文主义思想实施创建柏林大学的计划,并且在为期仅16个月的任职中,便将创建柏林大学的理想付诸实施。经过一年的筹备和努力,柏林大学在1810年秋如期开始了教学活动。法学教授施马尔茨(Schmals H)被任命为临时校长;1811年,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经过四轮角逐被选为第一任校长。很快,柏林大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德国大学未来发展的榜样。同期新建的伯恩大学、慕尼黑大学以及一些古老大学如莱比锡大学、海德堡大学等都纷纷仿效柏林大学的模式进行改革。就如史学家们所宣称的,“柏林大学的创办像一个燃烧点发出耀眼的光芒,一切光线全都从这里发出”[24]。德国的高等教育自此走上了迅速发展的快车道。
二、柏林大学的“教授治校”(www.zuozong.com)
从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实行改革的时候起,德国大学就开始注重加强教授在学校中的作用和地位;柏林大学建立起来之后,更是将这些理念推向极致,形成了德国现代大学最鲜明的管理特色。
柏林大学从创建开始,就深受在启蒙运动中兴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使得柏林大学从一开始便完全体现出迥异于传统大学的办学风貌,在组织模式上更是呈现出独树一帜的特征。新人文主义者最重要的思想主张就是极力推崇古希腊文化,倡导人性自由和个性发展。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接受新人文主义思想熏陶的威廉·冯·洪堡,深为新人文主义追求自由、个性的思想所折服,当后来重建德国高等教育的重担落到他身上的时候,新人文主义思想烙印自然就会在他的办学思想和实践中显现出来。在洪堡看来,修养或者说通识性的修养是人作为人最应该具有的素质,大学培养人才自然也应当从这个基本点出发。那么,在大学如何达成“修养”呢?洪堡认为,唯有探求纯科学的活动才是达成修养的不二门径。[25]当然,洪堡所说的科学的内涵比较广,他眼中的科学是建立在深邃的观念之上的、可以统领一切学科的纯科学,即我们讲的哲学。[26]在“由科学达至修养”的原则的指引下,柏林大学的创建者认为,从事科学研究的学术工作应当成为学者的最高职责,也应当是优秀的大学教师必须承担的责任。基于这种理解,柏林大学从一开始就把科学研究的学术任务认定为教授们的正式职责和要求。正如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指出的,“柏林大学从最初开始就把专门的科学研究作为首要要求……它认为在科研方面成就卓越的学者,也就是最好和最有能力的教师”[27]。为此,柏林大学聘请了一批具有学术热忱和耐得住寂寞的著名学者,像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哲学家费希特、古典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柏克、历史学家尼布尔、法学家萨维尼、农学家塔埃尔、化学家克拉普罗特等,都是在各自学科领域首屈一指且享誉全欧洲的杰出学者。在开学之初,柏林大学所聘请的教授就达到了24位,神、法、医、哲四个学部分别拥有3、3、6和12位。[28]这样一张“值得自豪的聘任表”[29]绝对是空前的。
在崇尚理性、自由的新人文主义者看来,学术研究要有效地进行,只能坚持理性的原则,要以理性为出发的原点,同时必须把自由精神作为学术研究的主旨。那么,如何才能让大学学者完全遵循理性的逻辑和享受自由的要求呢?大学创建者认为,首要的、必备的条件就是不能让他们无端地受到其他外部力量的干涉和牵制。要实现这样的目的,大学在组织模式的设计上首先就必须充分保障学者的权力,所以柏林大学在成立之初,其设计者在大学章程里便明确将大学定位为“(正)教授们的大学”,它所实施的基本管理原则就是“(正)教授治校”。首先,在学校层面,柏林大学建立了主要由正教授代表组成的评议会等管理机构。大学的各项事务,包括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基本上都由教授们做主,大学的校长也是由教授们选举产生。在基层,柏林大学采用了研究所和讲座相结合的学术组织形式。讲座原指学者们发表讲演的座位,后演变为一种学术组织制度。尽管讲座不是由柏林大学首创的,早在16世纪初由政府资助的永久性讲师职位及其讲座基金就开始在神、法、医、哲各学部中固定下来,[30]不过,到柏林大学时期,这一学术制度得到了强化。研究所以及类似的研讨班、实验室、医科诊所等都是与讲座并行的机构,都是教授们开展学术研究的场所。在这些基层学术组织中,大学教授们几乎掌握着所有的管理权力,比如,能够自主地选择教学内容和研究项目,能够独立地确立学科的发展方向,自己能够聘用工作人员(学术与非学术人员),能够自主地确定经费的使用,等等。可以看出,讲座及其主持人在德国大学中拥有举足轻重的自主权力,其地位是如此特别;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别的运行机制,使得它为德国大学的迅速崛起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似乎可以说,德国学术系统在1914年之前数十年所取得的巨大科学进步可能是由于学术专业(借助讲座制度)拥有一种独特的社会地位;它享有一种在德国其他部门中不可能出现的非常巨大的自主”[31]。处于基层和学校之间的层级是学部,也是由所属讲座教授组成的部务委员会实施管理。综合起来看,柏林大学从基层到学部再到学校层级的所有事务都是由教授负责管理和决策的。
柏林大学的教授在学校管理中享有至高的权力,典型地体现了“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与中世纪大学一样,这一管理模式的实施对促进德国大学的迅速崛起有着无可替代的功效,尤其在以下两个方面最为突出。
首先,教授们享有学术管理自主权,有效促进了大学学术水平的发展与提升。据陈洪捷教授的研究,19世纪的德国在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中都毫无例外地居于领先地位,仅德国一国所取得的科学成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世界其他各国科学成就的总和。德国在科学中的优势堪与英国的贸易和海上优势相媲美,甚至更有超越之势。而德国人之所以能够在科学界产生如此之深的影响力,主要归功于其大学。[32]而德国的大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首先得益于大学拥有一大批潜心科研的教授和赋予教授自主权的管理机制,其次才是基础和保障。其原因正如新人文主义者指出的那样,学术活动只能服膺于理性的逻辑,而理性的逻辑要求从事研究的学者是不能受非学术力量制约的,应当拥有一个自由和自主的研究环境。德国大学的管理正是满足了这种要求,给从事学术活动的学者们在大学范围内非常大的自主权,从而有效地激发了教授们的学术能力和学术水平,也进一步吸引了诸多优秀学者纷至沓来。德国教育史家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曾略带自豪地写道“举世的学者不断到德国走访或留学”[33],足见德国大学的魅力和影响。至“纳粹”执政之前,曾在柏林大学工作或学习过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就达30人之众。[34]比如,埃米尔·菲舍尔从1892年到去世一直在柏林大学工作,因对生物化学的突出贡献于1902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冯·贝林从1889到1895年在柏林大学工作,于1901年获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马克斯·普朗克1888—1926年在柏林大学工作,以量子理论的创立于191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于1914—1932年在柏林大学任教,因成功解释了光电效应于1921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些,都是柏林大学学术精英的代表。
其次,德国大学的管理机制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大学以及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建构了可资借鉴的模式。如何妥善处置政府和大学、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一直是高等教育管理和研究的难题,柏林大学的管理模式则为这道难题的破解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柏林大学主要是由政府出面新建的,在建立之初便承载了帮助恢复国家尊严、重整民族雄风的时代使命,自然不能脱离政府的控制和政治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柏林大学“本来就是学者与政府、学术与政治之间积极合作的产物”[35]。但深受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洪堡等人在关于大学地位等问题上坚持以“文化国家观”作为思想基础和价值准则,认为国家也是文化的体现,国家和学术均以统一的理性原则为出发点,大学和国家都应当共同服从于理性原则,二者互相结合,共同依存。[36]因此,国家应当认识到大学组织和学术活动的特殊性,对大学的管理必须尊重其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区别,更多地为大学的学术发展提供支持,而不是直接、具体地干预大学的运行,也就是说,必须赋予大学相应的自治权。为实现这种自治权,大学的运行显然不能受政府官员的直接指挥;否则,大学就有可能沦为政治的附庸。德国大学的处理方法就是把大学的管理权限直接交付到最通晓学术逻辑的大学教授手中,政府更多的是为大学的发展提供条件支持。在这样的组织构架下,大学和政府才能各得其所。可见,德国大学“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一方面支持了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学术的自治,促进了大学学术的发展,为正确处理政府和大学、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效解决问题的典范。
柏林大学的巨大成功,给德国大学树立了良好的标杆。德国大学纷纷学习其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整体上促进了德国大学办学水平的提升。19世纪,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在德国,这已经得到了公认,英国著名的高等教育管理专家阿什比(Eric Ashby)勋爵便誉之为“19世纪大学的理想模式”[37]。在德国模式的影响下,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如法国、意大利等都开始效仿德国大学的运行机制,“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在欧洲大陆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