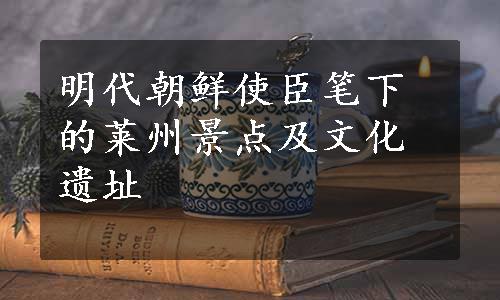
天启四年(1624),朝鲜冬至使书状官金德承在《天槎大观》中还提到了莱州的其他一些文化遗址和景点。
《天槎大观》记载了莱州福山、禄山:
福山、禄山俱在西北,两山相峙,皆产温石。福山俗名斧山,峰岭高峻,北临沦海。北魏刺史崔挺将顶上营观,父老云:“岭有龙道,恐不久立。”挺曰:“人龙相去不远,虬龙倏忽,岂一路乎?”遂营之。[101]
金德承的上述记载,应来自《明一统志》卷二十五《莱州府•山川》:“福山、禄山俱在府城西北五里,二山相峙,俱产温石。福山俗名斧山,峯岭高峻,北临沧海。北魏刺史崔挺欲于顶上营观,宇父老云:‘岭上有龙道,恐不可久立。’挺曰:‘人龙相去何远之有,虬龙倏忽,岂一路乎?’遂营之。”
“温石”,前面提到,即莱州滑石,白色的质地脆而不坚,碾成粉末后粉刷墙壁。蓝绿色的质地坚硬,可做雕刻的原料。莱州石料,宋代已闻名全国,宋代杜绾撰《云林石谱》就特别提到了“莱石”:“莱州石,色青黯,透明斑剥,石理纵横,润而无声。亦有白色,石未出土最软,土人取巧镌雕成器,其轻妙,见风即劲。或为铛铫,久堪烹饪,有益于铜铁。”[102]《万历莱州府志》卷六《大事记》中也记载:“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取莱文石。”“莱文石”,应该是莱州温石。乾隆年间文人,赏石家沈心在《怪石录》中还记载:“牡丹石,产掖县亚禄山,质较莱璧殊坚,色微红,极娇艳,可作器,今不易得。桃花石,产掖县亚禄山下土中,质与牡丹石等,色则绿白相参,琢为文房各具甚精。竹叶石,产掖县大泽山,色白质甚坚,其筋皆作竹叶形、个字、介字之属,遍体交加,且具风雪晴雨之态。惜姿稍粗,难入鉴赏。”[103]“亚禄山”在莱州城西南,禄山南。“大泽山”,在莱州城东南,与平度大泽山相接。
“福山俗名斧山”,地方志及朝鲜使臣金德承都做如此记载,实际上斧山“作斧形,故名”[104],斧山由来已久,应该是其正式的名称,《魏书•崔挺传》中就称“掖城西北数里有斧山”,就说明了这点。可能斧山旁有禄山,因福禄二字相连,故斧山就成了福山。莱州历史名人、明代首辅、大学士毛纪的墓地,就在今莱州城西的禄山前埠上。
关于崔挺的记载见《魏书•崔挺传》:北魏孝文帝时,崔挺任光州刺史(州治掖县),“威恩并著,风化大行”,太安十九年(495),孝文帝视察地方,在兖州召见了崔挺,了解了崔挺治理光州的情况后,“甚悦”。孝文帝又派有“清使之名”的散骑常侍张彝到光州进行实地考察,张彝考察后“采察谣讼,入境观政,实愧清使之名”,言外之意是,真正有“清使之名”的是崔挺。孝文帝曾对随从的人员说:“拥旄者悉皆如此,吾何忧哉。”崔挺还上书朝廷反对一人犯罪,株连全族的做法,提倡罪不株连,孝文帝也接受了崔挺的意见。当时发展生产,“州内少铁,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复铁官,公私有赖”。崔挺上书朝廷,在光州恢复设置主管铁器生产官员的建议,使衙门和百姓都得到了利益。崔挺为官清廉,掖县有一老人“年逾九十,……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岛,垂六十岁”。为感谢崔挺,决定赠送给他。崔挺曰:“吾虽德谢古人,未能以玉为宝,……竟不肯受”。崔挺“历官二十余年,家资不益,食不重味,室无绮罗”,崔挺治理光州,其政德不仅得到了朝廷的褒奖,更以其自身形象得到了光州百姓的拥戴。崔挺离职光州时,“老幼泣涕追随,缣帛赠送,(崔)挺悉不纳”。崔挺去世后,光州的官吏和百姓“闻凶问,莫不悲感,共铸八尺铜像于城东广因寺,起八关斋,追奉冥福,其遗爱若此”。史评崔挺“风操高亮,怀文抱质,历事著称,见重于朝野”。
崔挺治光州期间的事迹,地方史志也均有记载,《明一统志》卷二十五《莱州府•名宦》就载:“南北朝崔挺,魏光州刺史,风化大行。散骑常侍张彝谓曰:‘入境观政,独闻清使之名’。掖县有老人自言:‘尝使林邑得美玉,藏之海岛,垂六十年。今仰逢明政,愿奉之’。挺不受,及代去。老幼追送缣帛,亦不纳。”
据清《嘉庆续掖县志》卷一《古迹》记载,当时斧山还有碑刻,碑文曰:“光州刺史宇文公抚育边民,恩同赤子,治方清美,□甚文王之化,□曰过于□,老弱相□,故□山□建造碑铭”。“宇文公”,光州刺史中查无此人。这里可能指的是宇文恺,《隋书•宇文恺列传》记载,宇文恺出身于北周时期武将功臣世家,但“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隋初,曾“拜莱州刺史,甚有能名”。虽说,当时光州已更名莱州,但当地人极有可能仍习惯以光州刺史称之。隋炀帝时,宇文恺官拜工部尚书。
崔挺任光州刺史在郑道昭之前,崔挺、郑道昭及郑道昭之子郑述祖任光州刺史期间,都为当地老百姓做了许多事情,都是为“为吏民所爱”[105]的好官,再加上后来的“宇文公”,这不能不说是当时莱州人的福分。朝鲜使臣金德承记载了崔挺治光州的一段经历,也是对崔挺治光州的赞誉。
金德承在《天槎大观》中还提到了“无讼堂”:
无讼堂在治,宋时建,政和三年石月先生之记,词意质润。[106]
《明一统志》卷二十五《莱州府•宫室》记载:“无讼堂,在府治,宋建,政和三年(1113)有石月先生作记,词意质润。”“石月先生”,即余安行,因所居有岩如月故称“石月”,北宋进士,南宋初任朝议大夫,精通经学,著有《春秋新传之言集记》。石月先生为“无讼堂”作记,《天下金石志》有记载,只是“无讼堂”记作了“无私堂”:“《无私堂记》,石月先生撰,政和三年在莱州”。[107]《齐乘》卷五《亭馆下》记载:“无讼堂,莱州公署后,宋政和间建”。[108]元代《齐乘》和《明一统志》都提到了“无讼堂”,朝鲜使臣也予以关注,说明“无讼堂”在当时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清代《道光再续掖县志》卷上《古迹》记载说:“无讼堂,地无考。……据云在莱州公署后。”这说明无讼堂在清道光年间之前就不复存在了,否则,也应是莱州的古迹和著名景点。
金德承在《天槎大观》中还提到了莱州的几个寺观:
青罗观,永乐间仍旧修。
妙觉寺,元时建,皆在治。
资圣寺,金时建。[109]
金德承的上述记载,也应来自《明一统志》和《万历莱州府志》,《明一统志》卷二十五《莱州府•寺观》“资圣寺,在府城南门外,金大定(1161-1170)间建。妙觉寺,在府城内,元中统五年(1264)建”。“青罗观在府城内,永乐(1403—1424)间因旧重修”。《万历莱州府志》卷六《寺观•掖县》记载的更详细些:“资圣寺,在城西南里许,金大定间建,后殿有石刻卧佛,俗名卧佛寺。万历五年(1577)邑人刘祜修,僧纲司附。妙觉寺,在县城东南二里,元中统五年建,万历十六(1588)年邑人董用威修。”“青罗观在县治南,元时国戚皇姑学道之所,后为真人丘处机道场,赐名迎祥观,今为青罗观,习仪之所,道纪司附。”“僧纲司”“道纪司”,是地方衙门管理寺院和道观的机构,官员由朝廷或地方衙门任命。“僧纲司”,负责管理地方所辖的寺院和僧人。“道纪司”,负责管理地方所辖的道观和道士。莱州府的僧纲司设在资圣寺,道纪司设在青罗观,也说明资圣寺、青罗观在莱州府所辖寺观中的地位和影响。
前面提到“受宣堂在府东南隅,道人丘处机修炼于此”,“受宣堂”就在青罗观内,据清《掖乘》记载:“青罗观,(莱州)城东北隅,金泰和八年(1208)丘处机所建,道场赐名迎祥观,后人于其地筑受宣堂,元时为国戚皇姑修道之所。洪武丁卯(1387)改名青罗观。……观中今有王重阳石像、王重阳诗词碑刻、王重阳画像诗刻、石刻二种。”[110]“王重阳”,全真道的创始人,全真道第一任掌教,点化和培养了丘处机等全真七子。“王重阳诗词碑刻”,题有“终南山重阳真人亲眷碑”字样,《重阳真人结物外亲眷诗》注有“长春子书”。说明王重阳的诗词是长春子丘处机书写的。“石刻二种”,有“长生子书”字样,说明是长生子刘处玄书写的。《掖乘》成书于清道光丁亥年(1827),说明当时这些珍贵的文物都还在,可惜随着后来青罗观的被毁现在不知流落何方?
金德承在《天槎大观》中还提到了“幸台”:
幸台,汉武东游海,访安期生登此,当时碑刻尚在。[111]
“幸台”,《明一统志》卷二十五《莱州府•宫室》也有记载:“幸台,在府城南门,汉武帝东游海上访安期生,登此台。当时碑刻尚存,今已剥落。”明《万历莱州府志》卷六《古迹•掖县》也有类似的记载:“幸台,汉武帝尝游海上访安期生,幸此台,故名。碑刻剥落,即今城南门也。掖(城)西南二十里又有幸台社。”说幸台,“即今城南门也”,是说莱州城南门建在幸台的原址上。这一点,清代《掖乘》也有说明:“幸台,今城南门其地也。汉武帝东游海上访安期生,幸此。县志曰:碑刻犹存。雍正八年,重修城楼,遂失所在。”[112]元代《齐乘》卷五《亭馆下》也记载了“幸台”:“幸台,莱州城内,相传汉武帝东游访安期生所筑,有碑,字灭不可考。”[113]这也说明“幸台”碑刻的历史非常久远了,元代就风化得“字灭不可考”了。如果真是当年“汉武帝东游访安期生所筑”,即使是字迹全无,也是非常珍贵的文物。《明一统志》《万历莱州府志》和明末朝鲜使臣的记载都说“幸台”碑刻还在,只是字迹“剥落”而已,雍正八年重修城楼时,将“幸台”碑刻遗失不知所终,着实可惜可叹!
金德承在《天槎大观》中还提到了“轮井”:
轮井在北,石穴下洞,井口如轮,无雕琢痕。[114]
金德承关于“轮井”的记载,应来自《明一统志》卷二十五《莱州府•山川》:“轮井,在府城东北一十里,石穴下洞,井口如轮,无雕琢痕。”《万历莱州府志》卷二《山川》也有相同的记载。“轮井”,在宋代的《太平寰宇记》和元代的《齐乘》里都有记载,《太平寰宇记》卷二十《莱州府•掖县》记:“轮井,在县东北十里石穴下,洞于泉口如车轮,无雕琢之迹,自然而成。故号‘天井’,能兴云雨,人多祈祭。”[115]《齐乘》卷五《亭馆下》记:“六龙湾龙祠,莱州北,前有轮井,石口如车轮,号曰天井,能兴云雨。金泰和间(1201—1208)祷澍有感碑记存焉。”[116]这说明“轮井”至少在宋代在当地就有很高的知名度了。明代朝鲜使臣金德承能记下“轮井”,应该也是基于“轮井”在历史上就有很高的知名度。
清代《掖乘》对“轮井”也有记载:“轮井,城东北十里淇水村之阳,石穴下及于泉,深丈余,旁有一窍,水最甘冽,村人汲引者甚众,投之以石,匉訇作声。今居民于其口加砖石甃之,殊之天然之观。村人呼为昆仑井,盖因轮字而讹之也。平衍之地,周围皆土,此独为石,亦异也。……《齐乘》曰:‘金泰和间祷澍有感碑记存焉’,碑记今无存。”[117]“淇水”,我们在第四章第三节(三)会提到,也是明代朝鲜使者路经莱州境内的一个铺舍,淇水村现属莱州城港路街道办事处管辖。《掖乘》的记载说明二点,在清道光年间,轮井井口已做人为加工,已没了“天然之观”。二是《齐乘》记载的轮井旁的碑记也已“无存”。《掖乘》的作者为之惋惜,我们后人当然更有同感。
本章承接第二章,也是写明代高丽、朝鲜使臣对莱州文化景点及遗迹的观感。第二章写的是朝鲜使臣路过莱州时总的印象,即对莱州宏观的一些看法,本章则具体到每一个文化景点及文化遗迹,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印证,都说明了莱州有着绚丽多彩的山海风光,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莱州的文化景点及文化遗迹,给明代朝鲜使臣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朝鲜使臣留下的咏莱州文化景观的诗文,既是留给莱州的重要的宝贵史料,也是明代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注释】
[1][清]《乾隆掖县志》卷之二《学校》。
[2][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5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第439页。
[3][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7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57-159页。
[4][明]《万历莱州府志》卷三《学校•学田》。
[5][明]《万历莱州府志》卷三《学校•学田》。
[6][明]毛纪《鳌峰类稿》卷九《记》,北京图书馆明嘉靖刻本,集45-72。
[7][清]《乾隆掖县志》卷之七《艺文•记》。
[8][韩国]《天坡集》第二,《韩国文集丛刊》第95辑,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92年,第47页。
[9][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4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40页。
[10][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4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02页。
[11][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4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06页。
[12][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4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11页。
[13][宋]吕祖谦《东莱别集》卷十《尺牍四•与陈同甫》,《四库全书》第115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4页。
[14][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0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370页。
[15][韩国]《沙西先生文集》卷一,《韩国文集丛刊》第67辑,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90年,第38页。
[16]《宋史•吕本中列传》
[17][韩国]韩国首尔大学馆藏影印本《苔川先生集》卷二《朝天录》,第21页。
[18][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6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版,第161页。
[19][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4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版,第257页。
[20][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5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第439页。
[21][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5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第439-440页。
[22][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6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第161页。
[23][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7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59-160页。
[24][清]毛贽《勺亭识小录》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本,25-131页。
[25]《嘉庆续掖县志》卷四《艺文•记》
[26][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7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159-161页。
[27][唐]李德裕撰《李卫公别集》卷九、卷十,《四库全书》第107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0、296页。
[28][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7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90页。
[29][韩国]《天坡集》第二,《韩国文集丛刊》第95辑,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1992年,第53页。
[30][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3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93页。
[31][清]侯登岸《掖乘》卷之十四《园亭一》,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19-341页。
[32][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6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版,第64页。
[33][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6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第161页。
[34][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66页。
[35][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2-53页。
[36][明]任万里《海庙祀典考》,《乾隆莱州府志》卷十四《艺文•考》。
[37][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第308页。
[38][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416页。
[39][元]于钦撰《齐乗》卷五《亭馆下》,《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598页。
[40][唐]萧嵩等撰《大唐开元礼》卷三十六,《四库全书》第64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5页。
[41][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 中华书局1985年,第26页。
[42]孙家洲、杜金鹏《莱州文史要览》,齐鲁书社2113年,第83页。
[43][明]毛纪撰《海庙集》,山东省博物馆藏,清康熙六十年毛霦钞本。
[44][清]侯登岸《掖乘》,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19-157页。
[45][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4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502页。(www.zuozong.com)
[46][清]毛贽《勺亭识小录》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本,25-134页。
[47][清]《乾隆莱州府志》卷四《学校•掖县儒学》
[48][清]《乾隆莱州府志》卷四《学校•府儒学》
[49][清]《乾隆掖县县志》卷二《学校•学田》
[50][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14册,韩国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第247页。
[51][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6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第63页。
[52][宋]潘自牧《记纂渊海》卷十七,《四库全书》第93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10页。
[53][元]于钦撰《齐乘》卷一《山川》,《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524页。
[54][清]毛贽《勺亭识小录》卷一,山东省图书馆藏本,25-120页。
[55]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37页。
[56]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5页。
[57]刘海粟《读郑道昭碑刻五记•郑道昭书法艺术初探》,载《云峰诸山北朝刻石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85年,第12页。
[58]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榜书第二十四》,《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856页。
[59]叶昌炽撰,柯昌泗评《语石》,中华书局1994年,第426页。
[60]祝嘉《书学史》,中国书店出版社1987年,第136页。
[61]孙家洲、杜金鹏《莱州文史要览》,齐鲁书社2013年,第139页。
[62]白如祥辑校《谭处端 刘处玄 王处一 郝大通 孙不二集》,齐鲁书社2005版,第232页。
[63]白如祥辑校《王重阳集》,齐鲁书社2005版,第344页。
[64]白如祥辑校《谭处端 刘处玄 王处一 郝大通 孙不二集》,齐鲁书社2005版,第233、178页。
[65]白如祥辑校《谭处端 刘处玄 王处一 郝大通 孙不二集》,齐鲁书社2005版,第241页。
[66][清]侯登岸《掖乘》卷之十四《园亭一》,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19-341页。
[67][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6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第62-63页。
[68]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第421页。
[69]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第424-425页。
[70]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第421页。
[71]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第427、437页。
[72]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第188页。
[73]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第194页。
[74]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第420页。
[75]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第247页。
[76]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第457、458页。
[77][清]《钦定日下旧闻考》,《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98册第464页。
[78]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第200-218页。
[79]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第414、436页。
[80]赵卫东辑校《丘处机集》,齐鲁书社2005年,第565页。
[81]卿希泰《中国道教(第一卷)》,知识出版社1994年(沪版),第172-173页。
[82]丁鼎《昆嵛山与全真道》,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9页。
[83]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联书社2009年,第228页。
[84]钱穆《国史新论》,三联书社2005年,第146页。
[85]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联书社2009年,第234页。
[86][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6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第63页。
[87][清]侯登岸《掖乘》卷之一《园亭一》,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19-166页。
[88][清]侯登岸《掖乘》卷之一《园亭一》,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19-166页。
[89]陈垣编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53页。
[90]孙家洲、杜金鹏《莱州文史要览》,齐鲁书社2013年,第200-201页。
[91][清]侯登岸《掖乘》卷之十四《园亭一》,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19-167、168页。
[92][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6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第63-64页。
[93][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两宋名贤小集》卷三百六十三,《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64册第737页。
[94][宋]张君房《云笈七籖》卷一百八《列仙传•安期生》《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61册第250页。
[95][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6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第63页。
[96][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416页。
[97][清]侯登岸《掖乘》卷之二《山川二》,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19-177、178页。
[98][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6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第64页。
[99][宋]陈思编,[元]陈世隆补《两宋名贤小集》卷三百六十三,《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64册第759页。
[100][清]侯登岸《掖乘》卷之十四《园亭一》,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19-217页。
[101][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6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第64页。
[102][宋]杜绾撰《云林石谱》卷中《莱石》,[清]沈心《怪石录•卷第四十二》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本,第5页。
[103][清]沈心《怪石录•卷第四十二》吴江沈氏世楷堂刻本,第6页。
[104][清]侯登岸《掖乘》卷之十四《园亭一》,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19-174页。
[105]《魏书》卷五六《郑道昭传》。
[106][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6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第63页。
[107][清]倪涛《六艺之一录》卷九十四《石刻文字七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832册第38页。
[108][元]于钦撰《齐乗》卷五《亭馆下》,《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598页。
[109][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6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第63页。
[110][清]侯登岸《掖乘》卷之十四《园亭一》,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19-338页。
[111][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6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第63页。
[112][清]侯登岸《掖乘》卷之十四《园亭一》,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19-217页。
[113][元]于钦撰《齐乗》卷五《亭馆下》,《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598页。
[114][韩国]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6册,韩国首尔:尚书院2008年,第64页。
[115][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中华书局2007年,第416页。
[116][元]于钦撰《齐乗》卷五《亭馆下》,《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598页。
[117][清]侯登岸《掖乘》卷之十四《园亭一》,山东省图书馆藏稿本,19-187、188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