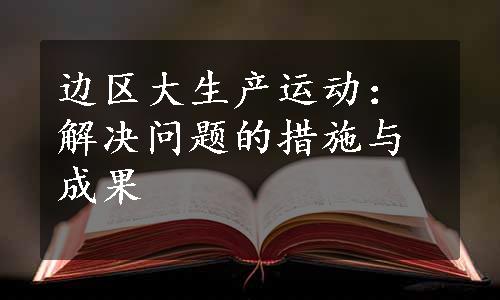
为了打破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提出适当地增加人民负担。1940年,实收公粮97354 石,占总收获量的6.38%,并陆续开征了畜产品税、药材税等。1941年,实收公粮20.2 万石,占总收获量的13. 85%。[30]此外,边区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还发行了数百万元的公债。而边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差,生产方式又很落后,农产品的剩余率极低,这自然导致人民负担过重,因而也产生了一些不满情绪。中共中央对问题的严重性很快有了认识,采纳了李鼎铭先生的“精兵简政”建议,同时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的精神指导下,专门成立了经济建设研究会、经济指导处,有计划、有重点地逐步加大发展生产的力度,尤其是农业经济。当时边区外援断绝,工业能力极弱,但农业还有一定基础,加之还可以利用军队垦荒,尚有潜力可挖。所以说边区政府将抗战经济着重点放在了农业上,并尽量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不失为一种良策。当时边区政府为了保证大生产运动的顺利进行,采取了积极鼓励民间劳动互助、强化安置移民、改造“二流子”、机关部队参加生产、进行劳动竞赛等一系列措施。
边区的劳动互助活动开始较早,但效果不是太明显,大生产运动后才大规模推广开。边区移民安置工作1941年后有了新的变化,边区政府为了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一方面仍积极安置外来移民,一方面有组织地对边区内的人口进行合理迁移,主要是将人口密度相对较大的绥德地区的人口迁移到延属、关中、三边、陇东等人口稀少之区。1942年,从绥德地区移出417 户、1483 人。1943年,安置移难民又是一个高峰,达8570 户、30447人,其中绥德地区移民为1836 户、4961 人。[31]在整个抗战期间,边区共安置移难民63850 户、266619 人。[32]有效地改变了边区许多地方地广人稀的局面,增加了边区的农业劳动力。如延安县,19 42年人口从1 9 3 7年的3 3 7 0 5 人增加到6 4 2 9 2 人,在新增加的31587 人中,有29704 人是移难民。[33]从中可窥见移难民在增加边区农业劳动力中的作用。
当时边区内还存在不少好逸恶劳、不务正业的社会闲散人员(老百姓称其为“二流子”),这些人既是旧的社会制度的受害者,同时他们又在不断地给社会制造麻烦,甚至危害社会。把这些人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新人,既挽救了他们本人,又可化消极力量为积极力量,为社会造福。早在南梁政府建立之初,就开始对“二流子”进行改造,提出争取与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后来,在陕北延安等地也有改造“二流子”活动。边区开展大生产后,改造“二流子”活动也越来越普遍。1942年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后,对“二流子”进行改造逐步系统化,先是对“二流子”进行确认和区分,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对策,对违反政府法令、危害社会的采取强制或半强制措施,对一般好逸恶劳、不务正业的,则采取寻保人,由保人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实行领导负责,群众监督评议,帮助那些确有困难的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将说服教育、监督、感化结合起来,使改造“二流子”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就。1943年,全边区共改造“二流子”5587 名,占总数的58.8%。[34]改造“二流子”活动对边区经济也做出了贡献,如1943年,华池县的138 名“二流子”,经过改造后,有92 人自己种地,22 人合伙种地,14 人揽工,还开荒608 亩。[35]
组织机关、部队参加生产开始于1939年春,边区政府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要求部分机关、学校、部队抽出半天时间参加农业生产。1941年初,边区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力度,驻边区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开荒生产,中央在边区的机关单位以及地方的各级机关单位都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去。1942年,大生产的效果已显现出来,当年比1941年少征公粮3.7 万石,使农民的负担也有所下降,这一成果更加鼓舞了边区的军民。1943年,留守兵团的部分伤病人员和不适合部队工作的人员、精减的机关工作人员都被动员从事生产。1944年,三五九旅率先实现了“耕一余一”(即耕种一年,可剩余一年的口粮)的目标,成为边区大生产的一面旗帜。边区的许多政府机关、学校等单位也有了一定的自给能力,一般可自给两三个月的粮食。机关、学校、部队参加农业生产,为整个边区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自给做出了贡献。
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各地还开展了劳动竞赛活动。1942年,延安劳动英雄吴满有的事迹被报道后,边区政府予以很高的评价,号召各地学习推广。1943年春,边区的《解放日报》发表了《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还先后发表文章对劳动竞赛进行宣传,并介绍了边区涌现出的劳动英雄的事迹。朱德总司令也号召边区部队开展劳动竞赛活动。边区各县、各分区先后都召开了大会,对劳模进行表彰奖励,劳动竞赛在边区全面铺开。如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代表政府奖励华池县的开荒英雄张振才耕牛1 头,这大大地调动了边区民众的生产积极性。边区政府为了总结生产经验,进一步发展边区生产,1943年11月,在延安召开了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67 名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的劳动英雄受到了奖励。张振才还受到毛泽东同志的接见,他所在的城壕村因做到了“耕一余一”,被授予模范村称号。大规模的劳动竞赛对边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大生产运动,到1943年,边区的粮食已自给有余。1940—1945年,边区新垦粮田250 余万亩,大部分农民做到了“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可剩余一年的口粮)。为解决穿衣,棉花种植面积也在边区迅速扩大,1939年在沿黄(河)区逐步推广植棉,到1943年达15 万余亩,“比1939年增加了约40 倍”[36],在关中分区的新正、新宁和陇东分区的合水、庆阳等地也试种了棉花。1945年,陇东分区植棉30000 亩,收获棉花30 万斤。[37]虽然一些地方棉田产量低,但在当时解决边区穿衣方面还是发挥了作用(参见1940—1945年边区的粮棉生产情况表)。边区农村经济的重要行业——畜牧业也快速发展起来(参见1940—1945年边区的家畜存栏表),这对解决农村耕畜和边区运输,以及对边区外贸易都有很大的积极作用。此外,其他一些副业生产也在边区兴起,如安定、绥德、延长等县养蚕业兴起。仅绥德分区各县在1942年养蚕户为9116 户,出茧37270.8 斤。1943年,绥德分区养蚕业进一步发展,养蚕户达11798 户,出茧54777 斤。[38]
1940—1945年边区的粮棉生产情况表
注:1944年棉花种植面积与产量为27 个县的统计数字。
本表根据南汉辰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 编,85 ~87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一文的相关资料编制。
1940—1945年边区的家畜存栏表(单位:头或只)
注:本表根据南汉辰的《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工作》(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 编,98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一文的相关资料编制。
总的来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取得的成绩是很大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边区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困死边区的企图,基本保障了边区经济的稳定和抗日军民的需求。在抗战八年中,边区人民总共提供公粮1014544 石,人均年负担1.3 斗。据不完全统计,边区人民还交购粮70119 石(缺1937年数)。[39]此外,边区人民还提供了大量草料、棉花等。这对于仅150 万人口,又十分贫瘠的边区而言,人民所做出的自我牺牲是巨大的。
【注释】
[1]《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 编),34 ~35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陇东的土地革命斗争情况》,见《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12 页,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2。
[3]《陇东分区1937年以来的减租工作总结(节选)》,见《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140 页,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2。
[4]《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见《六大以来》(上),798 页,人民出版社,1981。
[5]《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见《六大以来》(上),1088 页,人民出版社,1981。
[6]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767 页,人民出版社,1991。
[7]《陇东分区1937年以来的减租工作总结(节选)》,见《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143 页,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2。
[8]《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见《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106 页,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2。
[9]《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见《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8 辑),476 ~478 页,档案出版社,1988。
[10]《陕甘宁边区的土地问题》,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 编),222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11]《陇东分区1937年以来的减租工作总结(节选)》、《1944年春耕前关中地委关于减租工作的报告(节选)》,见《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147 页、224 ~225 页,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2。
[12]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财政概况》,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 编),8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13]《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456 ~457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14]《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456 ~457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www.zuozong.com)
[15]《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456 ~457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16]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928 ~932 页,人民出版社,1991。
[17]中共西北局研究室:《边区的劳动互助》,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 编),25 ~26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18]见《华池县志》,101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19]《边区劳动互助的发展》,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 辑),461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20]《张振财和模范的城壕村》,载《解放日报》,1944年1月3日。
[21]见《华池县志》,101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22]中共西北局研究室:《边区的劳动互助》,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7 编),35 ~36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3]王政新:《陕甘宁边区的粮食工作》,见《陕甘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273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24]西北财经办事处:《关于财政工作总结》,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 编),22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5]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215 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
[26]西北财经办事处:《关于财政工作总结》,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 编),22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7]《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事业概述》,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 编),400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8]《边区羊子的发展问题》,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 编),103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29]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92 页,人民出版社,1991。
[30]王政新:《陕甘宁边区的粮食工作》,见《陕甘边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273 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31]《陕甘宁边区的农业》,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 编),644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32]《陕甘宁边区社会救济事业概述》,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 编),400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33]吴力勇:《一支生产劳动军在延安》,载《解放日报》,1943年2月22日。
[34]《边区二流子的改造》,载《解放日报》1944年5月1日。
[35]见《华池县志》,103 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36]《植棉问题》,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编),593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37]见《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128 页,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90。
[38]《绥德分区四三年养蚕工作总结》,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2 编),166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39]《陕甘宁边区历年粮食收支对照表》、《陕甘宁边区历年财政收支对照表》,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 编),90 页、89 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