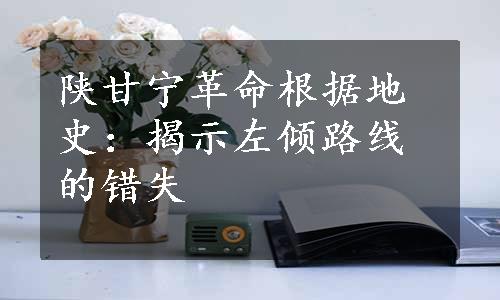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与后来在党内统治时间较长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虽然有形式上的差别,但其实质都是严重脱离中国社会的现实。王明虽也曾打出过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但主要是为了所谓反“右”,这实际上是把“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推向极端。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就是这种极端“左”倾思想的体现。这些错误路线在西北根据地的推行,必然要同注重实际的西北根据地的许多同志发生冲突,其分歧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政治路线的分歧。大革命失败后西北革命力量受到了一定损失,但因西北党组织在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前已有预感,苏联友人、时任冯玉祥部顾问的乌斯曼诺夫也及时向中共陕甘区委提出了应变建议,加之冯玉祥初期并不赞成蒋介石的屠杀政策,这就为西北革命党人提供了时机,采取了适时退守政策,将已暴露的同志尽快转移,各级党组织暂时转入地下活动。到“七一五”大清党时,陕甘党组织的退守工作已基本完成,绝大部分已成功地隐蔽或转移,为西北革命斗争保存了重要的骨干力量。特别是西北的党组织较成功地利用了西北地区小军阀众多、矛盾重重,同国民党中央也往往貌合神离等因素,在地方军阀武装中成功地潜伏下了一批革命党人或革命的同情者,这就为西北后来的武装斗争创造了良好条件。
1927年中共汉口紧急会议后,西北党组织明确提出到农村去、到军队去,利用中共地下党员大力开展兵运工作。从1927年10月到1932年底,先后发动武装起义、兵变达70 余次。这些武装斗争虽有不足之处,但对于打破西北的白色恐怖,重振西北人民的革命斗志作用巨大。后来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西北党组织对兵运工作仍十分重视,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分化瓦解敌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如谢子长、刘志丹等都亲自从事兵运工作,刘志丹还成功地控制了陕北保安县民团、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将其改造成革命的队伍。
除了兵运工作,陕甘的党组织还针对这些地区哥老会、土匪众多,如不妥善解决,则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很难成功的情况,对他们采取了分别对待、争取与打击相结合的办法,较成功地解决了会、匪为害的问题,并壮大了革命力量。如在南梁一带,刘志丹说服了黄龙山“大王”郭宝珊率部投向革命,对周围地区的哥老会会首“郑大爷”、“马大爷”等,甚至一些地方民团势力都进行了说服教育,使其为根据地做了许多好事。刘志丹同志还常告诫同志:“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24]西北地区革命党人将革命原则与灵活的斗争策略相结合,在当时来说是很得当的,确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当时的“左”倾路线代表,仅凭本本和主观想象去指导革命。他们对当时西北地区形势的复杂性,以及革命的艰苦和曲折性缺乏认识,对刘志丹、谢子长等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将高度革命原则和灵活的实际斗争策略相结合的做法不能理解,单纯强调阶级阵线,纯之又纯的“工农革命”。对于收编的一些农民起义武装不是进行教育和引导,而是采取排斥的态度,认为“土匪色彩浓厚”,甚至“缴枪”。为了达到红军应以工人为主的目标,脱离实际地设想要在西安招3000 名工人,去改造根据地的红军构成成分。并因此攻击刘志丹等勾结军阀、白军军官。他们不顾客观实际,不对敌我双方阵营进行分析,更不懂得瓦解敌人的重要性,一味蛮干,结果是四方树敌,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弄得红军供应无着,立脚艰难,使得西北根据地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其次,是军事路线的分歧。在开展武装斗争方面,早年陕甘共产党人进行了多次尝试,不断地总结经验,创造性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斗争方略。清涧起义失败后,开始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1928年渭华起义中,又认识到武装斗争同工农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性,在陕西东部地区曾大力发动群众,创建苏维埃政权,后又逐渐地认识到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刘志丹同志对此进行了认真总结,认为“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兵运失败的最根本原因[25]。不久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领导陕甘游击队,在陕甘边界开创了照金根据地,依托桥山同敌人周旋。而当时“左”倾路线代表者根本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事实,先是要红军北上,打通“国际线”,后又要南下打关中。刘志丹等同志据理力争,但被扣上“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的帽子,并被解除职务。“左”倾路线的指导,很快导致红二十六军覆没和照金革命根据地丧失。
1933年11月,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会议上,刘志丹同志沉痛地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在敌人力量较薄弱的桥山中段再创革命根据地。并为了广泛动员群众,扩大革命影响,在陕甘边地区开辟了三路游击区,逐步形成了以南梁为中心的新根据地。不久陕北根据地也创立成功,西北根据地再次兴盛起来。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再次泛滥,又给根据地的发展蒙上了阴影。他们否认敌强我弱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大反“游击主义”,主张红军应该“正规化”,同敌人打拼消耗的阵地战,并迫害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致使根据地人心浮动、对敌人的“围剿”难以打破。(www.zuozong.com)
最后,是关于土地革命路线的分歧。土地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不进行土地革命,便不能动摇封建主义的根基,也无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因而在1928年5月渭华起义中,就把打倒土豪劣绅、实现“耕者有其田”作为革命的重要任务,并在渭南崇凝苏维埃政权内设立了土地委员会,着手准备在附近50 余个村庄分田地,后因起义仅两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其后,西北革命党人通过多次斗争实践,进一步认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谢子长曾指出,“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要走井冈山道路,要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26]。1932年10月,红军在渭北武字区南原进行了分配土地的试验,1933年,又在照金根据地进行了土地分配,但不久这两块根据地均失陷。
1933年11月,南梁根据地开创后,在中共陕甘特委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工作,依据《井冈山土地法》的原则,结合西北地区实际和过去的斗争经验,确定了当时土地革命的方针,重点放在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上。对富农则征收其多余土地,一般不触及中农利益。此外还结合西北地广人稀的特点,分地仅限于川地、塬地。并提出分配土地应在革命政权巩固之区进行,对于游击区多限于分浮财。当时的这些基本方针较好地适应了西北革命斗争的实际,打击了封建势力,激发了广大贫雇农的斗争热情,同时又团结了中间力量。1934年7月,陕甘边特委在《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中,进一步明确要求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到1935年,土地革命在陕甘边的华池、庆北、新正、新宁等县全面铺开,有力地动员了广大民众,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陕北根据地也在1935年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将土地革命作为根据地革命的中心任务,并正式颁布了《土地法》。
对待土地革命问题,“左”倾路线代表人物,看不见蕴藏在农民阶级中的巨大反封建力量,对于动员农民群众,创建农村根据地,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则认为是极其错误的观点。错误地认为:“在中心城市爆发了伟大的工人斗争。必然形成全国革命高潮。”[27]王明在反“立三路线”的旗号下,把反资本主义同反帝、反封建并列,实质上是否认中国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种认识下,民族资产阶级、富农均成为革命的对象,因而其在西北地区的执行者指责刘志丹等一批实事求是的同志,攻击西北革命根据地土地政策右倾,是“富农路线”。特别到1935年秋,“左”倾路线在西北根据地恶性发作,为了全面推行其“消灭富农”等“左”的政策,借“肃反”之名扫除绊脚石,把斗争矛头转向了党内,迫害、打击坚持正确主张的同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根源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历史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无法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看不到中国社会封建势力的强大,片面地夸大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以及城市和工业无产者的作用,从而在阶级关系上,不但忽略了广大农民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特殊重要作用,而且反对同其他一切反封建力量联合,打倒一切,到处树敌,严重地孤立了革命力量。在革命策略和军事路线上,则过分强调城市暴动、进攻路线,陷入严重的单纯军事冒险。
此外,“左”倾路线代表者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是教条主义的,他们不是把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中国社会,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是孤立地、静止地去研究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作为一种僵死的教条,特别是将苏俄革命模式生搬硬套,凭主观想象来处理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列主义。“左”倾路线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推行,以及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也进一步说明了这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大敌。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凡在这三件事上犯了严重错误的时候,革命就受挫折”[28]。而“左”倾路线代表者恰恰是在这些革命的关键问题上犯了错误,因而用他们的路线指导革命,革命事业受挫就在所难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