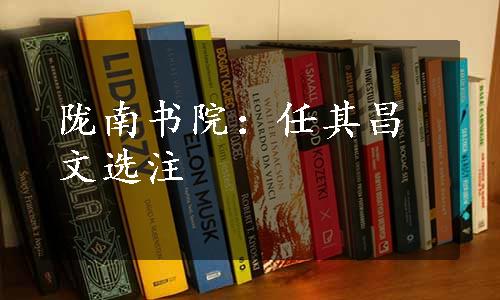
王安石论
【题解】本文认为前人对王安石的评价中,只有司马光的“不哓事”最为中肯,进而历数其不晓先王治国之道、不晓行政用人听言之事、不晓百姓生计之艰难,乃至最终造成“本欲强宋”而实则“祸宋”的后果。虽然并一定结论公允,但观点明确,同样发人深省。
后世之论王介甫者曰:“挟经术以误苍生。”夫介甫之于经,假也,非挟也,且又无术,术也者,变而通之以尽利者也。介甫惟不知此,故以之乱天下。其在当时,或曰奸邪,或曰奸恶。夫就其基祸而言,目之为奸,介甫虽不得而辞,而原其心,则本欲强宋非欲祸宋。目之为奸,介甫犹可得而辨也。惟司马温公[1]所云“不晓事”最为得之。若云狠愎[2],云引亲党、据要津、排异己、固权宠,亦非有他端,皆由其不晓事而推而致之者也。
夫先王之治天下也,本天之道,分地之利,尽人之情,制礼作乐,敷政明刑,必求不过乎物,不拂乎人而止,终不敢奋其私智,悍然恣睢[3]于天下。故夫诗书所载,自朝廷以达州巷,自于耜[4]以至出车[5],皆本之君民一体之意,念其室家之故,曲体其父母妻子缠绵悱恻之情。其朝廷之上,则师师济济[6];闾井之间,则皞皞熙熙[7],以故享国长久。有以诒翼[8]其子孙而后之继有天下者,亦得师其善政遗风以靖其民,阅万亿年而不敢失坠,则所谓经者是已。
介甫当宋政宽弛之后,奋然欲有为于天下。取祖宗之法度一举而灭裂之,创立新法,不究利害,欲立功而先犯众怒,欲牟利而重朘[9]民生。犹复掩其卤莽,借口周官。薄公议为流俗,仇正言为诬罔,遂令大臣结舌,台谏[10]窜逐,外至州县史稍知自爱亦纷纷而思去。是何为者也?夫我之所是而人举以为非,吾思焉,而必欲得其所为非。我之所非而人偏以为是,吾思焉,而必欲得其所为是。舍己从人,不执成见,可否得失之故可渐决于帷幕之内,而吾之所惓惓[11]者亦可以万全而无憾,此晓事者之事也。虽圣人岂有过焉?介甫纳天下于怀抱,而于理势之曲折,未尝一经其筹划,私心自计曰:“如此则富而利,如此则强而有功。”揣摩既穷,成效在目。预畏人之议之也,先取《周礼》之近似者附会而文饰之,以间执说者之口,而使无一毫憗[12]置于吾耳,以此不晓事而成为狠愎者也。于是,大臣如韩、赵、富、张、范、司马皆避位矣,而介甫则曰:“彼皆忌我之有功者也。”小臣如孔、苏、程、范皆谏疏日上,晓晓[13]不息矣,而介甫则曰:“彼皆负恃其才学欲挤我而自树勋绩者也。”追溯平生,执友尽与告绝,形影独立,无所藉手,遂推荐佥人[14]与为倡和。攻者欲力,守者欲牢。驯至元祐、绍圣[15],一反一覆,宵小盈朝,正士屏迹,而北宋亡矣。此非不晓行政用人听言之事,遂贻害于无穷者乎?
夫介甫学问文章夐[16]绝俦类,何以不晓事如是?是有故焉。昔者,周公之作《无逸》[17]也,曰:“先知稼穑之艰难,爰知小人之依。”此政事得失之源也。介甫家世虽非当时韩吕接踵卿相,然其父固官于州县者也。意介甫于阡陌圜阓[18]以及山林薮泽、边隅荒徼小民之生计之委琐艰危悉数而难终者,未尝一措心于其间,而幼而好学,亦必不分心于庶务,则民生之大利大害亦不过如牖中之窥天。以故读书愈多,聪明愈锢,欲其不执拗以基祸也,得乎?夫介甫不晓事既乱宋矣,后之不晓事而负其学问文章者,犹不少戒焉。可惧哉!
(《敦素堂文集》卷八)
【注释】
[1]司马温公:司马光,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死后追封为温国公。
[2]狠愎:凶狠固执。
[3]恣睢:放纵,放任。
[4]于耜:语出《诗经·豳风·七月》“三之日于耜”,本指农民修理农具,这里代指农夫。
[5]出车:指出门坐车的达官贵人。
[6]师师济济:指人互相尊敬,关系融洽。
[7]皞皞熙熙:形容人和乐自得。
[8]诒翼:犹诒燕.。《诗·大雅·文王有声》:“诒厥孙谋,以燕翼子。”谓为子孙妥善谋划,使子孙安乐。
[9]朘(juān):剥削。
[10]台谏:官名,主要职务为纠弹官邪。
[11]惓惓(quān):形容恳切。
[12]憗(yìn):损伤。
[13]哓哓(xiāo):争辩不止的声音。
[14]佥(qiān)人:小人。
[15]元祐、绍圣:宋哲宗年号。
[16]夐(xiòng):远。
[17]《无逸》:《尚书》篇章。
[18]圜阓:古代商业市区。
游麦积山记
【题解】本文以游踪为线,细致描绘了麦积山清雅秀丽的山水风光和精妙高超的造像艺术,抒写了安适恬静的心情。文笔流畅,语言清丽。
山在州治东南约百里,由甘泉镇东行十余里,两山环抱,曰峡门,峡尽稍平旷,突见孤峰侧立当路,左右无倚,形似农家麦堆。山顶有小浮图,房围松栝[1],葱茏委积,十余里外即扑人,听之如笙箫鸣于天上,盖松风也。
稍近,见石洞如蜂房,栈木似乱麻。至山足,石径屈曲,两垠皆山果,枝挂席帽,侧首乃可过,荨草厕其间,秋尚未萎,人触之辄被蜇。数转至瑞应寺门,僧延客入,饮以山茗。移榻天王殿外,面山坐,山色欲滴,久视之,岚光松荫,苍倩静深,殆染人襟袂。僧具午饭,饭已,导上牛耳堂。取道寺南,转西,路稍平,旁有山桃,食之甘酸。山半镌佛、菩萨像,长数丈,颜色剥落,略辨眉目,然日光所及,金碧犹灿然。北向入石门,壁间多前人诗碣,诗皆工,惟前明山右冯讷最著。又西向,石级十余层,缘崖建罗汉像约数百。西上又一石门,亦石级,崖间凿三洞,洞一佛像,皆石洞顶作井杆形,塓[2]以灰泥,书《法华经》[3],绘事极工。再西上,又一石门,亦石级,其地则石缺处补以木,洞亦三,像设如其下。再西向,又一石门,门外木梯三级,宽尺余,又缺漏,怯者多不敢登。入门,崖上洞亦三,地则全木无石矣。再西,无石门,又无外障,崖上架木栈,前人以太险,在崖上凿一石窟,竖裁尺余,横如之。蛇行入约十许步,出则登牛耳堂矣,石崖之最高处也,洞一,佛像亦一。再西,则又渐下,为洞尚十余。前明中,木栈为野火所烧,榱椽[4]间存,人迹绝不能至。闻僧徒有痴者曾入之,云内多石碑,惜不能名其字,吾意庾子山《佛龛铭》[5]其迹当在其内。寺中碑铭则后人所摹刻者也。崖上镌字殆遍,然皆不可读。惟宋人蒋之奇、游师雄题名了了可辨。游书四行,大七八寸,似颜鲁公。蒋书二行,反似黄山谷。何耶?第一洞外崖间嵌一断碣,文前十余行尚可读,大略言山上塔为阿育王八万四千宝塔之一,寺即起于其时,此无足辨。至云宋徽宗塔下得舍利数十、灵芝三十,本文即《葬舍利记》也,君荒臣谄乃至于此。碑首题曰:“秦州雄武军陇城县第六保。”此地迤西南,今尚名新军寨,而陇城县则不能指其处矣。寺东稍平衍[6],出门即塔院。再东,有菩萨殿三,楹已倾圮[7]。稍南而西,山石如象鼻临涧水,旁多细松,丛筱[8]障蔽若回栏。若在此筑一小亭,仰看山,俯听泉,亦佳境。然此地石冈曼衍,而寺僧名之曰:“莲花池”,可怪也。
次日平明,登石梁,梁在寺北山东,东西横亘约二百武,峭削如城墉,长松排列其上,如栅、如旌杠、如埤堄[9],根盘石罅,如蚪如龙“作其鳞之而”[10]。由寺门东北行,苦泥潦,盖梁下皆泉眼,常汩汩然。余告寺僧,疏泉开一渠,桥其上,亦由西而东之一曲也。于草树蒙茸[11]中得小径攀缘而上,有声戛然出草中,翳高树视之,雉也。既上又西向,时日方出,光映松桧,满山皆金翠晃耀。北望众山,参错盘亘,南北两涧,分流其下,水声琤琤,如鸣珩佩,倚树听之,久益清越。前视山上有人,在牛耳堂,衣裳飘飘,如挂于削壁之上,视身登时犹奇也。山阴及山顶,树木更茂,因王协亭使君邀往石门,遂不果至。
时同游者:苏绍卿、统武、张镜堂、登弟、张荩臣、思忠,门人刘子嘉、张育生也。
(《敦素堂文集》卷三)
【注释】
[1]栝(guā):古书泛指桧树。
[2]塓(mì):涂刷。
[3]《法华经.》:《妙法莲花经》简称,佛教经书。
[4]榱椽(cuīchuán):即椽子。
[5]庾子山:梁代诗人庾信,字子山。佛龛铭:《秦州天水郡麦积崖佛龛铭》的简称。
[6]平衍:土地平坦宽广。
[7]倾圮(pǐ):倒塌。
[8]筱(xiǎo):比较细的竹子。
[9]埤堄(pi ni):城上呈凹凸形而有射孔的矮墙。
[10]作其鳞之而:语出《周礼·考工记·梓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而:胡子。后人诗文中多用以形容须毛状的东西或指雕刻的鸟、兽、龙等的须毛耆鬣。此处比喻树根盘曲伸张之态。
[11]蒙茸:蓬松杂乱的样子。
游石门记
【题解】本文描写了石门远离尘嚣、幽深清丽的景致,篇末点明此山遭世人冷落的原因,含蓄表达了怀才不遇之感。笔触细腻,文字古雅清新,耐人寻味。
山在麦积北,于州治为正东。道里与麦积埒[1],远望之参错盘峙,色正黑,如浓云排空,树石皆不可辨。旁土山围之,益奇峭。至其麓,涧壑萦带,树林阴翳若无路。于石罅中弯环行,略通骑。树嵌石上,蒙密葱茏,青碧四合,日光穿漏下,有暗水,淙淙如奏金石乐,不可得而见也。凡三四转,至真武观外,地稍平,仰而观山,双峰对峙,高入霄汉,土人所谓南北峰也。真武殿阶前对树二柏,干大三四围,长不逾尺,枝叶丛细异凡柏,其状圆如瓜,大将及寻,奇木也。
次早,相率东向行,南北夹双崖,中流一水,崖上下及水涯皆杂木,檞[2]最多,松柏次之,间有细竹娟娟,孤洁如幽人在空山。其径以渐上,不甚崭绝[3],后行者视前人在树荫中,衣笠掩映如画图。凡南转三北转三,约四五里至山腰,两崖对峙如门,南北峰分划处也。峰皆孤耸,南峰之南又有一峰,谓北峰一、南峰亦一者,妄也。再东稍下,磴道一线,盖凿北峰为之者,尚可骑。再东数十武[4],则北向,大石突兀,西倚峭壁,东南临大涧,路在石上,有洼棱[5],略如阶砌,可措足,遂舍骑而步。至山神庙侧,坐石上憩焉。庙大一弓许,其北有大石在涧侧,移庙其上,于此构一亭,乃佳坐。少顷,仍北行,左崖右壑,路稍平,松毛厚数寸,赤蚁满地,好缘人衣履。再北,山罅大如渠,构桥其上,桥直南北,东西有栏槛。过桥,路又崎崟[6],攀缘上数十武,则祠宇在焉。三清殿前设木几坐,饮山茶数杯,乃上绝顶。顶势突起,高约十余寻,宽裁四寻,东西临涧壑,石色纯青,缘边皆小松。初登稍坦夷,十步外殊陡削,石面略似阶,级多凿成,铁索盘其上,怯者非此不敢举足。既登,四山皆低,天风浩然,真武祠南向稍宽敞。至祠后,则土山童童,欲来拱揖矣。曩闻缘涧至涧上皆古松,大数十围,间有自山底高出山尖者,浓荫翳日,根在石罅,如龙蛇夭矫[7],其涧又极深,天静无风,听之如龙吟虎啸,游人立其上,四望不知津涯。年来为道流,盗伐罄尽,喘汗而来,意兴顿索。坐殿角,少顷,遂相扶而下。再至三清殿小坐,续游所谓王母台三层楼者。由三清殿前东行,稍下,登磴道转而北,又东,不数武,苍崖如削,其上忽开丈许,构楼三层于其间。南向崖上杙[8]铁索平缀,凿石穴,西渐高,面壁直上,回视,则下临大壑,林阴荟蔚,寒涛浩渺,深不知几许。既登,楼极隘,以衣拂尘土,临槛坐,所视亦不远,遂下。又东,地形亦如象鼻,较麦积石鼻则绝大,袤长而圆,三面临深壑,地本宜亭、宜平栏,乃祠王母于此。门内向面山,一无所见,游者憾焉。问之,无他异。其东,石屏错峙,高几与南北峰埒,然薄弱,横看成岭侧不能成峰也。土人指缺处,谓《州志》“月出石门”即其处。信然欤?大抵此山无寸土,又少平地,亭台楼榭,位置固难,然太芜,略旷如奥如两者交失,岂柳州[9]所慨不在“丰镐鄠杜”[10]者耶?
同游共九人:先至者为王协亭使君、苏绍卿、副总兵刘成圆、镜堂之从子铎,后至者余与镜堂、荩臣、子嘉、育生也。
(《敦素堂文集》卷三)
【注释】
[1]埒(liè):等同。
[2]檞(jiě):古书上说的一种树木,即松心木。
[3]崭绝:险峻陡峭。
[4]武:古以六尺为步,半步为计。
[5]洼棱:低洼处。
[6]崟(yín):高。
[7]夭矫:屈伸貌。
[8]杙:用木桩楔入。
[9]柳州: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因为官柳州,故称柳州。
[10]丰镐鄠杜:语出柳宗元《锢姆潭西小丘记》文。丰:水名,流经长安。镐:地名,在今西安市西南。鄠(hù):地名,在今陕西户县北。杜:地名,在今陕西长安区东南。此四地都是当时京都长安附近的豪门贵族聚居地。此处谓石门景色优美,只可惜处地太偏僻。
张晚峰先生墓志铭
【题解】本文叙写了逝者家世及生平遭遇,详写其“笃于孝友”和挺身而出、保卫家乡的壮举,人物的神采风貌跃然纸上。叹息张公的早逝,言逝者的厚德必将有利后人。语言质朴,论说高亢有力,字里行间饱含对逝者高尚人格的尊崇和对蝇营狗苟者的批判。
公讳庆麟,字云卿,号晓峰。其先为关中三原人,明末西迁,遂隶籍秦州。高曾以来,世耕读,有隐德。父州学武生,喜读书,有儒者风。生子六,公其第五也。性端重,淡荣利,斥浮华,寡言词。与人交,守信义,不苟作煦煦[1]态,然劝善规过,济困扶危,始终一节,无少变易,与之游者皆以为有道人也。笃于孝友,封翁暮年,筋力衰,不良于行,公负而出负而入,侯颜色,侍盥栉,饮食必躬调而后进,如是者六年。及封翁殁,哀毁骨立,闭户不出,尽诚尽礼,识者以为难。有四兄一弟,敬爱臻至,食必同席,有未归者,常坐而待之。或间有疾苦,则日不食,宵不寐。弟尝疾笃,公终夜祷,或至叩头出血,以故,同炊者逾六十人,而门以内无间言,夫人孺子皆怡怡如也。
读书不为词华之学,观于外,似有不逮常人者,然当其决是非,别嫌疑,稠人广众之中,人各一言,言各一理,纷纷藉藉,势如乱麻,公徐出片言,曲中[2]窾会[3],人亦无有过之者。及退而考其行事,则言行相顾,无可指摘。故生平交游,多名下士,其于公之立身行事,皆退让以为弗及。
道光壬寅,补博士弟子员。己酉,举于乡。咸丰庚申,贡于礼部。同治壬戌,成进士,以知县用,分发直隶,当庚申之或售也。其四兄以子侄授经者多躬亲家事,势不能兼顾,属公早归,训家塾,公如言,遂不预廷试[4]。壬戌补试,后值逆回作乱,关陇骚然,公念乡井祸,又请假于吏部,归修坟墓。是时,西道承平越二百年,人不知兵,兵亦不能御贼,烽火四起,破名城、杀人民,不可胜数。吾州扼秦陇之交,东西南北皆当贼冲,州牧托公举行团练、保甲之役,而领其事者,各存意见,大都有名无实。值公归,乃请于上游,强以为西关团防长。公合众志,力阻异说,版筑攻击之器应时而集,城防得以无虞。托公殁于阵,嗣任者难共事,遂南游蜀,竟一年归,归即北赴畿辅[5],候补中间,听谳[6]于定州。热河大府皆以为能,委署广平,未赴任而卒。
呜呼!人生而师心,自用辄沾沾为大言以欺人,及窥其内而修于家,外而措诸身者,往往龃龉[7]不侔,一旦得志,则又文情饰貌以求富贵,营权利、享大名、登大耋[8],岂不比比然哉?而如公者,乃竟不令其有所表见而终,则又何耶?信如韩退之之所云“天者诚难测耶”!
公生于嘉庆二十三年二月初八日,同治七年五月初六日,卒于保定府寓斋,年五十有一。娶王氏,生子五。同治八年五月十五日葬于城北仁寿山之新阡[9]。
铭曰:“孰昌其德?孰掣其肘?天不假年,人将何咎?幽光必发,以贻厥后。”
(《敦素堂文集》卷四)
【注释】
[1]煦煦:和悦貌。
[2]曲中:完全符合。
[3]窾(kuǎn)会:要害。
[4]廷试:即殿试。
[5]畿辅:清代指直隶省的别称。
[6]谳(yàn):审判定罪。
[7]龃龉(jǔyǔ):抵触。
[8]耋(dié):年老。古指七八十岁的年纪,泛指老年。
[9]新阡:新筑的墓道。
与陶方之方伯书
【题解】本文先解释久未通信的原因及表达对陶公“仁心为质”的赞扬,后希冀对方训诲小儿,意旨在中间主体段表达,叙说自己编写《州志》的原委和进程,并通告与对方有关的一些编写事宜。平实的叙述中,恰当地表达出对收信者的崇敬之情,也尽显作者恭谨自谦的作风。
方伯大公祖阁下:
自棨戟[1]北指失候,兴居者三年于此矣,固由笔墨疏懒,然亦不欲以世俗寒暄语徒尘荃照[2]故耳。夏间闻以陕藩近莅青门,喜而不寐,有逾身受关中兵火之余,继以饥馑,生聚教训,理在得人。我公仁心为质,处得为之地,意白傅大裘裁法絮仁当不俟五考也。邻封多福,何快如之!
昌顽陋如故而精力日衰,昆季四人已失其二。晚岁薄福,顾影自伤,忝拥皋比[3],久忘惭恧[4],所幸门下多掇科名,天为谫陋[5]者藏拙,不可谓非幸也。去岁,敬甫方伯命修《州志》,似昌空疏,理当缩手,但以旧志将近百年,文献无征后起之咎,因请王大令权主持裁断,昌随其后,冀少误讹。自夏间施手,今略就绪,刻竣当在来岁。前在馨圃观察处,见手书论作志,陋习幸未全犯,然综核精审终亦未敢自信也。荒政、河堤、恤嫠系我公惠政之大者。河堤载入《建置》,荒政、恤嫠载入《食货》,《河堤记》、《恤嫠章程》载入《艺文》,惟《恤嫠章程》为公所自作。《河堤记》凡俚特甚,恐将来上累山斗高名耳。
小儿顽钝不学,乡捷忝叨计,偕北上过省之日,命其展谒,亲求训诲,敢乞示以学业,实维心愿。
(《敦素堂文集》卷五)
【注释】
[1]棨(qǐ)戟:油漆的木戟。古代官吏所用的仪仗,出行时作为前导。
[2]荃照:旧时书信中请人原谅的敬辞。
[3]皋比:本指虎皮。古人坐虎皮讲学,后指讲席。
[4]惭恧:羞愧。
[5]谫(jiǎn)陋:浅薄,浅陋。
史臆论
【题解】本文将盛衰治乱的历史变化比之于人的身体,贴切新颖。言史,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借史论今,指出前事是后事的“表的”,古人是今人的“龟鉴”,要他们总结历史经验,补偏救弊,开创一个新的中兴时期。(www.zuozong.com)
古今之大势,盛衰治乱而已。然盛有其所以盛,衰有其所以衰,治有其所以治,乱有其所以乱。如人之一身,血气调和则筋脉顺遂、皮肤充盈,虽有风寒暑湿之沴[1]气,亦不得而偶中。即中焉,可勿药而愈,亦可一药而即愈。惟或纵于酒色,朘[2]于思虑,伤于饮食,则其病先中于脏腑,而元气日以耗,气日以耗而血随之,则尩羸[3]之形成矣。于时,六淫害气,中之也易,而愈之也难。药一误投,则轻者剧,剧者死矣。
天下方全盛之时,朝政清明,民气和乐。文武之材随其大小而各有以效其用。此时,虽有敌国外患,挞伐之而已,必不能日侵月削,肆其强梁[4]而制吾生死之命。及夫承平岁久,朝野又安,君逸乐于上,日享无事之福;臣偷安于下,日忘匪躬之节[5],政之张者日以弛,事之治者日以荒。人才则日趋于钻营奔竞之途,名节颓而聪明日以耗。财用则日绌于中饱漏卮[6]之地,销蚀浸而府库日以空,又复致身[7]多歧,仕宦为壑。举天下之大,皆废其本业,而惟以身发财之汲汲。而肆习儒业者亦日习于谫陋,而不复知明经致用之为何事,而几欲效市上之攫金,病之剧也。至此,则气不举体,血不荣脉,而以病为命。偶有外侮,犹不知其贫且弱也,而姑为尝试。夫文不能谋也,视度支之可入吾槖者几何;武不能战也,视军需之可肥吾家者几何。战则辄败,和则不固,而国势于是乎岌岌矣。当此之时,苟不坐而待亡,必思所以振起之,而听言用人、修废举坠,名实又易于相贸。
则夫盛衰治乱之机,其以纷感而致危亡者多矣。古事具在史册,其无可征者乎?或曰:言今者必有騐[8]于古。是则然矣。然子之说,独言中兴,不及开创,何也?曰:开创之君,其在三代以上,则以圣人之德获天人之应,创制显庸[9],皆有百年必世之思,不惟诒厥[10]其子孙,且以师范[11]乎后世。其在三代以下,类皆聪明神武,身履艰难,其立法定制,虽有纯有驳、有短有长,均可以宏济苍生,肇造区夏,子孙善守之,亦足为百世不败之基。若守成者则不然,生而富贵,阔绝于民,其于人也,贤奸能否之分不能辨也;其于事也,裁决剖白之方不能精也。若继盛治犹可也,苟不幸值衰乱,则举朝无可依之人,守藏无可用之财,稽伍无可用之兵,盈牍无可采之言。否则,纷纷藉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责之以实则言富言强,皆不啻捉影而捕风,又其甚者,补偏救弊,不过一二事而止,而此倡彼和,举祖宗之法灭裂而废弃之,似真可收效于眉睫。呜呼!以此言中兴,中兴岂易易哉?
夫前事,后事之表的也;古人,今人之龟鉴也。愚故历征古帝王之中兴而有成与夫中兴而无成者,古诸侯亦附焉,数其行事,且备论其所以然,以就正于识盛衰治乱之正理与微机者,唐刘知己谓:“作史须才、学、识三者备具。”愚谓读史亦然,深自愧仄,故名臆说云尔。
古上邽任其昌自序。
(《敦素堂文集》卷七)
【注释】
[1]沴(lì)气:灾害不祥之气。
[2]朘(juān):耗损。
[3]尩(wǎng)羸:瘦弱。
[4]强梁:强横凶暴。
[5]匪躬之节:语出《周易·蹇》:“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指不顾自身利益而尽忠王室的节操。
[6]漏卮:有漏洞的盛酒器,比喻国家利益外溢的漏洞。
[7]致身:语出《论语·学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原谓献身,后用作出仕之典。
[8]騐(yàn):同“验”。
[9]显庸:明显的功劳。
[10]诒厥:参《王安石论》注。
[11]师范:可以师法的模范。
《史记·淮阴侯列传》后论
【题解】本文针对太史公“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矣”的观点,不袭成说,主张韩信之被冤死与不谦让无关,而是早在“欲王齐”和“固陵之困”时,就已引起刘邦忌恨而埋下祸基,韩信之死是功高盖主者的必然命运。分析透彻,且饱含对韩信的同情,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呜呼!淮阴侯之冤死也,岂尚有疑议哉?提孤军,亡四国,蒯通[1]开说,终不负汉,鸟尽弓藏,宗族歼灭,读史者至今为垂泣焉。顾史公以学道望之,此淮阴掇祸之由然也。谓不谦让则犹有说,何也?淮阴不谦让死,谦让亦死者也。其触高帝,启杀机,非谓不谦让之故也。方其初欲王齐也,高帝骂之曰:“吾坐困于此,日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为王。”逮张陈蹑足[2],虽假以空名,忮[3]心由此生焉。夫固陵之困[4],由诸侯之兵不至也。分地既定,淮阴即来,因之灭楚,汉业遂成。淮阴此时自谓算无遗策,功盖天下,而不知其祸基愈深,无可解免焉。何者?有分地而破敌,无分地势必以其主予敌,此高帝所介介焉,不能一日去诸心者也。
或曰:韩、彭[5]、黔楚令尹,所谓同功一体之人也,韩如此,彭、黔胡为者?曰:黔反矣。抑非高帝之所畏也。高帝之畏彭仲与淮阴埒然。自将其军,自食其饟,佐汉亡楚,厥功宜酬,虽劫取王封,究亦常情。淮阴受汉之秩[6],将汉之兵,食汉之食,解衣之惠,所求谓何?而乃乘危挟主,觊觎高爵,抱贞一之孤忠,蹈跋扈之逆迹,使君如负芒刺,其亦可哀也已。或曰:令淮阴被执以后,果不怨望[7],不矜伐[8],其亦免乎?曰:是不然。淮阴之能,高帝素知之,其功在人耳目,伐不伐自若也。高帝之待淮阴者如彼,能使其不怨望乎?其被诛也,高帝直不敢再信其心耳。故彭仲独死于吕后,若淮阴,则高帝之欲死也久矣。骤闻其死,而且喜且怜,怜其无反心也,怜其罪轻责重也。
然则,淮阴者必如何而后可?曰:乘人车者载人之患,衣人衣者怀人之忧,食人食者死人之事,竭才罄智,戡乱夷凶,功成受赏,王可也,后可也,即不王不后亦可也。淮阴沿战国之颓俗,谓王爵可胁取,抵死索求,屡以启雄主之忌,其于道何有焉?厥后,班孟坚[9]以不学无术目霍光[10],固不若史公之目淮阴为尤确云。
(《敦素堂文集》卷八)
【注释】
[1]蒯通:本名蒯彻,汉初范阳固城镇人,因为避汉武帝之讳而改为通。曾建议韩信与刘邦、项羽三分天下。
[2]张陈蹑足:张,张良;陈,陈平。语出《史记·淮阳侯记》:“张良、陈平蹑汉五足,固附耳语:‘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指张良、陈平建议汉王答应韩信的请求,立为齐王。
[3]忮(zhi):忌恨。
[4]固陵之困:固陵,地名,在今河南淮阳县西。楚汉相争时,刘邦曾被项羽困在固陵。
[5]彭:彭越(?—前196年),字仲,楚汉战争时汉军著名将领,西汉开国功臣,封梁王。
[6]秩:俸禄。
[7]怨望:怨恨,心怀不满。
[8]矜伐:待才夸功,夸耀。
[9]班孟坚(32—92):东汉辞赋家、史学家,字孟坚。继其父班彪基本完成《汉书》的写作。
[10]霍光(?—前68年):是汉昭帝时期的重要谋臣。
重修州城隍庙记
【题解】本文记述了州城隍庙的重修过程,描绘了城隍庙的位置、布局及其内部主要建筑,论说修建城隍庙的意义。虽篇幅短小,但内容丰富,结构谨严,且语言简练、平实。
光绪癸未秋九月,城隍庙土木丹艧[1]之工皆讫,州人任其昌为之记。曰:《礼》云:“郊祭天而社祭地,七祀[2]则有国门,蜡祭[3]旁及邮表、畷、坊、水庸[4]。”盖皆有功德于民,故教民美报焉。后世府州县城祀城隍,义当准诸此。
州城隍庙在州署西数十武,门临通衢,入则东西为长廊,旧僦[5]市人居,今斥[6]焉。北为乐楼[7],再北为重门,楼其上。入则为厦,东西列十曹,上为正殿,后为寝。又后为老母宫殿[8]。东祀圣母,西祀马王[9]。重门前之东祀药王[10],盖皆附着者。外旧有楼,西向,近购民居,向东建一楼以对之。楼后,北室设苍帝[11]位,南室设文昌位[12],中院砌砖炉为焚字纸也。迤北则主守者之居在焉。
庙之始于何年无可考,凡后所继治,碑石亦不尽载,年久渐有倾毁。己卯夏五月,地大震,榱栋欲欹[13],州人士悚惕于厥心,相议葺治。上自官府,下至民庶,城郭郊野,欢忭[14]乐赴,成事是期,不恤其资。于是欹者树之,倾者拄之,漫漶者敕而植之,剥落者洗而饰之,无废前规,足垂后观。是役也,经始于庚辰,越三岁乃蕆。事凡费缗钱若干,别书之。
夫城郭以卫民也,民得所庇而无以报其神,可乎哉?然已败而后治与甫败而即治则有间焉,故记其颠末以告夫供祭典守者。又前人谓神为西汉纪侯,脱高帝于荥阳者,夫生为忠臣,殁为明神,理宜有之。
(《敦素堂文集》卷三)
【注释】
[1]丹雘(huò):涂饰色彩。
[2]七祀:《礼记·祭法》:“王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指古代的七种祭祀。
[3]蜡祭:古代年终举行的祭祀百神的活动。
[4]邮表、畷、坊、水庸:邮表,古代交通要道及其交叉处竖立的路标。畷,田间小道。坊,街巷。水庸,水沟。此四者,古时均为祭祀对象。
[5]僦(jiù):租赁。
[6]斥:驱逐。
[7]乐楼:俗称钟鼓楼。
[8]老母宫殿:供奉骊山老母,即人类始祖女娲的宫殿。
[9]马王:一般俗称马王爷,全名叫“水草马明王”。道教的神明,全称“灵官马元帅”。传说长有三只眼,又称“三眼灵光”“三眼灵曜”。
[10]药王:孙思邈,世称孙真人,后世尊之为药王。
[11]苍帝:传说中主东方之神。
[12]文昌:即是文昌星飞临入宅的方位。这个方位在每一套住宅里都存在,只要是书房或书桌设于文昌位,则对于读书考试、写作、筹划均会有所裨益。
[13]欹(qi):倾斜。
[14]忭(bian):喜欢。
史平论
【题解】见于史书有“记事不平,论断不平”的弊病,本文指出读史者务必要“先酌其情理,后校其时势”,方能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持论妥当,说理透彻,举例丰富。
史平者何?所以平史之不平也。史何以有不平?记事不平,论断不平,皆其不平者也。或曰:作史者,千百世以上之人也,论史者亦千百世以上之人也,今于千百世以下而欲平千百世以上之不平,非偏见即臆说也,其可乎?曰:是不然。天下之变事也,其所以变则情理时势而已。事有是非,折之以理;理有通塞,遣之以情;情有向背,准之以时;时有顺逆,度之以势。如是,则古人如谋面,安在以往之事不可隃[1]付也?
夫作史者,褒一人,非必与其人有旧也,非必受其子姓之托也,非必受金馈米之龊龊然[2]也;贬一人亦然,非必怨其人与疾其后嗣也。而旁采异说,喜其新奇,中无春秋大公之道,备载简书则贤否冒乱[3]者多矣。其以六代而后,小说竞出,人自为书,传闻异辞辄成篇翰,谣诼[4]无端附着实迹,虽疑似无稽者,或久而犹存,而宵人[5]无良,恩怨间厕于其间。如魏泰[6]以王介甫为圣人,以章惇[7]为神仙,甚至宋人之所谓《碧云騢》[8]者,竟谤及范文正公。苟取此等以为载记,则史籍可尽废矣,而作史者或不免焉。呜呼!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起此之谓哉?
至如论史,宋人之迂刻可勿论已,《史记》为司马迁一家之言,览其辞或骇人听睹,原其义亦无舛焉。而东京之传之者,已斥其有大罪,至唐司马贞[9]作注,几欲洗垢索癣者,然犹曰:“《史记》隐而婉,较他史难读。”自班史以后,妄作毁誉者又复不少,则何也?甚如传论,本出一人,或数人共一事,而此伸彼缩,前轾后轩,不能测其意旨之所在。或偶率胸臆,肆为击断,或寓目皮毛,藉为口实,如此者又往往有之。后之读史者锲舟求剑,务徇前人,欲企通识,岂不难哉?
愚自髫岁[10]即喜读史,然苦无书。逮乡举后,假之友朋所谓廿四史,悉熟览焉。其间有始而信继而疑者,有始而疑久而疑不释者,不得已取其是非。先酌其情理,后校其时势,胸中若有所见焉,然不敢遽见之于言也。今老矣,联举其事,条而论之,以为生徒读史者之先资,使知不疑则不悟。凡读书皆然,不独史也。若夫全史之前后错忤,记叙乖疏,前人辨之而未尽者尤夥。愚学殖謭陋,又老而精力不逮,固不敢屑屑然[11]补往贤之阙也。
任其昌自序。
(《敦素堂文集》卷八)
【注释】
[1]隃:古通“遥”,遥远。
[2]龊龊然:局促拘谨的样子。
[3]冒乱:贪恋淫乱。
[4]谣诼:造谣毁谤。
[5]宵人:小人、坏人。
[6]魏泰:北宋士人,字道辅,襄阳人,出身世族。
[7]章惇:字子厚,福建浦城人,王安石变法的中坚分子。
[8]《碧云騢》:宋魏泰作,托名宋梅尧臣。
[9]司马贞:唐代著名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
[10]髫岁:幼年。
[11]屑然:特意、着意的样子。
翰林院编修吴君蜀江墓志铭
【题解】本文主体部分叙写逝者家世与生平遭际,盛赞其诗文出众、品行方正,抒发了对逝者英年早逝的痛惋之情。“铭”辞用韵文赞颂逝者才德,夹叙夹议,酣畅淋漓。
君讳西川,字蜀江,号梅龙,秦州人,世居北乡之卦台山。曾王父讳壮南,封朝议大夫。王父讳廷荣,诰赠朝议大夫,晋封通奉大夫。父讳鹏图,山西长子县县丞,晋封通奉大夫。君即贰尹公之第三子也。幼聪慧,不好儿戏事。七岁,贰尹公命作杏花诗,即能成章。九岁,应童子试。十八,入州学。逾冠,补博士弟子员[1]。嗣丁贰尹公忧服[2]未阕[3],母夫人亦弃养[4],破产营葬事,结庐渭曲,足不履城市者数年。辛酉得拔贡生,朝考未见用。归值军兴,为州县掌书记,后入贽[5]为内阁中书[6]。庚午,捷顺天乡试。逾岁,捷南宫,改庶吉士[7]。甲戌,散馆[8]授编修[9]。乙亥,卒于京寓。
吾乡先达少为诗古文者,君未冠已独肆力于此,明粹婉妙,多可传。自家中落,食粗粝无戚戚态,且不与富贵人往来。居京师,退直之余,不出庭户。然用能文善书,人遂多知之者。及入翰林,文名播京师,廉谨退让一如其曩时。而不意其竟至于斯也。呜呼!痛哉!人生不必皆才才矣,未敢妄意于富贵勋名,惟是埋头项笔砚间,此亦岂为非分事者?而犹湮阏[10]摧败,即食贫居贱之岁月亦不使多享。天耶?人耶?其谓之何哉?其谓之何哉?君以道光辛卯生,得年[11]财四十有五。妻刘氏,子二。宝瑀,翰林院待诏,其第五弟渭川子君以为嗣。宝璐,侧室刘氏出。
今年九月十八日将葬君,君弟来请铭,铭曰:“麟凤伏,德以藏兮。有其振之,是用彰兮。曷罻曷罗,札焉伤兮。天阏终世,嗟彼苍兮。”
(《敦素堂文集》卷四)
【注释】
[1]博士弟子员:古代博士所教授的学生。汉武帝设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令郡国选送,其后员数大增。唐以后也称生员为博士弟子。
[2]忧服:居父母之丧。
[3]阕:事情结束。
[4]弃养:父母去世的婉辞。
[5]入贽:携带礼品入朝谒见。
[6]内阁中书:清代官名,掌撰拟、记载、翻译、缮写之事。
[7]庶吉士:从进士中选出,进翰林院继续深造的预备人才。
[8]散馆:庶吉士经一年学习后举行甄别考试之称。
[9]编修:古代官职之一。该官职主要配置于储备人才功能的翰林院,所属工作为典簿记载。
[10]湮阏:湮灭阻塞。
[11]得年:去世时的岁数,多用于五十九岁以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