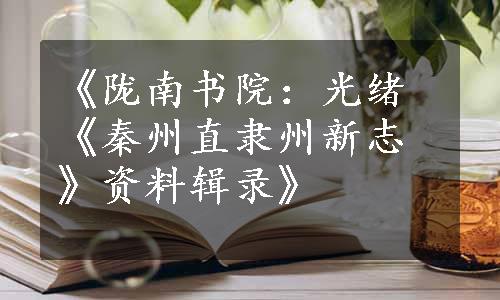
骆 诚
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秦州任其昌、伏羌王权合撰,光绪十五年(1889年)陇南书院刻本。分类明晰,考证精细,文字雅达,为一代名志。任其昌和陇南书院的创建者董文涣私交甚好,董在其《砚樵山房日记》多次提及。作为陇南书院的首任山长,他更是耳闻目睹、躬自经历了书院从创建到授徒的全过程,因此在纂修《秦州直隶州新志》时,对书院的记述比较详尽。兹按卷目先后予以标点辑录,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卷首《诸图》
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二《地域》建置附
陇南书院旧在岷州,曰文昌书院,后巡道移驻秦州,就旧道仓地改建焉。前为大门,门内西房三楹,院夫居。北为重门,门内为东西斋房,凡六院。东第一院北,亭三,为监院监课之所。西第六院北,西亭三楹,为监院常住之所。余生徒所居,凡四十五室。又北为砖门,又北为内院门。门内之南,东屋四楹,北之东屋三楹。又北为重门,西房一楹,为院夫常住之所。南位北向屋二楹。又北为讲堂三楹。堂后东西斋各三楹,为掌院住处。北庭三楹,供至圣、文昌、魁星神牌。西耳房二楹,东耳房一楹。讲堂之东,又一门,穿夹道而北,其东有房二楹;又北而西,门一,门内东西房各二楹。其北大门一,门内东西房各五楹。北房五楹,东耳房一楹,后小院东西房各二楹。光绪二年前巡道董文涣建。
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卷十二《名宦下》
董文涣,字尧章,号研樵,山西洪洞人。咸丰丙辰进士,以检讨纂修实录,议叙道员,除分巡巩秦阶道。道署在岷州时,前巡道严良训创立文昌书院,为三郡士子修业发名之所。大兵后,巡道移驻秦州。文昌书院久圮发,陇南文教遂替。文涣悯之,请括各州县叛回遗产,估充经费,营建陇南书院于道署之西,以居三郡来学者。舍宇饩廪,皆视文昌加广。涣既为择师主讲,又不时诣院亲与执书指授课试,日兼课经学古文辞,期进之远大。乡试之年,捐给寒士赴闱资斧。三郡文风之再兴,文涣力也。在官访求民隐,纵远无隔,校稽州境?独之民五百余户,免其徭役。除属县征粮吏役、披洒需索之弊,民尤德之。文涣学有根砥,尤工为诗,诗品优入中唐。在京师时,与长白桂懋、山西王轩等唱和成集,汇刻《十子楼吟》二十卷行世。
《秦州直隶州新志》州城图
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二十一《艺文三》
董文涣《创建陇南书院记》
古者乡有庠,党有序,闾有塾,里居有父师、少师,少师之教,是以道德一而风俗同。汉晋经师设黉堂、缮精舍,至宋,府州县学外分建书院,各设有山长。若周、陈、朱、吕治教之地,文献尤盛,学者宗之如日月江汉,德教所被,咸为名儒。
国朝因明旧制,书院择耆旧为山长,以启迪后学。教以尊亲长幼之节,离经辨志之方,以及天地事物之变,古今治乱之理,至于修齐治平、先后始终之要。而又养之以大烹,励之以宏奖,驯之以优容,需之以时日。噫!何其至也。故其教之成,则讼狱息、礼让兴;其才之成,则内外百官得其人,随所施为而无不当。所以俗美风移,鼓舞天下而莫之知,则书院之为益大矣!寝及后世,学校不修,书院存者渐失古意,上官诿之有司,有司以催科听政之繁,视同具文。为之师者未必尽择君子之儒徒,幽然自处其中,道德之旨,政理之体,固不素讲。士有聪明朴茂之质,而无教养之渐,则其才之不成灭,何足怪。天典民彝之叙,斁斯诡僻薄恶之习,胜吏承兵革之后,而治不教之民。呜呼!世道人心之所以日漓,刑罚盗贼之所以滋繁,皆以此也。
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书影
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陇南书院图
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陇南书院之记载
陇南文昌书院,旧在岷州道署之侧。自同治三载回逆扰岷,道署、书院并毁于火。厥后巡道驻节秦州,岁以为常。秦地当冲要,关陇未靖,军书络绎,官吏疲于供支,咸视书院为缓务,不暇之计。间有四方来学之士,皆以栖止无所,群然自阻。迄今十余载矣。壬申冬,予分巡莅此,叹人文之不振,慨然思振,惧无所欣也。取诸民,又恐民未孚,以为厉已也。于是请之制府,勘丈西河礼县叛产,贱其值,变价储之,以待兴筑。逾年,鞭策不(大)事,征收悉完,乃与州牧黄君翥先相州大城西仓,得亢爽之区,择期庀材,以杨令乃济董其役。地不足者,复售民房益之。藏经之室,诵讲之堂,休息之庐,至于庖湢垣墉,各以次为。经始于乙亥三月,告竣于丙子五月,计费缗四万有奇,而堂齐门庑,奂焉具备。
予顾而叹曰:“是役也,奚啻创,因名曰陇南书院,不沿文昌之旧也。”鲁侯作泮宫,诗人诵之曰:无小无大,从公于迈。又曰:“济济多士,克广德心。”陇南之俗,其君子敏于事、士之志于学者不少,特为兵与岁所苦,居无屋宇,市无书肆,无所资以讲习。今书院有其地,又得人师以为之师,而以修淳一易治之俗,而进茂美易成之才,日相与藏修息游,讲其德行,习其文艺,吾固信其教化之将行,而风俗之丕变也。夫教化可以变风俗,虽然必久而后至于善。昔欧阳子有言曰:“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须迟久之功。礼成俗醇,然后为学之成。”吾日望教之将行,而尤冀夫来者之能吾继也。于是本其意为记,以告来者。若馆舍宽则士舒,堂庑宽则校士者舒,除风雨之患、燥湿之疾,犹其末焉者也。(www.zuozong.com)
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二十一《艺文三》
姚协赞《谕陇南书院诸生示》
照得本道分巡三载于兹,于士习之有关系者无不力加整顿,实望尔诸生等,处为贤士,出为名臣,不欲以薄技寸长毕乃事也。然学问之道非躐等所可几,且宜严防他歧之惑。特就自己夙昔所致力者详揭以勉之,绝不敢望人以太高,亦不敢一任其自弃也,为此特示:
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之雕版(版原藏陇南书院,现藏天水市图书馆)
一曰立品以定其基。古人读书惟恐不成圣贤,今人读书惟恐不成科第,为人为己显然分途,故人才之成就相去太远矣。但国家以科名取士,而必谓不尚科第,持论虽高,转失为下。不倍之义,不知读书之学圣贤与读书之取科第,其事未始不一贯也。特后之读书者不知向上,平居但取腐烂,时文极力揣摩,不惟圣贤教人之心一毫不知,而于四书、五经亦遂茫然不解,遂谓为取科第之秘论。岂知根底不深,发而为文,亦肤浅而无足观,其幸取科第者十之一,不能幸得者十之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学殖荒落,老大无闻。即偶有幸得科第者,而于临政处事、治己、理民,每多颠倒,任情优柔不断,致局外之人遂讥儒生之无用,不学无术,良用慨然。胡安定之门人,稽古爱民,而吾则谓爱民未有不由于稽古者也。今与诸生约,必须先讲《小学》《近思录》以为立身行己之本。《小学》一书实与大、中相表里,故许鲁齐先生一生奉若神明。《近思录》一书荟萃先儒之精言,而实切于出处之用。诸生有志向上,务将此二书每日酌读三两页,必令精熟,暇则研穷其义理。但使修身、砥行、处事、接物以此二书为准,则人品卓然不苟,出则为循吏,处则为纯儒,是所厚望。且胸中有此二书,其见理必深,发而为文亦必不同肤浅之作。而先儒一切理学之书,遂可渐穷其奥,圣贤之基由此立,即科第亦必由此成。诸生其力图之,逮豁然贯通,当知予言之不谬矣。
一曰穷经以大其用。经有十三本,应皆知。近日读书者《仪礼》《尔雅》绝不与闻,《公羊》《谷粱》皆成赘说,《周礼》《礼记》无不裁减,《春秋》则但读《左传》,其中又多裁减,然则经书之所存者尚有几乎!人当束发受书,若按日读三百字,则《五经》不过数年可毕。乃近日之教子者,但求速成,少有聪明者无不令其早作诗文以为弋取科名之计。岂知文犹舟也,经犹水也,不知研索经书而但知作文,如行舟之无水,其必不能畅行无滞也,明矣!每见聪慧子弟至于终身而无成就,其病大都坐此。且经书又不仅为作文设也。每见通儒立朝,或侃侃直言,藉经义以悟主;或优优敷政,操经术以治民。名臣实绩可考,而知无烦缕述。尔诸生如有志向上,务须熟读经书,如《十三经注疏》及《皇清经解》等书以及通志堂所刻数种,须博览而归于约守,而《五经》白文尤不可忽。每见世人谈经解者,颇有所得,而考其本经,则不复能记,亦殊可笑。但穷经之功,亦非一蹴可至,须先择一二部熟读细解,按日课功,务期毫无间断,久之再推及其余,自然可有效验。勿贪多,勿助长,优游涵泳,经术遂可湛深。夫而后在乡可为宿儒,使后进有所观法,立朝可有展布,不致以空疏无据之学误人家国矣。
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之雕版(版原藏陇南书院,现藏天水市图书馆)
一曰读史以扩其识。一代之治乱兴衰,无不备载于史,往昔已成之迹,足当前车。故史鉴不通而遂讲治事,如长途征役,并无轨辙可循,其不至中,无所主误入歧途者几希。但史书浩如烟海,如不能提纲挈领,而寻行数墨,虽毕生竭力以读究,亦无当于身心。此谢上蔡记问该博,而程子所以谓之为玩物丧志也。然程子读史则又自谓不差一字,似亦未必不以博洽见长。程子之意盖亦无他,亦谓学者读史,见一善行则思量我必当学,见一恶事,则思量我必当戒;见其事成,则宜思其何以成,见其事败则宜思其何以败。且宜知古事之倖成者本多,而迫于时势误败者亦复不少。知其成败究亦不可以成败定其是非。如此,论人则知人,论世之识与克己修身之功、互见其增长。而一旦身当重任,遇事自有定见,不致惑于流俗矣。惟读史与穷经不同。经书为圣贤精粹之语,义理深奥,宜详解而细玩之;史书则糟粕多而精华少,欲求善取,必须善弃。大约纲领有数条:一曰国势,二曰人才,三曰治术,四曰风俗。读史于此四条辨得极真,分得极明,记得极清,久之,则数千年之治乱兴衰皆在吾之胸中,又何虑经济之不足济世乎!
一曰博古以游于艺。尝谓“诗以言志”。赋者,古诗之流。古人之诗赋,无非为言志之用。秦汉以来犹有古风,六朝以后渐趋轻靡,然为律赋之所自始。唐宋以诗赋策士,我朝因之,自大考翰詹,以至小试,无不研究声韵,搜索求偶,俾士子得以和声鸣盛,以抒其通今博古之才,二百余年代有传人。然康熙以来,人才蔚起,一时诸老先生手抉云汉,胸罗星宿,迄今读先正之诗赋,无不麟麟炳炳、殚见洽闻负声有力,断非一知半解之俗儒所能望其项背者。厥后,吴谷人先生空前轶后,自成一家,足为后学所师法。然究其源流,无非仍是枕经葄史,始能出言有章。至经史以外,如《楚辞》《文选》及六朝名人专集,均宜择要而读。若诗则古诗以外,唐宋八大家均宜窥其涯涘。今人学诗赋者,但读律赋数则,试帖百余首,不异矮人观场,安能独树一帜乎?昔汤文正公为一代名儒,不妨以词科起家。后人陷溺于辞章之中,偶能骈四俪六,便以为学问之道不过如斯,是人自误辞章,非辞章误人也。尔诸生有志风雅,应于穷经读史之暇,照以上所言之功夫次第行之,不必力求速效,优而柔之、餍而饫之、自能出风入雅而不厌于古,亦不悖乎时,润色鸿业,雍容揄扬,将拭目以俟矣。
至书法,为六艺之一,亦不宜过于草率。诸生端楷,其上者不过匀净,其下者则任意涂抹。亦宜于欧、柳等古帖先行,加意揣摩,必期力追前人。俟笔力坚凝,再用董、赵帖揣摩,有得所谓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者也。若不研究古帖,虽竭力弊精亦不能出人头地。
以上数则,要以立品为本,缘人品不立,则才华适以助其浮薄,经术适以佐其奸佞,而人才又奚足取焉?诸生勤而行之,将见文行交修,华实并茂,而文章、经济皆在其中矣。
光绪《秦州直隶州新志》卷二十二《艺文四》
董文涣《陇南书院落成示同舍诸生》
郡县设书院,礼教黉宫辅。矧当兵戈除,尤赖文治抚。文昌创赤水(文昌书院原在岷州道署之侧),固多历年所。英才广乐育,师道严重鼓。迄乎同治初,军书纷旁午。列郡继不守,烽火肆猰?。遂令养士区,千间荡一炬。青衿剧奔波,奚暇窥书圃。吁嗟儒服墜,阅年十有五。渝丧斯文欢,沈没志士苦。肄业投无门,未知地谁主。不有首唱人,畴兹废典举。伊予奉简命,分巡莅兹土。寒士失广庇,涓埃思小补。相地秦西仓,庀工兴百堵。讲舍周涂壁,学斋思栋宇。中可容百人,互以东西序。覆檐颇深邃,井灶粲可数。有竹左右之,绿阴敷庭户。于焉列生徒,何止除风雨。院长邦之言,(谓任士言农部)旧交深肺腑。文行府与谕,中流堪砥柱。不远千里来,多士亦鼓舞。予日士得师,大匠示规矩。若金受陶镕,若木从绳斧。治经与治事,二者实兼取。文艺后器识,菑畬惟训诂。涉猎无根原,潢潦涸立睹。贤愚岂殊辙,在不通今古。青云满目前,后尘望接武。旧观增轮奂,盛业绍邹鲁,诗以贻同舍,勉哉力共努。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