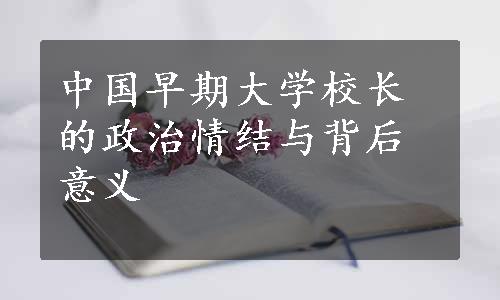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已经与过去那种同政治结构融为一体的模式相割裂,不将仕途经济视作为主要成就标准。近代中国政治腐败、社会混乱的现状使他们厌恶不已,疏离感得以产生。但是,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与近代社会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责任感的相互结合,一种“舍我其谁” 的精英意识油然而生。在对政治抱以鄙夷、厌恶的同时,却不得不或多或少深入其中——或抨击,或议论,或被深深卷入,力图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他们实际并无力改造的政治现实。[2]
客观考察民国时期大学校长会发现,他们当年可能抱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即一方面热衷于文化教育,视为根本之道,另一方面经受不住种种刺激或诱惑,不由自主地涉入政治之中。胡适曾经言道:“政治只是我的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然而,在前文中我们能够看到,不论是蔡元培、胡适还是罗家伦等校长,他们在“忍不住的新努力”之中是如何的投入,以至于政治投入并未亚于他们甚为重视的文化、学术建设。
我们无法忽视蔡元培在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的几年之内所做的种种政治方面的努力: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让整个北京知识界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师生先后于15日、16日接连两天在天安门举行群众性讲演大会,蔡元培先后发表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劳工神圣》的演说,[3]其政治热情的燃烧有不可遏制之势。再有,蔡元培以“南人”而居北京政府简任大学校长之职,与孙中山就南北议和问题产生距离,并多次发表政治言论。而在20世纪20年代的“好政府主义”这一幕政治话剧中,蔡元培俨然扮演着北大知识分子社群的政治上的领头羊角色。诸如此类的活动还有很多,但是蔡元培在担任大学校长期间都没有溢出“议政”的范畴。胡适与蔡元培在政治努力方面具有重合之处,而且胡适在论学或掌校过程中贯穿的学术独立与教育民主,其背后表现出的是对人权、自由、民主的坚守,对世界与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对人类前途的深沉忧思,对民主政治的坚定信念。总之,研究发现,这二人作为有着欧美教育经历的知识分子,在担任大学校长期间间接参与政治的基本主张与行动思路大有相同之处,他们都表达期盼政治清明的愿望,表达对民主与法制社会的热切期望。然而,在经历了一次次“出而谈政治”的历练之后,无论是蔡元培还是胡适,最初致力于文化、教育的心境早已发生改变,他们的社会形象并不因为任职大学校长一职而缺乏“政治属性”的油彩,预谋改变,谈何 容易。(www.zuozong.com)
至于以罗家伦为代表的大学校长,其与蔡元培、胡适等校长对于追求政治的心境颇为不同。罗家伦与国民党整合权力结构的趋向甚为一致,遂流于政治活动方面积极的状态,典型的政治倾向让其在高等教育场所中明显感受到生存不适。虽然无法否认罗家伦等校长致力于学术的政治性目的,但是更应该引起后世思考的是,罗家伦校长的政治活动并非仅仅基于个人的荣辱得失,更是希望中国走上“独立而富强”的现代化之路的政治“愿景”,只是在实践这一“愿景”的道路选择上出现了个性直至政治生命的“走调”。
由此可以看出,在近代以来的政治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蔡元培、胡适、罗家伦等大学校长或主动或被动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与主张,有时会在舆论上喧嚣一时,煞是好听好看,可始终无法解决社会实际问题。暂且不论这些大学校长在文化、教育方面欲达成的目的,仅就政治方面来说,他们欲解决的现实问题,实在是盼望国家的统一与安定,从而能为政治的规范化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和平、发展的环境。这种政治目的并非不可取,只是在现实政治力量的消长或崛起并不以良好的愿望为转移。不管是通过寓政治于学术的方式,还是通过直接演讲、集会等方式,民国大学校长的本职工作毕竟不在于此。而且他们提出的政治方案过于书生气,其思想理论依据多源自西方政治理念,这或许会产生或多或少的思想影响,只不过作用于实际政治之时,其效果就微乎其微了。然而,需要意识到的是,尽管他们的政治“呐喊” 与“行动”十分脆弱,毕竟形成过一定的影响或声势,也产生过某些作用。蔡元培等人常言自身仅仅代表知识界而聊备一格,“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这一方面似乎表明这些校长自身并不完全具备干政治的气质,另一方面也会多少受制于校长这一带有教育、学术性质的工作职务。然而,民国大学校长的政治改良性格已然侵入骨髓,尽管他们所倡导的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主张多限于舆论层面,但是这其中所具备的政治意义颇为显著。总之,蔡元培、胡适、罗家伦等人对政治的介入,展示了身处教育高位的民国大学校长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参与政治的模式和对民主、自由等的发扬,这一事实本身似乎远胜于他们的实际“政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