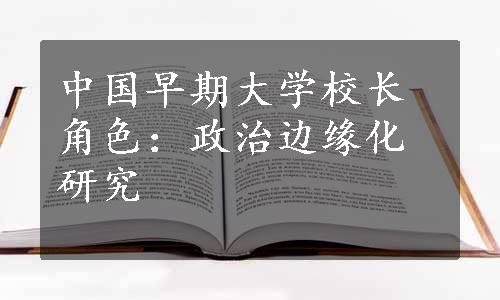
传统的政治文化造就传统知识分子以“道”自任的政治人格。在政教一体化的社会中,传统知识分子常常被视作政治化的承担者而居于重要地位。然而,一种角色在经过自我认同之时,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同。然而社会认同并不来自先赋,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依靠社会结构的特征以及国家对知识分子政治人角色的赋予。[62]因而,面对民国时期特殊的社会状况,尤其是传统政治文化发生根本性崩溃的条件下,知识分子在政治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变化,其被边缘化无可避免。
所谓边缘化,是一种比较抽象的说法,它是相对于主流、中心来讲的。大学校长的政治边缘化首先起自国家政治体制的变化。从帝国专制到共和政体是时代的进步,然而此时的共和政体是有限的多元政治,而非责任政治;政治体系中有一套精密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封闭的心理结构起着支配作用。反映到作为知识分子的大学校长是否被政治边缘化的评判,则由大学校长的教育工作与政治国家的实际联系、大学校长对于政治权力机构的影响来决定。具体来讲,民国大学校长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已经脱离传统知识分子与君主的共生的文化环境。知识分子早已在时代的感召与自身意识觉醒下脱离与政治权力统治者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生存状态。另外,一部中华民国史,基本上就是混战中的军阀的合成史,民国军阀是影响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武夫当权的时代领导者是否还能做到知人善任,似乎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话题。中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和混战的时代,军事冲突引发的战争直接导致社会的剧烈动荡,全国的教育事业处于缓慢发展乃至停滞的状态,在教育被视为可有可无的形势下,大学校长地位远远不足以与一介武夫相抗衡,其政治上的边缘化也是可以理解的。
自汉代以来,以儒家政治文化为核心的政治体系,不仅将政治话语解释权“赋予”儒士,而且形成以儒士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构成对整个社会人心的统摄。然而,进入风云际会的20世纪初,近代中国进入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命运似乎在瞬间被改变,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知识分子”(士阶层)同官僚阶级的固定关系(依附、升迁之途)断裂[63]。这种变化莫过于四民之首位置的丧失,政治日益边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存危机。而作为知识分子的主要聚集地——大学,其主要功能不再被定义为政治功能,更多看重文化功能。同样,作为执掌大学的校长,他们的政治人角色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随着道统的瓦解,学统与政统的分离,以及西学进入并强势影响传统学术,产生向以科学为中心的现代学术的转型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职业专业化、分工细致化的推进的转变。1912年《大学令》颁布,明确规定大学分成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标志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知识体系和知识建制的初步确立。在学术转型过程中,学术对象由主观转为客观,研究方向由诵读经典、注疏经典向理论分析、实验论证转变,学术性质由主“德”变为主“知”,学术的品格走向“学—政”“知—用”“理—器”“学—术”的二途分疏,学术活动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职业。[64]与此同时,学术的职业化要求大学内部人员要有明确的专业分工,大学校长也不例外,这种角色成为现代社会中一种独立的职业。它不断强调大学校长自身的职业素养,要求获得更加专业的知识和管理技能,完善教育理念、管理理念、专业思想的发展过程。根据北洋政府教育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中的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总辖大学全部事物。”同时《大学令》中还规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员为会员;大学校长可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65]这是民国时期最早的有关大学校长的较为权威的法令、法规之一,从中可以看出民国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校长统一领导、管理大学内部事务,大学校长角色的职业化由此展开。由此看出,大学校长的政治角色边缘化成为 必然。(www.zuozong.com)
同时,朝着职业化与专业化发展的大学校长也会带来一种趋势:相对游离于社会。而且,不断争取独立、自由的地位,使得民国大学校长也失去与地方社会和国家政治那种更加贴合的内在的制度性联系。他们的文化权力变得很虚拟,因此对政治权力的影响是以一种话语的方式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学校长政治角色出现边缘化。
国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导致大学校长政治角色边缘化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传统的“四民社会”的解体和现代“市民社会”的兴起,导致传统社会重心失去,而新社会的重心却仍处于模糊之中。简单地说,“市民社会” 是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的一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领域。它由相对独立而存在的各种组织和团体构成,它是国家权力体制外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治社会,是衡量一个社会组织化、制度化的基本标志,具有独立性制度性的特点。[66]在民国初期,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逐渐发展带动市民社会的萌芽。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市民社会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拥有很大程度的独立自主性,不受国家的直接控制;其二,改变中国传统依靠血缘、地缘等关系维持的局面,其内部运作主要依靠契约;其三,将民主管理制度落入实处,如民主选举、民主议事等程序的落实;其四,带有很强的专业性。例如,体现中国近代市民社会萌芽标志的教育会、商会等组织的涌现,其数量与规模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近代市民社会的初步形成,显示了社会力量的重新分化,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重新思考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虽然市民社会中的各种行业自治组织并不将自己放置于与政治国家的对立地位,但是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传统社会中将学术完全视作政治一部分的看法,而是以独立的眼光将国家归入“民族—国家”的范围之下。例如,很多处于教育会中的教育者不再将自己定位于依附于政府,纯粹为政府培养人才的政治工具,而带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从事教育活动。[67]从这个意义上讲,市民社会的发展对大学中知识人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大学的性质随之发生变化,大学校长从政治场域退出,自觉接受政治边缘化。
最后,近代国家观念和民权思想在法律和政治层面否定传统社会的不平等性,传统知识分子丧失了社会的特权。以“力本”为中心的机械主义的“群”的世界将各个国家、国家之下的人民时刻置于一种充满竞争的环境之下。在这个充满紧张冲突的“力”的世界中,能力的竞争显得颇为重要。获得一种适合竞争的生存能力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作为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获得教育与学术方面的杰出成就显然成为他们立足于高等教育领域的不二法门。另外,民国时期大学校长对政治的理解,早已经超越平民政治或投票政治的阶段,而上升为一种专门的事业。这种专门的事业需要专门致力于其中之人。暂且不论民国大学校长在智识、学识、德性等方面的地位,仅就其作为维系中国文化之不堕、学术之不衰乃至进步而言,民国大学校长怎会有如此多时间与精力,积极、高效地游走于不同领域之间?毕竟,大学校长的本职工作不在于政治,时代的发展更多地给予大学校长追赶先进教育的动力而不是从事政治的努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