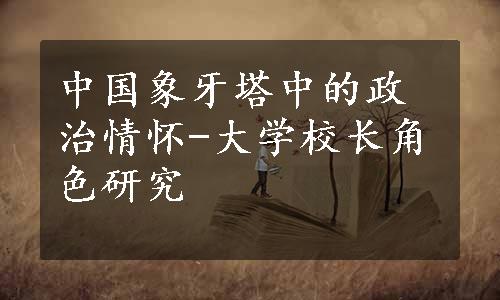
1.政治寓于学术
竺可桢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将《大学》中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融入大学之中,将“修齐治平”的理念与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紧密结合。一方面,作为一名科学家,竺可桢重视大学在学术研究、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使命。身处中华民族承受丧权辱国之痛的时代,他深感大学应该承担起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责任。另一方面,竺可桢留学8年,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美国大学服务于社会理念对其留下深刻印象。正是在这种多重的文化教育融合的背景下,加之社会现实的紧迫感与个人使命感的驱使,竺可桢将政治寓于学术,赋予大学崇高的历史使命。
受到西方科学精神熏陶的竺可桢,意识到科学在社会中的贡献,他认为,没有科学就无以立国。与此同时,国人对于科学的无知深深触痛竺可桢。因此,他积极推进将科学思想与大学理念相结合,在救亡图存的主旋律下,形成独特而丰富的科学救国思想。首先,创办科研机构,为科学研究鸣锣开道。竺可桢将科学研究视为科学救国的前提,而科研机构的设立提供最基本的平台。浙大是当时最早设立科研机构的少数几所大学之一,其中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史地教育研究室、理科研究所数学部、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等成为浙大乃至中国科学人才“栖息地”。其次,致力于科学人才的培养。在抗战危亡时刻,竺可桢毅然走出书斋承担各种教育科研机构的领导工作,在更加广阔的实践领域里培养优秀人才。最后,践行科学与人文并重的科学教育理念。竺可桢强调科学人才必须兼具专门知识与人文精神。他认为大学教育“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103]。竺可桢着重培养学生扎实的知识功底,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齐头并进,相辅相成。
竺可桢将教育与拯救中华,转移国运这一神圣使命相结合,如其所说,希望浙大学生学习先哲“不忘致用,实行为国效劳的精神”,成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104]面对救亡图存的压力,怀抱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竺可桢自觉承担起“政治中介人”的角色。尽管他一直保持中立立场,但是却不自觉地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与世界观作为教育的特权。竺可桢多次提及学生应该具备成为领袖的各种素质,在走向社会后能够成为激浊扬清的新兴社会力量和维护国家正义的栋梁。
竺可桢上述科学救国理念蕴含着大学的两大职能: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而他对于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也颇为重视,“一个大学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在于能使每个毕业生孕育着一种潜力,可令其离开校门以后,在他的学问技能品行事业各方面发扬光大”[105]。竺可桢提出两种改良社会的途径:其一,让经过训练、拥有知识、掌握技能的学生走向社会,达到改良社会之目的;其二,利用师生掌握的科学技术、文化优势,直接造福于社会政治。[106]基于此种理念,竺可桢任校长后,抗战过程中浙大每到一处都尽量为当地建设做出贡献,给地方留下“永久不磨的影响”,真正将理念付之于实践。
竺可桢认为,大学还应该承担转移社会风气的责任,为社会带来良好的道德风尚,并履行对社会的监督和批判的职能。“大学能彻底地培养理智,于道德必大有裨益。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是。所以道学问,即是尊德行。”[107]同时,混乱的社会现实迫切需要大学承担这一使命:面对专制统治日益加剧,大学应该继承民主精神,并且积极宣传民主与法制;面对政府的腐败堕落,大学应该培养公私分明之人,“我们就希望顶好人才、顶廉洁的知识阶级去做官,唯有这样,公家的事才能办好” [108];面对国民素质的普遍低下,大学生应该成为国民素质的代表,大学生应将大学赋予的气质、品性散播于社会。
2.对于政治的“超然”与“介入”(www.zuozong.com)
每一个知识分子个体,作为扮演社会角色,承担社会职责的个人,其行为取向通常取决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就个人行为而言,纵观历史,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一般都具有学者身份。而他们所具有的学者姿态通常是“探究式”姿态与“关怀式”姿态的结合。不消说,大学校长在其最初的学术之路上一般具备“探究式”的学者姿态,在不关乎政治的前提下具备超然与冷静地探索生命意义与宇宙真谛的追求,并由此而思考学术的价值与意义。而“关怀式”学者姿态,即把个人的道德感与价值观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观照。这种姿态使得民国时期的大学校长继承一贯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理路,关心社会、国家,投身于现实关怀。大学校长所具备的两种学者姿态,不仅仅表明其关心教育、学术之缘由,还说明大学校长之所以能够比一般人更有担当之原因在于其所具备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现实关怀。
竺可桢是一位典型的同时具备“探究式”姿态与“关怀式”姿态的大学校长。纵观竺可桢一生,可以看出,他始终服务于科学事业。仅就竺可桢任校长13年间,他都没有放弃以自身的学术活动直接推进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发展,以科学家独有的超然与冷静的姿态,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追求科学纯粹的“意义”而非“意识”。带着这种科学探究的姿态,竺可桢往往比很多大学校长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他在政治中的中立立场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科研终极意义的探寻。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任何有良知的大学校长都不会放弃“关怀式”姿态,而竺可桢也不例外。他无数次地勉励学生“以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不能灭亡与不可灭亡之民族为职志” [109],“民族自由重于个人自由……” [110]。但是竺可桢充满理想色彩的政治观及其个人意志与具体的政治现实往往产生摩擦甚至冲突。他虽然不同于胡适的“讲学复议政”和蔡元培的“书生论证”,区别于罗家伦的“直接参政”。但是,他也不是一个能把书斋坐穿的纯知识分子。竺可桢只是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体现着“关怀式”学者对于忧国忧民的世事关怀。
另外,求是精神虽然首先是作为科学精神加以倡导的,但是竺可桢把它进一步深化、扩充之后使求是精神的内涵远远超过科学精神,成为竺可桢的人生哲学,成为其不断追寻以便确定或引导自己生活道路的现实指针。他之所以能在政治上坚守“中立”并且还能在政客中间周旋,实在因为他信守并笃行“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哲理,保持其本人在污浊的社会政治领域“出淤泥而不染,濯青涟而不妖” [111],遂为主持正义者所敬,而使倒行逆施者难以加害。竺可桢常常以近代自然科学的先驱伽利略、布鲁诺、哥白尼等人同中世纪传统势力斗争的事迹来勉励学生。在竺可桢看来,要坚持求是精神,必须永久忠实于真理。竺可桢所谓的真理是和社会利益一致的,这意味着竺可桢勇于为了社会利益而放弃个人利益,因此他在大是大非面前带有一种高度的政治智慧。
竺可桢作为享誉世界的科学家以及“东方剑桥”的缔造者,自然被国民党视为文化教育界的楷模,并试图拉拢之。虽然在担任校长期间竺可桢被拉入参加国民党的某些政治活动,如“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竺可桢受命参加庐山谈话;抗战期间,竺可桢兼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1939年,竺可桢担任三青团监察会监查,之后参加高级党政训练班等。在这些活动中,竺可桢多以挂名出席,对于这些职位和会议始终有所排斥。虽然竺可桢积极参加国民党领导的各项社会建设,并配合国民党进行教育、科研形式的救国活动,但是这一系列工作并不能表明竺可桢已被当权者同化,甚至产生强烈的依附作用。它们是竺可桢建立在爱国主义诉求基础之上的急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行为体现。而且,就竺可桢执掌的浙大在战后遭遇“被抛弃”的冷遇来说,无不从侧面表明竺可桢对国民党的冷淡态度。因此,“政治场”的拉拢并没有在竺可桢身上完全体现,由此而拒绝了其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之旅中滑向政治歧途。
因此,竺可桢在大学内怀抱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情怀,以一种独特的“介入”方式抒发着其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国家关怀;然而,这种独特的“介入”在竺可桢以至后人道德眼中,更多的是一种“超然”与“冷静”。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