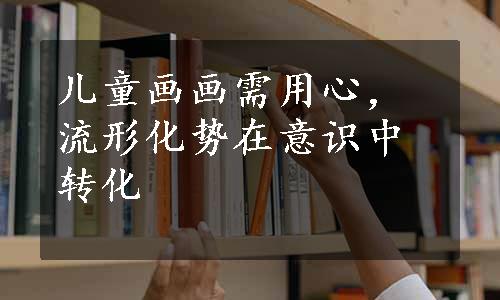
作为民间手艺人,艺术秉性也表现出喜新厌旧的心理。难免心猿意马,异想天开,有时脑子出现了的一些想法,自己也意想不到。想法在“意念”中胡乱构成,这也是一种构思。“思”是心脑作用,而“想”是意识成“相”。有构思还不一定冲动,当“构思”发展成“构想”就要付诸行动了(具体可参看第八章“玉雕的思想维度”)。这实在是莫名的动力,驱动着去找一个现实的物体,来变现“构想”。这就是“意”的能量。总是先有意,才有动。即便是儿童要拿笔画画,也是有意的。
流形化势以变幻无常的形态进行。“形”是流动的,态势随着念头的生起瞬间化掉刚刚成形的幻象。其实这就像“梦”,闭眼时做梦,睁眼也在做梦。这也是忽然想到“流形化势”这个词的原理。
在这里,“流形”指的是如液状的流动形式。把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液状的流动形式,用玉石再现出来。流形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流形,是“流”出来的形式,像液状流动一样顺势而成。构思顺“流”而生,有时追根溯源,有时触景生情,有时忽然想到……制作亦然,因材施艺,自然成形。流形主要体现在视觉层面,就是眼睛看到的形态。
《文心雕龙》提到“形生势成,始末相承”。形成什么样的势,取决于作者处理玉石之间关系的态度与能力。比如说,喜欢水流的样子,也喜欢玉石这种材质。可是,水是水,石是石,玉是玉。它们的质地有别,生成异径,存在因时,所散发出来的信息也大为不同。如果把玉石仿制成水的样子。手艺再好,就算是超写实,也不可能把玉石变成水。绝大多数的人都热衷于用自己惯用的材质去再现另一种材质的形态,并以此为乐,乐此不疲。自娱于这种势态,满足过一时的初级快感,许多人没多久就玩腻了。因为那不是感觉后而悟到的势态。所以不由自主地寻求更深一层的感觉形态,一种符合自己内心频率的势态。换言之,寻找外物实有的势态,并在主体内在的维度去契合它。
如何契合呢?“化势”!就是把视觉、听觉、触觉到的“相”在意识中融为一体,留下一种感觉,其实这是外在的势转化成内在的势。类似禅宗说的那个“悟”的东西,无法言传,是抽象的。在人的圈子里,想让人知道“抽象的感觉”,几乎不可能。这和“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是一个道理。就算是自己此时的感觉瞬间,就不是彼时的感觉。就像赫拉克利特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样。所以必须找个载体,好比“魂要守舍”,让这感觉有着落,附着在具体的材质上。又因为不同材质必然有不同的属性,这样就得处理好两种不同属性的介质关系,于是另一个“相”就出现了,这是超以象外的反照,“相”后之相,是“抽象感觉”的具象化。
化势可以理解为把某势化去,也可以理解为被化过的某势。如果说“流形”是给外行看热闹,那么“化势”是留给内行去悟门道。流形观象,化势随心。流形是载体,化势是处理关系。可见“化势”是赖以“流形”这样的载体,来转化作者的情感思想。比如,喜欢溶化的形态,又喜欢玉石,于是就想办法把玉石表现成溶化的形态。若只是为了表现溶化的形态,儿童就能办到,抓一把泥,自得其乐地捏起来,不管别人看像不像,反正自己觉得像。儿童的无意识表现到载体上,就是初级的抽象或者说是无意识的相。如果大人也想表演成儿童的样子,那就不是无意识,而是有意识,至少还有潜意识。毕竟经历了成长过程,看过无数的“相”,听过很多很多的声音,体会过很多的事。这时的人完全是社会中的人,不仅要处理好自身的心理生理的内部关系,还要处理好个人与人类群体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人与大自然之间相互影响协调的关系。这关系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就像鱼在水中不知水,人在气中不知气。只要在世界中一存在,就有这些关系。好比买了手机卡,一旦开通,就进入某种网络。那些图像、声音和现象都是载体,经历过之后这些“表象”就过去了,甚至不复存在,“象”被抽掉了,留下的是阅历,是想法,是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这类抽象的东西。此时想回到无意识的状态,已经很难了。可见在这里,喜欢溶化的形态,只是表象,而深层的情感或想法,迫切地需要找到合适的载体,即流动的形式,溶化的势态,这是抽象观念的具象呈现形式。
于是顺着“溶化”去化,以水“溶”,以火“熔”。溶(熔)以后才能相容,才可以融到一块,不分彼此,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包容。水火不容我化而容之。
以作品《化了》为例,寿山石和玉表面看起来,材质很接近,硬度不同,玉质如一。寿山石仿制玉佩也是当下流行的做法,这叫顺流而思,顺流而做。但仿制还不能满足的内心需求。而此时的内心需求是什么,还不十分明确,若隐若现,若有若无。越刻意去想越想不出,只好顺思潮起伏,顺流寻找。当参看此石的红黄色时,可能联想火热,越想越热,热到什么程度……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就在这一瞬间,灵机一现——“热”得足以溶化玉石。接着联想进一步展开:玉文化是中国古老文化独具特色的重要一脉。寿山石文化是新兴的玉石文化,继承玉文化到今日,正值物欲淹没道德的时代。接下来就设想把玉佩人性化,设想为不愿意沦为商品,更不愿意因为自己的美而勾起人的贪欲。于是玉佩只好自行化去,化作斑斑血泪,化作点点忧心。洒向大地,一绝色相。此时在自我营造的意境中找到了虚拟理论依据。玉石熔化后流下去,滴下来,溅起来……最后定稿。于是“这一念”贯穿着整个制作的过程中。仿佛是灵魂植入胚胎直至成形,此谓化势而成。玉器溶化,多反常!能想到这一步,体现心物感应而激发构思的灵性,以超现实的思维,通过构思玉器熔化的形态,玉、石、思维异质同构,犹如动态的齐物论。绝不在技术层面,也不在设计层面。那往往是一念生的闪现,是感悟效果。知道了有这样做法,就可以轻易地触类旁通,随心所欲地“万象更新”了。
《一桶天下》 2000年 何马 作(www.zuozong.com)
《化了》 2004年 王三三 作
寿山芙蓉石 6cmx1.5cmx14.5cm木:8.5cmx3.6cmx4.5cm
《化现》 马来西亚水玉、寿山芙蓉石 何马 作
再如2000年夏天的作品《一桶天下》,材质为寿山山秀园石,其质地和颜色像使用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木制水桶的材质,仿制一个。而围成水桶的一块板设计成缺了个口。里面的水,从缺口流出,流到“地面”汇成一个像中国大陆地图的形状(从北往南看的方向)。而“地图”还在流,有一边已经流到“悬崖”边,这位置恰好是中国地图的海域范围,也包含台湾的板块。水流,顺流而下,因为落差,势必形成瀑布式的激流。什么样的形势?什么样激流呢?作品要表达的意思就不言而喻了。
这是顺流而作。化“一统”在一桶里,凝固激流而成像,把多种不同的“势力”包容在一处,融为一体,这也是“化势”,把多种的势化为一势,再转达出去。(2001年在福州三和茶馆展出时,当时的市委书记赵学敏先生看到后,提议更名为《缺一不满》。后收录在《中国寿山石雕艺术家精品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
雕过玉石的人都知道,处理玉石中的裂纹、杂质固然很费神的,却远不如构思来得伤脑筋。时常会发现自己喜欢的材料,买到手后又不知道该刻什么。那是因为自己惯用的题材很有限,导致表现手法不够多样,而无法去应对各种材质。不像做泥塑、不像画画,相对灵活一些。所以多数作者一生的作品,几乎雷同。也想创新,却创不出,这因为被经验的惯性所致,佛教里说是“我执”。究其原因,大概是长期以来一直习惯于把自我意识强加于玉石中,没有真正地把自己放在和玉石平等的位置,忽略了玉石的天然属性与人性之间的微妙关系。而作者经过和玉石的长期磨合,一旦察觉了玉石本身的主体性,就会发觉玉石似乎也逐渐了解人的秉性。然后仿佛是“我”收到玉石自身流露出来的信息,感召“我”,引导“我”去构思与创作。此时很自然地把玉石天然形成的形状、色彩、质地,和人的美感形式、感情色彩、道德素质相对应。这样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开启智慧,好像是玉石提醒我可以做什么,可以怎么做。我称之为“物我同构”。这样“我”和玉石在不知不觉中共同创造了一个新的语境。由于每个人经历不一样,创作出来的形式也不一样,都会给人带来新的感受,这便“创新”。
光影形式的意象作品
顺着“溶化”去化,以水“溶”,以火“熔”。溶(熔)以后才能相容,才可以融到一块,不分彼此,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包容。水火不容我化而容之。呈现出来的是抽象观念的具象形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