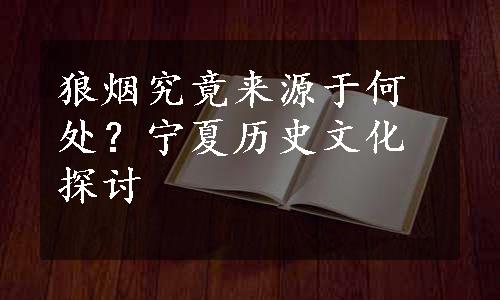
吴忠礼
在我国历代文史典籍中,往往用“烽火狼烟”“狼烟四起”等带有“狼烟”的词句来形容战场、战争和敌情。显然这些词语和成语的广义概念均与战争有着密切联系,而狭义的概念一般皆谓传递边防军情的烽燧及其传播敌情的方式方法。为什么与战火相关的军情要使用“狼烟”这一名词呢?其答案似乎很容易找到。如《辞海》作如下解释:“狼烟,烽火。古代边疆烧狼粪以报警,故名。”[1]但仍然不解其意,为什么报警非得燃烧“狼粪”呢?《辞海》该条继续作解释说:唐朝大文学家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广动值》一卷中作了权威解释,因为“狼粪烟直上”[2],远距离的人都能看得见,所以边防军才利用狼粪燃烧所产生的烟具有直冲天空的特点,皆取狼粪为发烟燃料,后来才引申以“狼烟”作为战争、战场的代名词。古人在《酉阳杂俎》中对于“狼烟”如是说,而当代人又是怎样解释该词词义的呢?由商务印书馆编纂出版的中国语文辞典之巨著《辞源》,对于狼烟的释文比较清楚,它在“狼烟”条下,第一句就是“狼粪之烟”四个字。接着又说明为什么边关报警要燃烧狼粪,因为它有“烟直而聚”“风吹之不斜”[3]的特点。以上两大权威辞书对“狼烟”有相同的解释,所以人们对其不敢有丝毫的怀疑。1987年8月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成语大辞典》对于成语“狼烟四起”的解释为:“狼烟:狼粪的烟,古代边防报警的信号。”[4]至此,不难发现,古今各种有影响的权威工具书,它们对“狼烟”的释意和内涵前后如出一辙,即狼烟是狼粪燃烧的烟。
经过这番梳理之后,看来对于“狼烟是狼粪燃烧的烟”的结论是铁板钉钉、铁案难翻了。但笔者还是觉得,虽然古代边疆的人口比现在稀少很多,但也不至于豺狼遍地、狼粪成堆吧?因为如果当你了解古代边防报警的实情和制度之后,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古代边关传递军情,的确是使用烽燧相传的办法。烽,指夜间通过燃烧可燃物的火光报警;燧,指白天通过释放不完全燃烧可燃物的烟焰报警。据史书记载,这种报警方式至少于西周之时就已经在使用,如发生于西周的“烽火戏诸侯”“一笑失江山”等故事中,就反映了周代烽燧报警制度的存在。从西周到明清,时间历经2000多年,各地的边防线上,战争不断,警报不断,即使在无警的情况下也要举烽燧,特别是早晚要各报一次“平安”烽燧。如此岁岁月月、日日夜夜地举烽燧,能有那么多的狼粪供边防报警使用吗?事实上是绝对不可能的。笔者认为,不管权威著作上对于“狼烟”作如何解释,读者自己还是要独立思考和实事求是。为了达到报警的目的,叫边防军去找狼粪,谁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呢?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就地取材,利用各种柴草、树木等可燃物进行燃烧才是解决问题的可行办法。
那么“狼烟是狼粪燃烧的烟”这一概念假如被否定了,对它的正确解释应该是什么呢?笔者个人的浅见为两条。
其一,“狼烟”是由地域和地名演变而形成的。从古代战争史来分析,大的战役往往多发生在农耕民族、中央政权与游牧民族、边疆地方政权之间,其战场也多数发生在北方或曰西北地区。唐朝大臣吕温在所作《三受降城碑铭》中写到,自从三受降城[5]修成以后,北方胡人(时指控制大漠的突厥部落)不敢轻易内犯漠南,如果北方游牧部落(唐朝时指漠北新主宰者突厥人)敢于轻举妄动,“小则责琛赆,受厥角,定堡寨,一隅之安;大则倒狼居,竭瀚海,空若塞万里之野”。[6]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自从三受降城军事要塞筑成以后,其小的功能表现为游牧民族一些部落再也不敢南下抢劫骚扰了;而大的作用表现为可以凭借三受降城为根据地,主动出击,一举将胡人的巢穴荡平。此处的“狼居”,当指少数民族大范围的游牧地区或具体指北方少数民族大首领定居的王城(又称龙城),由此而引申出文人墨客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往往把少数民族内犯的战争警报(烽燧)以“狼烟”来代指。因为战火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从“狼眠虎踞”的漠北胡地燃烧起来的,故古人有些作品又把“狼烟”称为“狼望之烟”[7]。何谓“狼望”呢?它的本意是说狼性多疑,行走时总要不断左右回头张望,故称“狼望”“狼顾”,后又进而引申为“坏人的形象”。如明朝万历年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李汶,他曾于防秋时站在宁夏后卫花马池长城关向北方瞭望,有感而作了《长城关远眺》一诗,诗中写道:“驱车直上傍烟霞,到处羊肠石径斜。远岫逶迤抱雪谷,翠微陡绝搏风沙。三春不解毡裘服,五月时开桃杏花。狼望龙城近在掬,惊心别是一天涯。”[8]这里龙城,亦称龙庭,泛指北方,又特指游牧民族大首领祭天、诸部首领居住的都城,一般多认为其地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故而此处的“狼望”即北望龙庭所在的方向。
另外,司马光在其名著《资治通鉴》中则更加明确地将“狼望”直截了当作为地名使用。该书在引用颜师古对《汉书》的解释中写道:“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师古曰:“狼望,匈奴中地名。”其意即谓“狼烟候望之地”[9],亦即“狼来了”的意思。
为什么古人基本相信报警均采用狼粪呢?实乃唐宋以后许多名家名著大多解释为狼粪所燃“狼烟”“烟直”之故。举凡南宋罗愿的《尔雅翼》、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清代陈元龙的《格致镜原》等名著都一致认为边关报警之所以燃烧狼粪,是因为“狼肠直”,故其粪烟亦直。[10]这种推论简直荒唐可笑,地球上哪里存在直肠子的哺乳动物呢?又哪里有直肠子动物所排粪便燃烧就“烟直”“风吹不散不斜呢?”真可谓天方夜谭、奇谈怪论。他们的书中谁也没有说自己亲手做过实验,无非是人云亦云,辗转传抄罢了。
笔者持“狼烟”应为生活在大漠中的游牧民族的地名说。与此同时,还要刨根发问,为什么游牧部落的地区要以“狼”字组词(狼烟、狼望、狼顾和狼山等)呢?据笔者浅见,因为生活在内地的农耕民族总是认为生活在大漠中的游牧部落既不懂礼仪,也不奉正朔,而且出行骑马,来去如闪电,食肉饮酪衣皮毛,且性野嗜杀,视其为狼虎之群,“禽兽畜之,不属为人”[11],“譬如禽兽”[12],所以他们的南犯入侵被南人称为“狼来了”,推而广之,其居牧地也就被内地人称为“狼居胥山”。(一说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肯特山,另说为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境内的狼山。)对其南犯军事行动的警报(燔烟),自然而然就被称为“狼烟”了。甚至对其大汗(首领)亦谬称为“狼主”,民众被贬称为“狼兵”,称其游猎为“兽聚”和“鸟散”。[13]总之不把北方、西北的游牧民族视为人类。
其二,笔者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古代学人持“天人合一”和“天人相应”的哲学观点,认为天与人的关系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二十八舍主十二州”。[14]因为“天道”与“人道”两者是相类、相通的,进而导致自然与人为的相通与统一,即认为头顶上的天区与脚底下的地域应是一致的。如西北天空二十八宿之一为参星,其组成有颗狼星,按《史记·正义》的解释:“太白、狼、弧,皆西方之星。”[15]“狼角变色,多盗贼”[16],所以《正义》又曰:“狼星为野将,主侵略。”[17]狼星在天区的位置居于西北方向。战国时期楚国大文学家屈原在他的《楚辞·九歌·东君》中写道:“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的一首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有两句曰:“西北望,射天狼。”[18]可以看出狼星的方位为西北。所以居牧于西北和北方的游牧部落一有军事行动,就叫作“狼星动了”;西北一带将要发生战争,对此进行报警的烽燧就被称为“狼烟”了。边民关于北方的形势变化,称为“狼望”“狼顾”,即大家常常朝着西北方观望,《汉书》谓之“民且狼顾”也。[19]另一种解释为,形容某人的长相不好,行为又如同狼行,总是多疑而左顾右盼,人们称此为“狼顾”。渐渐这个词就代指敌人、敌方,即北方胡地和胡人。甚至将生活在那里的部落(民族)也统称为“犬戎”了,因为犬与狼本为同种吧。明朝宁夏巡抚杨守礼在他所写的《春晚巡中卫》一诗中,就直接把“狼烟”称为“胡虏烟”。[20]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所谓“狼烟”乃系泛指游牧部落中某一地区或某一地点之代名词,而绝非对狼粪燃烧的烟的称呼。民间口语有一句调侃的俗语——“没事干拾狼粪去”,这句话表达了“拾狼粪”是一种惩罚,因那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因为“狼烟”根本就不是用狼粪燃烧所产生的烟火,如果真是狼粪燃烧的烟,那要多少狼粪呀?仅以明朝为例,明朝北方设有“九边重镇”,宁夏镇位列其中,但面积最小,所管辖范围内先后筑有烽燧墩就有512座。[21]那么“九边”烽燧总墩数和不属“九边”防区的烟墩数量,按保守估计至少也有一万座吧。按照朝廷的要求,有军情需按规定施放烟火,而即使没有军情,也要按时“举空烟”(放平安烟),谁能计算出全国或宁夏一年要消耗掉多少狼粪呢?谁又能收集到这么多的狼粪呢?故作者认为“狼烟”不是也不可能是狼粪所燃烧的烟,而是地名的代称。
近几年笔者见到有些文著(含工具书)中,对于狼烟是狼粪所燃烧的烟的传统错误解释作了纠正。但大多仅改写为“狼烟,不是狼粪燃烧的烟”,到此为止。那么,“狼烟”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仍然所涉鲜见,基本上还没有给读者一个明确的交代。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狼烟”的研究还有待专家们继续探讨、商榷,作出合乎逻辑的科学的结论。
(吴忠礼,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注释】
[1]《辞海》(中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普及版),第2330页。
[2]《辞海》(中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普及版),第2330页。
[3]《辞源》,商务印书馆,1979年(修订本)第一版,2002页。
[4]王剑引:《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709页。(www.zuozong.com)
[5]三受降城即唐朝朔方大总管、韩国公张仁愿于景龙三年(709年)在今内蒙古地区所修筑的三个军事据点:东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境内;中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境内;西受降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中旗境内。
[6]张钟和、许怀然校注,(清)汪绎辰修:《银川小志·古迹·三受降城碑铭》,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1页。
[7]吴忠礼:《宁夏历代方志萃编·万历朔方新志》第4卷《於越娄奎朔方风俗赋》,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第13A页。
[8]范宗兴校注:《增补万历朔方新志校注》,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16页。
[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34《汉纪》,中华书局,1956年,第1104页。
[10]李正宇:《“狼烟”考》,《寻根》,2006年第2期。
[1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8《汉纪》,中华书局,1956年,第601页。
[1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汉纪》,中华书局,1956年,第383页。
[13](汉)班固:《汉书》卷64上《主父偃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801页。
[14](汉)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342页。
[15](汉)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346页。
[16](汉)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306页。
[17](汉)司马迁:《史记》卷27《天官书》,中华书局,1959年,第1307页。
[18]唐圭璋主编:《唐宋词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410页。
[19](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3《汉纪》,中华书局,1956年,第451页。
[2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3《汉纪》,中华书局,1956年,第451页。
[21]吴忠礼:《宁夏历代烽燧大起底》,《宁夏文史》,2019年第10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