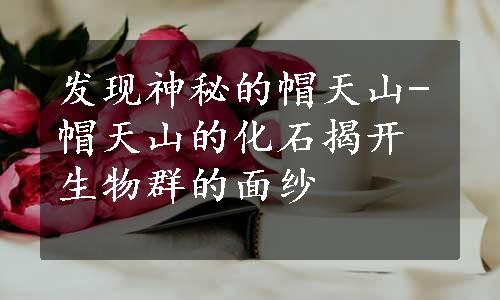
加拉帕戈斯群岛,位于南美大陆以西1000千米的太平洋上,隶属厄瓜多尔,群岛面积7500多平方千米,由海底火山喷发的熔岩凝固而成的13个小岛和19个岩礁组成。由于气候多样性和火山地貌的特殊自然环境,不同生活习性的动物和植物同时生长繁衍在这块土地上,奇花异草荟萃,珍禽怪兽云集,这块土地被称为“生物进化活博物馆”。
帽天山,位于云南省澄江市城区东边6千米处,因形如一顶草帽而得名。帽天山方圆不到1千米,海拔仅2026米,在素来以山高谷深著称的云南红土高原上,这样海拔的山可谓是其貌不扬,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座小山包也没有什么名气。
▲帽天山生物群想象图
但世界就是这么奇妙,这两个相隔万里之遥的地方,冥冥中注定要联系在一起——在探究生命起源的领域里,如果说加拉帕戈斯群岛是在与达尔文进行面对面地对话,那么,帽天山就是来自远古生命的、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回应。
把时间拨回1984年7月1日——那一天,下着毛毛细雨,34岁的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侯先光和一位当地的向导,正向一片寂静的帽天山走来。已经在帽天山搜寻了半个多月依然一无所获的侯先光的心情和天气一样阴郁,他不知道,神秘的帽天山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对他敞开心扉。
事实上,侯先光把目光盯在帽天山,并非无的放矢。沉睡了几亿年的帽天山,早已若隐若现地向人们展示了自己。早在1907年和1910年,法国学者就在澄江一带进行过地质古生物调查,留下的《滇东地质状况备忘录》记录了他们发现化石的过程。抗战时期,中山大学分部迁到澄江办学后,该校教授带领地质系学生在抚仙湖周边东面、北面的山区也发现过化石,但由于战乱和条件限制,未能有重大的发现。1940年,我国地质学家何春荪来到澄江东山调查磷矿资源,并发表《云南澄江东山磷矿地质》一文,其中也曾提到帽天山“页岩内有一种低等生物化石”,“德国米士教授获有三叶虫化石”。在这之后,也有不少科研人员来到帽天山,试图探索帽天山的“内心世界”,但由于各种原因,都无功而返——帽天山已经撩起的面纱一角,似乎又要无声无息地掩上了。
▲侯先光先生
▲三叶虫化石
天道酬勤,机会总是留给更有准备的人。
曾戏言自己的工作就是“找石头,敲石头,研究石头”的侯先光,无疑就是帽天山探访者中最有准备的那一位。侯先光1981年在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获硕士学位并留在该所工作后,从大量的研究文献中看到了“帽天山有化石”的记录后,就一直对帽天山情有独钟。据他回忆,在那半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天一大早就出门,爬两三个小时的山,然后就是不停地在人迹罕至的野地里找寻石头、敲开石头。
这一天,来到帽天山后,侯先光围着帽天山走了一圈,最后选定了西山坡作为当天的工作场所。然后和往常一样,与同伴挥着铁镐,剖开土层,将一块块石头挖出来。侯先光则手持铁锤,不停地敲开石头,检视会不会有所发现。(www.zuozong.com)
▲侯先光先生在实验室
叮叮当当的敲石声在山坡上回荡了六七个小时后,突然,侯先光眼前一亮——自己一锤下去,一块石头应声裂开,一个栩栩如生的虫体出现在石面上。“纳罗虫!”侯先光失声惊叫起来。
他知道,随着生存于5亿多年前寒武纪的无脊椎动物纳罗虫化石的出现,神秘的帽天山的面纱,已经被他揭开了。
此后30多年,侯先光的人生轨迹就再也没有离开澄江生物群化石。他总共砸开了十多万块石头,采集到了上万块保存有动物软躯体的化石标本。这些新采集的化石,有100多种动物的化石是以前从没有发现过的。
▲纳罗虫化石
一个巨大的、前所未见的澄江生物群终于重见天日,“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此展现在世人面前。
30多年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起1984年7月1日的那个下雨天时,侯先光描述了当时发现化石时自己的真实感受:“自己觉得时间已经凝固,整个世界都静止了,血液也停止了流动,整个人是懵的。我呆呆地看着那个标本,泥岩湿漉漉的,泛着油渍的光泽,这个虫子就仿佛在水底游动。我拿着化石的手控制不住地抖动起来……”
▲帽天山古生物化石首发点
的确,侯先光值得骄傲,他那一声清脆的敲击,仿佛就是那些静静躺在石块中的史前生物们的回声,叩开了时光隧道的大门,开阔了人类的眼界。随着这声清脆的敲击声,人类打开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此后,舒德干先生、陈钧远先生等专家学者,也为帽天山生物群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2003年,由侯先光、舒德干、陈钧远3位科学家共同完成的名为“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的科研项目被评定为该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