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正式卷入二战,巧合的也正是这一年,奥斯卡组委会决定正式开设纪录片奖项。如果不是由于纪录片制作时效的原因,2个月后的首次颁奖将会颁给《12月7日》(December 7th),当然美国奥斯卡的众多评委不会身处战争漩涡之中而忘记12月7日这一特殊日子,所以一旦纪录片《12月7日》1943年制作完毕,评委们就迫不及待地把满腔爱国热情化作选票投向这部片子。1944年的颁奖典礼上《12月7日》毫无悬念地捧走“小金人”。这一时期的纪录片都是关于战争的直接纪实作品,是一种“镜像”式的反映,其话语权明显归属于纪录片的出品方也就是国家。
(一)早期话语权由国家掌控
纪录片的话语权是纪录片作为信息传播主体的潜在现实影响力,按照福柯的理论,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话语关系,“我们始终停留在话语的范围中”[10],纪录片的图像、声音传播是话语获得的一条有效途径。早期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中,观众看到更多的是由国家掌控的一种话语权。
话语权力理论由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首先提出,认为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权力和话语”,话语是一种控制力[11],他揭示了话语、知识和权力之间相互建构的互动关系。其他如葛兰西的“领导权”、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等思想也共同丰富了话语理论。
权力产生话语,话语体现权力。对于纪录片所记录的社会事件,观众可以有多种评价,每一种评价或者话语的背后都隐藏着立场或者权力。就像《监守自盗》(Inside Job,2011)一片中一样,出现在片中面对采访的问答是经过导演筛选的声音,这些回答中体现了导演的话语权力。片中发问者代表着权威,纪录片的媒体制作方行使这一权力发问,正常情况下采访人是处于权力的强势方,被采访人虽然用支支吾吾或语焉不详的回答行使了自己的话语权,但在采访人的咄咄逼人的提问面前沦为弱势方。《监守自盗》通过表面上双方都行使自己的话语权来体现客观和全面,但其中隐藏的话语权代表着一种社会责任。图3-4为《监守自盗》的宣传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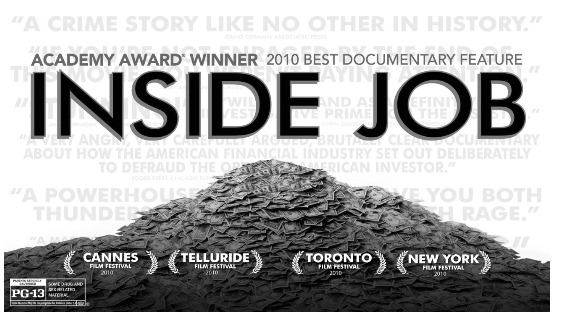
图3-4 《监守自盗》宣传海报
和《监守自盗》一样,纪录片经常采用访谈形式,对于其他一些访谈内容同样可以进行话语权力的分析。纪录片导演为了表现自己的话语权力在选择被采访人的回答时有意运用了其闪避回答的技巧。闪避回答与模棱两可和含混不清有关,是一种故意的不相关问答,面对处于强势的掌握媒介工具的提问,被采访人只能是闪避回答。
闪避回答可分为明示闪避和暗示闪避。明示闪避是指答话人或多或少公开告知提问人他对提出的问题不予回答。典型的明示闪避有“无可奉告”、“我不知道”等说法。暗示闪避是指答话人故意不正面回答,回答时采用一些宽泛、含蓄、曲折的表达方式,没有提供提问人真正希望得到的信息。闪避回答作为一种交际策略,是新闻采访、日常会话中一种常见的语言现象。
《监守自盗》一片中大量采访的对话体现了话语权力的分配。记者与哥伦比亚商学院院长Glenn Hubbard之间对话则是明示闪避,当记者问“谁是你的咨询客户”时,Glenn Hubbard明确拒绝回答,并皱着眉头下了逐客令。与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Martin Feldstein的采访中,Martin的回答“wha wha wha,I don't know…”在结结巴巴中用明示闪避拒绝了回答。
纪录片话语权主要掌握在创作者或创作者所属的控制集团手里。纪录片较为特殊,存在相当比例的独立纪录片制作者,但独立纪录片制作者并非完全自行掌握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其话语权与出资者相关。
纪录片的话语权首先包括纪录片发布主体的话语权,主要为导演在对于真实材料的掌握、剪辑和发布基础上所拥有的。以早期奥斯卡获奖纪录片中前3年为例,《丘吉尔之岛》(加拿大电影局)、《中途岛战役》(美国海军,20世纪福斯电影公司)、《柯柯达前线》(澳大利亚情报局)、《莫斯科反击战》(苏联)、《战争前奏曲》(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沙漠胜利》(英国情报部)、《12月7日》(美国海军战略服务处)7部纪录片涉及加拿大、美国、苏联、澳大利亚、英国5个国家,完全是国家话语权的展示,这些纪录片的出品方、投资者、人员来源等都是国家层面完成的,其话语权较为明晰地为国家所有。
迈克尔·摩尔的纪录片虽然是其自己的公司独立完成,属于依靠票房获取利润的商业行为,《科伦拜恩的保龄》也为他捧回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貌似话语权是其个人所有,但仔细分析其作品,特别是由于在片中他的观点通过直接出现在画面中为观众所知晓,他本人一直被认为是民主党的政治代言人,其纪录片在制作过程中也与民主党支持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华氏911》成功播映并获奖之后,在这一年的中期选举中,布什所在的共和党惨败,在参众两院都失去了控制权后,民主党在参众两院12年后首次占据多数席位,似乎民主党在摩尔的纪录片中掌控了话语权,因此很难让人相信话语权是摩尔一人掌控。(www.zuozong.com)
其次,纪录片的话语权包括不同纪录片创作者之间的话语权控制。同一事件可能有多部纪录片反映,但影响力存在大小差异,例如《监守自盗》在众多关于金融危机的纪录片中脱颖而出,该片的话语权就是建立在对其他同类型纪录片的控制和影响之上的。再如对于中国艾滋病问题的记录,曾经也有多部不同角度予以表现的纪录片,但获奖作品《颍州的孩子》更具权威性,对于其他同类作品也存在着明显的话语控制。
话语权作为一种潜在的现实权力,更多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权力只能存在于群体中,权力是个人基于自身利益的全面权衡,出让自身的一部分利益交由他人掌控的一种社会行为。纪录片的话语权就是观众出于对个体自己或整个社会发展的形势考虑,将自己的部分利益交由纪录片导演来间接控制,但这种控制是潜在的,需要通过社会的职能部门来完成最终的行为。
大卫·麦克奎恩在《理解电视》中曾说过:“所有的再现任何时刻都只能有一个单一视点。”[12]纪录片展现给观众的信息远非全面的情景或背景,而只是包含一个非常有限的部分,因为纪录片传播出去的信息都只是导演把关取舍后所留下来的部分,是就真实世界的某一部分进行的再现。如何再现?再现什么内容?这就是纪录片导演的权力书写,但这种权力书写多数情况下并非导演本人所单独拥有。
(二)平民的话语
纪录片是对于历史的一种书写,而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权力的书写,可以认为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而记忆则具有个人化的性质,福柯认为记忆是历史所不能吞没的场域[13]。前文所提及二战期间的纪录片话语权基本被国家所掌控,是一种明显的权力书写形式,而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观众和评委逐渐转向为青睐一种民间的、个人化体验性质的纪录片影像书写形式,特别是以记忆的名义进行的个人书写。
1950年以后的几个时期,纪录片强调平等视角的表现,不再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格局进行真实素材的排列,而是以平民的角度拍摄与组织画面。奥斯卡获奖作品转向强调“小人物”记忆的真实,特别偏爱根据日记或根据回忆录拍摄的题材。
二战给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带来长久痛苦的记忆,与二战期间由国家投资书写的战争影像不同,1946年以后再没有关于二战的直接纪实性的纪录片进入奥斯卡,但相关题材特别是犹太人受到的迫害却一直在获奖纪录片中以个人记忆的方式进行反映。《灭绝种族的大屠杀》(Genocide,1982)由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和奥逊·威尔斯配音讲述,是按照600万被屠杀犹太人的平民视角进行的有关二战的个人回忆。这是第一部获得奥斯卡奖的对二战罪行进行回忆与反思的纪录片,实现对战争这一传统上由权力书写的主题转向到记忆书写的形式。
在这部纪录片中之后,《终点饭店:克劳斯·巴比的一生》 (Hôtel Terminus,1989)以267分钟的片长讲述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号称“里昂屠夫”的里昂警察局头目克劳斯·巴比的罪行,他80年代才被抓捕归案,但该片没有以权力书写的形式讲述其罪行,而是通过大量当事人的采访,通过这些人的记忆勾勒出纳粹的罪行。这种个人回忆式的处理方式对于纪录片的再现历史起到更加真实、贴近的效果。该片除获奥斯卡奖外还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戛纳电影节的奖项。
到20世纪90年代,平民记忆的影像形式在奥斯卡纪录片中占据绝对优势,特别是1996年,评委不约而同地将长、短两部纪录片奖的选票都投给了关于二战期间纳粹暴行的个人记忆的影片,它们分别是《卡里·安卡利斯:一位幸存者的回忆》(One Survivor Remembers:Kary Antholis)和《受人怀念的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 Remembered)。记忆书写增添了纪录片的人性关怀,避免了战争镜像的单调。
记忆是人类的一种心智活动,是过去的经验在大脑中的记录,而纪录片通过影像的形式将这种记忆形象化。记忆是人类单个主体所存储的内容,但只有在具体的社会交往中才能发挥作用,也就是必须以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的形式出现。纪录片所记录的是单个人的记忆,但在播映过程中形成群体的交往,将个人记忆放大于社会之中。
“9·11”事件之后,普通美国人突然于平静的时局中对政府外交政策产生困惑,愕然于世贸双塔倒下的巨大震撼之中。“9·11”事件的第二天,总统乔治·布什发表演说,称发生的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是对全体文明世界的袭击,并呼吁国民团结起来打一场与众不同的反恐战争。美国人通过个人记忆将自己想象成灾难受害者,而奥斯卡获奖纪录片对于事件的记忆是由《世贸双塔》来完成的,而它则是由分别为消防队员和警察身份的兄弟俩的个人记忆所构建的,在美国政府、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媒体的共同作用下,关于“反恐”的集体记忆合理地产生了,纪录片也通过记忆书写达到了初步的目的。
奥斯卡对于世贸大厦的记忆是由另外一部获奖纪录片——《走钢索的人》(Man on Wire,2009)完成书写的,这里的记忆是由菲利普一个人的记忆转换成集体记忆的。菲利普17岁时,报纸上一则关于世贸大厦动工的消息令他兴奋不已,他希望登上这个人类建筑的巅峰完成自己的梦想,准备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他却始终不曾停下追寻的脚步。当菲利普最后站在世贸大厦之间450米的高空钢索上,从容地以各种优美的动作行走时,他个人的记忆最终被纪录片所书写,被记录于“9·11”事件之后美国人的心中。奥斯卡获奖作品就是这样从早期的简单权力书写过渡到当下的记忆书写之中,纪录片的故事性和贴近性得到极大的增强。
每当世界发生大的变局或者当权力发生转移时,由胜利者书写历史是不争的事实,而从权力书写到记忆书写的变迁过程则体现了奥斯卡获奖纪录片的多元化分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