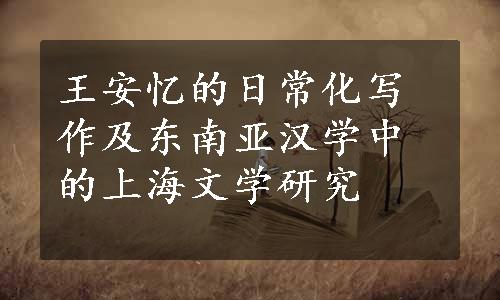
黄 妃
王安忆把目光投注于日常生活实与整个大环境的变化有关。上海文学素有描写市民社会的传统。此传统曾一度中断。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常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五四之后,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是政治的、启蒙的,在主流意识形态之下,日常生活的题材被忽视与遗忘。1949年后,左翼文学大行其道,个体消融在党与民族的集体意识之中,日常生活书写在历史叙事的主题面前变得琐碎、平庸。但是这种情形到80年代之后有了改变,启蒙使命和人文主义关怀被商业大潮所取代,官方的意识形态逐渐退出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在后工业社会里,知识分子开始以新的姿态面对新的现实。在商业经济社会里,都市地位提升了,个人从集体中挣脱出来,市民阶层受到重视,他们所崇尚的俗世生活进入了创作的视野。平民群体的生活价值获得关注,创作与历史叙述开始分离,文学多元化的格局遂形成。因此,有论者认为王安忆的都市题材频繁的出现,不仅是她个人兴趣的转移,也是呼应90年代文坛对于宏大叙事的反驳。(1)在这背景之下,人们被压抑的欲望和思想得到空前的释放和表达,理想主义被击溃,物质欲望的伦理崛起。在创作上,宏大的观念语式被俗世的审美文化所取代,日常生活重回作家的创作视野中。文学由单一化、政治化转向世俗化和多样化,由符合政治的要求转向表达个人的追求。市民社会浮出台面,人们怎么生活变成一件重要的事,而文学开始关注最实际的生活面,即普通人的生存状况。
面对外在思潮的变化,王安忆的态度是谨慎的,在多元缤纷的都市意识中,王安忆推崇俗世生活的价值。她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如下:
事实上我们看小说,都是想看到日常生活,小说是以和日常生活及其相似的面目表现出来的另一种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肯定和我们真实经历的日常生活不同,首先它是理想化精神化的,还有是比较戏剧化的,但它们的面目与日常生活非常相似。人的审美一定要有桥梁,就是和日常生活相似。
日常生活虽不是社会生活的中心,王安忆却把她对日常生活的感受和观照转化为一种审美和历史的实践。(2)她把日常生活和艺术审美联系起来,体现她一贯坚持的小说观,即小说是建立在现实世界材料基础上的心灵景象。(3)王安忆打破精英的立场,消弭正统艺术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把日常生活审美化。她写出大历史背后的“小历史”,也就是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所说的挥别“大叙事”走向“小叙事”的文化语境,(4)那是柴米油盐的日常。
王安忆认为如果以文体来说明上海,那么上海和小说特别相投的地方,就是世俗性。上海与诗、词、曲、赋,都无关的,相关的就是小说。因为它俗,所以消除等级差别,以至沉渣泛起。而且以消遣为乐,但他的闲心不是艺术心,好去消受想象的世界,而是窥秘心,窥探各家长短,与狗肚鸡肠之事,带些隐私性质的。王安忆写上海,因为她知道上海的灵魂就是世俗性,而小说所表现的就是俗世的面目。它不具有诗词曲的高雅,而是“归还给思想以人间烟火的面目”。所谓人间烟火就是《长恨歌》中平安里的几个男女的吃喝、打牌、情欲与龃龉。王安忆重绘日常的世事,重新赋予上海的俗世生活价值。她把写作的重点放在日常生活,是为摆脱传统的僵化模式与思维方式,以否定的形式趋向更多元的面向。
王安忆以日常生活作为自己价值的依托与她个人的境遇有关。文革时,敏感且早熟的王安忆早已感受成长的孤独。当时的上海给人一种末日来临的无依感,基于这种感受,王安忆笔下的人物就具有某种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只抓住眼前实际的生活,以尘世琐细的生活,来填补孤独与空虚的精神状态。
王安忆的创作转向日常,还取决于她个人的历史观,即她诠释历史的方式。在访谈《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中说:
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道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
王安忆看待历史的方法有别于历史学家之坚持找出历史的真实,她无意于宏大的历史叙事,反之关心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王安忆认为无论多大的历史变故,表现在小说中都应是具体的日常生活。外在的战火硝烟、政治浮沉都只是短暂的浮光掠影,日常生活尽管琐细卑微,却是时间流逝里最扎实的人生,而扎实的人生才可使生活蒸腾出奇光异彩来。王安忆在作品中企图挖掘的便是芸芸众生悲欢后面的生活力量,和他们面对生活的顽强态度。王安忆深刻地理解当一代人都在叹息精神信仰倒塌的时候,人们只能贴近日常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念也于焉产生。在她的作品中,无论是80年代的《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好婆与李同志》,还是90年代的《长恨歌》《妹头》和《富萍》,上海都仅是文本中的远景,她着力凸现的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弄堂生活和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意识”。(5)王安忆以日常性写作呼应了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1901—1991)的说法:“人必须是日常的,否则,他将什么都不是。”(6)
从1982年发表的《流逝》开始,王安忆便着力刻划一种充满质感的生活。她从平实的生活里看到人生的飞扬,也从琐碎平庸中找出意义。王安忆不强调程乃珊笔下“蓝屋”(7)的上海,也不写动乱时候的上海,而是从生活中挖掘出意义来。《流逝》中的欧阳端丽原是富贵人家的少奶奶,但文革的生活把她磨练的坚毅且刚强。她从操守家务,在劳动生计里体验生活的意义和俗世生活的乐趣。而生活本身也是不曾间断地支持她活下去的力量。她节衣缩食,甚至“尝到了节约的乐趣,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她把旧旗袍修改成孩子的衣服,“尝到了创造的滋味”。她到工场间做临时工,对工作“感到兴趣,看见从自己手里绕出了一个个零件,整整齐齐地躺在纸盒子里,又兴奋又得意。”除了维持家中的基本生计外,端丽也应付家中的各种出其不意的事件,如文光报名到黑龙江插队,文影到江西之后患病回来等。这些事情的锻炼把端丽过去潜藏的力量都唤了回来。文革后,都市里的生活又回到常态,端丽因此多出许多闲暇的时间,但却无端生出寂寥的情绪。端丽才领悟到过去艰难的日子中的生活乐趣与感慨,其实充满生活的质感,而生活的意义正是在这种质感里。
王安忆坚持于日常生活书写,因其发现日常物质化的内部隐藏的是一种生活的韧劲。她欣赏平庸日常,并表现出宽厚的态度,因为她看到一种生活的热情,一种都市里生存的姿态,她也同样地对这样的生活产生认同。王安忆说:
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上半叶,你到淮海路来走一遭,便能感受到在那虚伪空洞的政治生活下的一颗活泼跳跃的心。当然,你要细心地看,看那平直头发的一点弯曲的发梢,那蓝布衫里的一角衬衣领子,还有围巾的系法,鞋带上的小花头,那妙不可言,用心之苦令人大受感动。
王安忆写出一种人们在政治压力底下,依然顽强坚持生活的热情。王安忆对于生活内在韧劲的体悟也表现在一群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的旧遗民身上。胡迪菁、王琦瑶这些人在虚无的时代,以生活安慰她们的孤寂芳心。例如《文革轶事》中的亭子间聚会和《长恨歌》中的“围炉夜话”,就是这座都市的遗民在文革时,以他们有限的经验去回想这座都市曾经有过的繁华似锦。他们的过去在政治压抑之下早已失落,未来又茫然不可知,只有眼前的生活才是安定踏实的。
亭子间的油烟腾腾,油锅噼噼剥剥地爆,这有一股温暖和单纯的日常气氛,叫人心中安定踏实。它使人想起一点一滴细水长流的生活。它是那种最不可少的基本生活细节,这细节充实了我们寂寥的身心,是使我们在无论多么消沉的时日里都可安然度过的保证。它像最平凡的水那样,载起我们人生的渡船。
王安忆从腾腾的油烟、单纯的日常气氛,以及心中的安定踏实感受,发现了生活世界的意义。(8)简言之,生活本身具有意义与审美价值,也因此,审美溢出纯艺术的范围,进入日常生活中。尤其是2000年出版的《富萍》、2003年出版的《桃之夭夭》,更可看出王安忆对俗世生活的理解与同情。在《富萍》中,有如是描写:
她们诚实地劳动,挣来衣食,没有一分钱不是用汗水换来的。所以,在这些芜杂琐碎的营生下面,掩着一股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
王安忆把俗世中的劳动化解在一股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里而成为一种单纯的美。在她的俗世生活的描写里,没有像过去对精神乌托邦追求的焦虑。《乌托邦诗篇》中的精神追求曾经是王安忆的探索方向。但回到最实在的地方,王安忆发现生活才是人们心灵的慰藉。如果王安忆的日常化写作只是停留在物质主义的层面上,关心的是躯体欲望和享受,那么她的写作将流于浅薄。王安忆的不同在于她描述日常经验的真实细节的同时,也体现心灵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存在,她要赋予日常生活一种意义。
王安忆也看出即便在翻天覆地的变化里,尽管其中有许多无奈与落寞,上海人对生活还是执著地坚持着。如在《妹头》中,不论时代多么落寞黯然,人们还是一样地追求摩登:
每一条弄堂里,都闲逛着几个不同届别的社会青年,他们吃着家里的闲饭,竟还追赶着摩登。住在这条街上,又是个青年,命运不济,也跳脱不了摩登的浪头。
此外,从王安忆的日常化叙述里所蕴藏的是一种都市精神,而这现象以上海的都市文化来凸现。这座都市的真正本质就在于日常生活,以及由这日常所传递出来的市民意识。上海人以其特殊的方式,表现都市的内在文化精神。王安忆的《长恨歌》在日常生活的叙事上达到了一个高度。(9)她以王琦瑶的一生作为上海市民生活的写照,王琦瑶的照片登在《上海生活》,就像是“上海生活”的注脚。这可说是“上海生活”的芯子,穿衣吃饭,细水长流的,贴切得不能再贴切。王安忆揭示了都市的内在精神就是日常生活,因此日常生活是活泼的、恒常的,而且有其意义。
王安忆肯定日常生活的价值,她对日常生活意识的表述可由其对生活细节的描写看出。她通过直接叙述再现生活场景来描写细节。这种方式在80年代的作品《流逝》中已有所表现。后来的《长恨歌》和《富萍》更是把叙述技巧发挥到极致。在细节的叙述中,王安忆观察到日常生活的内在精神,也结合了她对生活的审美感受。如美人图的月份牌、摩登的发式、粉红旗袍缎子上的绣花,以及泛着幽光的棕色地板和垂着流苏的麻织床单所构筑出生活的精致美。又例如《长恨歌》中平安里的桂花糖粥的香味,《富萍》中一床枣红底白花的被子,经过太阳照射后的厚厚松松的味道,这些家居细节也因其美感而有了意义。
除了展现生活中的美,王安忆也说:
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这是烟火人气的感动。那一条条一排排的里巷,流动着一些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东西,东西不是什么大东西,但琐琐细细,聚沙也能成塔的。那是和历史这类概念无关,连野史都难称上,只能叫做流言的那种。流言是上海弄堂的又一景观,它几乎是可视可见的,也是从后窗和后门里流露出来。(www.zuozong.com)
王安忆不排除日常生活中的个人性、世俗、琐碎,而且细节描写在她的作品中占据极大篇幅。《长恨歌》第二部中的四个章节基本上写的即为饮食男女。王安忆直接描写王琦瑶在炉边做饭的情形,王琦瑶成了王安忆小说中一个最有创意的厨师。因为她的高湛厨艺,所以吸引一群朋友到她的家里吃喝闲聊。王安忆由这些细节的描写里营造出家的气氛。(10)王安忆对于生活的洞察,让我们理解对容易被忽略的家居空间应该培养更多样的观察视角。这种专注在琐碎的细节上的生活方式,让日子过得相对容易。
在患难的时代里,除了日常之外,外在的历史变动与他们其实没有多大干系。只有生活才是人们最切身的问题。王安忆内在思考的蜕变,正因为她不愿意回避生活本身,反之唤起生活的内在诗意。在《富萍》中有段巨细靡遗的细节描写,王安忆描写房间的设计,屋里的摆设,以及家具的由来,原来“楼上买了一个大橱,尺寸太大,无论如何抬不上去,任何一个角度,都在楼梯拐弯处卡住,无奈,就与楼下商量,转卖给他们。他们欣然答应,连价钱都没问一下”。还有对这个大橱的样子也精细地介绍,“这个大橱十分气派,漆成橘黄色的水曲柳贴面,边缘勾着简洁的线条,无脚的西洋的款式,对开门,镜子镶在里面,一边挂大衣,一边是抽屉。老实说,这个大橱和他们家也一点不配,是配那种洋派的资产阶级人家”。最后是东家买“一个三人长沙发。奶奶一看这沙发,就晓得是什么价钱了。钢管镀克鲁米的沙发架,木头的流线型扶手。坐垫和靠垫的席梦思,奶奶手一摸,就摸出里面是怎样的小弹簧,又是如何排得密,又软又不会一坐一个坑。沙发面是绿平绒,绒头相当细密,又柔软又硬扎。奶奶想,这也是过去的资产阶级才用的。沙发在他们家里,也大不配,可毕竟增添了一点生活气息”。奶奶从东家的房里所添加的物质看到生活的活力。王安忆的描写,也像是一个空间的展示,把其中物质层面的装饰展示出来,经由奶奶的眼睛看到一个家庭建立起生活的美。通过细节描写,生活不再仅仅是刻板的表象而已,还有装饰与活力。(11)
在王安忆的笔下,叙述本身就是诠释。《富萍》中,王安忆写孙达亮在棚户区盖的房子时,她写道:“白墙,黑顶,红门窗,连着一道斑烂的砖墙,多么鲜亮的一座小屋啊。屋内呢,石灰水刷了墙,地铲平了,用罗细了的土洒一层,借个磙子压实压光。”在此,她在细节上进行细腻绵密的叙述,勾勒出上海郊外穷人家的房子面貌,而短句,简洁词汇的应用则贴近一种接近自然的朴素美,把文本中的叙述和作者的意绪诠释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如此,由日常细节的叙述所体现出来的美感,也看出王安忆美学观念的转变。王安忆身处在后现代的都市社会里,都市里多元价值的吸纳,也是她在创作思考上变化的原因。
从叙述方法的层面来说,日常往往与写实相联接,写实更容易再现细节。王安忆说过:“基本上我是一位写实作家”(12),也就是她的创作表现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性,刻划生活中确实有的人,表现生活中确实有的细节。例如她的作品《本次列车终站》《流逝》等便是采用直观写实(13)的叙事手法,运用最真实的生活细节,按照时间的流动叙述生活,把人生的升降沉浮从细微处显现。《长恨歌》中王安忆的直观写实手法再次发生变化。她并没有放弃故事的内在逻辑力量,但打破小说以情节取胜的传统,把生活细节加上个人繁复且细密的叙述语言,放大叙述者对细节的心理感受,而赋予细节高度的审美内蕴。万燕说王安忆用女红的手法,沉湎于缝纫的无限的针脚与编织的无休止的缠与绕,这是纯女性的生活内容之一,重复、单调、与社会无缘,有的是女人编织的韧性与执著。(14)
所以说王安忆的都市叙事充满日常的柴米油盐、流行的服饰、幽深难测的弄堂等意象,她放大细节,呈现生活常态,再经由阐释性的叙述语言,在文本中塑造一种抽象的生活氛围。这种文本中的意象连缀应用,与日常化的常态叙述方式,其实是在王安忆内在心灵的控驭下完成的。因此王安忆说:
我属于写实派,我喜欢现实生活的外部状态,因为存在的合理性,而体现出平衡、对称的秩序,我要求我的故事空间亦有这样的美感。但空间里或者说舞台上发生的,是我内心的情节。
她以日常细节为素材,结合内在心灵感受,叙写具象的生活形态。尽管王安忆的小说结构松弛散漫,也无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却内蕴了无限诗意。
(本文整理自作者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系首次发表。)
(1) 李泓:《构筑城市日常生活的审美形式——论王安忆的城市小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6期(2001年11月),第67页。
(2) 李雪梅:《王安忆:日常化写作的一个例外》,《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第20页。
(3) 李新:《上海的芯子:日常生活的恒久性——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一解》,《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49页。
(4) Jean-Francois Lyotard著,黄宗慧译:《后现代状况》,收录在Jeffrey C.Alexander,Steven Seidman主编,吴潜诚总编校:《文化与社会》,台北:立绪文化公司,1999,第398—415页。
(5) 李泓:《构筑城市日常生活的审美形式——论王安忆的城市小说》,《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6期(2001年11月),第65页。
(6) Henry Lefebvre,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John Moore(tr.),(Lond on;New York:Verso,1991),p.127.
(7) 《蓝屋》是程乃珊的代表作,指的是小说中曾经繁华一时的豪宅。
(8) 王峰:《从文本到生活世界——文本阐释的几个意义层次》,《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第34页。
(9) 李新:《上海的芯子:日常生活的恒久性——王安忆上海小说主题一解》,《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50页。
(10) Gang Yue,“Embodied Spaces of Home-Xiao Hong,Wang Anyi,and Li Ang”,in The Mouth that Begs-Hunger,Cannibalism,and The Politics of Eating in Modern China,(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315.
(11) 周宪:《日常生活的“美学化”——文化“视觉转向”的一种解读》,《哲学研究》2001年第10期,第68页。
(12) 2003年12月15日,本人与王安忆作访谈,她这么说。
(13) 邓寒梅:《张爱玲、王安忆上海小说的叙事策略》,《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报)》第29卷第2期,第55页。
(14) 万燕:《解构的“典故”》,《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第54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