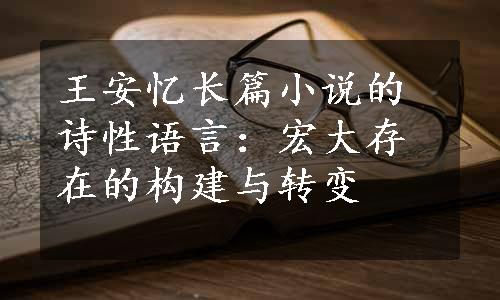
伍燕翎
“语言首先为一切有目的的深思提供道路或僻静的小径。没有语言,一切思想和行动就没有能够借以激发和发挥作用的那一度。因此,语言本来并不是思维、情感和意志的表达。语言原本是人的本质在其中,首次可以符合存在以及存在的召唤……”
——海特格尔:《人,诗意地栖居》
翻开中国文学史的第一章,我们读到的是《诗经》。《诗经》是初民最早以歌谣形式来探知外部世界的“巫术之音”。它是中国诗歌的源头,也是初民用以表述情感的方式。随之的楚辞、汉赋、乐府诗和中国古诗之瑰宝——唐诗,皆可看出以诗之形式来表达生活的内容。即使是古代文论巨著《文心雕龙》也采取了骈文和赋这种美文的形式,这无疑说明了“文学自觉时代文论的言说主体对言说方式诗意化的自觉性体认”。(1)由此,我们相信,中国古典文学在表现人类思维方式时用的皆是一种“诗性的语言”。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学尤其诗学的传统确实可看出诗性智慧的投射。意大利伟大哲学家维柯(Vico,1668—1744)亦曾经把上古异教民族或哲人最初的智慧称之为“诗性的智慧”。(2)
兴盛于20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对“诗意性”(poeticity)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基础。在西方文艺美学史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名专著《诗学》对“陌生化”的诗学理论提出了最初步的概念。他说:“给平常的事物赋予一种不平常的气氛,这是很好的;人们喜欢被不平常的东西所打动。在诗歌中,这种方式是常见的,并且也适宜于这种方式,因为诗歌当中的人物和事件,都和日常生活隔得较远。”(3)“陌生化”最早源于文学评论家的诗学理论,主要为了发掘和揭示诗歌语言本身的“诗性本质”。这也是后来俄国形式主义者极力推崇的。他们相信语言是人们在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最初始时冲动产生的,它本是一种诗性的创造活动,根植于原始人类最初的心灵感动,并成为他们的诗化哲学。据形式主义学派的说法,人类初始的语言非常富含诗性,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语言逐渐失去原有的“诗性本质”,并随之僵化,放弃了语言最初的诗意性和灵动性。故此,形式主义者主要的工作即是重新寻回和挖掘语言本身原有的“诗性本质”,让后来我们日常惯用的机械化语言还复其身。陌生化诗学理论较后成熟于20世纪初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Victor Shklovski,1893—1984)的手中。在什克洛夫斯基著名的论文《作为手法的艺术》中,他刻意区分了散文式的语言建构和诗歌语言规律的相对立。他认为散文式的语言有如熟悉的动作,一旦成为习惯性便变得无意识和机械性了,反之诗歌语言中“没有平稳语音的异读规则”或“允许有难发的音的组合”更为人注目。(4)由此,什克洛夫斯基提出:
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的视象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反常化”手法,是复杂化形式的手法,它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延,既然艺术中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5)
上面提到的“反常化”即是对“陌生化”诗学理论的最初诠释。由此可见,形式主义者追求的是对事物最原始的感受和最初面貌的感知。由此,倘若我们要从呆板和僵化的惯常生活形态里抽离出个人对事物的最切身体验,则有必要使用艺术化的手法,即是诗语的“陌生化”来回归到人类最早的诗性语言去。
仔细爬梳中国现代小说史,小说的现代性发展自“五四”现代化进程以后,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中国现代小说一直沿着“小说抒情化”的发展轨迹,形成了小说散文化的独特文体。以废名(1901—1967)首开“田园小说”之后,小说散文化逐渐受到重视。沈从文(1902—1988)、郁达夫(1896—1945)、萧红(1911—1942)、孙犁(1913—2002)等,到对小说语言散文化尤为偏爱的汪曾祺,更是将此文体的发展推前了一步。著名小说评论家杨义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将类似的小说笔法理解为“小说的‘散文化’”。(6)从小说散文化的发展谱系来看,中国现代小说这种抒情的散文笔法,很多时候被文学评论者认为是“小说诗化”。人物、情节和环境的淡化,使得小说家更着力处理小说语言的问题。诚如对“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的汪曾祺而言(7),他对“诗化小说”的看法是:“所谓诗化小说的语言,即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纯散文的语言。这种语言,句与句之间的跨度较大,往往超越了逻辑,超越了合乎一般语法的句式(比如动宾结构)。”(8)这点和俄国形式主义主张“陌生化”的诗学理论略有相似之处,即是写作者渴望超越固有的叙事和语言形态,进行语言的反规范。
从中国现代小说诗化的传统派生出去,王安忆可视为继汪曾祺以后,以散文化的笔触来呈现小说的当代作家。从她早期的小说《雨,沙沙沙》到“三恋”,已经可以看出王安忆对抒情语言的偏爱,更何况她是当代少数能把小说语言理论付诸于实践的作家。从《长恨歌》(1995)、《富萍》(2000)到《上种红菱下种藕》(2002),她这时期对长篇小说的着力表现,显然看出她正处于写作最巅峰的时刻,而这时她对小说语言的实验和实践也可谓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本文尝试从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核心——“陌生化”手法的视角下来探索王安忆的小说语言。
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手法的艺术》一文开宗明义表示“艺术是用形象来思维”,说明“形象”对文学尤其诗歌的重要性。他借用波捷勃尼亚的理论基础,指出:“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即藉助于形象的思维,而形象的任务即藉助于它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对象和活动归组分类,并通过已知来说明未知。”(9)我们可以这样来认知这段话,即作者只有通过形象化了的事物才得以更能掌握事物的特性,尤其对难以认识和理解之事物而言,“形象”有助于厘清、整理和建构我们的思维或思考模式。然而,何以只以诗歌作为藉助于形象的思维?倘若用什克洛夫斯基自己的解释,乃是因为“诗意性形象是造成最强烈印象的手段之一”。(10)
中国哲学里,早有老子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认为“无声”“无形”是实物之外所有的想象意蕴,这才是事物至美的境界。中国文学传统尤其注重“意象”,并且着重的是“言外之意”。晚唐司空图提出“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和“味外之旨”是古代文论对“意境”“意象”的进一步要求。俄国形式主义者主要是在现实的处境中找到艺术的表达,把日常所感所知升华到艺术化的语境之中。
王安忆善于驾驭长篇,《长恨歌》一直被认为是她对中国当代小说最大的敬礼。王德威因此说她是继张爱玲以后真正的海派传人也不为过。以王安忆向来的小说语言而论,《长恨歌》确实有较高的文字密度,即使是用语的组合或意象的选取,亦是经王安忆精挑细选。
《长恨歌》写一个上海女子王琦瑶的一生之余,也同时完成了一部上海文化史。这部隐约看出作者仿拟雨果《巴黎圣母院》的小说构造利用了极大的篇幅来描述场景: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和上海弄堂的女儿。这些意象的选择无疑间接地加深了作者对小说主题的审视,以及读者的阅读印象。《长恨歌》可说是王安忆小说中意象堆砌得最多的一部。从《长恨歌》的第一章,已经看出作者对这些意象的撷取的用意。先看她给“弄堂”和“流言”的各种形象:
“那种石窟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们都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幅官邸的脸面……”(4)
“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有一些私心的。”(5)
“上海的后弄更是要钻进去人心的样子。”(6)
“弄堂里横七竖八晾衣竹竿上的衣物,带有点私情的味道……”(6)
“上海的弄堂真是见不得的情景,它那背阴出的绿苔,其实全是伤口上结的疤一类的,是靠时间抚平的痛处。”(7)
“上海弄堂如果能够说话,说出来的就一定是流言。”(8)
“这些流言是贴肤贴肉的……”(7)
“流言是要老派一些的,带薰衣草的味道的……”(7)
“拐角楼梯的弄堂房子的流言则是新派的,气味是樟脑丸的气味。”(7)
“流言总是鄙陋的。它有着粗俗的内心,它难免是自甘下贱的,它是阴沟里的水,被人使用过的,污染过的。它是理不直气不壮,只能背地里窃窃喳喳的那种。它是没有责任感的,不承担后果的,所以它便有些随心所欲,如水漫流。”(9)
“上海的弄堂是藏不住大苦衷的。它的苦衷都是割碎了平均分配的……”(11)
类似的描述在《长恨歌》里俯拾即是。以上例子加黑的形容词语,虽然全是用以描绘弄堂和流言,但它们无不是紧贴着上海市民日常的生活气息。王安忆有一句贴切的话这样形容上海的弄堂:“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6)细读之下,王安忆对一事一物的洞察无不是来自她的日常生活,这使她对四十年代上海以及活动于此空间人物的心理掌握得极为准确。什克洛夫斯基的“反常化”即是要恢复人们对日常事物细部的视察,乃至从僵化和麻木的事物寻回对生活最初的感受。《长恨歌》近乎大量读到类似上述极富表现力的短句,尤其突显的是,这些以“……是……的”判断句式表现了作者主观的叙事口吻,同时也反映了语言的可感度。
诗意性形象的建构主要是来自文学语言的可感性。语言的僵化主要是因为日常用语的习惯和普及,故而陌生化语言追求的则是感官反应出来的第一印象和感觉,换言之,陌生化语言着重的是直观的、可感的语言。这种产生于主观、直觉和感性的审美效应恰是什克洛夫斯基所说的“反常化手法”。他以列夫·托尔斯泰只写其所见,洞察秋毫的写作笔法进一步说明。他说道:“他不用事物的名称来指称事物,而是描述第一次看到的事物那样去加以描述,就像是初次发生的事情,同时,他在描述事物时所使用的名称,不是该事物中已通用的那部分的名称,而是像称呼其他事物中相应部分那样来称呼。”(11)根据以上的说法,“反常化”着重的是作者直观的主观印象。因此,小说家若要加以描述初次出现的人物、场景和事物时,敏锐的视听观感就显得无比重要了。王安忆不仅从各个角度抓准了事物最鲜明的特性,同时,她把上海的各种风情以最自然无饰的语言还原到日常生活的原貌上,构成了小说中完整和统一的叙事风格。
什克洛夫斯基指出:“凡是有形象的地方,几乎都存在反常化手法。”(12)王琦瑶,这个人物形象是用“时间”来刻画的:
“她不数日子,却数墙上的光影,多少次从这面墙移到那面墙。她想:‘光阴’这个词其实是‘光影’啊!她又想:谁说时间是看不见的呢?分明历历在目。”(115)
“那面墙上的光影,简单熟过骨头里去的,流过了一百年一千年的样子,总也不到头的,人到底是熬不过光阴。”(286)
“她收起烟还得再坐一时,听那窗外有许多季节交替的声音。都是从水泥墙里钻出来的,要十分静才听得见。是些声音的皮屑,蒙着点烟雾。有谁比王琦瑶更晓得时间呢?别看她日子过得昏天黑地,懵里懵懂,那都是让人搅的。窗帘起伏波动,你看见的是风,王琦瑶看见的是时间。地板和楼梯脚上的蛀洞,你看见的是白蚂蚁,王琦瑶看见的也是时间。星期天的晚上,王琦瑶不急着上床睡觉,谁说是独守孤夜,她是载着时间漂呢!”(318)
《长恨歌》里写尽了王琦瑶的一生,其中有繁华,也有沧桑;有青春,也有堕落,读不尽的是关于一个女人从生到死的人世岁月。然而,王琦瑶脸上的岁月却不是掠过无痕,王安忆利用有形的光影来写无形的光阴,以实写虚,又添了无尽唏嘘。王安忆把人们对“时间”的感觉还原到王琦瑶身上,让我们看见时间正从王琦瑶身上一点一滴地流失呢!“熟”“熬”“搅”和“载”几个动态词性的使用,也同时展示了主人公和时间之间的挣扎和拉锯。
早在写作《长恨歌》以前,王安忆在《当前文学创作的“轻”与“重”》一文,曾对她的小说语言风格作了相当自觉地说明:“我近来常常感到所谓写小说,就是一定要把小说语言和日常语言去区别开来,小说是小说自己的话。既然这样,在小说中戏剧性地模仿人物语言以至于达到类似日常生活的真实性,就越来越值得怀疑了,我以前写人物对话,总是说‘他说……’‘她说……’,照录不误,现在这种写法我总力求加以避免。这看起来是个小问题,但我认为是个大问题,根本的问题。归根到底,小说语言是一种叙述性的语言,也可以说是语言的语言或抽象化语言。小说家寻找一种生活中没有的语言去描绘生活中到处可以碰到的一些经验现象,包括语言现象,这是问题的关键。”(13)很显然,王安忆是有意识地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小说语言的材料,在俄国形式主义者看来,这就是艺术为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而存在,而这种对审美需求的满足主要是使人们恢复对生活的感觉。王安忆所谓“生活中没有的语言”并不是指文学中精雕细刻的美丽辞藻,而是王安忆自觉地将小说语言和日常机械性的用语区别开来,因为,她需要在生活经验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叙述语言来描绘生活的体验。
《长恨歌》写作不久后,王安忆在复旦大学的授课上,对“抽象化语言”有进一步的说明。王安忆提出语言作为小说之建筑材料时说过,相对于具体化的语言,小说的语言应该是抽象化语言。她认为抽象化的语言是“都是平白朴实的语言,是最为简单最无含义”的语言,同时也是“以一些最为具体的词汇组成的语言”。(14)这种完全放弃了时代感、色彩性和个性化的语言,恰恰是王安忆所努力追求的。王安忆身为上海人,可是她并没有采用南方特有的方言俗语,反倒是对北方汉语进行了最凝练的提升。她钟意于抽象化的语言,因为她想“用这些最常见,最多见的词汇描写任何一种特别的情景。”(15)且看她要读者如何去感受王琦瑶内心的孤独和寂寞:
“爱丽丝公寓是这闹市中的一个最静,这静不是处子的无风无波的静,而是望夫石一般的,凝冻的静。那是用闲置的青春和独守的更岁作代价的人间仙境,但这仙境却是一日等于百年,决非凡人可望。”(97)
“一次次恋爱说是过去,其实都留在了脸上。人是怎么老的?就是这么老的!胭脂粉都是白搭,描绘的恰是沧桑,是风尘中的美,每一笔都是欲盖弥彰。”(310)
王安忆提出的“抽象化语言”其实是基本词汇中使用得最为普遍的,然而恰是这些普遍通用的词汇让人觉得最具生命力和感受力。同时,因为这些词汇的组合恰是来自大多数人们的生活经验,而王安忆以他们的经验为前提,以他们的感受为体悟,摈弃个人、时代的语言色彩,使读者不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或特定经验的准备来阅读。什克洛夫斯基说道:“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感受能力,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接受定势。文学作品如欲永葆其可感性,就必须不断地变换其表现形式,因为表现形式的变化,从另一种意义上而言就是感受方式的变化。”(16)《长恨歌》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建立于诗性形象的建构,而王安忆取自于日常生活的抽象化语言正是语言陌生化的一种表现手法。“陌生化的实质是针对读者的逆反心理而发出的一种挑逗。它的基本方法是通过变换表现方式来更新读者的接受意识,借以打破读者的接受定势。”(17)
意大利的哲学家和语文学家维柯早在俄国形式主义者之前就从人类学研究来说明“诗性语言”的缘起。他说:“我们发现各种语言和文字的起源都有一个原则:原始的诸异教民族,由于一种已经证实过的本性上的必然,都是些用诗性文字(poetic characters)来说话的诗人。……我们近代人无法想象到,而且要费大力才能懂得这些原始人所具有的诗的本性。我们所说的(诗性)文字已被发现是某些想象的类型(imaginative genera),原始人类把同类中一切物种或特殊事例都转化成想象的类型……”(18)我们于此得知,人类最初的语言不是用于认知和推理,它是有诗性的,诗性的本质主要是在于情感的投射,因此,语言最初的艺术本质即是诗。诗的本质后来被我们理解为一种想象的类型,这主要是仰赖人们的直观。
这一点和俄国形式主义者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反常化”的最终目的有所相似。他说:“那种被称为艺术的东西的存在,正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更成其为石头。”(19)上面对诗意性形象的建构的探讨,主要就是恢复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可感,而某程度的可感性很多时候是来自人们主观的直觉观感。我以为,诗性语言的直感更多时候是从第一视觉和嗅觉上建立起来的。王安忆即是利用女性在视觉和嗅觉上特有的细腻和敏感来建构她的小说语言。从《长恨歌》开始,她小说中诸多意象已经是直接来自对视觉和嗅觉的感受。例如,她描述上海弄堂的“流言”就予人极为深刻之印象:
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阴沉气有时是东西厢房的薰衣草气味,有时是樟脑丸气味,还有时是肉砧板上的气味。它不是那种板烟和雪茄的气味,也不是六六粉和敌敌畏的气味。它不是那种阳刚凛冽的气味,而是带有些阴柔婉约的,是女人家的气味。是闺阁和厨房的混淆的气味,有点脂粉香,有点油烟味,还有点汗气的。(8)
作者仰赖自己主观和直接的情感想象,将“流言”和气味联系起来。读者因此对流窜于上海弄堂的流言有了更多更深刻的遐想。这些“薰衣草”“樟脑丸”和“肉砧板”的气味仅属女性特有,而“板烟和雪茄”“六六粉”和“敌敌畏”这些男性专有的气味则是和流言沾不上边的。因此,在“阳刚凛冽”和“阴柔婉约”的对比之下,即刻就能反衬出“流言”是女人家的,是闺阁和厨房的,是有脂粉气、油烟味和汗气的。王安忆利用她独有的女性触觉来描写自己对上海弄堂的认知,她赋予弄堂的气味是来自她对日常生活所见所闻的直感,这就是“陌生化”理论的主张:只有恢复语言意象的可感性,才能重建语言的审美功能;只有让文学语言跳出程序化、自动化、概念化的束缚,才能保持人们对诗意语言的追求。
俄国形式主义者在追求诗性语言提出“反常化”作为艺术手法的同时,认为反常化的目的在于,人们在面对视像的创造和审美的过程时,能够将人们对事物的感觉,或审美的过程延长。这对长篇小说叙事而言,确是相当重要的。长篇小说要能够前后贯彻,意象和语言的组合配搭必须谐调和统一,才能建立起小说叙事的完整。王安忆善于驾驭长篇,但她更擅于在长篇小说中安置适当的艺术形象。《长恨歌》以后,王安忆的长篇小说愈来愈趋向感官上的投射。2002年出版的《上种红菱下种藕》,王安忆几乎将女人灵敏的嗅觉和锐利的视觉发挥得淋漓尽致。翻阅全书,从沈溇的老屋,从华舍街到鱼得水大酒店,从柯桥到镇碑,无一处不是散放着气味和颜色。这种“视觉”和“嗅觉”上的“还原”可说是陌生化的一种诗意写作手法。陌生化,主要是抵抗日常话语的机械性,将我们首次目视耳闻的事物以最强烈的情感诉诸于形象。
《上种红菱下种藕》用的近乎是一种干净而简约的叙述语言,尽管王安忆每次出手写人写景都是一贯细描细写,然而,较之于《长恨歌》,《上种红菱下种藕》则是比较直接和利落的白描笔法。我们先来看《上种红菱下种藕》一系列对场景的描述。王安忆写沈溇老屋的灶间:“熏黄的灶身上隐约可见粉红粉绿的莲花。”(1)写老屋烟囱的烟:“白色的一缕,升到顶上,轻轻地绽开一朵花,花瓣垂下来,谢落了,然后,新的花又绽开了。”(5)通过秧宝宝的鼻子,嗅出了沈溇的气味:“是人粪、鸡粪、鸭粪,在太阳下发酵的气味。还有草木灰、柴灰、灶灰的气味。溇头里的臭水气味也传过来了。”(51)再则老屋四周随时季映照出的颜色:“老屋忽然又换了一种颜色,变成一种统一的姜黄色。好像是太阳走动的结果,光线变换了角度,将其中的黄全盘倾出,连秧宝宝也染上了这姜黄的基调。”(53)沈溇是王安忆首先要给上海劳动阶层勾勒出的一个栖居地——朴直和单纯,“粉红粉绿”“白色”“花”“姜黄色”“黄”“太阳”“臭水”和各种气味等字眼的组合,无一不是和劳动人民的生活脉搏紧紧环扣,其中更是洋溢着他们的健康和积极。
从沈溇到华舍镇,王安忆主要通过蒋牙儿和秧宝宝这两个女孩的游荡来勾勒镇上的面貌。虽然《上种红菱下种藕》的笔触已经脱离了上海都会的锦绣繁华,但华舍镇依旧还是繁忙的。王安忆给华舍镇选择的色调有:“河面反射着白亮的光”“琉璃瓦的顶,金光四射”“镇碑的花岗石面,在强光里,变成金属一样的钢蓝”“河面在烈日下,颜色变浅了。草、苇叶、萝卜花,也都浅成一种灰白的颜色”“灶间里也是静的,水斗、水泥地、花岗岩的台子,全收干了水分,变成灰白的颜色。砧板,也是晒白的……上方没有一丝云,白热的天空。”(78)华舍镇是小说主要的场景,是秧宝宝和她女性朋友成长的摇篮,故此,小镇的面貌在视觉上予人强烈的印象是很重要的。视觉形象是一个由物象到意象的中介,但是视觉对象成为意象的过程,则需要个人的意识情感的充分参与。维柯认为原始人类说的“诗性语言”,就是这样一种想象类型的语言。王安忆在小说中建立的艺术形象则是把这种想象类型的语言还原到事物原有的物状之上。陌生化手法要在“描述第一次看到的事物那样去加以描述”,而王安忆则是这样将事物还原到人类的视觉和嗅觉之上。
陌生化技巧创造出的诗意形象主要是恢复人们对生活的感觉。而视像作为可视之象是人们用视觉和嗅觉捕捉到的事物表现形式。王安忆非常擅于抓取事物外在的形式和本质特征,呼唤她的读者回到事物的现场,去感受他们第一次见到某事物的感受。这种对事物外在形式的描述在小说中并不是没有内涵的。例如,《上种红菱下种藕》通过以下的视角来看华舍镇。
秧宝宝被母亲寄放到华舍镇来上课,那时她刚认识了蒋芽儿,她的作业是在和蒋芽儿闲逛华舍镇时做完的:
“秧宝宝的作业本就散发着各式各样的气味。鱼虾的腥气,烂菜皮的腐味,鸡鸭的屎味、泥气味、水气味、尘土气味、杂货店的蚊香味、烟味、零食上的甘草味。”(2002:38)
通过一群外地迁居于此的东北人眼睛来看:
“是因为货多少走出一些,还是叫左邻右舍的烟火气熏得屋子里那一股辛辣的药味,和山货的乏土味,淡下去许多,取而代之的是油酱味,腌菜味,腐乳味,衣服上的肥皂味。……有一阵轻盈的铃声传来,嘁哩喀喳的,是闪闪店里的风铃。这声音真就是带颜色的,粉蓝,粉红,粉白,间着亮光,是小铃铛里的小锤子,一悠一悠。”(194)
秧宝宝和父母住进酒店里,她站在高处来看小镇时,小镇的面目却是另外一个样:
“底下的镇子,也改了颜色。那水泥的灰白,灰白里嵌的几道墨线,是老屋的骨脊,以及河水的浑绿的线条,原先是蒙在水气和空气中的微屑合成的雾障后面,形成灰黄的暗淡调子,现在却染成较为明亮的姜黄了。”(208)
这些“鱼虾的腥气”“烂菜皮的腐味”“鸡鸭的屎味”“泥气味”“水气味”“尘土气味”“油酱味”“腌菜味”“腐乳味”“衣服上的肥皂味”等等,作者不用顿号,只引逗点,然后连续抛出各形各式的气味,旨在说明这些气味显然属于小镇上的劳动人民。《长恨歌》以后,王安忆虽然没有离开书写上海的万种风情,但是她的《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确是以一种更朴素和谐的笔调来叙述上海的另一面。《富萍》已经看出作者在上海都会和农村之间徘徊的焦虑身影,而《上种红菱下种藕》则表示了作者回归到村庄小镇上的决心了。因此,作者用的色调,如粉蓝、粉红、粉白、浑绿、姜黄,色彩浅淡,光亮鲜明,皆一一昭示着作者对小镇的热爱。
除此之外,王安忆对女性情谊之间尤为机敏的触觉也可说是用嗅觉搭建起来的。秧宝宝、蒋牙儿和张柔桑之间的友情是猜疑,是嫉妒,也是焦虑,彼此全然无法容忍第三者的存在,只要秧宝宝和蒋牙儿靠近一点而忽略了张柔桑,“蒋牙儿的嗅觉又起作用了,她嗅出些危险的征兆”(135),不久即对秧宝宝做出了动作,好让张柔桑知难而退。
“她们互相抱着对方的身子,嗅到了对方的气味:肥皂的气味里夹着太阳和甘草的气味,就像某一种特别的植物……”(128)
秧宝宝对李老师家的生活气息也是何其敏感,尤其是她和李老师家的媳妇陆国慎,那种女性之间微妙得无法言喻的感情是依靠“嗅觉”来诠释的。陆国慎为她折叠的衣服“有陆国慎手上的防护霜的气味”;陆国慎喜欢点卫生香,点的是一种檀香的盘香,秧宝宝又觉得“家中就又有了一种陆国慎的气味,檀香味。”(149)
镇子上的空气不对了——“倒不是说它已经发生什么事情了,而是,气味”,这也是蒋牙儿本能嗅出来的。“蒋牙儿嗅嗅空气,灵敏的小鼻子里传入了什么异常的成分,她预言道:要出事,真的要出事!”(143)过了不久后,沈溇的老屋果然是出了事。干部开口向公公打主意要他火葬,请公公拆去他在自留地上为自己造的坟时,聋子公公即刻闭门入内,王安忆借众人之口说道:“那不是听出来的,是闻味道闻出来的!”(164)不久后,干部自行到公公的自留地上去拆坟,秧宝宝把这幕看在眼里,尽管是反驳、挣扎,秧宝宝最后哭了。一直跟在她身后的两个朋友,蒋芽儿和张柔桑,也各自在她不知情的背后陪着她哭了。王安忆一贯对女性细密的心思又一次依靠她机灵的嗅觉。张柔桑站在秧宝宝后面哭了,而站在最远处的蒋芽儿也哭,“她看得并不清楚,可是她嗅都嗅得到这个下午的伤心空气。”(167)同时,王安忆并没有放弃张爱玲的衣服哲学。拆坟一幕之前,王安忆对两个女孩的衣服描绘是“前一个是粉红色的格子衬衫,套着苹果绿色的毛线背心;后一个是红黑白镶拼的运动衫外套,翻出淡黄碎花的衬衣领子”;拆坟过后,“她们身上衣衫的诸多色彩,全调进了一种透明的颜料,变浅,变暗,沉暗中,有一层隐藏的明亮,这又使得颜色变轻盈了。”意外事件之前,衣服的色彩呈现多样和明亮,随后才转入暗和沉,又逐渐为暗和沉所掩盖,给情节增添了悲观的色彩。
诚如什克洛夫斯基说过:“形象的目的不是使其意义接近于我们的理解,而是造成一种对客体的特殊感受,创造对客体的‘视象’,而不是对它的认知。”(20)陌生化技巧对事物的“还原”不仅能够使人们褪去对事物原有的认知色彩,而且能够卸去事物陈旧的意义负荷,避免了已认知事物对人们思维的束缚,从而使人们更深入、更全面和更准确地认知事物,探索世界的本质和人类存在的意义。
“隐喻”(metaphor)在希腊语的合成词metaphora。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和《修辞学》中多次论及隐喻的构成方式与修辞功能。他认为语言按其形态表现可分为逻辑的、修辞的和诗的三类。诗的语言不同于逻辑的语言和修辞的语言,其区别就在于诗极大地依赖于隐喻;能够正确达意的语言样式是逻辑语言,隐喻因歧义丛生而不具有确定的指称表意功能;因此,隐喻是语言表达的反常样式或非本质样式,它的功能或目的不是“指称达意”而是“佳肴里的调料”。(21)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解释其实已可看出隐喻对诗语言的重要。前面也说过,维柯认为原始的异教民族是使用诗性语言说话的民族。因此,语言最初的诗性特征,已经蕴含强烈的情绪和奇特的想法,而类似的语言特性确实必要扎根在隐喻上,而隐喻恰恰又是极富含诗性的。我这里不对“隐喻”和“比喻”作修辞格上的区分,主要从“陌生化”手法的基础上来探讨“隐喻”在诗性语言上的价值和意义。
维柯在谈到《诗性逻辑》时尤其对诗性的比喻作了这样的解释:“凡是最初的比譬(tropes)都是来自这种诗性逻辑的定理或必然结果。按照上述玄学,最鲜明的因而也是最必要的和最常用的比譬就是隐喻(metaphor)。它也是最受到赞赏的,如果它使无生命的事物显得具有感觉和情欲。最初的诗人们就用这种隐喻,让一些物体成为具有生命实质的真事真物,并用以已度物的方式,使它们也有感觉和情欲……”(22)之前说过,“陌生化”理论的提出,主要也是藉助已知的诗性形象来说明未知的物象。故此,隐喻在诗性语言上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这里再一次以王安忆对“流言”的描述来说明比喻作为基本修辞格在小说中的作用:
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阴沉气有时是东西厢房的薰衣草气味,有时是樟脑丸气味,还有时是肉砧板上的气味。它不是那种板烟和雪茄的气味,也不是六六粉和敌敌畏的气味。它不是那种阳刚凛冽的气味,而是带有些阴柔婉约的,是女人家的气味。是闺阁和厨房的混淆的气味,有点脂粉香,有点油烟味,还有点汗气的。(8)
这样的句式很明显是“比喻”传统修辞格的运用。作者连续抛出了喻体,如“薰衣草气味”“樟脑丸气味”“肉砧板气味”“板烟和雪茄的气味”“六六粉和敌敌畏的气味”等等。类似以“是”字作为判断式的句子结构,很明显是以此物类比他物,于两种不同的物体中找出事物的相似性。上海弄堂的流言因此让读者感觉了它的生命力,也由此掌握了流言从各视角下反映出来的特质。
然而,什克洛夫斯基对“比喻”有更进一步的解释:“即比喻仅仅是诗人可能会采用的多种陌生化手法中,较为彰明显着的一种。它体现了诗歌的一个总倾向,那就是将表现客体移植于‘新的感受域’中,而这种经由比喻而实施的‘语义的转移’,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根本所在。诗或艺术作品,就整体功能而言,就是一种大的‘比喻’,就是一种‘语义的转移’。”(23)早在《长恨歌》时,已经可以看出类似比喻所带来的“语义的转移”。以上面那段对“流言”的描述为例,“流言”在比喻的修辞格上显然投射了流言的特质,而更重要的是,流言本身在“语义的转移”上暗示了主人公王琦瑶一生的悲剧。
这里再另举一例说明“语义的转移”:
“篮里的花无意间为王琦瑶作了点缀。康乃馨的红和白,是专为衬托她的粉红和苹果绿来的,要不,这两种艳是有些分量不足,有些要飘起来,散开去,这红和白全为它们压了底。王琦瑶在红白两色的康乃馨中间,就像是花的芯,真是娇媚无比。……她的花篮里也有了花,这花不是如雨如瀑的,却一朵一朵没有间断,细水长流的,竟也聚起了一篮。……白色的婚服终于出场了,康乃馨里白色的一种退进底色,红色的一种跃然而出,跳上了她的白纱裙。”(63)
以上这段话是描述王琦瑶参选上海小姐时的情景。作者采用了“花”和花的鲜艳颜色作比喻:“康乃馨的红和白”“花的芯”“花篮里也有了花”以及以康乃馨的白来类比她身上白色的婚服,作者在这里运用了语义的转移,她将王琦瑶的美丽从原有的语义中拽取出来,放到“花”这喻体上去,于此产生了另一语义的存在。作者以“花”喻“人”,隐含着王琦瑶如花的美丽,以及这种美丽的昙花一现。小说中后来说到王琦瑶的女儿薇薇的新娘装扮时,作者同样以花来比喻:“这真是花朵绽开的那美妙的一瞬,所有的美丽都偃旗息鼓,为它让道的。”(313)尽管我们看到的都是花朵绽开最美丽的霎那,然而,这两个上海女子很显然是无法抵住花开花谢的循环定律。作者对“花”的描述即是对角色的命运的勾勒,“当它被当作一种风格手法被运用,且其目的是为了达到一种寓意效果时,才会具有‘诗意’”。(24)
人类的词语多半是比喻性的。诗性语言就是借助隐喻以提供超出其本身含义以外的东西,摆脱抽象思维和语言的规范和束缚,充分发挥联想、直觉和想象。诚如维柯在研究诗性语言时,如此说道:“诗性语言的产生完全由于语言的贫乏和表达的需要。诗的风格方面一些最初的光辉事例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些事例就是生动的描绘、意象、显喻、比譬、隐喻、题外话、用事物的自然诗性来说明事物的短语,把事物的细微的或轻易感觉到的效果搜集在一起的描绘,最后是加重语气的乃至累赘的附加语。(25)类似的诗性隐喻在《长恨歌》中比比皆是。王德威曾用“酣畅绵密”来形容王安忆的文笔。(26)我以为,“绵密”一词尤其能说明《长恨歌》的语言特质。作者大量运用“以此比彼”的隐喻手法,从而突破常规语言的单一性,传达文字以外的意义。又如《长恨歌》开篇,即有一节对弄堂上空飞的鸽子加以描述:“屋顶上放飞的鸽子,其实放的都是闺阁的心,飞得高高的,看那花窗帘的窗,别时容易见时难的样子,还是高处不胜寒的样子。”作者从“鸽子”的视角下来看上海这座城市,这种采用特殊的旁观者的写作手法,不可谓不是另一种“语义的转移”。
相对于《长恨歌》,其后的《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在诗性隐喻上的使用则削减了许多。《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的笔调更为写实,语言亦是自然和简单多了,并且较之于《长恨歌》许多“是”字结构的判断性句式所带出的隐喻手法,后两本小说大多使用的短句叙事更显直接。这里尝试从《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找出一些采用比喻的例子:
“沿墙放一圈沙发,像机关的会议室。”(2000:8)
“他们大多换了半身戏衣,勒了头,也没有上头饰,都像是戏中的慵状美人,有那么一点点腻味。”(2000:148)
“两页衣襟便像翅膀样地支开着。”(2000:176)
“老街就变得鲜艳起来,像一幅油画。……老街褪去姜黄的底色,还原了黑和白,真正成了一幅中国水墨画。所有的细部都平面地、清晰地、细致地呈现出来,沿了河慢慢地展开画卷。”(2002:20—21)
“这使她变得有些怪异,有一点像动物。外界少有刺激,立即作出反应。”(2002:28)
“一把谷种放手出去,好像一张雾,落下,再一张扬,又是一张雾。”(2002:33)
诗性语言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把这些联想序列的词语带入话语的组合中,从而产生不确定的、多义的隐喻含义。最初的语言主要不在于认知和推理,反之是用于情感的表现。“比喻可以说是一种歪曲的说法,诗人采用意象的旨趣就恰恰在于这种‘语义转移’,即将表现对象移置于另一层面。熟稔的事物经诗的点化而变得陌生,变得有如初次相见一般。”(27)庄子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说的就是这样的道理。
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陌生化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摆脱机械性的语言规范,从而恢复语言艺术的可感性。因此,“语言陌生化”就是对常规语言的偏离和扭曲,刻意造成语言理解和感受上的陌生感。语言陌生化在诗性语言的创作是必要的。这种超出语言常规的技巧性处理可使语义、语音和语法因此而变形。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语言陌生化绝不是刻意使语言标新立异或哗众取宠,反之,通过这种偏离语言常规的异化写作,语言即时获得重生并找到它的生命力和存在价值,给人在语言审美上一种新的感受和体验。《长恨歌》以后,王安忆在紧接下来的《富萍》对超常规的语言试验作出了另一次更大胆的尝试。《长恨歌》语言绵密,句与句之间其浓度极高,尤其在大量的判断式句式中,更显现了小说叙事的完整性。相对之下,《富萍》的语言则显得简洁和单薄许多。然而,王安忆放弃《长恨歌》那种粘密和琐屑的小说语言之后,即刻在紧接下来的长篇小说,尝试用自然直接的语言来叙述故事。以下从《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来探讨语言陌生化的几个方面:(www.zuozong.com)
ⅰ.量词的活用/错用
“大块大块的太阳光投进来……”(2000:159)
“……四个人连成一串出了门”(2000:160)
“到了车站,大家都默了下来,在车站上站了一片。”(2000:163)
“弄里的地上,积着红色的炮仗纸。天不亮时已经扫过一遍了,可是到了午后,又炸了一层。”(2000:172)
“不少窗户洞开着,注进阳光去,含了一汪亮光。”(2000:175)
“经过一领水泥桥,就到了镇东边的口子上。”(2002:7)
“此时的老街喧嚷起来,人们从几领桥上过往着,店铺里也略有生意了。”(2002:21)
“石桥的栏上,搭了谁家的棉花胎,一领桥一领桥过去……”(2002:75)
“床前挂一块名牌,刻上木匠姓名籍贯做落款,然后收一只红包。”(2002:124)
“不仅有树,有盆花,还有一眼井。”(2002:155)
“可见天边的朝霞,细长的,一道橘红,一道粉紫,一骨朵一骨朵的白云。”(2002:208)
“倚了栏杆摆起一溜长桌,铺了白桌布,上面放着一盆盆的食物……”(2002:210)
以“块”来测量充分的太阳光,一反惯用的“片”;“串”和“片”原用以物体,这里拟物化放到人身上;炮仗炸了一“层”,指的是炮仗声四方层层传来;“汪”带深广之意,多用在水,现用于光线;“领”指示上面的位置,用在“桥”表示人打从上边过;其他如“一只红包”“一眼井”“一骨朵一骨朵的白云”和“一溜长桌”皆是量词的活用,强烈描述了所表达之物状。
ⅱ.词语的陌生化运用
“我们家小朋友怎么还没有下学,是不是留晚学了?”(2000:19)
“做扔手绢的游戏。”(2000:20)
“走一路打一路招呼,还站下脚和人说话。”(2000:34)
“她也有当无地听听。”(2000:35)
“加急的活要晚上加。”(2000:81)
“我就把这小鬼做掉去。”(2000:84)
“一时与我闹闹气,并不会有旁的什么心。”(2000:166)
“是因为货多少走出一些。”(2002:194)
上述加黑的词语在现代汉语规范的运用上恐怕是错误的。然而,王安忆却尝试打破了语言固有的运用模式和习惯,以陌生化的处理手法,让读者在阅读上感觉生疏和反常的语言用法。“下学”“留晚学”“站下脚”一贯的用法是“放学”“留堂”“停下脚”,虽不是词语上的错用,但至少不是惯用。王安忆以此一新读者之耳目,乃是陌生化的处理。此外,“当无地听听”“有旁的什么心”等等在用语上是不合规范,然而着此一字(词),正是王国维所说的:“意境全出矣。”
ⅲ.词类活用
“心思容易活。”(2000:46)
“她包了一眶眼泪。”(2000:94)
“眼睛里放着光亮。”(2000:120)
“吃了外甥女的呛。”(2000:217)
“眼睛周围的皮肤显得很肉。”(2000:83)
“富萍和奶奶生了隙。”(2000:94)
“这姿态有着一种虔诚。”(2002:122)
“公公戛哑的声音在水一般的月光里踌躇。”(2002:125)
王安忆认为动词是语言最主要的支撑。她说过:“动词是语言中最没有个性特征,最没有感情色彩,最没有表情的,而正是这样,它才可能被最大限度地使用。”(28)《富萍》少了《长恨歌》用在各种修辞格上的形容词性,却以动词直接表示人物的行动,增强了视觉上的直观,也具体化了物象的可感性。“活”用于心思、“包”用于眼泪、“放”取之“发放”、声音以“踌躇”拟人化,隙是“生”出来的,在在看出王安忆活用动词,使小说语言更趋陌生化,产生一定程度的新鲜感。除此,“肉”当形容词用,“虔诚”作名词用,诸如此类的词性“异化”,都是刻意突破语言规范,制造出一定的审美效应。
王安忆是当代少数能在写小说的同时又自觉于实践语言理论的作家。她阐释自己的小说观提出“不要语言的风格化”以后(29),继而于1989年发表的《大陆台湾小说语言比较》一文已经暗示自己应该“创造并掌握一套抽象语言的表述方式”。后来,她更是对“抽象化语言”进一步说明:“它的语言都是平白朴实的语言,是最无简单最无含义因而便是最抽象的语言……‘抽象化语言’其实是以一些最为具体的词汇组成,而‘具体化语言’则是以一些抽象的词汇组成。”(30)距《长恨歌》五年之后的《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即是她对“抽象化语言”最成功的实践。
如果我们说《长恨歌》是王安忆长篇小说至今最为闪亮的硕果,那么《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应该是王安忆写作风格转变以后另一张辉煌的成绩单。若是仅仅从小说语言的角度来衡量,《长恨歌》无疑是展示了王安忆在小说语言上最彻底的实验和努力。《长恨歌》的小说语言之密之浓绝不是她之后的小说可以比拟的。《富萍》和《上种红菱下种藕》很显然是王安忆尝试回归到她早期较为平实自然的语言风格上。当然,写作这两本长篇时,王安忆在语言上的实践可说是处于水到渠成的时刻。她是如此坚信,她对语言的掌握已经是“可运用于各种类型的创作,用于各种表达,因为一切风格化、个性化的语言其实都是由它派生出去的……”(31)从《长恨歌》到《上种红菱下种藕》,王安忆无疑在小说语言上经历了一次纯粹性的转变,恰如她的小说主题一样,从书写上海城市的繁华和沧桑,再转向农村小镇的平淡和安稳。然而,这其中的转变其实昭示着王安忆再一次展示了现代汉语表达无尽、无限的可能,因为她在实践抽象化语言的同时,我们深深感觉:王安忆那些最具体、最无个性、最朴实的语言竟然潜藏着最内在的塑造力。
王安忆在小说语言上的努力,实则可以从上述陌生化手法的理论基础看到共同之处。俄国形式主义者所主张的“陌生化”是建基于“文学性”上的。一部作品的艺术价值绝非是它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而是取决于它的构成方式本身,即是如何写作的手法问题,因此,文学性就被视为文学艺术的“主人公”,而陌生化手法即是要将文学自身的最本质特性重新挖掘出来。罗曼·雅各布森(Jakobon,Roman Osipovic,1896—1982)说过“文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笼统的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其为文学作品的东西。”(32)在形式主义者看来,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因此文学性只能在文学世界中去寻找,这样,文学就成了一种超然存在的、独立的自足体。换言之,文学存在的价值或文学的本质特性就只能在文学作品中寻得。
陌生化技巧的运用其实是再一次把文学语言的地位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它利用人类最初始以诗歌建立言说和思维的方式,更新人们对事物的有关经验,从而打破由日常经验所形成的固有的定律和范式。由此,论者有言:“陌生化的另一种含义,就是要向语言的诗性本质复归或还原。”(33)然而,陌生化手法的提出,与其说在某程度上恢复人类对现实和生活上早被钝化和自动化的感受,不如说它在复活原始人类在远古生活中所闪现的“诗性的智慧”。诚如维柯所言:“诗性的智慧,这种异教世界的最初的智慧,……一种感觉到想象出的玄学,像这些原始人所有的。这些原始人没有推理的能力,却浑身是强旺的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34)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正是需要寻回这些已逐渐缺失的想象力来确定“我们的存在”,这也是王安忆为何一直渴望在小说中“创造一个宏大的存在”。(35)所有语言诗学的问题最终其实都不指向语言和文学本身,而是指向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学,恰是海德格尔的名言:“存在是语言的家。”从《长恨歌》到《上种红菱下种藕》,王安忆的小说语言最后复归到最朴质无饰的语境,这其中的努力无疑是对中国现代汉语一次伟大的探索。回到这篇论文最初的探讨,我不禁想问:这是王安忆长篇小说“诗性语言”的建构,还是对人类“诗性的智慧”的重构?
(本文系首次发表。)
(1) 李建中:《原始思维与古代文论的诗性传统》,收入李建中,《古代文论的诗性空间》,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2) 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61页。
(3) 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页。
(4)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收入什克洛夫斯基等著,方珊等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北京:三联书店出版,1992年,第5—6页。
(5) 同上,第6页。
(6) 杨义认为:“小说的‘散文化’,乃是小说的自由化、随意化,它把小说的环境化淡,人物化虚,情节化少,而唯独把情绪化浓。”参阅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85页。
(7) 汪曾祺著,陆建华编:《汪曾祺文集》(文论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20页。
(8) 同上,第85页。
(9)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收入什克洛夫斯基等著,方珊等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第1页。
(10)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收入什克洛夫斯基等著,方珊等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第4页。
(11)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收入什克洛夫斯基等著,方珊等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第7页。
(12) 同上,第8页。
(13) 陈思和、王安忆等:《当前文学创作的“轻”与“重”》,《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5期,第14—22页。
(14) 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13—316页。
(15) 同上,第317页。
(16) 张冰:《陌生化研究:俄国形式主义诗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92页。
(17) 张冰:《陌生化研究: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第206页。
(18) 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第162—163页。
(19) 张冰:《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第6页。
(20) 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收入什克洛夫斯基等著,方珊等译:《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第8页。
(21) 李凤亮《隐喻:修辞概念与诗性精神》,收入《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3期(总第56期),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142页。
(22) 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第180页。
(23) 张冰:《陌生化研究: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第168页。
(24) 鲍·艾亨鲍姆:《论文学:历年论著选》,引自张冰:《陌生化研究: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第169页。
(25) 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第213页。
(26) 王德威《海派文学,又见传人》,收入王德威:《如何现代化,怎样文学?》,台北:麦田出版,1998年,第384页。
(27) 张冰:《陌生化研究: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第204页。
(28) 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第315页。
(29) 王安忆认为:“风格性的语言还是一种狭隘的语言,它其实缺乏建造的功能,它只能借助读者的想象来实现它的目的,它无力承担小说是叙述艺术的意义上的叙述语言。”参阅王安忆《我的小说观》,收入王安忆:《漂泊的语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332页。
(30) 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第313、316页。
(31) 王安忆:《心灵世界——王安忆小说讲稿》,第318页。
(32) 引自张冰:《陌生化研究: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第80页。
(33) 张冰:《陌生化研究:俄国形式主义诗学》,第85页。
(34) 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第161页。
(35) 王安忆:《小说的物质部分》,收入王安忆,《漂泊的语言》,第338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