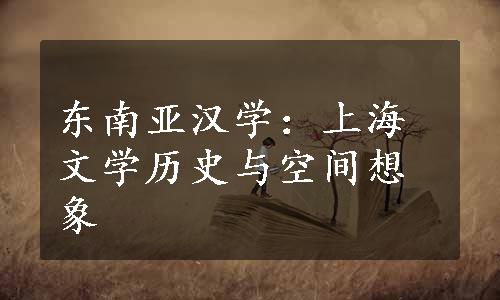
伍燕翎
“从整体上说,像我们这些‘同志’是打着腰鼓扭着秧歌进入上海的。……而个别到我们家,再个别到我们家的‘我’——一个‘同志’的后代,则是乘了火车坐在一个痰盂上进的上海。”
早在《长恨歌》(1995)之前,王安忆即有意要为她自己或她自称为“同志”的后代在上海这座美丽之城寻找一方安身之地。对自小和母亲一起从他处来到上海居住的王安忆来说,她或许亟需迫切在上海安置她自己和像她一样的“同志”们后代,只有在上海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繁华梦,这些“外来户”才不至于成为精神上放逐和游离的居住者。从90年代初期的《纪实与虚构》(1993)伊始,王安忆即念兹在兹上海这座城市,“上海”近乎成了她接下来的小说的创作符码,或许在她心中“早已一厢情愿地和上海这城市认同了”。(1993:9)
李欧梵说过:“一个城市需要一个‘她者’才能被理解。”(1)打从《纪实与虚构》开始,王安忆即有意建构“她者”的上海谱系。她尝试在这部小说描述解放前曾外祖母、外婆到母亲的生活经历,以及她自己在解放初跟随母亲和其他同志们“打着腰鼓扭着秧歌进入上海”寻找一部家族寻根史的亲身经验。作为一个“同志”的后代,当她随着父母进入上海生活的那一刻起,便不由自主地陷入“身份”的两难:一边是说普通话的家和“同志”的世界,一边是有着久远历史和复杂人际关系的本土上海市民——“我们使用的语言不是上海话,而是一种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这样的语言使我们在各自的学校和里弄里变得很孤独”(20)——她因此注定要开始寻找自身的历史。读毕此书的后来,竟发现那些“坐着痰盂进上海”的故事原来也是王安忆曾有过的经历。她如此道出:
我母亲到这城市当说是故地重归,她却俨然是一副外来者的面目。她不说这城市的语言,她不穿这城市的流行服装,她不打算和这城市的亲属们重叙旧情。我是到很久以后才知道母亲原来是出生在这城市的,这个发现叫我很激动,它使我感觉到自己和这城市的亲缘关系。(1993:464)
读者的发现或许和王安忆发现母亲源自上海的激动相去不远。“我”(或王安忆?)自称自己的家庭一直是迁入上海的外来户,没有亲友,没有家族,只能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漂泊无垠。这种被放逐无根的虚无感,加上王安忆经历了八十年代“寻根热”的上海,很快就促使她要为自己找一处安身立命之所在。她说:“在当时的‘寻根’热潮的鼓动下,我雄心勃勃地,也企图要寻找上海的根。”(2)由于寻根的渴望和努力,迫使王安忆从一部血缘异质性的家族史中寻找可以驻留的定点——上海。于此,在1995年问世的倾力之作——《长恨歌》以30万字之篇幅叙写了“上海生上海长的王琦瑶”的一生,此部小说写的是王琦瑶如何从一个魅艳风情的少女变成另一个遍历风尘的女子。女人是经,上海是纬,《长恨歌》因此再次构成王安忆“寻找上海”的张力。接着,发表于2000年《收获》第四期的《富萍》再一次动用王安忆在上海生活的积累,同样表现了书写“我城”的强烈欲望。然而,她这次已从上海的神话走出来,企图回到上海市民最现实的“草根”生活里头。历史上的上海风华已经不再,文学中的上海传奇却有待延续,“上海”作为王安忆小说的书写场域,必是“同志”们抹不去的文化记忆,更是她身为同志后代“创造世界方法之一种”。此文章从王安忆两部姐妹篇——《长恨歌》和《富萍》来探析作者如何在其小说中通过“空间”和“历史”来勾勒文本中的上海。
“站在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1995:1)
历史上的上海是由弄堂搭建起来的。那里聚集了无数老百姓们劳动的血汗和结晶,上海大部分的人口,其实是普遍低层人们的栖身之所。上海文化的生活化、通俗化和市民化,几乎全都凝聚在那里。王安忆意识到倘若要写一座城市的故事,上海的弄堂无疑最能反映出其城市的形象、身世和命运。弄堂由此成为上海这个城市空间一个最好的叙事视角,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弄堂具备了王安忆后来以书写普遍市民日常生活为事业的条件。上海市民的衣食住行多数活动在弄堂里,他们的喜怒哀乐也同时表现于弄堂。这里几乎充分展现了人们的日常活动,因此它无疑给王安忆的小说提供了最好的叙事场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作为上海象征的弄堂,它其实是上海文化的表征和场域。王安忆显然是想藉着这个场景来讲述一个“城市的故事”。这故事彻头彻尾只说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悲剧,但是王安忆的用心何止那么简单?她何不是想藉着这个女子的命运来诠释她自小从家族史上对栖居之城的认知?
虽然栖居于今天的上海,王安忆大部分小说几乎不约而同回避了上海国际化都市最醒目的空间坐标:摩天大楼、商厦和大型超市、咖啡厅和酒吧,霓虹灯和歌舞场等等现代进程的消费空间。在中国近代史上,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的上海,它无疑是文学里重要的场景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上海的复兴和时尚文化的影响,上海作家尤其不断在创作中探寻上海地域的文化特征,或者多数评论者称之为“文化身份”。在城市现代进程的背面,昔日的十里洋场却也同时是许多人的“集体记忆”。现代化表征和怀旧式的追忆所带来的潜在矛盾,促使王安忆只能想象和追恋昔日的“海上繁华梦”。因此,《长恨歌》不厌其烦用了一个章节委婉有致地描述上海某个面向的地理坐标。“站在一个至高点看上海”,王安忆让读者看到好几个上海典型的城市局部,其中有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和最能代表上海的女儿——王琦瑶式的女子。
这几组意象的描述是这样被带出来的:“站在一个至高点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3);“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阴沉气有时是东西厢房的薰衣草气味,有时是樟脑丸气味,还有时是肉砧板上的气味”(7);“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闺阁通常是做在偏厢房或是亭子间里,总是背阴的窗,拉着花窗帘”(12);“鸽子是这城市的精灵”(16)和“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20)。流言、闺阁、鸽子和上海的女儿,无一不是表现于弄堂的一道风景。王安忆在所选定的城市坐标里勾勒出弄堂的各种面目。90年代的上海,政府为美化市容和追求现代化征程,弄堂可能被迫面临被拆除的厄运。弄堂和上海联系着的不仅是其悠久的历史,它更是确确实实负载着城市记忆的所在。然而,这城市空间在趋向国际化和日益膨胀的现代化建筑群中,即变得消隐、萎缩,或遭拆除等命运。
弄堂昭示着“过去”和“历史”。它背负着人们在过去生活的一种文化记忆,也是个人记忆和集体想象的载体。这很显然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那本名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所强调的“想象的共同体”(3),意即人们可在那依然残存着的集体记忆和想象中,创造出自己隶属的地方和精神的归属。上海弄堂作为时间存在的见证,王安忆因此以装载了无数故事的弄堂——上海最古老、最典型的历史标志来见证这座上海的起起落落,而上海这座城的命运恰是可以用王琦瑶的一生来比拟的。正如王安忆坦言:“我是在直接写城市的故事,但这个女人是这个城市的影子。”(4)弄堂成为王安忆可发挥想象的空间,借以叙述一座城市的故事。
有论者说到,王安忆从1980年代“雯雯”系列到1990年代初开始的小说,是一种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的转移。(5)很显然,在前期,王安忆关怀的是女性成长到女性隐秘的情欲和性爱,到了《长恨歌》表面上看似一个女人的情情爱爱,实则却是女性空间的主体建构。这主要是因为王安忆早期的女性多少还依附于男性的活动范畴和话语之中,而后来这个属于女性“自己的房间”似的空间才真正看到王安忆“以日常话语的再现以及女性叙述方式的运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创作”。(6)
王安忆选择上海作为女性空间的建构绝不是没有来由。1990年代现代化上海国际大都市给她带来了焦虑。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尤其进入1990年代以后,上海的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人现代化生活图景的中心想象,可是这带给作家的却是一种潜藏的、内在的焦虑,但同时它也激活了王安忆敏锐的女性触觉,让她一再努力地对所居之城搜索,并努力复活人们对这座城市的记忆。王安忆说过这样的话:“我生活在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一直都是潜心关注的。”(7)
作为现代国际大都市,上海在1930年代已经经历了这个城市最辉煌的岁月。享有“东方巴黎”美誉的十里洋场是经由这样一连串的符号架构起来的:有声电影、巴黎时装、西方剧院、形形色色的夜总会、百货大楼、赌博、舞厅派对、跑马场,和拥有中国最早的电车、电灯、电话等等,也一样拥有许多商业和城市的罪犯,这一切都充斥着当时的报刊、杂志和广告。这么一个有现代气派的上海都市无疑是要让人迷失其中。尤其当旧黄的月历牌在一张张被撕掉之后,人们竟然发现他们生活在这个座城市是多么地孤立无援,甚至显得被动和乏力。
在现代化的镁光灯下,文学上的上海同样的璀璨华丽、纸醉金迷。王德威说“也许一个国家的危疑颠沛,正是为了成就一座城市刹那的文学风华”(8),这不是没有道理。1927年,鲁迅和许广平到上海来同居,直到鲁迅于1936年逝世都没有离开过上海。上海于他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给孩子取名“海婴”意即上海出生的婴儿;矛盾笔下《子夜》的上海是金融风云、股票交易的角逐场;曹禺《日出》的上海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罪恶之地,新感觉派施蛰存、穆时英笔下那些上海的赛马会、狐步舞、夜总会、咖啡馆、酒吧、电影院、跑马厅等摩登场所,无一不让读者联想到波德莱尔笔下那个充满罪恶、妓女、颓败、酗酒的19世纪的巴黎。
如今王安忆站在一个更高点上来看上海,而王琦瑶不过是她为旧上海制造的其中一个意象。她其实可以替换1930年代上海的旗袍、咖啡、影院、报刊、广告、电车、霓虹灯等等曾经闪亮一时的物品,然而,王安忆认为,“王琦瑶的形象就是我心目中的上海。在我眼中,上海是一个女性形象,她是中国近代诞生的奇人。”(9)这话其实已点明王安忆眼中的上海即是女性的化身,她要以女性底子有的刚毅、艰苦和坚韧来承担上海这个城市有过的苦难。《长恨歌》因此写了一个旧式上海女子——王琦瑶的悲剧人生。她首先在解放前参选沪上淑媛获得“三小姐”的名衔,李主任当初垂青她的美貌而将之金屋藏娇,她在爱丽丝公寓度过了她最动人和辉煌的岁月年华。李主任不幸空难中死去以后,王琦瑶只好回到平安里去自谋生路,每日做得几碟小菜,却也安然无恙地度日;后来她生命中陆续出现了几个男人:程先生、康明逊、老克勒和萨沙。那个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孩子父亲的男人在她生命里走了又来,她也没有太多怨言,照样把孩子带大。时间就从王琦瑶在给人缝制服饰、洗米拣菜、煮菜烧饭、替人打针、怀孕生子中一点一滴地流逝。这个女人的一生最后落得他杀的下场,那些四十年来和她纠葛不清的情欲和钱财才因此烟消云散。王琦瑶的生命是在上海的弄堂里完成的。这个城市空间确是女性空间的再造。王琦瑶的生命即是一座城市的命运和身世。这座城为王琦瑶一桩又一桩上演的事件提供了最好的场景。王安忆写道:“一九六六年的夏天里,这城市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弄堂,那些红瓦或者黑瓦、立有老虎天窗或者水泥晒台的屋顶,被揭开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258)所有的事情最终不过是过眼云烟,只有这个城市空间在给王琦瑶制造许多不可知的命运的同时,才逐渐意识到“女性”其实和她所居住的城市并存。诚如王安忆所言:“女人无法取得优势,无法改变必须依附于男人生存的命运。而到了城市这一崭新的再造自然里,那才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女人与男人,竟也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了。”(10)由此,《长恨歌》从城市鸽子居高临下的观视下,对发生于弄堂的一切事物作了历史上最好的见证。
小说以弄堂来呈现女性空间,其中还有一些场景所赋予的意义更是为此作了一大注脚。“爱丽丝公寓”原本就寓意着暧昧不清的含义——“爱丽丝公寓是这闹市中的一个最静,这静不是处子的无风无波的静,而是望夫石一般的,凝冻的静”(97)——这预示了王琦瑶无疾而终的爱情。这里是李主任包养王琦瑶的地方,李主任有闲才来访,王琦瑶只能无尽无止的等待,两人的爱恋绝不是建立在真心上,公寓于是充满了情欲、寂寥和空虚。还有就是江南小镇邬桥,邬桥有着和弄堂完全不同的气质——“邬桥可说是大千宇宙的核,什么都灭了,它也灭不了,因它是时间的本质,一切物质的最原初”(129)——它是一处干净、宁静和祥和之地,是王琦瑶情伤以后到婆婆家来疗养的地方。爱丽丝公寓的落寞正好可以从这里填补,它和喧嚣的上海不同,这个朴质的世外桃源一直是王安忆渴望的,因此它又不断地出现于她日后的小说,《富萍》的“梅家桥”就是邬桥的再现。
这些空间的形成肯定有着一定都市文化的底蕴,它们的建构可说是源自作者对其城市的深刻感受和认同。王安忆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就是女性。”(11)王安忆要借助城市鸽子的眼睛,“站在一个至高点看上海”,所关怀的焦点才显得更为准确和辽阔。有建筑学家认为:“一个生动和独特的场所会对人的记忆、感觉以及价值观直接产生影响,所以,地方的特色和人的个性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人们会把‘我在这’(I am here)变成了‘这是我’(I am)”。(12)王安忆何曾不也想通过上海来表述她的女性关怀,但最为重要的是“她”(众多王琦瑶式的上海的女儿)——这个“坐着痰盂进上海的”同志后代寻找一方安身立命之处。
日子很仔细地过着。上海屋檐下的日子,都有着仔细和用心的面目。倘若不是这样专心致志,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最具体最琐碎的细节上,也许就很难将日子过到底。(1995:247)
上海弄堂的感动来自于最为日常的情景,这感动不是云水激荡的,而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这是有烟火人气的感动。(1995:6)
在男性宏大政治军事视野中,女性日常化的民间叙事一向微不足道。然而,在王安忆笔下,那些以大量笔墨书写女主人公日常起居的平常事却变成叙事核心,承担起民间叙事举足轻重的文化使命,表现了女性与历史,或女性与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女性在历史上向来受漠视(歧视),女性的历史从来就不记载在字里行间。然而,王安忆却是企图颠覆文学里惯有的男性叙事,尝试从1990年代努力建构和经营的女性空间里,以女性最细碎、无聊和俗气的生活细节来诠释一个民族对历史的记忆和想象。这无疑是以王安忆自身的记忆为基础:
上海,我从小就在这里生活。我是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在小市民堆里长大的。其实,我父母都是南下干部。我对上海的认识是比较有草根性的,不像别人把它看得那么浮华的,那么五光十色的,那么声色犬马的。好像上海都是酒吧里的那种光色,抽抽烟、喝喝酒,与外国人调调情。我觉得上海最主要的居民就是小市民,上海是非常市民气的。市民气表现在对现实生活的爱好,对日常生活的爱好,对非常细微的日常生活的爱好。真正的上海市民对到酒吧里坐坐能有多大兴趣。(13)
王安忆小说对日常化生活细节的感受,从《长恨歌》伊始已经达至巅峰状态,到后来的《富萍》,甚至《上种红菱下种藕》(2002),笔调可说是有一种“人淡如菊”的淡然。《纪实与虚构》的时候,已经可以看出王安忆建构家族历史的用意,她要完成的是个人的、女性的历史。那些向来从男性眼中建立起来的宏大叙事,在王安忆那里却变得一己和小我。她的小说看似写的是上海,实则是从上海的历史变为个人的历史,而这种个人的历史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叙述完成的。王安忆表态:“我对历史也有我的看法的,我认为历史不是由事件组成的,我们现在总是特别强调事件,大的事件。我觉得事件总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的,等它成为事件实际上已经从日常生活增值了。历史的变化都是日常生活里面的变化。”(14)
历史上的《长恨歌》是写唐明皇和杨贵妃轰烈一时的爱情哀歌,王安忆的《长恨歌》同样以悲剧收场,然而却是一个女人再平凡不过的人生图景。王琦瑶的一生展示了上海40年的历史和其文化特征。这部小说在不同时间和空间背景之下连缀起来的生活细节,让读者同样感受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感。王琦瑶每天的生活意义不在于护士神圣的救人使命,却在于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围炉夜话”,讲故事,猜谜语,发明简单游戏来玩乐,聊天、吃饭、搓麻将等等。王安忆是如此细微地描述日子的家常,然而正因为有淡然如水的生活托底,王琦瑶抵抗日常生活的坑坑洞洞才更见女性独有的坚韧。王琦瑶经历了国乱、建国、“文革”,甚至“后文革”时期,但她的一生却临危不惧地生活在整个宏大的历史叙述当中。王安忆有意淡化小说中建国初期到“文革”十年间的时间和政治背景,“日常化”的都市空间和形态相反地更被凸显出来。若放在历史和政治宏大的叙述中来看,王琦瑶——一个普通上海市女子在平常生活中的小情小爱,却更真实地揭示了社会底层面的生活。
《长恨歌》关心的是王琦瑶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摆弄服饰、做饭烧菜、养小孩、好打扮、办派对等等,不禁让人觉得王安忆是何其刻意去回避40年来历史的真相和真实。这点她也不否认:“我个人认为,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譬如上海街头妇女着装从各色旗袍变成一式列宁装,我关注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因为我是个写小说的,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我不想在小说里描绘重大历史事件。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就应该表现日常生活。”(15)王安忆这点说得何其决绝,因为她原就不打算建构宏大的历史叙事。然而细读小说,这话其实欲盖弥彰。《长恨歌》在个人叙事的背后其实隐约看到了王安忆对历史的想象:
一九四六年的和平气象就像是千年万载的,传播着好消息,坏消息是为好消息作开场白的。(48)
王琦瑶住进爱丽丝公寓是一九四八年的春天。这是局势分外紧张的一年,内战烽起,前途未决。(101)
这是一九四八年的深秋,这城市将发生大的变故,可它什么都不知道,兀自灯红酒绿……(120)
一九六零年的春天是个人人谈吃的春天。(221)
一九六六年这场大革命在上海弄堂里的景象,就是这样。它确是有扫荡一切的气势,还有触及灵魂的特征。(258)
屋角里坐着一个女人,白皙的皮肤,略施淡妆,穿一件丝麻的藕荷色套裙……这就是一九八五年的王琦瑶。(331)
《长恨歌》的时空横跨了40年。一个女人也好,一座城市也罢,毕竟共同经历了四十年代十里洋场的璀璨,五十年代的上海解放,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前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上海都会。尽管“他们又都是生活在社会的芯子里的人,埋头于各自的柴米生计,对自己都谈不上什么看法,何况是对国家,对政权”(224),然而这个城市的历史始终是王安忆无法回避的。她确实要把自己对历史的想象嵌入王琦瑶再平凡不过的一生,因此,上海最动荡的文革时代,王琦瑶居然还安然无事地在弄堂里过着搓麻将、和男人游戏的悠闲日子,王安忆拒绝宏大叙事,超越了历史叙事的崇拜,然而无可否认,她最无以回避的,还是人类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对历史空间的想象。
另外一点可从王安忆所选择和刻画的人物形象来看。不管是《长恨歌》还是《富萍》,几乎都看到王安忆沉溺于书写小人物的生活形态。王琦瑶告别爱丽丝公寓以后,回到平安里来生活。平安里这地方是上海最让人觉得污秽、粗俗的地方。伴着王琦瑶在这里生活的是严师母这类大事小事都要串门子的孺妇,打牌、针线活、打麻将、下午茶等,成了平安里最写实的生活画面。还有,那些后来围绕在王琦瑶身边,为的是她的一箱黄金条的老克勒、长脚,甚至是自己的亲女儿薇薇,他们的嘴脸都显得何其卑微和猥琐。可是王安忆说,写《长恨歌》时恰恰吸引她写下去的,“是王琦瑶从选美的舞台上走下来,走到平安里的一间屋里,屋里的客人,从资产阶级渐渐换成外币黄牛、长脚等人,这就是我所认识的历史”。(16)说到底,无论历史怎样变迁,作家关注的是宏大叙事以外那些专心致志过日子的边缘人物,正是这些不为人道的生活形态,达到了小说欲“补正史之阙”的作用。
早在《长恨歌》写作之前,王安忆已通过一篇短篇小说《“文革”轶事》分析了上海给她的感受:
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样富于情调,富于人生的涵义:一盘切成细丝的萝卜丝,再放上一撮葱的细末,浇上一勺热油,便有轻而热烈的声响啦啦地升起。即便是一块最粗俗的红腐乳,都要撒上白糖,滴上麻油。油条是剪碎在细瓷碗里,有调稀的花生酱作佐料。它把人生的日常需求雕琢到精妙的极处,使它变成一个艺术。……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将人生、艺术、修养全都日常化、具体化,它笼罩了你,使你走不出去。(1993:20)
如此精致的生活细节读来不免让人觉得有点怵目惊心,仿佛日子要是一出了轨就很可能伤了自身。2000年的《富萍》展示了一个更有人间烟火的贫民区,王琦瑶的细致和琐碎已经逐渐消解,剩下来的是细水长流的生活态度。王安忆的小说语言越走下去就越显得自然平实,《长恨歌》时的委婉细腻不见了,但不能否认的是,她小说语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来自日常生活的具体可感。《富萍》的说话简洁、干净,运用无数短句,如“富萍和奶奶生了隙”“四个人连成一串出了门”等等。又比如富萍的长相就这样被作者带了出来:“富萍长了一张圆脸,不是那种荷叶样的薄薄的圆脸,而是有些厚和团,所以就不像一般的圆脸那样显得活泼伶俐。”(27)又说:“富萍是有一种妩媚的,不是在长相里,也不是在神气里,而是在周身上下散发出的气息里面。这和她扬州的乡风有关,和青春有关,当然和性别也有关。”(28)王安忆确是有意和宏大的叙事抗衡的,她甚至尝试以更平实无华的小说语言来和历史的宏大叙事抗衡。回到她之前说的——“历史的变化都是日常生活里面的变化”——我们现在也许就可以理解她的用意,而以下张旭东对她的解释则就更能说明王安忆的心意了:
“世俗日常生活的精致与繁杂瓦解和抵消了历史的震荡和它的“宏大叙事”,它充满于时间之中的是毫不忸怩的肉体放纵以及被称之为生活的艺术的东西。……而在上海,日常生活领域是躲避历史和它的激进化形态的最后的避难所,它也是一块练习意识形态移情的训练地。这种移情总是关涉到对时间、历史和社会变革的政治信念。”(17)
我们对上海历史的记忆永远是由文字记录的大小事件和人物所组成,似乎只文字才得以让我们理解这个社会有所存在的意义。但是,王安忆对历史的诠释却是来自你我最熟悉的日常。书本上历史的记忆总是背负太多,而王安忆笔下平庸的生活记忆何不一样也同样背负着另一种存在的使命?王琦瑶是那个被大时代洪流怎样也吞噬不了的一个平淡无奇的小人物,然而她那无以消解的欲望、爱恨和情愁尽管和历史潮流相悖,却是上海人(个体)对生存或生活空间的想象。因此我们说,历史宏大的叙述,最终也许必须“召回到个人的、日常的、琐碎的、常态的反宏大叙事语言(anti-grand narrative rhetoric)”,因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历史的情境中,找回对所居之地的认同。
“这风情和艳是四十年后想也想不起,猜也猜不透的。这风情和艳是一代王朝,光荣赫赫,那是天上王朝。”(1995:47)(www.zuozong.com)
“那龙虎牌万金油的广告画是从上海来的,美人图的月份牌也是上海的产物,百货铺里有上海的双妹牌花露水、老刀牌香烟,上海的申曲,邬桥人也会哼唱。”(1995:144)
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即宇文所安)在《追忆》一书中对中国古典文学在追忆“时间”而写出“不朽”的文学作品作了如此解释:“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同往事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既然我能记得前人,就有理由希望后人会记住我,这种同过去以及将来的居间的联系,为作家提供了信心,从根本上起了规范的作用。就这样,古典文学常常从自身复制出自身,用已有的内容来充实新的期望,从往事中寻找根据,拿前人的行为和作品来印证今日的复现。”(18)王安忆大部分的小说常都被人说成“怀旧小说”,《长恨歌》尤是。这部小说从开篇即以一种感伤的叙事口吻来缅怀上海的弄堂、闺阁、流言、出生于1940年代的所有上海女儿,还有之后的片厂、开麦和拍照、沪上淑媛、上海小姐竞选、公寓等等,都在看出作者缅怀上海旧时风月的努力。这些描述和想象显然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让王安忆能够在重构昔日上海的同时,把自己对当时上海的想象重现出来。
王安忆为何要重拾上海的怀旧情怀呢?李欧梵用了杰姆逊的观点来解释后现代文化中常出现的“怀旧”。他说杰姆逊用“用的词是nostalgia,可能不能译为‘怀旧’,因为所谓的‘旧’是相对于现在的旧,而不是真的旧。从他的理论上说,所谓怀旧并不是真的对过去有兴趣,而是想模拟表现现代人的某种心态,因而采用了怀旧的方式来满足这种心态”。(19)换言之,王安忆在《长恨歌》创造出一个怀旧的世界的同时,她是多么渴望过去的上海情怀也可以再现于她处身的现代化上海。因此,她只好通过《长恨歌》重新呼唤过去,企图回到历史的现场,希冀藉着历史传统所承载的文化记忆来延续其历史的功能,而她又期许一个民族集体性的怀旧或许可以做到这一点。李欧梵说“她不断塑造着旧日的上海,这个上海并非为她所亲历,只存在于她的想象之中”(20),实际上,我们难以预测的是王安忆的怀旧视野竟是如此辽阔。
《长恨歌》怀旧的审美心理很多时候是出自作者对文化记忆的想象。人们可以借助过去对社会的记忆来透视他们对生活的态度、生存价值,甚至人类的精神归属。这部小的策略是通过旧上海的繁华梦来建构小说家对其城市的文化认同。我们看《长恨歌》里如何描述“城市”和“女性”之间的关系:
她对着镜子梳头,从镜子里看见了上海,不过,那上海已是有些憔悴,眼角有了细纹的。她走在河边,也从河里看见了上海的倒影,这上海是褪了色的。她撕去一张日历,就觉着上海又长了年纪。上海真是不能想,想起就是心痛。那里的日日夜夜,都是情义无限。(144)
走在1990年代现代化上海的街头,王安忆的怀旧可以说是因为她更认同和爱恋上海的现代性。“她这一颗上海的心,其实是有仇有怨,受了伤的”(144),因此,王安忆才更觉得自己需要“寻找上海”。《长恨歌》的写作动机,王安忆已经说得很明白。她说:“《长恨歌》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21)《长恨歌》的“怀旧”虽然是拉开了时空距离和心理差距,但实际上,因为作者对怀旧世界作出不尽的想象,让她不得不更靠近和认同当下的现实环境。
接下来的《富萍》其实更可以看到王安忆从怀旧走出来以后,尝试努力安置自己在上海这座现代之城。同样是写上海,然而《富萍》着力描写的却是这城市的边缘地带。王晓明的一篇长文《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企图对王安忆从《长恨歌》到《富萍》在书写上海的转变作出探讨。从淮海路到梅家桥,很显然王安忆已经告别昔日的海上风华,如今的梅家桥处于上海最边缘的地带,它收敛了十里洋场风云一时的璀璨,梅家桥却是一片建在垃圾场上破旧不堪的棚屋,居民以拾荒、磨刀、贩食、折锡箔为生计,即使是主人公——18岁的农村姑娘富萍也来自扬州乡下,有那种乡下人独有的木讷、呆滞、粗糙、迟钝和乡气。然而,王安忆又似有不甘,让富萍涉足于上海两个特性非常极端的空间:一个是奶奶和保姆们,也是上海人心目中“真正的上海”——淮海路;另一个是舅舅等运垃圾的船工为代表的闸北区苏州河边的棚户区。从海上来,如今又回到上海去,王晓明简括一句:那是王安忆对旧上海的咏叹。(22)不管怎样,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认同仍旧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老问题上,即中心/边缘。论者都说《富萍》完成的是一部移民史。富萍是奶奶抱养的孙子还未过门的媳妇。她被奶奶从扬州乡下带到上海来,她然后为孙子成天看守孙媳妇富萍。富萍到了上海,上海是她小小世界里的另外一扇窗子,她在这窗外看到了另一个她难以融入的不属于她的世界。然而这世界却从此改变了她的一生。
《富萍》的命名是深具寓意的。这群居住在上海的人其实全是“外来者”,宛如“浮萍”,一直是无根无垠的继续漂泊。首先是奶奶,她的身份其实最为尴尬,她虽然在上海帮佣了三十年,又远融不到上海的血肉里边去——“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年,奶奶并没有成为一个城里女人,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而是一半对一半。”(5)——然而,她却很努力地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上海人。她在上海三十年,拥有上海户口,学会几句洋文,也“是个有身份的奶奶”,可是她又丢不了旧习,她称“东家”改不了口叫“师母”;可是奶奶也相当有影响力,一对小姐妹因为她欣然接受了扬州菜和越剧;又比如她做保姆这一行,“只有她挑人家,不会人家挑她。而且她拿定了,只在西区的淮海路上做,只做上海人,那些说山东话的南下干部家里,她是不做的”(7—8)——然而,奶奶心中却一直没有放弃还乡养老的计划。有次,奶奶进入棚户区去舅舅家找富萍,即刻就得到棚户区居民的认可,视奶奶为座上宾,对他们而言,来自淮海路的奶奶才是真正的上海人。奶奶住进棚户区无疑是上演了另一幕移民仪式。奶奶形象的刻画很明显就看出她是个很努力向中心靠拢的人。诚如王安忆把奶奶写得如此决绝:“奶奶所住的淮海路,在他们住闸北的人眼里,是真正的上海。所以,舅妈穿过棚户内的长巷,遇着人问她上哪里去,她就朗声答到:到上海去。”(157)
正因为有奶奶垫底,王安忆真正的目光其实要指向在上海边缘的底层社会。因为奶奶的唆使,李天华到上海来接富萍回乡去。然而,富萍一来是因为逃婚,二来是不想回到乡里,于是她这次又逃到舅舅居住闸北区苏州河边的棚户区。这里显然是邋遢、污秽和贫穷的象征,苏州河上的船工虽然是以运送垃圾和粪为生计,但是在他们却处处体现出对生活顽强的生存意志和坚韧的生活态度。比如舅舅、舅妈同样是来自扬州乡下的移民,但是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的生活也终于熬出了头。王安忆的故事说到这里,显然还没意思给漂泊无依的富萍靠岸,那富萍最后的归向是何处呢?这仿佛也是王安忆这些年来在书写上海的同时念慈在兹的问题。富萍从开始就被奶奶带到真正的上海去,然后又经舅妈要她留在棚户区,这个过程已在在显示出边缘意识对身份认同所起着的作用。富萍一直都不愿意回到乡里,但是她在上海的生活很容易就露了底——“她紧绷绷的,透出一股子鲜艳的乡气。和她的表情一样,她的行动也是迟钝的,看上去很‘木’”,“这姿态也有一种鲜艳的乡气。城里女人不会这样开放自己的肢体,步子也不会这样碎而轻捷,有一点像台步”(28)——在淮海路和苏州河之间挣扎以后,王安忆最后安排她来到前面说过的梅家桥。
近代上海的历史是一段移民的历史。《富萍》所有的人物都属于上海的外来者。这个以1960年代为背景的移民史最后要寻找的精神归属将何处寄托?那里会不会是一处无法勾勒出来的、不存在的上海绘图?富萍的出现也许是对历史和空间想象的反抗,因为即使再怎么努力,上海这座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城市毕竟还是难以安身立命。陈思和在一篇文章《论海派文学的传统》,曾经这样解释这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像上海这样一种移民城市,它的许多文化现象都是随着移民文化逐渐形成的,它本身没有现成的文化传统,只能是综合了各种破碎的本土的民间文化。与农村民间文化相比,它不是以完整形态出现的,只是深藏于各类都市居民的记忆当中,形成一种虚拟性的文化记忆,因而都市民间必然是个人性的、破碎不全的。”(23)
由此观之,富萍若选择在上海安身,必要从她原有的民间记忆中重整个人的立足点。她笔下勾勒出的梅家桥虽然和现代化上海有所差距,却最能反映出王安忆对民间文化寄寓的一种崇高理想。诚如她说:“这是真正的劳动吃饭的生活,没有一点悔对内心的地方。”(2000:150)富萍最后没有在上海的中心淮海路落脚,也没有栖居于上海边缘的棚户区,她最终选择离开棚户区更边缘的地方——梅家桥落脚。富萍在那里结识一对靠糊纸盒为生的母子,其儿子是个残疾人,富萍就这样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并且在那里落叶归根。王安忆之前积极“寻找上海”,最终却回归到她当初坐着痰盂进上海的来处,她到底要寻找怎样的上海呢?富萍在梅家桥跟着这对母子糊纸盒过日子,“富萍的心情很安谧,因为这对母子都生性安静”,(241)富萍选择在“残缺”(青年是一残疾人)的下层生活层面中生活,过的是一种宁静、诚实、善良和有尊严的生活。这幅美丽的人生图景说来似一座桃花源,却是王安忆努力经营的一幅上海绘图,只有在这里才找到人们何时何地都得紧守的一种生存态度。
从《长恨歌》开始,王安忆孜孜以求一座“城市的故事”。她站在上海至高点来看这座城的当儿,也许有过那么一刻她是要迷失其中的。诚如她晓得:“在这个地方,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他也从不知道,别人从哪里来。”(24)那一年,她踉踉跄跄坐着痰盂进上海,目的就是要“寻找上海”。从《长恨歌》到《富萍》仅仅五年之间,王安忆已经无法回避上海这座城确是她终身的依归。海上繁华梦也只是一时风华,王琦瑶(王安忆)最终是要告别舞台上的昨日光辉,来到后台换上富萍那套朴素的衣服,再回到平实里头去。即使她曾那么狂热地书写“我城”,最终为上海绘出的不过是一幅最平淡无奇的人生图景。繁华落尽,平淡是福。这也是王安忆心里知道:“我们便只有一条出路,走向我们自己。”(25)
(本文系首次发表。)
(1)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37页。
(2) 王安忆:《寻找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年,第2页。
(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1999年。
(4) 王安忆:《重建象牙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92页。
(5) “公共空间主要指的是文学关注于女性与政治、历史、道德、人文关怀等领域,其特点是思想性、道德性和公共性;与之相对的私人空间则是指文学主要表现个体的女性欲望、意识、潜意识,其主要特征表现为私人性和个体性,以私人空间为主的小说即使涉及到社会历史道德,也是作为私人空间中成长的羁绊和批判的对象而出现的。”参阅张浩《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论王安忆创作中女性空间的建构》,收入《中国文化研究》总第34期,2001年冬季卷,第162页。
(6) 张浩:《从私人空间到公共空间——论王安忆创作中女性空间的建构》,第163页。
(7) 王安忆:《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89页。
(8) 王德威《文学的上海——一九三一》,收入王德威:《如何现代,怎样文学:十九、二十世纪中文小说新编》,台北:麦田出版,1998年,第269页。
(9) 王安忆《形象与思想——关于近期长篇小说创作的对话》,收入王安忆,《重建象牙塔》,第207页。
(10) 王安忆:《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页。
(11) 王安忆《上海的女性》,收入王安忆:《重建象牙塔》,第86页。
(12) 凯文·林奇著,林庆怡等译:《城市形态》,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94页。
(13) 夏辰:《讲坛上的作家系列访谈之一——王安忆说》,收入《南方周末》2001年7月12日。
(14) 刘颋:《常态的王安忆 非常态的写作》,原载《文艺报》2002年1月15日。
(15) 王安忆:《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原载《文艺报》2000年11月11日。
(16) 王雪瑛:《‹长恨歌›,不是怀旧》,《新民晚报》2000年8月6日。
(17) 张旭东:《上海怀旧——王安忆与上海寓言》,收入张旭东:《批评的踪迹——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1985—2002)》,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55页。
(18) 斯蒂芬·欧文:《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页。
(19) 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第45页。
(20) 李欧梵:《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文学评论》1999年第5期,第45页。
(21) 王安忆:《更行更远更生——齐红、林舟问》,收入王安忆:《重建象牙塔》,第191—192页。
(22) 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第10页。
(23) 陈思和《论海派文学的传统》,收入《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第一期,2002年,第6页。
(24) 王安忆《城市无故事》,收入王安忆:《漂泊的语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429页。
(25) 王安忆《城市无故事》,第431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