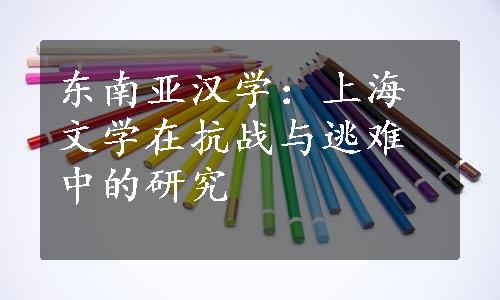
青 禾
1941年5月20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晨星》上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
诗人杨钟的南来与杨骚在福州别后,已经有三年不见了。虽在报章杂志上,时时看到他的消息,但是从武汉而湘西,从湘西桂亭,我却终于没有机会和他在旅途中一见。现在他从抗战的陪都,经过香港,而到了这长年是夏的南国,我们很庆幸旧友的天盖,同时又欣幸着南荒的热带上,重增上一执笔的战士。诗人是曾经到过各战区去慰劳将士、视察过抗战的实况的,我们希望他能于征尘暂洗后,将他的所见所闻,都写出来报告给我们。文化人在这一战乱时代里所能做的事情并不少,尤其是在文化和我国不同的这南岛,我们希望诗人杨骚能给予我们以簇新的制作,而增加些我们的兴奋。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晨星》主编郁达夫。郁达夫应《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之邀,于1938年底到新加坡宣传抗日,他对老朋友杨骚的南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喜悦。
新加坡,久违了,杨骚回来了。踏进这块陌生而熟悉的国土的那一刹那,杨骚的心中涌起了一种近乎亲切的感觉。
新加坡变了,尽管它的背后,是殖民者的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是殖民地各民族人民的苦难和不幸。它已经抛弃了过去的荒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它迅速地变成一个军事要塞,海上和空中的交通枢纽,繁华的贸易商埠。宽阔的大街,高大的楼房,刚刚建成的耗资一百五十万元的雄伟的法院大楼……杨骚也变了,他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为了寻找出路、寻找黄金的迷茫的失意青年。已经是一位知名的诗人,一位爱国主义的执笔的战士。他肩负着宣传抗日的使命,他的心中没有凄凉,没有往常的那种漂泊感,他是迈着坚定的步伐踏上这块故土的。
南国的海风轻轻地抓着他的衣服,抚摸他的脸颊,仿佛在辨认一下这位昔日的朋友,狮城的橡树在风中弹奏着他熟悉的音乐,仿佛想唤起他过去的回忆。
老朋友周筼来了,啊,还是老样子。在过去的那段凄风苦雨中,是他给了他难忘的友情和温暖。
三弟杨维来了,久别重逢,多少家事要说,多少亲情要诉,使他们凄然落泪的是母亲的死,他们都没能回去为她老人家送终,这使他们都感到深深的负疚和遗憾。
杨骚先住在三弟的家里,以后在龙溪会馆住过一段时间,又住到赵芳路29号。杨骚惊喜地发现,在这块曾经使他感到凄凉无依的土地上,聚集着如此之多的新朋故旧:胡愈之、张楚琨、王纪元、高云览、汪金丁……当然,还有郁达夫。
郁达夫伸开双臂热情地迎接老朋友。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是战士与战士的拥抱,这是作家与诗人的拥抱,这是诗人与诗的拥抱,这是知己与知己的拥抱。他乡遇故知,这是人生的一大幸福。杨骚来到郁达夫的家里。郁达夫住在中峇鲁一幢小洋房的二楼和他的大儿子郁飞及女友李筱瑛住在一起。在他那间曲尺形书房里,他们促膝谈心。老友相聚,岂能没有酒?杨骚自然谈起国内的抗战,谈起陪都重庆,谈起文协,抗战访问团,谈起皖南事变,谈起他这次南行的使命和周公的指示。谈得更多的是郁达夫。郁达夫是个容易披肝沥胆的真情男子,何况对着故友知己。他谈得很多很多。妻子离异回国与他人结合去了。新加坡如今来了许多国内的文化人,虽然大都是过去熟悉的朋友,可是,以《南洋商报》主编胡愈之为中心的文化人和以《星洲日报》为中心的文化人,旗鼓分明,彼此对垒,而他偏偏在《星洲日报》编副刊,叫人又尴尬又孤寂。他对南洋文艺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写了一篇《几个问题》,却引起新马文化界却料不到的一场文字论争。他漫游马来亚,写了一些游记,却被人认为是国难当头,竟醉生梦死,游山玩水……
郁达夫越说越伤心。
“达夫,别往心里去,你的爱国我理解,朋友们也都会理解的。”
杨骚用他那带着漳州腔的普通话安慰道。
郁达夫举起手中的大酒杯,一饮而尽,以此来表示对朋友理解的感激。
杨骚知道,达夫在暴露自我这一方面虽然非常勇敢,但他在迎接外来的攻击上却是非常脆弱的。他有“一颗努力向善和上进的灵魂,但必须有爱情与友情统以抚胞和鼓励”。(巴人《记郁达夫》)
这时候,朋友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对于郁达夫比什么都重要。
杨骚的话不多。但他的确给孤独的郁达夫以莫大的安慰。十几年后,当杨骚去世之后,巴人在他的纪念文章《记杨骚》中这么说:“大概由于杨骚深沉地表现了对达夫的友情的温暖吧,达夫从各方面都表现积极了。”
有一次,他们谈到了林语堂,那时,郁达夫在《华侨周报》译载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他说,你的老乡寄了美金来,一定叫我翻译,林语堂和杨骚、郁达夫都是老相识,自然有话可谈。自从30年代初,由于种种因素,杨骚与林语堂的关系已经疏远了。1932年初杨骚自上海回漳州,与林语堂太太廖翠凤同坐一条船,一个在三等舱,一个在二等舱,杨骚没有去看她。但是,杨骚对林语堂还是了解的。他以自己的方式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他的《吾国与吾民》取得巨大成功。去年,又把他在重庆北碚的小洋房借给“文协”使用。他写《京华烟云》,在给郁达夫的信中说,是为“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这一点,杨骚是相信的,他以为,以郁达夫的优美文笔来译《京华烟云》自然是一件好事。可惜,由于忙,郁达夫没有译完这部小说。钱用光了,译文尚未出来,郁达夫感到对不起朋友。杨骚非常理解他的这种心情,杨骚的理解,多少减轻一点郁达夫的那种负疚的心情。这一次,杨骚谈到林语堂似乎有些感慨。前不久,他刚刚得到许地山去世的消息,作为漳州人,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情在诗人的胸中读过。
杨骚找到胡愈之,很快地,通过关系,他来到怡和轩俱乐部南侨总会,获得陈嘉庚先生的聘请,出任《民潮》主编。《民潮》是南洋侨总会的会刊,半月刊,十六开本,每逢十日、二十日出版。创办会刊是南洋闽侨总会刚成立时就决定了的。“鉴于南洋各地华人对中国抗战的实际情况了解太少,当时新马各报无法及时和全部将国内情况反映;另一方面,南侨总会也很需要一份属于自己的宣传刊物,因此,就由南侨总会筹办《民潮》半月刊”,转引自《杨骚与‹民意›半月刊》,历史和机遇使杨骚担负起主编《民潮》的重任。杨骚到新加坡原来是想能编一个报纸的副刊,对主编一个刊物,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为了把刊物编好,他想请楚云协助。
楚云是杨骚的老朋友。1935年,楚云在上海参加《读书生活》半月刊的编辑工作。《读书生活》常常发表新诗,不时有读者提出关于新诗的问题,楚云想起新诗界已有名气的诗人杨骚,便把几期“青年习作”的新诗剪下,连同一些读者来信,托友人转会尚未谋面的杨骚,请他评议和解答关于新诗的问题。不久,杨带着写好的稿子来找楚云,他们都是福建人,在上海可谓是老乡了,却又不懂对方的家乡话:楚云是福安人,福安话和漳州话有很大的区别,两个老乡只好用官话对话了。后来,楚云到重庆“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还带杨骚到他们出版社的门市部买过《资本论》等进步书籍。1941年5月,楚云“疏散”到新加坡,在南洋女子中学任教,并兼任《南洋商报,青年和学习》编辑。(陈松溪《爱与楚云》,自南日报;1992年11月13日)。
楚云欣然答应协助处理编务。刊物原来拟名为“南侨”或“闽侨”,杨骚与楚云商量后觉得这名称不够理想,建议改为“民潮”,既和“侨”音相近,又有“民主潮流”之意。他们的意见得到陈嘉庚和李铁民(南侨总会秘书《民潮》督印兼发行人)的同意,正式定名为《民潮》。(同上)
楚云是1928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他尽力帮助杨骚,从开始筹备到第二期出版,他每天都有一定时间到编辑部。第二期出版之后,由于杨骚对编辑工作已经熟悉了,楚云便不再来帮忙了。(陈松溪、黄安榕:《杨骚与‹民潮›半月刊》,见厦门大学出版社《杨骚的文学创作道路》)。
1941年8月10日,《民潮》创刊。《民潮》是综合性的刊物。包括政治、时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文章及文学作品,也反映华侨妇女、青年和学生活动,并设了“乡讯”专栏,刊登反映福建近况的通讯、报道及专文,《民潮》忠于南洋闽侨总会的宗旨,努力呼唤华侨社会加强团结,支援祖国抗战事业。杨骚在创刊号上发表《民主运动在祖国》。他指出:祖国的民主运动如大海的浪潮汹涌澎湃,尽管那些反民主的所谓“忠实同志”以种种大逆不道的罪名,什么“灰色汉奸”“分赃”“夺取领导权”“颠覆政府”“异常”等等反对民主浪潮,……
此时的新加坡,抗日宣传活动,如火如荼。杨骚的工作环境是好的,他既得到陈嘉庚的支持,又得到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有同在星洲的知名人士,如胡愈之,沈兹九、巴人、蔡高岗、高云览、王纪文,有在香港的乔冠华、金仲华,还有在国内的胡风、叶以群、林林等。对他帮助最大的要数巴人,他“是非全职人员当中最常来的作家”,有时为了应急,巴人一期就为他写了几篇杂文。(《杨骚与民潮》半月刊》)《民潮》在众多的抗日报刊中,显示了自己的特色。
8月4日,许地山在香港病逝,新加坡华侨各界举行追悼会。《民潮》推出“纪念许地山先生特辑”,杨骚发表《哀念地山先生》。(《民潮》1941年11月10日第1卷第7期)《民潮》编辑部设在武吉巴梳路梁氏总会的楼下。杨骚住在赵芳路29号,与作家、新闻工作者蔡高岗合租一房间。他天天到《民潮》办公,有时甚至彻夜不归,反正家对于他,只是一张床。几十年后,当时在侨总会秘书处任职,如今已年逾古稀的林云先生说:“杨骚天天到《民潮》社,埋头写稿、审稿、处理版面……杨骚平时说话不多,也不大注重仪表,穿着很随便,不过,他说话的态度倒是很温和的。”(见《闽南日报》1988年6月18日)
1941年11月8日凌晨,构建完一篇文章,刚刚入睡,他突然被一阵轰炸声惊醒,在重庆,他听惯了这种可怕的声音,他一跃而起,匆忙中看了一下腕上的手表,正是凌晨4点。“十九架来自印度支那南部的日本基地的海军轰炸机,未先发出警告,直通这个灯火通明的城市。炸弹大部分投中轰炸目标登加和实里达两个机场,一部分则投在闹市区,造成二百亚洲人伤亡”([英]哈·弗·皮尔逊著《新加坡通俗史》)。
一个多月后,英军从柔佛新山撤退到柔佛海峡南岸的新加坡岛,新加坡成了“四面倭歌”的孤岛了。
兵临城下,战火纷飞。杨骚没有畏惧,《民潮》停刊后,他同文化界同仁,积极投入抗敌保卫星岛的群众热潮之中。杨骚和巴人、郁达夫、胡愈之、王纪元、张楚琨等人组织“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他们在炮火中培训青年干部,准备担任民众武装的政训工作,组织演讲队、戏剧队、歌咏队,到群众密集的地方去进行抗敌宣传。一直到兵临城下,英殖民当局才允许华侨参加抗战,然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15日下午5时15分,白恩华将军带着求和的白旗,到武吉知马路福特汽车厂的经理办公室,站在日军第二十五军司令官的面前,接受山下将军的命令无条件投降。当天晚上8时半,新加坡的英军放下了武器。”
2月9日,杨骚和一批文化界人士,搭大航舰逃出即将沦陷的新加坡。
2月12日,杨骚来到苏门答腊东海岸的一个叫萨拉班让(石励班让)的小岛上,开始了他三年的隐居生活。
杨骚在这个荒僻的小岛上遇见了巴人和他的女友雷向予,巴人、雷向予和郁达夫、胡愈之等人比杨骚早几天逃到这里,后来郁达夫、胡愈之等六人与巴人、雷向予分离,准备上苏门答腊,经由巴东去爪哇的巴达维亚(雅加达)。巴人、雷向予则因语言隔膜和社会关系不多等原因留了下来。杨骚改名杨笃清,隐居在萨拉班让对面的邦加岛上的门托克(文岛)的一个漳州老乡的家里。杨骚的三弟在新加坡旅居多年,认识不少同乡,加上这些小岛上有许多闽南华侨,语言相通,便于隐居。
3月12日,苏门答腊和爪哇相继被日军占领,与马来亚仅有一水之隔的廖州岌岌可危。杨骚听到这个消息,很着急。他想,巴人和小雷都是北方人,不会讲闽南话,要在这华侨社会里隐蔽下来是十分困难的,便去找他们,说:“住到山里去吧,我跟你们一起住。让我们结上亲戚关系,小雷算作我的妹妹,你作了我的妹夫,这样,我就可掩护你们了。”
他们在萨拉班让对面的亚里岛上的一个叫牙生比(狭何)如山芭(小乡村)住下来。
这是一片胶树园,一条二三尺宽的小河在胶园中间穿过,流淌着血一般的红水。在胶树园正中有一所白木板房屋。他们就隐居在这所房子里。房子的主人叫任生,是一个外表冷淡内心热情的“广西客”,杨骚对主人说:“我是在新加坡开小店,做小本生意的。他是上海人,在书店里当伙计。因为怕飞机轰炸,早已逃到萨拉班让。现在听说新加坡店面给炮火毁了,回去不得,索性来山芭住一时,看平静一点以后再说。”
这自然是他们事先编好了的假话。
这是一所两进的房子,前厅,左右两个厢房,从偏门进去,是后厅,也有左右两个厢房。厨房紧接在后厅的披檐下,相当宽大。巴人他们住在前厅的右厢房,杨骚和主人的叔叔住在左厢房。
有一天晚上,他们在屋子附近散步。这里除了树胶,还有槟榔,疏疏落落的槟榔一直排列到半里外河湾的尽头。这里曾经繁荣过,留下不少遗迹,倾倒的房子,破旧的机器。凄清的夜,凄清的风。他们多想喝点酒,多么想唱一唱抗日救亡的歌曲,让这些高吭的歌声,在那些败草丛中,在那些槟榔树顶飞扬。
但是,不能,他们是隐居者,他们是没有真实姓名的生意人。
杨骚的心情是压郁的,一腔热血到南洋来宣传抗日,不想落得如此境地。他恨日寇的凶残,他也恨自己的文弱,抗敌无路,报国无门,怎不叫人气闷。
他总是睡不好觉,总是做梦,说梦话,睡在右厢房的巴人甚至能听到他的梦话。巴人说,这演说似的梦话,是诗人“幻想的奔放”。
杨骚曾想自己开一块农园,可是,锄头在他的手中显得太重,不到十下,便气喘流汗而且两手一下子起了两个血泡。他到直落岛探听消息,从一家吉兰店(小杂货店)里买回两把德国斧头,悄悄地用纸头包扎好,夹在皮箱衣服里。一天,他特地请来任生,打开箱子拿出斧头,让任生赏识。
“好斧头!要是转卖给我,我也要哩。”任生说。
杨骚一听,立即拿回斧头,依然用纸包好,像母亲放孩子到摇篮里去似的,放回箱子去。
关上箱子后,杨骚不说一句话,静静地望着窗外的树梢和天,夜里,闲得发慌的时候,他又悄悄地从箱子拿出那两把斧头,在暗淡的灯光下端详、抚摩着。
此时的杨骚在想什么呢?他果真在这两把斧头上托寄着田园。不久,传来日本海军在萨拉班让登陆的消息。他们把书放到任生的铁箱子里,藏起来。因为书本身就是一种危险。
苦闷的杨骚只有喝酒了。好在这种酒不怎么伤胃。这是家酿米酒。主人任生是个酿酒行家,杨骚便买了糯米,请他做。
他们在这里隐居了四个月。
这四个月里,由于杨骚在华侨社会里语言的方便,他成了不会闽南话的“普通人”巴人和小雷的保护者。
日本陆军终于在萨拉班让驻扎下来,这是一个阴影,杨骚常常到直落、到萨拉班让、到所有朋友住着的各岛上去,最后,他在亚里找到了住处。巴人他们也经亚里到老城,又从老城到巴耶公务,找到了胡愈之和郁达夫。
临别时,任生再次提出想买他的那两把德国斧头,杨骚说:
“这斧头早已给朋友拿去了!”其实,那斧头还放在他的皮箱里。
诗人在这斧头上面寄托着什么样的情思呢?或许,这是把诗人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的桥梁;或许这是种幻想,诗人在这幻想中,能够得到片刻的安宁;或许,这是一种武器的象征,诗人在这武器的身上,寄托着胜利的希望。
不久,杨骚来到楠榜直落勿洞,这是苏门答腊南端的一个小镇,这里住着许多华侨。
这时,时局已经“定”了,“秩序”在逐渐恢复。必须找点事做,才能和当地的华侨融为一体,便于长期隐蔽,也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
杨骚与当地华侨和张楚琨、林枫等人合伙开设木炭肥皂厂,掩护度日。他们的肥皂厂设在“甘榜”古邦克拉迈小山丘上。周围都是印尼人,房东太太也是印尼人,他们称她“玻璃太太”,他们相处得很好。玻璃太太常来教杨骚他们学印尼语。
半个多世纪之后,林枫在一篇回忆他们当时生活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诗人杨骚对这里的环境很满意,生活很愉快,每当月明之夜,诗兴勃发,便独自吟诵不已。有一次他低声哼着一首英文歌,我觉得很好听,问他是什么歌,请他教我唱,他说,这是一首圣诗,不是歌,但有些年青人把它当情歌来唱,诗句很美,……诗词的大意:我怎么能离开您,我怎么能与您分离,只有您占有我的心,亲爱的,相信我。您拥有我的灵魂,紧紧地绑在一起,没有人值得我爱,只有您。我对他开玩笑说:杨大哥您还年轻,也可把它当作情歌来唱,也许会唱出一位“亲爱的梅娘”呢。他忙答说:不,不,我只是借以来抒发对祖国的怀念。
杨骚和张楚琨是老朋友了,他和张楚琨爱人以表兄妹相称,这也是闽南人的习惯,亲切又不容易引起注意。张楚琨是南安人,50年代在厦门当副市长,以后,担任过中新社副社长、全国侨联顾问。杨、张两家关系密切,后来,杨骚的儿子和张楚琨的女儿的名字,以“泳”字排辈。
1944年6月,杨骚和当地侨生陈仁娘结婚。
这是一桩以安全为目标的婚姻,这桩婚姻却给杨骚带来一个温馨的家庭和三个儿子。
陈仁娘的祖籍在福建安溪,可以说和杨骚同是闽南老乡。但安溪对于陈仁娘来说,只是一个遥远而悠久的名词。陈仁娘的父亲是镇里一座基督教堂的执事,母亲是当地人,陈仁娘生于1919年,是父母的第三个女儿,那时,正在中学里读书,然而,她读的是印尼文,对中文几乎一窍不通。他们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既然是在当地生活的华侨,能没有个家?有个家,对于杨骚,自然是安全得多。而对于陈仁娘也是一种保护,当时,日本人到处抢没有结婚的“花姑娘”。他们的婚礼是在教堂里举行的,那时,纤瘦的新娘子,穿着一件乳白色的婚纱。在教堂里结婚,穿乳白色婚纱的陈仁娘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贤妻良母,她善良贤惠,温柔体贴,她把丈夫当成自己的终身依托。她一直珍藏着那件乳白色的婚纱,半个世纪之后,她对儿子说:“日后死了,我要穿结婚时穿过的那件婚纱。”是的,这件婚纱记载着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记载着她一段美好的记忆。
她去世之后,她的儿子找到了这件泛黄的薄软的婚纱,把它披复在她的身上。
这件婚纱和她一起化为青烟,飘游到杨骚的身边。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时,杨骚的妻子陈仁娘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当她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已经是1946年的1月了。
杨骚给他们的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泳南”,泳者,浮也,这或许是诗人对飘泊南洋的一个纪念。而这纪念的背后,似乎又有更深切的感情,南洋、南洋,没有祖国,何谓“南洋”?!不久,杨骚举家来到阔别四年的新加坡。五年前,他到新加坡是为了宣传抗日的,如今,日本投降了,他该做些什么呢?杨骚似乎有些茫然和凄惶。这时,他写了一首诗,叫《夜半低吟》,这首诗曲折地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什么病啊,什么病?(www.zuozong.com)
我,常在夜半从恶梦中惊醒:
梦见小鬼在我肚里踢球,
梦见疯子扼我可爱的红婴。
什么病啊,什么病?
我,常在夜半从恶梦中惊醒:
梦见寂寞去世的母亲,
梦见毒蛇绕我的腰身。
什么病啊,什么病?
我,久不梦见笑脸温情,
久不梦见山绿水青,
好久啊,更不梦见苍苍的大海,
让我飞鱼般跳跃、游泳,
更不梦见骑彩虹,生白云
什么病啊,什么病?
尽是恶梦纠缠不清。
我,在梦中,时而无限悲愤,
时而大吃一惊,
时而呜咽不成声,
时而又热泪淋淋……
什么病啊,什么病?
在梦中,我挣扎、呻吟,
我挥拳打,用头拼,
总扑个空,或碰着钉。
这样,就这样吓醒。
醒后呢?黑夜还是沉沉,幽幽静静,
但闹钟敲一声、两声,
或鸡唱一声、两声。
(见《风下》,1946年6月22日)
这是记实,也是象征。这梦,是刚刚过去的日据时期那种提心吊胆的恶梦般生活的回声。恶梦般的生活虽然过去了,但新的生活却又是令人捉摸不定。他虽然受命南行,但战争使他失去了各种联系。我们从“梦见疯子扼我可爱的红婴”中完全体味到诗人对未来的担忧,然而,诗人依然渴望大海,渴望“飞鱼般跳跃、游泳”,渴望“骑彩虹,生白云”,渴望告别那多梦的沉沉的黑夜,迎接那“鸡唱一声、两声”。诗人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已经不是单身汉了。他有一个家,一个妻子,一个儿子,他的工作还没有着落,他还要靠朋友的接济来维持生活。一天,他路过武吉巴梳路梁氏总会,不禁驻足留连,这是一个多么叫人难忘的地方,在这里,他度过许多紧张而愉快的日子,这里也曾留下过他的朋友们,胡愈之、郁达夫、巴人、楚云……的身影。郁达夫,郁达夫哪里去了呢?听说他遭到了不幸,但愿,那仅仅只是失踪,失踪,总是会找回来的。战争,实在有太多的死亡,但为什么要偏偏是他呢?不,不是真的。他意外地碰到了巴人,起初,他几乎没有认出他来,一脸的大胡子,这是那个风流倜傥书生?这是那个只小他一岁的“妹夫”,然而,他的胡子实在是好看,实在是给他增添了不少飘逸。杨骚对胡子似乎有特殊的好感,这大概和他小时候临摹古书插页上的英雄画有关。他自己也曾经留过胡须,他曾给家里寄过一张照片,并提醒家人注意他下巴的一撮小山羊胡,弄得家人莫名其妙。他邀请他到家里,会见了他的妻子陈仁娘。久别重逢,劫后余生,要说的话很多。最后落到各自眼前的生活话题上。杨骚告诉巴人,日本投降后,他们的肥皂厂结束了,分散所得的财产,他分得了一座有几百株橡树的橡胶园,但是,印度尼西亚在闹革命,橡胶园是不能生产了。他只能靠发了财的朋友们的接济生活。“将来,我只能搬到胶园中去住,数数橡树过日子吧。”
他自嘲地笑了。
笑过之后,便又欣赏起巴人的胡子,还邀请巴人到照相馆去合拍了一张相。
1946年,杨骚(左)与王任叔合影
这张照片四十年后被刊登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的封二上,在这张照片中,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杨骚;削瘦的脸颊,鼻梁上架着一副深色镜框的眼镜,眼镜后面,是一双略显忧郁的眼睛。薄薄的嘴唇紧闭着,只把一丝微笑漫不经心地留在嘴角,微皱的西装里没有结领带,甚至连衬衫的领扣都没有扣上。这是一个清贫、散淡而忧郁的诗人。杨骚在城郊东岭中学找到一个教师的位子,举家住到一个小椰子林的破茅屋里。战后的杨骚依然是清贫而多病的。清贫而多病的杨骚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写两幕话剧《只是一幕》,写诗歌《杨德乐的农妇》,写歌词《华侨青年进行曲》,这歌词经谱曲,在《热带新歌》上发表,很快在华侨青年中传唱开了。
他和胡愈之、沈兹九、洪丝丝等人发起和编辑《大战与南侨》,做了一些具体的编辑工作,“这本厚厚的书,用血泪的事实,控诉了日军南进后对南洋各地华侨犯下掳掠残杀的滔天罪行,内容丰富,证据确凿,还附有不少珍贵的历史图片,这本书在国内恐怕难见到。我曾保存有一本,可1963年叫海南侨务局‘征用’去了。”(见洗东《思念的浪花——忆伯父杨森》,《芝山》1983年第2期)
在新加坡吉宁街四十二号上海书局新加坡分局的楼上,新南洋出版社出版一个周刊《风下》,创刊之初,注意力集中于战后世界局势的探讨,自1946年6月以后,重点转向对国内形势的关注。
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了。人们脸上刚刚浮现的胜利的笑容消失了。海外华侨关切祖国命运,渴望了解国内形势的真相。《风下》发表了《救国有罪民主该杀》《内战大规模打起来了!》《苛政猛于原子弹》《天下一家,一家天下》《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人民翻身与换朝代》《准备迎接伟大的新时代》等一系列“卷首言”,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将美国援助国民党政府,助长中国内战,促使中国分裂的两面政策公诸于众,从而激起了华侨新的爱国热潮。《风下》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成了读者“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清贫的时候胃痛的杨骚,为《风下》的成功奉献自己辛勤的劳动。
《风下》主编胡愈之这样说:“《风下》从内容到形式都较清新可贵,这主要得力于许多著名作家和知名人士的热情支持……至于杨骚、巴人、汪金丁、卢心远、陈仲达、张企程、吴柳斯、沈兹九等流亡在南洋的文化界朋友,则是《风下》的作者和记者,又是《风下》的编委,每期都有他们采访的新闻、通讯和各种文章发表。”(胡愈之《南洋杂忆》)杨骚还热情地参加《风下》周刊创办的“青年自学辅导社”的改卷工作,为华侨青年的成长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为团结广大华侨反蒋拥共,促进祖国的早日和平民主、自由解放,陈嘉庚、胡愈之、张楚琨、高云览等人创办《南侨日报》,杨骚积极参与《南侨日报》创办工作,同时加入了胡愈之等人组织的中国民主同盟南方总部。《南侨日报》发刊后,杨骚收到白薇的一封信,希望恢复关系。因已成家,终于没有回信。四十六岁的杨骚面对现实。在过去的漫长的岁月里,他曾经对不起别人,别人也曾经对不起他,而现在,他再也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妻子和儿子了。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白薇,没有忘记这个曾经使他无限幸福和痛苦的朋友。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曾以“素”署名发表文章,以此来表示对她的怀念。
他的胃病终于越来越严重。医生对他说,“需要休养,不能过劳”。于是在1947年的冬天,到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养病。巨港的朋友办一家肥皂厂,他在那里帮忙,做一点管理账目的工作,而大部分时间仍在休养治疗。不久,肥皂厂亏本结束,他的胃病又不见好。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转椰城(雅加达)就医,还是时好时坏,最后决定做胃切除手术。1950年2月3日开刀,到3月出院。至此,这个折磨了他几十年的胃病,才算得到根治。
在他治病期间,他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古老的中国以全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1950年8月,当巴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特命全权大使来到雅加达时,他们又相见了。杨骚给这位老朋友新大使留下这样的印象:“我看出他的变化:第一,胃病由于割治,已经好了,他的身体健康得多了。第二,人更现实了,虽然还是沉默寡言的。而他对于祖国的一切新措施,总时时表现出抑不住的兴奋。”
1950年4月,杨骚应邀到《生活报》工作,编副刊《笔谈》,《生活报》是一家华侨爱国民主报纸。1951年总编辑王纪元被捕驱逐出境。杨骚继任总编辑兼副社长。在这里,他再一次与老朋友楚云共事。
1950年初,中国与印尼建交后,雅加达的华侨分为两派,各同乡会馆、慈善团体、华语学校,都为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派人所掌握。另一派却占有中华会馆,由“快乐世界”娱乐场的亲台湾国民党的商人所支持。两派斗争相当激烈,加上国民党文化特务的造谣惑众,斗争显现出极为复杂的局面。在这复杂的斗争中,《生活报》旗帜鲜明地支持新中国,宣传新中国,不断揭露反动派的各种宣传阴谋,表现出可贵的爱国精神和斗争精神,受到广大华侨的热烈欢迎。
杨骚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生活报》的工作,每天早上带着饭盒到报馆,写稿,编稿,审稿,报纸出版后,就在报馆内,吃带来的冷饭当午餐。他的饭量越来越少,身体也见虚弱,总是咳嗽。但他似乎把自己身体给忘记了。2月10日,杨骚在给养女杨雪珍(红豆)的信中这样写道:
“你应该好好学习,求进步,最要紧的是不要读死书,应该参加各种可能和合理的实际活动。目前祖国已经完全改观,家乡也正在实行土改,一切的一切都在革新迈进。你应该加倍努力,才不会落在时代的后面,变成对人民对国家没有用的多余分子。这是杨骚对后代的勉励,也是对自己的勉励。他正在尽努力,不让自己落在时代的后面。
印尼当局右倾,进步人士的安全受到威胁。不时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杨骚的家门口走动。有几次,他们窜进家门,而杨骚却从后门走脱了。8月16日,印尼政府大举捕人,杨骚事先得到消息,得以幸免。由于环境恶劣,他在朋友的掩护下,躲藏了四个月,一直到年底,才又回到《生活报》。在紧张和危险之中,杨骚的第二个儿子出生,这个儿子后来继承了父亲的事业。
在《生活报》工作期间,杨骚写了大量的社论、评论、杂谈。从这些文章中,我们看到诗人的另一个侧面:政论家的风采。
1952年11月8日,《南方日报》发表杨骚的《短歌三首》:
《为庆祝十月革命三十五周年而作》
劳动使猿猴变成了人,
十月革命使人看到了光明。
歌颂吧,劳动!
歌颂吧,十月革命!
劳动创造了人类的一切,
十月革命使一切为着人。
歌颂吧,劳动!
歌颂吧,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以前劳动者不被当人看待,
十月革命以后劳动成为神圣和光荣。
劳动吧,不停地劳动!
劳动吧,为了更美好的将来!
这是杨骚给祖国的见面礼。
这首诗热情澎湃,真切感人。这可以看成是杨骚心迹的表白,“劳动吧,不停地劳动!劳动吧,为了更美好的将来!”杨骚回到祖国来,正是为了“劳动”。“他想在文艺界重整旗鼓,真正写出一些他所想写的东西来。”——他的老朋友巴人是了解他的,是的,他所能从事劳动的,就是手中的笔,这笔,以前,曾经是他倾诉苦闷的传声筒;以后,又是他为人民、为民族解放向黑暗势力抗争的武器;如今,在新中国,他要使它成为创造美好未来的劳动工具。
1952年9月25日,杨骚举家离开雅加达回国。11月7日到广州,结束了他长达十一年的南洋之旅。
(本文是摘选和整理自作者著《杨骚传》,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8。)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