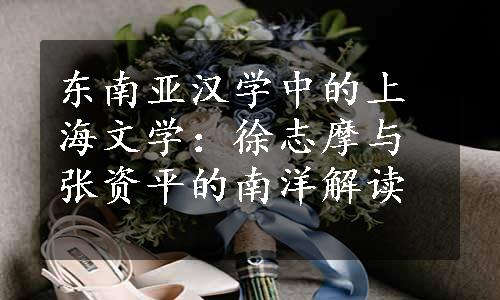
林春美
虽说早在公元7世纪就开始有中国人移居南洋的记录,而元明之时中国人更是已经广泛分布于南洋各地,(1)然而直至20世纪前半叶,“南洋”对于中国人而言,始终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概括性的指涉中国领土以南的群岛。这些地方在现代文学作品里偶尔被称之以其名,然而地名本身并不具任何相互区别的意义,也不足以在作家心里唤起任何鲜明独特的轮廓。对于作家而言,它们是一个集体,是中国以南零零碎碎的一片海域和陆地,是面目相近以致迷糊的热带群岛。
在航空尚未普遍取代水路的年代,南洋是中国作家西行抑或东归的必经之处。在20年代,因往返欧洲和中国大陆而途经南洋的中国作家为数不少。(2)《中国作家与南洋》一书的作者指出,“南洋”虽然也出现于这些过客的笔下,但是他们所提到的南洋,“只是浮光掠影,只是平面描写,缺乏广度与阔度”。(3)本文并不打算从这些浮光掠影里追索这些现代作家对南洋的再现(representation),而只是企图从这些作家凭着感性的第一印象所作的书写中,认识他们如何感知南洋。
本文以两位中国现代作家——徐志摩和张资平——的作品为例开展论述。徐志摩是浪漫潇洒的诗人,张资平是善于生产三角多角恋爱故事的通俗小说家。他们两人无论在取材倾向、写作风格、甚至人生道路方面,都没有可以相提并论之处。本文把他们并置而谈,主要是因为两人都曾有作品提及南洋,虽然写法迥异,但是有趣的是两人的南洋却可以互为补充说明。两个性质各异的作家,建构出的南洋形象却颇为雷同,这或许更能说明这种“南洋性”之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普遍性罢。
1928年年底,热带小岛新加坡被写进了浪漫诗人徐志摩的文章里。那一年,徐志摩为结婚近两年的太太陆小曼奢华的生活方式、吸大烟的恶习、捧戏子的热衷、特别是她与戏子翁瑞午之间的暧昧关系,而备受精神折磨。为了不使自己的创作生命被这种痛苦所消磨,也为了让陆小曼有冷静反思的空间,他于是决定远游。(4)当年六月中旬,他踏上豪华邮轮,开始了他为时近半年的环球之旅。他先东渡日本,然后横穿太平洋抵达美国,再穿越大西洋去到英国,最后访问印度。(5)照他的行程与该篇文章写作的日期——11月1—2日(6)——推测,新加坡应该是徐志摩从印度回返上海中途的歇脚处。
与其他中国作家一样,徐志摩马上也非常强烈的感受到了迥异于北方的、闷热而潮湿的热带气候。终日挥汗如雨的情况让多产的通俗小说家徐訏甚至失去写作的心情,但是,因雨后烦热而致的昏沉心绪,却让徐志摩写出了他向来比较少从事的文体:小说。也许昏沉的境况适宜虚构,更甚于抒情吧?单就小说的题目,已经足以看出作者的昏沉状态:《浓得化不开》(新加坡)。(7)——这种精神状态,可能也与他远游半年之后的疲惫不无关系。
11月的新加坡适逢雨季。《浓得化不开》就从南洋风雨草木等自然景观对于北方人林廉枫的感官所起的刺激作用说起。(8)像赤道上的大太阳会让温带地方来的人无法适应一样,赤道上的骤雨,在林廉枫的听觉与视觉上,都引发特别怪异的感觉。雨打芭蕉,听在他耳里,不是中国古典诗词中最常引起的“早也潇潇,晚也潇潇”的闲散情绪,而是“有铜盘的声音,怪”(页73);雨洒小草,看在他眼里,别有一股“蛮劲”,一种“情热”。雨露之恩在此地不是以中国传统的温柔方式出现,而是变异成一种蛮相,一种“外表凶狠”的“变相的爱”(页73)。
在这种蛮、凶狠、急劲儿、“狼虎似的”风雨的灌溉下成长的草木,都相应带着热、烈、浓的色调特点:“蕉心红得浓,绿草绿成油”(页74)。徐志摩的“南洋色彩”是大红大绿的。他说红心蕉“红得浓得好”,而且就是要“浓得化不开,树胶似的才有意思”(页73)。他认为新加坡的植物,就必须以那种热烈浓稠的色调,标明自己的地方性——如树胶之拥有亚热带特产的身份——才能确立自己的特殊意义。徐志摩路经新加坡的1928年,是正值新马文学界激情呼唤建立本地作品的南洋色彩的时期。我们无从得知徐志摩对新马文坛状况是否曾经留意,但是,从他对大红大绿的审美的接受,我们可以说:徐志摩应该是最早通过诗化的文字、感性的色彩肯定南洋的意义的中国作家。
徐志摩是个诗人。在他短短十年的创作生命中,以诗创作收获最为丰盛。(9)在《浓得化不开》里,他藉林廉枫的意识,透露自己的诗之泉源:“自然的变化,只要你有眼,随时随地都是绝妙的诗。”(页73)在与他所醉心的翡冷翠或康桥的自然环境大异其趣的新加坡,他也没有例外的看到了诗,可是,却是“一首淫诗”(页74)。——作为“万千小生物的胎宫”,有着“从来不知厌满的创化欲”的“自然”(页74),若被诠释为“淫”,那么任何国度的自然界都无法不淫;然而,由于“热带的自然更显得浓厚,更显得猖狂”,(页74)因此,在徐志摩看来,热带自然“更显得淫”。
中国人有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之说,认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与气质习性,与孕育他的自然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浓得化不开》也若隐若现的透露同样的观念。小说对芭蕉(的巨灵掌)、傻榈树(的毛大腿)、无花果树(的要饭腔)的描写,或许可以简单解释为修辞学上的拟人化手法;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我们却要怀疑在拟人化的字面修辞或比喻的运用底下,是否积累着在小说里尚未完全明朗化的意识形态。廉枫乘坐戴回子帽的马来人驾驶的厂车上街散心,沿街所见,是“野兽似的汽车”和“磕头虫似的人力车”——在“马来人”及其“回子帽”等充满“番邦”特征的氛围里,交通工具所标示的物质文明竟然都变形成前文明阶段的自然生命形态。而一路上的树木与行人,是“长人似的树,矮树似的人”。(页75)人与自然已被两厢混同了起来,两者变成可以互为对调的本体和喻体,对自然的体认与对人的体认不须有太过严谨的区别,因此上段提到的热带的自然的浓厚、猖狂,不免也可以改动成“热带的自然浓厚,热带的人猖狂”——正因如此,所以即使廉枫所到的一座湖亭边明明置有表征着文明的水位度量尺,可是在浓得化不开的热带气流里,“肉糜的气息”是足以使文明昏沉的,果然,廉枫在湖亭里撞见“糊成一饼”(页76)的一对正在亲热的男女。这是热带的自然的人化,或也可说是热带的人的自然化。徐志摩所感知的热带的人与热带的自然是也“糊成一饼”的,双方都可以从彼此身上照见自己、体现对方。
一般认为,自然是文明的前夕,文明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成果。然而,一旦文明变成了阻碍幸福的咒语,站在文明对立面的自然就会摇身一变,变成了幸福的乌托邦。南洋也是如此。
恋爱小说家张资平的小说里浮现过新加坡、马来亚、爪哇、婆罗洲、兰贡(即仰光)等东南亚诸多地域的名字,然而,如前所述,这些地方没有特别的意义,对作者而言,它们只是整体性的南洋群岛;(10)可是,不论这些南洋群岛如何“糊成一饼”的面目迷糊,它们总带着一个鲜明的标记:它们是他的小说人物的“异域”。
张资平小说里的男女情欲在中国社会境况中常常会引来道德义理的干涉。无法见容于社会礼法的男女于是梦想逃到另一个国度,一个“可以自由恋爱,可以逃避社会施加的压力,例如媒妁之言的婚姻以及不幸福的婚姻生活”的“异域”(11)。在几篇小说里,南洋就是这被点名的异域。
在长篇小说《苔莉》里,克欧爱上了表兄的第三个妾苔莉,他希冀可以全然占有苔莉,可是他也非常清楚自己和苔莉的乱伦关系一旦公开,则两人一定将为社会所斥责与唾弃。克欧和苔莉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到家乡,二是逃到异域。回乡,对苔莉来说,就是回到丈夫身边,心甘情愿的当他的三姨太太(她是摩登的女学生,并不甘心当妾);对克欧来说,就是割舍自己对苔莉(肉体)的迷恋,明媒正娶一个门当户对的黄花闺女。这两者都意味着向传统社会与伦常义理靠拢。逃到异域,则他们不须要再扮演社会加诸他们的角色,而可以完全忠实于自己的情欲。最后,他们选择逃到另一个国度,一个用彭小妍的话来说是“没有‘文明’的法律来羞辱对情欲的追求”的国度。(12)这个“国度”,是南洋群岛。在私奔南洋前夕,克欧进行了一场毁弃文明的仪式,他一面把象征文明的书、手稿、大学毕业证书一一烧毁,一面责骂这些物件所代表的社会规范。(13)“文明”在这里是扭曲人类自然情欲需求的礼仪之邦,而南洋,因为在作家的想象中可以一任情欲自然抒泄,于是被暗示为没有文明法律的化外之地。
在《性的屈服者》里,类似的人物关系与解决方法重复出现。吉轩和馨儿原本是一对情侣,可是在吉轩到外地求学期间,馨儿被吉轩的哥哥诱奸,当吉轩学成还乡,馨儿的身份已是他的嫂嫂。吉轩对嫂嫂馨儿存有性幻想,馨儿对他也未尝无意。然而由于对乱伦的恐惧,以及对馨儿的一种又爱又恨的复杂情感,吉轩一直克制着自己的情欲。后来,吉轩的哥哥去了婆罗洲做生意。遥远神秘的婆罗洲之旅成了两人关系发展的转机。在吉轩护送馨儿到南洋寻夫的途中,之前并没有任何淫荡征兆的馨儿竟莫名其妙的做出大胆的挑逗,她“只穿一件淡红色的贴肉衬衣懒懒地躺在一张疏化椅上”,并且还“像才喂了乳,淡红色的乳嘴和凝脂般的乳房尚微微的露出来”。(14)她不仅对吉轩一点也不避忌,而且还一心要使吉轩“犯罪”,甚至为要阻止吉轩外出而把钥匙放进自己的贴肉的衣袋里,挑战吉轩来取。而吉轩,虽然也感受到伦理道德的压力,但是最后情欲还是战胜了伦理。叔嫂之大防,终于在奔往南洋——义理所不及之异域——的途中被消解了。
在另一篇长篇小说《最后的幸福》中,美瑛因为无法从丈夫身上获得心理和生理方面的满足,于是把她的“恋爱之力”转引到妹夫黄广勋身上。她和广勋的暧昧关系后来被丈夫的前妻之子阿和知晓,并以此来威胁她。阿和的威胁让美瑛不由想起在乡间,感情出轨的妇女所遭受的酷刑:妇女被捆缚在柱子上,被丈夫的族人用鞭子抽打、用锥子戳刺。这所谓的“宗族的制裁”让她不寒而栗,于是不得不向阿和屈服。后来,美瑛在阿和的陪同下到兰贡寻找也是去做生意的丈夫。途中,她重遇旧情人松卿。当船在新加坡靠岸之后,美瑛托辞要休息几天,故意拖延到兰贡的行程。她在新加坡终于有机会和松卿单独出游,两人乘火车北上马来亚散心,美瑛在海水浴场看到赤条条搂抱着跳舞的土人,大受蛊惑,于是在当晚与松卿发生了肉体关系。其实,美瑛与松卿的关系跟她与广勋的关系一样,一旦被揭发也是要面对“宗族的制裁”的。在美瑛南洋寻夫的路途中,作为“宗族”的代言人的阿和依然存在,然而,异域的场景与氛围,却似乎已足以瓦解“宗族的制裁”所构成的威胁。
从上述几篇小说看来,道德伦理是文明社会订下的规范,情欲则是一个人自然而原始的需求。当情欲违逆了义理,社会就会引用文明法规对之加以制裁。那些出轨的男女只有逃到南洋才能为他们的情欲找到一个安全的出口,因为南洋是没有轨道的,因此也就没有所谓出轨不出轨的问题。换言之,南洋处于义理与律法之外,它是自然之地,然而也显而易见是化外之邦。(15)
对从文明古国来的人而言,他们在南洋看不到他们所熟悉的文明思想轨道。这一方面说明南洋是相对于文明的“自然”,是原始情欲的保护区;另一方面则说明南洋是相对于文明的“不文明”,它不存在由文明社会演化出来的礼法规范。文明轨道之缺席虽然有时也是他们所庆幸的,但是庆幸之余他们又总觉得它具有某种不透明性,以致他们无法理性的诠释它。因此在这个层面上,南洋也是神秘的。神秘,借西蒙波娃的解释是:“它并非是指一种完全沉默的、黑暗的和不存在的状态,而是在暗示一种断断续续的存在,这种存在使它本身变得朦胧不清。”(16)朦胧不清,是“糊成一饼”的另一个说法,其实正是徐志摩和张资平的南洋印象。波娃在论述所谓的女性神话时曾经非常精彩地指出,男人因为难以识破女性的特殊体验,于是她被认为在本质上是神秘的。女性“神秘”的神话带给男人莫大的兴奋和快感,因为感觉和一个活生生的神秘人物在一起,总比和人的真实关系更有诱惑力。而这种“神秘”,“直接隐含于绝对他者的神话之中”,并且只会存在于被看成次要的他者(Other)身上。(17)从徐志摩和张资平的小说里,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拥有优厚的历史与文明家底的现代作家,正是从一个非常“男性”的角度来体验南洋的。
在《浓得化不开》里,徐志摩就以非常诗意的文字将南洋“女性化”。小说主人公廉枫回到旅店之后,他在湖亭所见的具象化的欲望诱惑,再加上雨后的烦热所设下的“昏沉的圈套”(页77),致使他的理性一时间失守,他对欲望的幻想顿时得以释放。欲望的暗流在还没有定型成一个黑女人的线条和轮廓之前,先以一股波动的彩流的姿态向他飞骠而来,他在凌乱中感觉到的尽是热带特有的浓烈艳丽的色调:火焰似的大红、墨晶似的乌黑、金漾漾的流蜜、最后是饱和着奶油的朱古律……而最终在他脑海里萦回不去的感觉不单是色,更是那股浓得化不开的“朱古律皮肉的色香味”(页79)。这种热带棕色人种的肤色(以及体味?)制造了一种异国情调,轻易的让他联想及西方艺术中相似的格调,孟内画的黑人和最早画朱古律肉色的高根于是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把这相互“混迹”的人与自然置入艺术的殿堂并无法使徐志摩的新加坡“高贵”起来,相反的,他对高根的评价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他的眼中映照着的这个地方的“蛮相”。他觉得,高根的作品之所以能“开辟文艺的新感觉”,是因为他“到半开化,全野蛮的风土间去发见文化的本真”(页79)。像孟内的奥林比亚那样在鬓上插一朵花的朱古律姑娘虽然让他惊艳不已,但惊艳之中不乏“半开化,全野蛮”所带来的“打猎”般的刺激——而徐志摩在那女子出现之前后,都很“巧”的提到了猎户星座——不管是狩猎,还是被猎,在化外之地,都必然会更加刺激。
在旅店楼下惊鸿一瞥的朱古律姑娘,很快的在廉枫昏沉的睡梦边缘变成了“妖”“艳”的性幻象,带着她浓重的色浓重的香接近他、挑逗他;廉枫在慌张中冒出一句“救驾”。这“救驾”与他之前断断续续哼着的京调《戏凤》有关,在行文上算是“前呼后应”,而且这京调的穿插在小说的结构上当然也别有趣味;但是,要认识徐志摩所感知的南洋,我们却无法不去挖掘这戏文底下的意识形态。李凤姐居住的梅龙镇虽然被她自誉为守礼最严谨的地方,但是相对于正德皇帝来自的京城,也不过是个乡野小镇;而李凤姐,再怎么美丽动人,也只是上不了殿堂的村姑罢了(李凤姐最终也是“没命”进宫的)。在朱古律姑娘的幻象和李凤姐的形象相互重叠的混乱中,林廉枫(徐志摩?)变成了微服出巡梅龙镇的“孤王”,而南洋,则“拟人化”成得君王雨露之恩的李凤姐。可以这么说:徐志摩是藉虚构的形式,通过主人公林廉枫的感官,来叙述他本身对南洋这个女性化了的他者的感受。徐志摩出身文化源远的中央大国,新加坡是刚“开埠”不久的赤道边上的弹丸小岛;徐志摩是康桥培育出来的西化绅士,新加坡当时则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不论是站在中国抑或西方的本位上,新加坡对于徐志摩都只是一个边缘地带,他在这里很容易就生发一种理所当然的优越感。优越感阻止他去理解,不理解增添神秘感,神秘感最后催发了幻想。
其实,廉枫这个角色还出现在徐志摩其他两篇小说里——一篇就题目看来明显是本篇的续篇,题为《浓得化不开之二》(香港);另一篇题为《死城》(北京的一晚)。(18)若我们把这三篇分别以三个不同的地方为背景的小说放在一起读,则徐志摩感知中的新加坡将会在其他两地的参照下更容易被理解。
徐志摩对香港最初的印象是他一再重复的“富庶,真富庶”(页83,84)。虽然在他到山上去玩的途中也碰到一个引起他诸多幻想的女子,但这个女子与之前浓艳得颇具攻击性的朱古律姑娘大异其趣。徐志摩把她比喻作罗马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薇纳斯(即维纳斯)——虽然这又是关于女性的一个神话,但这里主要突出的是她的慑人的美丽。徐志摩把她的腰身比喻为山的腰身,进而从她“浓浓的折叠着,融融的松散着”(页85)的腰身摆动看到了“动在静中,静在动中”的宇宙运作。女体的诱惑很快的就被“净化”,女性的肉身刹那之间完全变化为宇宙的肉身。廉枫感觉到“这当前的景象幻化成一个神灵的微笑,一折完美的歌调,一朵宇宙的琼花”,一切山光水色,“形成了一种不可比况的空灵,一种不可比况的节奏,一种不可比况的谐和”(页87)。他体验到一种情感上的升华,顷刻间,香港在他的凭眺下变成了蓬莱仙岛。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他“也回复了各自的辨认的感觉”——这种“辨认的感觉”在新加坡迷糊昏沉的精神状态中自然是无法“回复”的——觉得眼前的景色虽然与适才的灵异不同,但是也别有一种美丽。他用了“绿玉”“紫晶”“琥珀”“翡翠”等高贵的装饰物来形容这幅“天然图画的色彩”(页88),在意趣上已大不同于用以比喻新加坡的“火焰”“流蜜”“朱古律”。
至于北京,徐志摩本来打算把它写成一座“死城”,不仅前门城楼看来像一个骷髅,而且主要的故事也是发生在一座墓园里。小说中的荒城、凉月、银霜、鬼火虽然酝酿了一种萧索诡异的气氛,可是,廉枫却在一个外国女子的坟墓前感到了“一种超凡的宁静,一种解放,一种莹彻的自由”(页98);这个早夭的女子在他心里唤起的竟是“爱的纯粹的精灵”,而他所爱的人的死,也让他初次会悟到了“生”(页100)。不论守墓老人诉说的是如何凄惨的故事,它终究是一种现实,而非无从理解的一团神秘。而且,因为曾经爱的洗礼,所以尽管“世界是黑暗的”,然而廉枫却“永久存储着不死的灵光”(同上)。
萨义德(Edward Said)在他的巨著《东方主义》中指出,依据西方的观点看过去,“东方暗喻着危险,西方理性总是被东方的异国情调所瓦解;而东方的神秘吸引力,更代表着和西方正常相左的价值”。(19)若我们把萨义德所说的西方换成中国,而东方换成南洋,同样的意思还是可以成立,因为对于这个大国的人来说,南洋何尝不是充满神秘异国情调的、足以瓦解他们的理性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在香港,大自然的神奇可以平伏廉枫的幻想;在北京,对生与死的体悟可以让他滋生爱的力量。他在这两地经验到一定程度的感情的净化或者升华,而这种理性的体验无法在南洋获得。到了新加坡,大红大绿再加上朱古律色的皮肉所构成的南洋色彩,调制出一种异国情调,只会激发他蠢蠢浮动的欲望。
西方通过想象东方化了东方,同样的,中国也通过想象南洋化了南洋。所以,如若上述把“西方—东方”置换成“中国—南洋”的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有论者提出的“中国是西方的‘他者’、女性化的空间”(20)的论点,也就可以被置换成“南洋是中国的‘他者’、女性化的空间”。这一点完全可在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欲望朱古律中得到印证,他所叙述的朱古律姑娘形象,其实也就是他的南洋想象。
张资平没有把南洋具体化为一个女体,但这并不是说他不是站在男性的位置对南洋进行叙述,而是作为一个通俗小说家的张资平,更注重的是他的作品的可读性。他不像徐志摩那样花费心思去琢磨文字的诗意,他单刀直入,直接就把南洋“性化”。性化,其实也是女性化,因为女性在男性面前,主要是作为性存在的。(21)《最后的幸福》里的美瑛渴望得到情欲的自由,然而当面对真正“自由”——可以随心所欲赤条条相拥起舞——的土人(应该也是朱古律色的吧?)时,她又不免把这种自由行为贬斥为“真野蛮的习惯”(页670)。这些土人的“野蛮”行为与她所内化的社会道德价值相左,然而却具有瓦解“宗族的制裁”所标示的文明律法的力量。土人之舞的强烈蛊惑性,正是美瑛与松卿野合的直接激素。在这个也可以解读成“中国的理性为南洋的异国情调所瓦解”的创作意识下,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作家对南洋的刻板印象。《最后的幸福》初版于1926年,然而里面所叙述的马来亚形象却与二十年代的当地情况相去甚远。我们或许可以从硬体与软体两方面的建设来指出张资平的谬误。十九世纪以来,英国殖民者为了搜刮马来亚的财富,不得不先发展当地的基本设施。至二十世纪初年,马来半岛的铁道系统一方面已连接几乎所有锡矿产区与马六甲海峡沿岸的重要码头,另一方面亦延伸至内陆地区,连接橡胶种植区与城市。(22)基本设施的设立带动经济的成长,继而逐渐改善当地社会的生活品质。在文化建设方面,当时的马来亚也并非一片空白。马来世界的革新运动(Gerakan Modenisasi)在十九世纪末已由一群从埃及学成归国的青年掀起波澜。(23)1906年,他们出版一本改革杂志al-Imam,企图通过这本意为“领导者”的刊物来唤醒族人。该群革命者被称为“青年界”(Kaum Muda),他们呼吁族人积极革除陈腐的传统习俗,并强调应该吸收西方所有不与回教教义相左的正面价值。(24)因此,尽管他们的改革运动是从宗教出发,在1906年前后当他们开始兴办新式学堂(madrasah)时,所设计的课程却是跨越宗教的门槛,涵盖了包括阿拉伯语、英语、科学、数学及地理等多元的现代知识。(25)在政治方面,他们与向来臣服于皇权的传统族人不同,他们更推崇西方的那一套民主制度。(26)马来世界的这一群改革青年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五四运动时期那些文化/文学革命者,双方都意识到铁屋子的存在与呐喊的必要,双方都慧眼结识了赛先生与德先生。前者被称为“青年界”,与后者所办的刊物《新青年》在名字上有不谋而合的玄妙。《新青年》标志着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新文化运动的肇始,“青年界”的出现也有同样的意义。而可能令许多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群朱古律皮肉的青年第一本改革刊物al-Imam的初版,在时间上,竟比陈独秀等人的《新青年》还早了近乎十年。(27)既然当时的马来亚在基本设施与文化上已有了这般的建设,那么在名胜地也可以轻易看到土人的“野蛮习惯”的叙述就显得过分夸张。我们不排除当时尚有“裸体的土人”存在的可能,但是那绝不可能出现在张资平所说的乘火车可以到达的、商业相当发达的有名的锡矿产区。
徐志摩曾经在他的《自剖》里藉一个朋友的口说出他之所以从事文学创作的原因:“正为是你生活不得平衡,正为你有欲望不得满足,你的压在内里的Libido就形成一种升华的现象,结果你就藉文学来发泄你生理上的郁结……”(28)我们可以藉这段话来理解他笔下的新加坡。香港是一个富庶的地方,况且它在地理位置和历史关系上和中国密切,于是对徐志摩而言不存在神秘和难理解的问题。北京是古都,又是他曾经求学和后来任教之处,是他的记忆之城,也是与他的现实生活攸关的真实世界。他在这两个地方必须符合现实原则(principle of reality),他必须遵守理性世界里清醒的自我的行为准则(虽然私底下的浪漫念头还是可以偷偷“作怪”的)。但是,在偏远而陌生的新加坡,在理性的“辨认的感觉”被闷热的气候和异国的情调弄得昏昏沉沉的地方,他的不得满足的欲望(不美满的婚姻的郁结)就得以藉对这南蛮之地的描写发泄出来。他在《死城》里曾说“不到一个适当的境地你就不敢拿你自己尽量的往外放,你不敢面对你自己;不敢自剖”,把这里的所谓“自剖”与他的同名文章参照,就可知新加坡是他可以“藉文学来发泄生理上的郁结”的“适当的境地”,而朱古律姑娘,是他的libido的具体化与形象化。同样的,在张资平的小说里,南洋是libido可以避开检禁(censorship)而抒泄出来的地方。在这样的语境中,南洋,就是人格结构中最不可知、最不可捉摸的一个层面。如此一来,徐志摩和张资平感性认知中的南洋,倒是与当时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副刊,如《浑沌》《洪荒》等被如此命名的涵义,发生一定程度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这个层面上,这两个南洋过客与早期中国南来作家对于新马的感知,是有相似性的。
[1]徐志摩:《年轮》,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
[2]黄傲云:《中国作家与南洋》,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1972年。
[3]邵华彊编:《徐志摩研究资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4]张资平:《张资平小说选》,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
[5]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年。
[6]刘炎生:《徐志摩评传》,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
[7]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8]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www.zuozong.com)
[9]乐齐编:《精选徐志摩》,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
[10]萨义德、王志弘等译:《东方主义》,台北:立绪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1999年。
[11]波娃西蒙、陶铁柱译:《第二性》,台北:猫头鹰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
[12]Fuzian Shaffie dan Ruslan Zainuddin,Sejarah Malaysia,Selangor:Penerbit Fajar Bakti Sdn. Bhd.,2000。
[13]彭小妍:《海上说情欲:从张资平到刘吶鸥》,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年。
(本文曾发表在《柳州师专学报》第19卷第4期,总第58期,2004年12月。)
(1) 详见巫乐华《南洋华侨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第4—6页。
(2) 黄傲云《中国作家与南洋》(香港:科华图书出版公司,1972),第12页。
(3) 同上。
(4) 详阅刘炎生《徐志摩评传》(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第234—245页。
(5) 徐志摩这次旅游的航程及其在旅程中所写到的人与物,详同上书。
(6) 见邵华彊编《徐志摩研究资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第642页。
(7) 此篇小说收集在徐志摩唯一的一本小说集《年轮》(上海:中华书局,1930)里。本文所引有关徐志摩小说的所有文字,皆出自此书,不另注。
(8) 这里的“北方”仅相对于“南洋”而言,并非特指中国地理历史中约定俗成的南北之分中的北方。然而,就主人公林廉枫不时哼着京调的情形看来,他虽然未必来自中国北方,但却是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于北方的主流文化的。
(9) 他共得诗近两百首,出版过四本诗集。见《素描徐志摩》,收录于乐齐编《精选徐志摩》(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
(10) 在张资平的《苔莉》里,克欧要与苔莉私奔到“南洋群岛”,而不是到南洋的其中一个地方。对于张资平而言,安排他的小说人物私奔到婆罗洲与私奔到新加坡或爪哇岛,似乎没有任何分别。作家对南洋模糊的总体性感知,由此可见一般。
(11) 彭小妍《海上说情欲:从张资平到刘吶鸥》(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筹备处,2001),第35页。
(12) 同上,第39页。
(13) 同上,第40页。
(14) 张资平《性的屈服者》,见《张资平小说选》(广东:花城出版社,1994),第144页。本文所引有关张资平小说的所有文字,皆出自此书,不另注。
(15) 张爱玲《倾城之恋》里有一个情节,可以作为此处的注脚,或一个额外的论据:南洋华侨范柳原看上了名门小姐白流苏,“他爱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而且因为“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他担当不起这诱奸的罪名”。所以他跟她说想把她带到马来亚去。马来亚让他想起森林,到马来亚意味着“到原始人的森林去”,他认为唯有这样,白流苏才会“自然”一点。其实那时马来亚与上海和香港一样,都是英帝国的殖民地,然而对于多数中国现代作家而言,上海和香港虽然有传统礼教束缚,但终究还是文明古国;马来亚的对传统礼教“免疫”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它终究是化外之邦。
(16) 波娃西蒙《第二性》,陶铁柱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第261页。
(17) 详阅同上书,第十一章。
(18) 《死城》作于1927年12月,发表于1929年1月;《浓得化不开之二》不知作于何时,发表于1929年3月。见邵华彊编《徐志摩研究资料》,第643,646页。虽然在写作时间上《死城》要比两篇《浓得化不开》都来得早,但是在出版成单行本时却被排在此二篇之后,可见作者有意为他的人物安排的行程是新加坡—香港—北京。这与他本身环球远游后的归程是相似的。
(19) 萨义德《东方主义》,王志弘等译(台北:立绪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1999),第79—80页。
(20) 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记》(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5),第69页。
(21) 波娃西蒙《第二性》,第3页。
(22) Fuzian Shaffie dan Ruslan Zainuddin,Sejarah Malaysia(Selangor:Penerbit Fajar Bakti Sdn. Bhd.,2000),p.145.
(23) Ibid,p.115.
(24) Ibid,p.336—337.
(25) Ibid,p.115—116.
(26) Ibid,p.366.
(27) 《新青年》1915年创刊,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始改名《新青年》。见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5页。
(28) 见乐齐编《精选徐志摩》,第287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