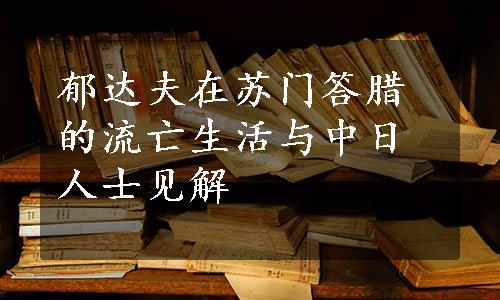
王润华
自从郁达夫(1896—1945)在1945年8月在苏门答腊失踪以后,中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国的学人,历尽千辛万苦,设法寻找出他在流亡时期的实际生活情况与失踪之原因。最早关于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及其死亡的报告,是在他失踪一年后才出现。作者胡愈之,是中国一位文化界名人,他和郁达夫同时从新加坡逃离到苏门答腊,而且流亡期间,多数时间还生活在一起,胡愈之于1946年8月回返新加坡担任《南侨日报》主笔,这时候他才写《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1),非常详细的叙述郁达夫从新加坡逃到苏岛避难,怎样在伪装华侨商人之下,经营酒厂生意,再度娶妻成家等事情,由于胡愈之和郁达夫在苏岛来往密切,长时间因工作之关系,天天生活在一起,因此这篇《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不但使我们看见他的日常私生活,同时也使我们了解他当时的思想感情。自从这篇报告发表后,这问题广泛地引起注意。接着很多与郁达夫在苏岛一起逃难的朋友,也纷纷将自己所知道的写出来。这些出自中国文人的报告,虽然其中有误解捏造之处,或因民族感情和痛恨日本人而有所歪曲和袒蔽,大体上都是翔实可靠的,在1969年之前,是构成郁达夫在苏门答腊之传记资料之主干。
由于郁达夫是在日本侵占新加坡之前逃到当时的荷属苏门答腊,他在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编辑之极力提倡文学运动,所以当地华人很尊敬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发表了很多关于郁达夫在新、马及苏岛的生活。新马文艺界对研究郁达夫在南洋的最大贡献,是在资料的正路上。文中资料,即使在中国,也没有人去将它搜集和整理出版,但是新马文艺界却做了,而且做得很好,使目前研究郁达夫在1939年以后的生活与著作的人,感到很方便。(2)
日本学者虽然在日本侵略战争结束后,就开始注意这问题,但一直没有什么重大的贡献。1969年日本铃木正夫发表了一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原住在苏门答腊的日本人的证言》(3),终于才有了突破性的发现。因此又使我们对苏门答腊时期的郁达夫生活与思想之了解加深一层,向前推展了一步。铃木正夫通过通信、电话与面谈的方式,录取了一百多位曾与郁达夫在苏岛有过来往的日本人之供证,其中十个当时日本驻苏岛宪兵或商人之报告最为重要,因为他们与郁达夫在苏岛有相当频繁之来往,而且产生很亲密之有情,他们坦白的将亲眼看到和知道的情形讲出来,因此,揭露了很多郁达夫在流亡时还未被人知道的日常及感情生活。有些方面的实事,譬如郁达夫和日本军人与商人不平常的来往和交情,在中国人的报告中就很少透露,这可能因为怕有损中国人重视所谓“人格”而故意蒙蔽。铃木正夫这份调查的报告,最大的贡献,是找到证实郁达夫被日本宪兵谋害的证人。宪兵惧怕郁达夫在战后成为有力的战犯证人而将他杀害的控诉,虽然早在1946年由胡愈之提出,但由于缺少事实根据,一直被许多特别是中国以外的学者所不敢完全肯定的接受。铃木正夫的结论,使“控诉”或“猜测”成为铁一般的实事。
文本的目的,是要将目前各国学者所发掘出来,有关郁达夫在苏门答腊流亡生活的实事,一点一滴,一片一片的缀串起来,构成一幅比较完整的记录。这样也许我们更明白郁达夫最后的日子是怎样度过的,他当时想着的是些什么。
1939年的时候,很多日本的动向已明显,他们决心要侵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9月3日在欧洲爆发时,日军在德国纳粹政府控制下的法国同意之下,侵占了印度支那半岛南部。1941年12月7日,日本军机偷袭美国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同一天,日军在马来亚东岸的吉兰丹州海滩登陆,而且猛烈轰炸马来亚北部的飞机场。马来亚没有充分备战,当时的英军主要是防御性质,遇到日本突然的猛烈攻势,连迎战也没有能力,一下子就慌乱起来。
1941年12月8日,英国两首战舰——主力舰威尔斯太子号与巡洋舰击退号,在六十余架日机猛烈的轰炸下,沉没在彭亨关丹附近的南中国海面。英国遭到惨痛的损失后,东南亚的制海权也跟着丧失,因此马新的沦陷也在旦夕,因此日军现在能向四处进攻了。
郁达夫早在1939年前来新加坡,受聘于《星洲日报》,担任副刊编辑。由于他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写小说成名的作家,所以他在新马华侨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力。他南来之前,在中国已经公开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之发展与侵略,而且积极参加反日活动。(4)
运用他个人的影响力,他替反日的华侨筹赈会的募款尽了很多功劳。英国新闻处委任他为《华侨周报》编辑,专门推动抗日宣传。他除了编辑工作,还负责收听日方的宣传广播,而且选择其中重要部分,翻译成英文。(5)在其他担任过抗日活动的职位中,比较重要的是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及文化界战时干部训练班班主任。(6)
当日军从北再往南长驱直下时,英国殖民地政府呼吁华侨同心协力阻挡日军攻占新加坡。英国当局便开始与华侨领袖商讨联合抗日事宜,经过慎重考虑,当时商界巨人陈嘉庚接受英政府的提议。12月底,在陈嘉庚的领导下,新加坡华侨抗敌委员会(Chinese Mobilization Committe),不但得到新加坡总督珊顿·汤姆士(Shenton Thomas)爵士的支持,而且还得到当地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协助。郁达夫被委任为执行委员,同时负责文艺组工作。此外,他也是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7)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新加坡就开始准备军事防御工作,可是当时的计策是防止敌人从南方海马进攻。现在从后面马来亚打来,因此前功尽废。防御工作化整为零。另一方面,虽然华侨愿意与英军携手合作,共同抵抗侵略者,而且英国政府提供军事训练,但是这种准备在最后一分钟前才产生,一切都太晚了。后来由于理解到顽强抵抗不会成功,更何况英军并没有死战到底的决心,当总督拒绝在危急时机撤退抗日华侨到安全地区时,陈嘉庚便于1942年正月三日撤退至苏门答腊。然后从苏门答腊再前往爪哇。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陈嘉庚都住在爪哇。(8)
在陈嘉庚从新加坡疏散到苏岛的当天,华侨总动委员会召开一项紧急会议商讨应对局势。会议上一致同意陈嘉庚的看法,抵抗到底会造成无谓的大牺牲,英军不会战斗到底。新加坡沦陷在日军手中以后,抗日分子一定会残遭杀害。可是,他们并没有立刻逃离新加坡。1942年正月二十七日,英军开始将军队撤退到新加坡,30日晚已将马来半岛完全放弃。新加坡在马来亚南端,只有一水之隔,双方有一道半里长的长堤连接着。因此当日军占领柔佛,整个新加坡便挨受日军大炮的轰击。眼看着新加坡朝不保夕,郁达夫和其他十八位文化界人士在2月4日突破日军的封锁,乘船冒着炮火撤退到荷属苏门答腊。十二天后,新加坡终于失守,英军投降,日军占领了整个新加坡。(9)
同船逃往苏岛的十九人中,很多是来自中国的作家,而且极多是新加坡报人。他们之中,郁达夫、王任叔(巴人)、胡愈之、杨骚,都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后面两人目前还住在中国大陆。
根据胡愈之和王任叔的回忆,他们一船人逃离新加坡后,便航向苏岛。黄昏的时候,他们行到加里曼,一个距离新加坡最近的荷属小岛。由于他们之中多数没有签证,因此在那里被迫停留了两天。后来他们分成几队人马,分头乘船前进,于2月6日傍晚抵达斯拉班让(Slatpandjang),也是一个小岛。郁达夫一行一共七人,其中包括王任叔和胡愈之。2月9日,郁达夫、胡愈之及其他被荷兰官员遣送到孟加丽岛(Bengalis Island),王任叔留在斯拉班让岛上,住了有六个月之久才离开。
郁达夫前往孟加丽岛只是短期性的,因为他的最终目的是回中国去。他原来的计划是这样的:希望荷兰政府发给他签证前往爪哇,然后从那里乘船取道印度回中国去。可是荷兰殖民地政府拒绝了他的申请。绝望以后,他只好在恐慌中彷徨度日。马六甲海峡在窗外怒吼,收音机传来新加坡日愈恶化的消息。2月15日当他和同伴们获知新加坡被日军占领,个个吓得呆住了,苏岛附近荷兰军马上撤退到爪哇。郁达夫和他的逃难朋友现在可自由行动了,可是已经没有船只航行,结果还是无路可走。后来认识一个热心的华侨名叫陈仲培,他原来是一个从孟加丽岛到巴东岛的渡轮公司的老板。他便好心的派一辆小船把郁达夫及其同伴送到离孟加丽岛不远的巴东岛(Padang Island)的巴东村,这是2月16日的事。(10)
郁达夫他们抵达巴东村后,受到陈仲培家庭热情的招待和帮忙。他们在陈家附近租了一间屋子,便暂时安定的住下来。巴东村是一个偏僻荒凉的地方,村民主要是印尼人,全村中只有寥寥数家华人。郁达夫前后在那里呆了一个半月。他发奋学习印尼文,同时也做了一些诗。他的遗作《乱离杂诗》共有十一首,多数是这时候作品(11)。其中第一至第九首抄录于下:
(一)
又见名城作战场,势危累卵溃南疆;
空梁王谢迷飞燕,海市楼台咒夕阳。
纵欲穷荒求玉杵,可能苦渴得琼浆?
石濠村与长生殿,一例钗分惹恨长。
(二)
望断天南尺素诗,巴城消息近何如?
乱离鱼雁双藏影,道阻河梁再卜居。
镇日临流怀祖荻,中宵舞剑学专诸?
移期舸载夷光去,鬓影烟波共一庐。
(三)
夜雨江村草木欣,端居无事又思君;
似闻岛上烽烟急,只恐城门玉石焚。
誓记钗环当日语,香余绣被隔年熏;
蓬山咫尺南溟路,哀乐都因一水分。
(四)
谣诼纷纭语迭新,南荒末劫事疑真;
从知邦上终儿戏,坐使咸阳失要津。
月正圆时伤破镜,雨淋铃夜忆归秦;
兼旬别似三秋隔,频掷金钱卜远人。
(五)
久客愁看燕燕飞,呢喃语软泄春机;
明知世乱天难问,终觉离多会渐稀。
简札浮沉殷羡使,泪痕班驭谢庄衣;
解忧纵有兰陵酒,浅醉何由梦洛妃?
(六)
却喜长空播玉音,灵犀一点此传心;
落地月明思故国,穷途裘敝感黄金;
茫茫大难愁来日,剩把微情付苦吟。
(七)
犹记高楼诀别词,叮咛别后少相思;
酒能损肺休多饮,事决临机莫过迟,
漫学东方耽戏虐,抒呼南八是男儿;
此情可待成追忆,愁绝萧郎鬓渐丝。
(八)
多谢陈蕃扫榻迎,欲留无计又西征;
偶攀红豆来南国,为访云英上玉京。
细雨蒲帆游子泪,春风杨柳故国情;
河山西戎重光日,约取金门海上盟。
(九)
飘零书剑下巴东,未必蓬山有路通;
乱世桃源非乐土,灾荒草泽尽英雄。
牵情儿女风前烛,草檄书生孟初功;
便欲扬帆从此去,长天渺渺一征鸿。
根据胡愈之的解释,前面七首是为一个爱慕的女子而作。郁达夫在新加坡与王映霞离婚后,才认识她的。她是盟军电台的广播员,后来在新加坡沦陷之前,随着盟军撤退到爪哇的巴达维亚(椰卡达)。据说郁达夫在巴东村的时候,他常常走路到附近的小镇上去聆听她从爪哇传来的广播。《乱离杂诗》第六首《却喜长空播玉音,灵犀一点此传心》据说是指他每周至少有三天上街去听她的声音的单思之苦。第八首及第九首是向陈仲培惜别而作。陈是福建金门人,所以有“约取金门海上盟”句。(12)
在彭鹤岭
在巴东村过了一个半月隔离的生活,郁达夫又开始坐立不安起来。爪哇的荷兰殖民地政府在3月9日还未开战,就向日本投降了。于是苏门答腊及附近岛屿都落入日军手中。郁达夫和他的朋友又要动脑筋去寻找一个更安全的藏身之所。他们分散成两批,分头逃命去。郁达夫和王纪元在一块,他们找到一个海边小镇叫彭鹤岭,离开巴东村大约有十英里路程。得到一位当地华侨商人寇文成的帮助,他们开了一个小摊子卖杂货。郁达夫改名换姓,叫作赵德清,王纪元叫作汪国材。听说他们生活很苦,坐在街边卖东西,简直变成乞丐了。(13)
一个月以后,大概在4月中旬,郁达夫知道他们再不能藏身在那小市镇上。自从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变成昭南岛后,许多不愿与日军合作的人,只要有办法,就纷纷逃出新加坡,如潮一般涌到附近之小岛。因此彭鹤岭这穷乡僻壤也引起日本密探之注意。他们经常听到别人传说,从新加坡来的日本侦探和汉奸,不断逮捕新加坡反日知识分子,并遣送回新加坡,然后加以严刑拷问,很多甚至被处死。
日本密探捉人的风声很紧,郁达夫终于又决心往他处逃亡。他想逃到苏门答腊岛内部去躲藏,因为那里没有认识他的人。当他在苏门答腊岛的东部登陆后,即沿着士叻河(Sungei Siak)往内地走。开始有王纪元陪他走,后来王纪元在路上病倒,只好在末旦(Utan),途中一个小镇住下来治病,郁达夫和一个陌生人改乘舢板前进。到了北干峇鲁(Pekan Baru),他乘巴士车到巴耶公务(Pajakumboh),大约离开北干峇鲁有一百五十公里。郁达夫在《乱离杂诗》第十一首中,记述这一段劳苦的行程:
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
地名末旦埋纵易,楫指中流转道难。
天意似将颁大任,微驱何厌忍饥寒?
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此前贤路已宽。
郁达夫大约在1942年5月初抵达巴耶公务——一个位于苏门答腊中部的小市镇,当时的人口约一万人。可是并不如他当初所想象的能够隐姓埋名、相安无事的过日子。他的出现,马上引起当地印尼华侨的怀疑,他们以为他是日军方派去的耳目。虽然他身上带了好几封介绍书,当地侨领由于对他有所怀疑,而拒绝帮忙。
原来当地华侨对郁达夫的身份的怀疑,是由一件意外事件所引起的误会。从北干峇鲁巴士车前往巴耶公务途中,车子被一辆日本军车叫停,搭客不知道日军的目的只是询问去北干峇鲁的路线,他们都惊慌的下车,往树林逃命。郁达夫没下车,并以流利的日语告诉他们到北干峇鲁之方向。一个日本军官离开时,还向他敬礼。郁达夫来到这个有两千华侨的市镇,暂时在一间叫华侨旅社的旅店住宿。他在旅店的记录簿上签上赵廉两字。他留了胡须,样子像日本人,而又有人认出在路上与日本军官谈话的就是他,因此郁达夫是日本侦探的谣言马上传遍了巴耶公务。(14)
郁达夫不但化名赵廉,胡愈之说,他同时撒谎说他生于日本东京,父亲经营古董店,因此他是在东京受教育。根据铃木正夫的访谈报告,有两位与郁达夫有很好交情的日本人也这样说,不过地点是神户,不是东京。(15)日本宪兵大约在1943年5月底知道郁达夫能说流利的日本话。有一天他拜访巴耶公务有钱又有社会地位的侨领蔡成达,希望后者帮忙找房子。当他走进蔡家,一个日本宪兵正在和蔡成达为一事件争论得面红耳赤。他们之间语言不太通。蔡知道郁达夫会讲日本话,就叫他作通译。蔡成达,又名蔡清竹,是当地有名之侨领,荷兰政府封他为“甲必丹”(Kapitan),所以有华人问题,日本军方多数向他交涉。在这事情之前,蔡曾帮忙郁达夫办理户口登记,成为巴耶公务的合法居民。郁达夫后来成为蔡成达的助手。蔡与日本人交涉华侨事物时,郁达夫就当翻译(16)。在铃木正夫的报告中,有一个叫关根文的人,是日本米星产业公司的职员。1944年1月,他被派到巴耶公务,在附近的米星产业公司负责烟草的收集和交易,以及农园的经营。在访谈中,他说:
在我到的第二天,就遇见赵先生,他担任华侨会长蔡的翻译,当我把名片递给他时,我很惊讶,他用正确的日语说:“哎!关根先生,请坐,请坐!”……另有秋山隆太郎,当时日本在苏门答腊划分成九个行政区,他是西海岸州的巴耶公务分州之分州长。他也在供证中说:
1944年到1946年4月战争结束前,我任分州长。在我就任不久,赵先生来做礼貌性拜访。当时巴耶公务的华侨长,是位姓蔡的,他只会说印尼话。由于赵先生日文流利,并在中国人中有影响力,因此我们对华侨政策的实施,都先得通过赵先生。郁达夫到巴耶公务的时候,裤袋里只剩下几百盾。过了二三个月,已差不多用光了。幸好这时候他有差事做。胡愈之和其他新加坡文化人也陆续到了巴耶公务。汪金丁在1942年9月18日到那里,他说郁和胡先后到王任叔则较晚,8月左右才到。他自己回忆说:“八月初,我终于在山巢爬了出来,沿这小岛的海岸,上溯到北干峇鲁,经岛的中部高原地带,而到了愈之他们住下的巴耶公务。那时纪元去巨港,达夫在花的国日本宪兵部当通译,化名赵廉,住家却在巴耶公务。”(17)
这一群朋友,后来生活也成了问题,因此想做点小生意赚钱。刚好这时他们收到一笔约四百盾的难民救济金,这是泗水华侨捐募的,再加上当地华侨投资两百盾,他们开始经营一间酒厂。开酒厂的目的,除了解决生计,也可以用来掩护作为反日的知识分子之身份,这酒厂命名为“赵毅记酒厂”,九月一日开始营业。赵廉挂名做老板,胡愈之做记账的,张楚琨(新加坡报人)做经理。(18)
这间酒厂的生意很好。开了六个月,刚好日本驻军大大增加,所以顾客中以日本人为最多。所以铃木正夫所访谈过的日本人,多数还记得赵豫记酒厂之事。前面提过的日本米星公司派去巴耶公务的职员关根文,记忆犹新地说:
1944年6月,在离华侨街三公里地方,有个叫“赵豫记酒厂”,开始制造“初恋”和“太白”这两种酒。日本军人和商人喝许多这种酒。这造酒厂似乎由华侨们投资,并实际经营,赵先生地位,只是指导和顾问而已。酒的原料米,当时是管制品,我利用我工作的方便,帮助他们储存米和获得瓶子。另一位池内大学,是日本发电厂职员,在1943年3月被派到苏门答腊。后来常被派到巴耶公务管理工业、交通等事。他也记得因酒而与郁达夫有过来往:
因为我们有制酒的原料——糯米,所以结识了赵先生。我和赵俩人都喜欢喝酒,他几乎每天固定的,用我给他的一部分米,制烧酒请我喝,我们称此酒为“富士山”(Gunung Fugi,古浓,印尼话山之意)。那时我二十八岁,大概他想我易相处,或因我有什么本事,所以要和我交朋友。
此外他还说:“赵先生喜欢酒,了解他造酒,给他特别配合的糯米和砂糖的是我,山下部队当然也帮‘古浓富士’酒不少的忙。”
1942年除了开酒厂外,郁达夫并接受日本宪兵大队通译的工作。开始他推辞说要照顾酒厂,不能去武吉丁宜(Bukit Tinggi)——当时的宪兵总部。但是宪兵方面不肯放人,他就不敢坚持到底。宪兵总部设在离巴耶公务三十公里的武吉丁宜山上,郁达夫只好暂时住在那里,通常每星期回巴耶公务一两次。所以王任叔在1941年8月到那边时,“达夫在花的国日本宪兵部当通译,化名赵廉,住家却在巴耶公务”。他首先见到的是胡愈之。汪金丁在九月到时,过了几天才见到达夫:“达夫和愈之先生几位,是在几个月前就到了那里的。因为达夫在宪兵部做通译,而宪兵部又是距离巴耶公务有四点钟火车路的武吉丁宜,所以一个礼拜回来一次。我到公务的第三天才见到达夫。”(19)
郁达夫在武吉丁宜的生活,寂寞且无聊。他无事时,经常陪宪兵喝酒或嫖娼。因为他性格奔放,时时刻刻要留神不说错话,因此很苦闷,听说每次回到巴耶公务来,他便向他的落难朋友“把拘禁了一个礼拜的话都倾吐出来,精神就特别感到畅快”。(20)可是在另一方面,郁达夫却因为做了日本宪兵的通译而得意。走在路上,有日本警察向他敬礼,而印尼人都称他“端”(Tuan,老爷或先生之尊称)。他住的是荷兰式的洋房,家里书很多,都是从宪兵部搜罗来的。平时谈话,口气很大,他似乎已经不怕身份泄露,他会这样说:“没问题!这里华侨都知道我是谁,有什么问题?到宪兵部告诉我吗?我先把他抓起来,Kasih setengah mati(印尼话,把他打个半死)。”(21)
通译的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了多久?胡愈之只说与酒厂的开办差不多同时。前后工作时间不过六七个月就结束了。我在上面引用过汪金丁的话,他在九月中旬抵达巴耶公务,达夫已暂时因通译工作而住在武吉丁宜。而根据我上引王任叔的话,达夫应至少在八月就去上任了。铃木正夫访谈过的一位宪兵(姓名没公布,以F代表)(22)说,他在1942年4月至1943年正月这段期间,在武吉丁宜宪兵部当庶务员,他承认当赵廉当通译时,常常看见赵廉出入宪兵队。有一位武吉丁宜宪兵队警务主任(姓名保密,编名B)告诉玲木正夫说:
我是在1943年7月到1944年10月在武吉丁宜宪兵队。那时他已辞去宪兵队工作,在巴耶公务卖烧酒给日本人……我是管理内务事情,山下部队驻屯在巴耶公务,加上附近有些欧洲俘虏,所以我常到那里去。有时我上他家拜访,我听他亲口说,从1942年到1943年初,在武吉丁宜宪兵队任通译。
由上面的片段记忆看来,郁达夫做通译的时间确实很短,1942年9月左右开始,1943年3月前已辞掉,前后大概六七个月。根据中文资料,他辞职的经过也很传奇。郁达夫要走,宪兵部不肯,(于是他只好虐待自己,鸡鸣即起,用冷水冲凉,让自己伤风,吃鸦片,喝酒,让自己咳嗽……好证明自己是有肺病。)最后他进入一间叫“萨瓦伦多”的医院,他送那个日本医官几瓶酒,于是,不久他证明是有病的。这时宪兵司令调到他处,便批准他的辞职请求。(23)
铃木正夫的访谈中,泄露一项事实:郁达夫虽然正式在1943年初辞去日本宪兵队的通译工作,但以后他继续提供义务的服务。一位当时在武吉丁宜的宪兵班长说:“我认识赵先生是因为:1943年下半年,我和他一起在武吉丁宜宪兵队工作,有半年之久。当时我去过他巴耶公务的酒店好几次,所以我晓得一点关于他的事情。”郁达夫到宪兵队去,就是做这位D先生的通译官。他说:
在我赴任到武吉丁宜时,他已不当通译了,但我们需要一位可靠的翻译时,都去找他。当时我的地位不必雇佣私人翻译,他之所以愿意替我翻译,好像是企图利用机会帮中国人的忙。如果我说他的翻译有错时,他会立刻上前说些好听道歉的话。我和他来往,可以知道华侨们的动向……
中国资料方面常常称赞郁达夫利用通译之方便来救人,这位日本宪兵班长的供词,正是旁证。胡愈之说郁达夫常欺侮日本人不懂印尼话,盘问嫌疑犯时,经常自问自答。吴柳斯曾经有一个时期和郁达夫常在一起,他说:
在他任职的七个月当中,我知道他只有帮华侨,帮印尼人的忙,并没有陷害一个人。谁都知道,他是道地的外江人,满口浙江口腔,外省话是不懂的,尤其在他任职期间,他的印尼话,不只是说不好,连听也听不大懂,而在苏西地区的普通话就是印尼话。所以当宪兵队长要他通译的时候,他常常自问自答,好比演戏一样,不论什么人被抓到宪兵部去,给他如此一来,都释放出去,于是,被抓的人,既不知是为什么被抓的?又不知为什么被释放的,然而大家都知道,这是郁先生帮的忙。(24)
这些话也许有点夸张,但郁达夫相信常利用其工作帮助过不少人。汪金丁也亲口听见郁达夫这样夸耀自己的功劳:
据达夫说,他这一次是跟着日本人去到苏门答腊北部的阿齐,去侦察联军“间谍”的。日本人在表面上装得很诡秘,其实到了什么地方也仍是要酒,找女人。也的确抓到了几个很有嫌疑的,然而达夫说,日本人既不懂荷兰语文,也看不懂那些物证,一切非先问他不可,于是经过他一通译,这些情形很严重的人被视为无足轻重,放走了,连重要的物证也被达夫销毁了。(25)
铃木正夫的报告也泄露了郁达夫另一面的生活:他除了因为做通译而跟日本宪兵队有来往,平时也常跟日本军人或商人做朋友。其中好几位日本人和他有了很深的友谊。关于这一点,中文资料大概是故意不说,不是不知道吧。山下正,一名日本富九七一七部队长,他的部队从1943年1月1日到1946年6月底,驻守在巴耶公务附近。虽然由于军职在身,不敢有太多来往,但他与郁达夫还是有友谊,私下有来往。当山下正的部队撤退时,(我派一位部下,送他一套我在新加坡做的西装为纪念品,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上面提过日本米星公司职员关根文便是郁达夫的好友。他回忆说:
赵先生是我的亲密好友。他跟我非常亲近,而且无论哪一方面也都是我的老师。赵先生的人品,我知道很清楚:在日本人之中,我是和他来往得亲密的了。可是他以往的身份,因感到切身的危险不愿提到,因此也没听说过。
关根文和郁达夫(曾计划战争一结束后一起搞贸易公司),所以他说“如果赵先生不是行方不明的话,我也许不会回到日本的”。我上面提过帮忙郁达夫购买糯米的池内大学,也承认达夫和他(来往得非常亲近)。他说“经常到赵廉先生那儿去吃油腻的中国菜”。做过巴耶公务分州州长的秋山隆太郎也承认(在苏门答腊留下印象最深的,说来还是赵先生的事情):
……我和赵先生互相信赖在公私两方面都非常亲近。他是极为亲日的,但是对我这分州长的头衔好像保持着一步的距离。时常让赵先生请客,也时常由他做菜宰野猪吃……(www.zuozong.com)
回国以后,跟过去的伙伴提议给赵先生写信时,听说他死了,感到很可惜。中国方面的资料,固然没有报告事实,但从中国难民跟郁达夫来往之小心之报告看来,一定事出有因,胡愈之说,当时他们难民中暗地里进行反日之活动,不过没有让郁达夫参加或知道。他承认郁达夫似乎知道他们的活动,但却装着不知,对这事也不闻不问。(26)
汪金丁的《郁达夫的最后》也有这样的一段:
……我们这批流亡的朋友在那时有个对外绝对秘密对内绝对公开的组织,组织的生活,使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上都有了中心……不过这个同人的组织并不包括达夫在内。(27)
由此可知,郁达夫的中国朋友也认识到他跟日本人的来往很密切,有小心警惕之准备。
尽管郁达夫和日本人的来往多到使他的中国朋友对他采取小心的态度,驻守巴耶公务的富九七一七部队的部队长由下正的副官甚至说“赵先生和睦协作,真是巴耶公务的汪精卫”(这是由下部队第四中队军医西本矢的供词)但各方面的资料,都说华人和印尼人都很尊敬他,没有视他为“汉奸”,这一点连日本也这样说。关根文就有这样的回忆:
一般说来,他对日本人很友善,丝毫不怀敌意。华侨他们也不以常使用的名词——汉奸,加在他头上。每隔一周或十天,日本宪兵要去侦察他行动一天。听说他曾担任宪兵分队通译,但他从未对我说起过去的工作详情。有时他搭我的卡车到巴东,一次早卡车上,他愤愤不平地说:“有人以为我是(中国方面的)间谍,他们若疑心,最好是做次彻底的搜查。”
郁达夫周旋于日本统治者和难民之间似乎很成功,日本人相当信赖他,对他有好感;而避难的华侨及当地印尼人也受他极力保护。像汪金丁这段话,很多中国资料都这样说:
许多人都找他,一个不相识的老太婆要买一盒公价火柴,也请他写个条子,介绍她去组合;一个商人有几千公斤辣椒要请出口准字,也来请他设法相帮疏通;又一个什么人家的房子,日本人要强迫租住,也是来找他;自然啦,什么人抓去更是非达夫出面营救不可。我记得有一个人犯了杀人罪,要求减刑,也来请他起草递到法院去的控诉书……(28)
1943年初,郁达夫辞掉日本宪兵队的正式通译职位,回到巴耶公务定居。他就告诉朋友说,他很想结婚。这时候,有两个荷兰女人和他来往。巴东也有一个交际花跟他很好。他有两句诗“老去看花意尚动,巴东景物似湖濆”。(29)便是描写他常去巴东请朋友做媒。他不但认真,而且要快。主要原因是:有一个家庭,可以减少日本人对他身份之怀疑。郁达夫由于声明在先,不讲求美貌或出身,很快就与一位巴东的女子结婚。介绍人是巴东旅店的合股老板吴元湖和戚汝昌。那女子原名叫陈莲有,是一位印尼华侨,原籍广东台山。小时丧父,被陈家收养,她生父原姓何,因此郁达夫替她改用原姓而取名为丽有。
郁达夫的婚礼1943年9月15日在巴东的荣生饭店举行。附近很多社会名流都受邀请(30)。一位武吉丁宜宪兵队班长(D氏)还记得这回事。他说:“我记得在1943年被邀请参加他的婚礼,听说新娘是巴东华侨少女。”据说结婚证书是郁达夫自己拟定的。
结婚证书上的姓名、籍贯、年龄都是伪造的,以求掩饰他的原来身份。郁达夫原是浙江富阳人。生于一八九六,因此一九四三年的时候是四十八岁而不是四十岁。(31)郁达夫写了四首诗来纪念这次的结婚,其中第一及第二首抄录如下:(32)
洞房花烛礼张仙,碧玉风情胜小怜。
惜别文通犹有恨,哀时庾信岂忘年。
催妆何必题中馈,编集还应列外篇。
一自苏乡羁海上,鸾胶原易续心弦。
玉镜台边笑老奴,何时归去长西湖,
都因世乱飘鸾凤,岂为行迟泥鹧鸪。
故国三千来满子,瓜期二人聘罗敷,
从今好敛风云策,试写胜王蝴蝶图。
其中“惜别文通犹有恨”是指他的新娘是个文盲,从未受过教育。由于郁达夫不通台山话,他们夫妻日常只好借用印尼话来交谈。郁达夫时常在朋友面前开玩笑地叫她作“bodoh”,印尼话即笨蛋或傻瓜之意。池内大学还记得:他有时写诗,说他正完成着时,并解释其意思。如果他太太正好走过来,他立刻转变话题说:“她很笨,但是太太还是笨的好。”这位贫寒出身的妻子很多人都记得她。关根文说:
在我到赵家赴约时,总有位二十七八岁的中国女人在旁边,最初我以为是女佣,后来她肚子渐渐大起来,并生下一位男孩。他告诉我男孩的名字叫大亚,并写给我看。他叫他太太“nian nian”或叫她“nyonya”(女人),有时他甚至开玩笑说;“这是个bodoh”(愚笨)。我时常尝到赵夫人亲手烧的菜。
郁达夫的亲密朋友如胡愈之等人的资料大亚都作大雅。关根文跟铃木正夫谈话时,以为郁达夫告诉他“大亚”是要讽刺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郁达夫和这妻子生活得很和谐。直到郁失踪后,这位无知识的妻子才知道丈夫赵廉原名郁达夫,一位来自中国的名作家。(33)中国方面资料都说,郁达夫所以娶一位文盲,主要是不会泄露身份。
1944年左右,日本在苏门答腊成立军政监部,武吉丁宜变成管辖苏门答腊各地的司令部。因此日本军人来得很多。据说郁达夫和日本军方关系已没有以前那样好,连巴耶公务荷兰式的房子(汪金丁抵达时看到的)也被占去了。怪不得关根文在1944年1月派到巴耶公务做买卖,他看到郁达夫的屋子是极其简陋的:“他的家很小并简陋,在泥土地房子中间,只有一张方桌和几把椅子,左侧堆积很高的书……”
在武吉丁宜宪兵部也增加很多特务,其中一些是从新加坡调来的,因此对新加坡文化界领袖很了解,有一个华人叫洪根培的,便是新加坡与亚练成所受训的,专为日本人侦察华人动向。抵达武吉丁宜不久,他便识穿赵廉原来是郁达夫。而且告他是盟军的间谍,并请当地一间华校校长作证。可是郁达夫没有被捕。胡愈之解释日军没有采取行动,主要是想利用郁达夫做线索,看看他的其他同路人是什么人。因此暗地里将他的行动加以紧密监视。本文上面所引关根文的话“每隔一周或十天,日本宪兵要去侦察他行动一次”,大概就是指这件事。郁达夫这时常常告诉他的朋友说,他的安全成了问题,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但由于监视太严密,没法逃跑。胡愈之见风声很紧,又还有机会,便先逃去棉兰躲藏起来。(34)
在1944年以后,赵廉即郁达夫的秘密应该被很多日本军人和当地华人知道。在铃木正夫所访谈的日本人中,有一位武吉丁宜宪兵警务主任(B氏)在1944年就知道了:
在我由武吉丁宜转到东部的Bagansiapiapi(岩眼亚比,为印尼最大的渔场)后,一位学者模样的中国人,他是由新加坡来,在那里制造肥皂,他告诉我:赵廉就是郁达夫,曾任《星洲日报》编辑,试着去爪哇没有成功,才留在苏门答腊。我完全不相信这人的话,也没有再转告其他人。
关根文也记得(在1945年1月还是2月左右,他告诉我,除了赵廉外,他另有一个名字叫ㄩˋㄉㄚˊㄈㄨ。)另一位武吉丁宜宪兵班长(D氏)也说,(我听说:赵先生这个人是乔装,同时,用的也是假名。在我转到司令部后,也听到相同说法。我还听说,当我在武吉丁宜时,他可能还有另一个名字。)很可能因为郁达夫替宪兵做过翻译,人缘也好,所以只受监视,宪兵并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向盟军投降。郁达夫很快就从某方面知道这消息,非常兴奋,马上四处奔告,打算接办日本人在巴东的报纸,把苏西的华人组织起来,并且要策划组织一委员会,庆祝和平及欢迎盟军的降临。(35)
1945年8月29日晚上,郁达夫在家里跟几个朋友商量结束“苏西华侨繁殖公司”(又称华侨农场)的事宜。当初开农场之用意,是要使华侨免被日本人招去做苦役。大约八点钟的时候,胡愈之说,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8月29日晚间,郁先生和三四位客人……八点钟以后,有一个人在叩门,达夫走到门口,和那人讲了几句话,达夫回到客厅里,向大家说,有些事情,要出去一会就回来,他和那人出了门,从此郁达夫就不回来了。(36)
喊达夫出去的人,是一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像一个台湾人,也像印尼人。和达夫说的是印尼话。达夫出门时,身上穿着睡衣和脱鞋,可见并不预备到别地方去。朋友等到午夜过后,还不见他回来,便各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清晨,达夫的妻子要分娩,邻居们便赶来帮忙,因为郁达夫还未回家。生下的这个女儿,取名为美兰。这时他们虽然很焦急,但不能确定是失踪,因为平时郁达夫经常一声不说,就在朋友家过夜,甚至几天不回家,也是常事。后来四处打听一下,从当晚步出门口之后的现象看来,似乎有点不妙:
……据附近一家咖啡店的伙计说,当晚郁达夫从家中出来,和一个不相识的青年进了咖啡店,两人用马来话交谈。那人似乎托达夫帮忙一件事,达夫表示不答应,不久两人就出去了。在离咖啡店不远是一条小路,十分荒凉,只有一家印尼农民的茅舍屋,那印尼农民曾看见当天晚上大约九点前后,有一辆小汽车驶到那路上,里面有两个日本人,汽车停了许久,又有两人过来,上了汽车,就驶走了,那条小路晚间见不到光,所以不能分辨车上乘客的面貌。(37)
根据这种情形,巴耶公务的华人首先肯定带走郁达夫的人,一定是日本人,因为当地只有他们才有汽车。
郁达夫失踪的第二天,一名在武吉丁宜宪兵队警务班的宪兵(C氏)到巴耶公务作例常巡察。因为他与郁达夫来往了一年,便照常去拜访他:
我想是在战后的几天,日期已记不清楚,我因巡察任务到巴耶公务,照常去赵先生家拜访,我感到奇怪,大门是关着的,当我进去,发现赵太太在哭,我问了她才回答:“前天晚上有两位印尼人来找他,他说有事要出去,到今天还没回来,我很担心,可否请你代为寻找一下?”我答应她去搜查,回部队后,我就报告长官,部队开始调查,几天后并没有找到他的踪迹。当时邦人和军人等,离队逃亡、杀害等事件,相继发生,加上印尼独立运动展开活动,人心混乱,搜查工作变得困难。在此情况下,我们没有完成寻找赵先生的工作!就离开苏门答腊,进入收容所。在收容所听说,联军方面也在搜索赵先生的下落。
另一名日本宪兵(A氏)也记得曾奉命搜查郁达夫:
战后赵廉失踪这件事是真实的。当时我移驻到巴耶公务宪兵队,任务是维持当地治安和保护日本军队等。我记得很清楚,在1946年1月前,长官要求我们合作,搜查赵廉私人住宅。我亲自协助检查赵廉屋子有二三次。由开始搜查到四月中我离巴耶公务为止,只是查出赵廉离开家的情况而已。
还有第三名宪兵(D氏)也曾帮忙搜查郁达夫之下落:
1946年5月间,我被调到棉兰司令部,曾接到通知,要我们打听赵廉消息。我的老战友们说,他们也去调查这事,因为赏金很高。
中国资料方面也有叙述宪兵出动人马来打听追查郁达夫下落之事。不过正如胡愈之所说的,他们不相信日本宪兵真的不知真相,而是故作猫哭老鼠之状,实际上是他们所谋杀。很多中日人士都同意,由于日本投降到盟军派兵接管苏岛期间,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尤其再加上印尼独立运动积极乘机而起,在这段无政府之真空状态中,造成很多无法无天之事情发生。
第一次肯定郁达夫死亡的消息,是来自驻扎棉兰的盟军总部,那时正是1946年8月。不过这声明很简单,只说是被日本宪兵所杀害,而且是由被审讯的日本战犯所透露出来。除了这种说明,没有其他的证据,没有日本宪兵因为涉及杀害郁达夫而判死刑。至于郁达夫被杀害的理由,中国人士都解释说,因为郁达夫担任宪兵队通译,亲眼目睹宪兵残害被征服的人民,再加上他本身是一位知名作家,担心战后将成为一位强有力的控诉日本宪兵的证人,因此先下手为强,将他杀害,消灭一个必将控诉他们的证人。(38)
铃木正夫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根本不相信郁达夫是被日本宪兵杀害,他比较相信被印尼人杀害的说法。可是当他继续访谈了很多当年与郁达夫有来往的日军时,出乎他意料之外,有关人士供词说,郁达夫是宪兵所杀,而且证据确凿可靠。铃木正夫说:“到了后来随着调查的进展,意外而且非常遗憾,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所杀害变成了确定性的事实。”由于顾虑证人的安全问题,铃木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因此不顾证人及详细杀害郁达夫的经过事实提供出来。他只透露杀害事件是由几位来自武吉丁宜队的宪兵所策划。有一位宪兵私下秘密决定,瞒过上司,叫几个部下把郁达夫处决。他们用一个印尼人把郁达夫从家里引出来,然后带到别处将他处死。后来那印尼人也失踪了。事情发生后,参与其事的几位宪兵因畏罪离队,全部失踪了。其中一位参与者,在事情发生后,离开部队,改名换姓,混入军队,后来与普通日本士兵一起被遣送回国。至于被杀害郁达夫的动机,正如中国人士所说,是要消灭有资格在审讯战犯时的证人。
郁达夫神秘失踪后,留下妻子何丽有,儿子大雅及郁达夫失踪第二天才诞生的女儿美兰。他留下遗嘱两张,交巴耶公务保存。这是1942年及1944年农历元旦以赵廉之名写的。第一张述及他对中日两国之见解,郁达夫说:“中日不但是邻国,从历史、文化上来看也是非常接近,因此中日应该携手并进,而不应有敌对。今日虽有不如意之事发生,但以后仍是携手的……”(39)第二张详细提到他在中国及苏门答腊财产之分配。关于身边的产物他说:
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有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存二万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宽二十五米达,工一万四千余盾,凡次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子大雅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定,故不算。(40)
关于郁达夫的产业,所有他当时的朋友,未曾清楚叙述内中之情形。跟他来往很密的日本商人关根文说,他除了替华侨经营酒厂,还有这些事业:
他自己经营了一个造纸厂,原料是竹。精白和薄的纸,用以包装香烟,较厚和粗糙的纸,用做包装纸。我也全力协助这家造纸公司,由巴东三菱公司处,获得漂白剂中氦化物。造纸必需的纸浆,则由日绵公司获得。大概在一年半后,由于这些原料难以购买,因此关闭。另外由华侨赵先生的协助,还开了个肥皂公司,看样子,赵先生的生活、津贴,全仰华侨。
从各种资料看来,郁达夫在巴耶公务避难期,真的摇身一变,从浪漫作家,化成一位相当能干的商业才人。由于他的交际手段高,人缘好,再加上成功的周旋在华侨与日本人之间,因此他能办理普通人不能做到的事。
1949年,郁达夫的遗孀及儿女三人,由巴耶公务搬迁到巴东住,听说得到蔡成达之照顾和帮忙。不久何丽有重嫁给领土岛上的印尼华侨刘松寿。他的生意由于受到印尼排华的影响,据说后来回去中国大陆。(41)至于大雅和美兰,由蔡成达带到椰加达去,由他女儿抚养和教育。
郁达夫在什么地点被害?尸体葬在何处?一直是一团打不破的谜。1953年8月30日,巴东及苏西一班文化教育工作者,为了纪念郁达夫及其他十一位遭日本宪兵杀害人士,在离开武吉丁宜三公里之华侨公墓,树立一纪念碑。这地点常被误为郁达夫遇难之地点。(42)
∗本文原作于一九六八年至一九六九年,当时铃木正夫的访谈尚未出版。现在将新的资料穿插进去,能够弥补郁达夫流亡苏门答腊的生活记录之残缺。
(本文收录在王润华《中西文学关系研究》,台北:东大图书,1987。)
(1) 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香港:咫圆书室,1946年)。这个报告原有副题《给全国文艺界协会报告书》,先在1946年9月的《民主》上连载。
(2) 新马华人在这方面的贡献,最好的成绩是:(一)温梓川编,《郁达夫南游记》(香港:世界出版社,1956)。(二):李冰人与谢云声合编,《郁达夫纪念集》(南洋热带出版社,1958);(三):李冰人编《郁达夫集外集》(南洋热带出版社,1958)。
(3) (注三)这一篇访问记录《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原苏门答腊在住邦人的证言》原附录在伊藤虎丸、稻叶昭二及铃木正夫合编,《郁达夫资料》(东京大学洋文化研究所,1969)。
(4) 关于郁达夫在新加坡马来亚之生活,我在“A Study of YU Ta-Fu's Life in Singapore and Malaya,193901942”(作于1969)一文中有详细叙述。
(5)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上下册,1946自印本),第48—56页、及第66页。
(6) 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第2—3页。
(7) 温梓川,《郁达夫别传》(在马来西亚出版的《蕉风月刊》上连载,143至163(1964至1966),见154期,第69页。
(8) 见陈嘉庚,《南侨回忆录》,第346—347页。
(9) 见王任叔,《记郁达夫》,收集于《郁达夫纪念集》(第11—16页),第11页。王任叔(巴人)是十九人中的一个。
(10) 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第4页。
(11) 陆丹林编,《郁达夫诗词钞》(香港:上海书局,1962)。
(12) 见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第33页及第43页。
(13) 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第9页;王任叔《记郁达夫》,在《郁达夫纪念集》,第11—13页。
(14) 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第14—15页,及佚名,《郁达夫先生遇难前后》,收集在《郁达夫集外集》,第238—239页。佚名是一位印尼华人,据编者李冰人说,郁达夫以前在巴耶公务时,常与他有来往。
(15) (注一五)本文所引用铃木正夫的《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原苏门答腊在注邦人的证言》,是根据需要情形,分别采用下列两种译文:(一)杜国清所译,发表于《纯文学》,九卷一期(1971年1月),第40—64页。(二)美国人梅其瑞(Gary G. Melyan)译,《郁达夫遇害之谜》,刊于《明报月刊》,第六十期(1970年12月),第54—61页。梅只节译其中重要部分。
(16) (注一六)胡愈之,《郁达夫之流亡与失踪》,第16—17页。
(17) (注一七)王任叔,《记郁达夫》,收集于《郁达夫纪念集》第13页。
(18) 金丁,《郁达夫的最后》,《郁达夫纪念集》,第76页,及胡愈之,《郁达夫之流亡与失踪》,第20—21页。
(19) (注一九)金丁,《郁达夫的最后》,《郁达夫纪念集》,第76页。
(20) (注二〇)金丁,同上,第78页。
(21) 金丁,《郁达夫的最后》,《郁达夫纪念集》,第76—77页,这是汪金丁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他说当时王任叔也在场。
(22) (注二二)由于怕引起法律上的麻烦,铃木正夫访谈过的七位宪兵都没有公布真实姓名,只冠以ABCDEFG代表。
(23) 金丁,《郁达夫的最后》,《郁达夫纪念集》,第81页。
(24) 吴柳斯,《纪念郁达夫先生》,《郁达夫纪念集》,第71页。
(25) 金丁,《郁达夫的最后》,《郁达夫纪念集》,第80页。
(26) 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第32页。
(27) 金丁,《郁达夫的最后》,《郁达夫纪念集》,第78页。
(28) (注二八)金丁,《郁达夫的最后》,《郁达夫纪念集》,第81—82页。
(29) (注二九)陆丹林编,《郁达夫诗词钞》,第41页。
(30) (注三〇)温梓川,《郁达夫别传》,《蕉风月刊》,157期,第76—79页。
(31) (注三一)温梓川,《郁达夫别传》,《蕉风》,157期,第77页。
(32) (注三二)《郁达夫诗词钞》,第40—41页。
(33) 佚名,《郁达夫先生遇难前后》,收集于《郁达夫集外集》,第243页。
(34) 金丁,《郁达夫的最后》,第85—89页。
(35) 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第23页。根据金丁的报告,郁达夫对这些行动很冷淡,(他认为绝对不可以“动”。日本宪兵仍然有权力可以抓人。见《郁达夫纪念集》,第91页。
(36) 见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第27—28页。请参考佚名,《郁达夫先生遇难前后》,《郁达夫集外集》,第24—42页。
(37) 见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第27—28页。请参考佚名,《郁达夫先生遇难前后》,《郁达夫集外集》,第24—42页。
(38) 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第30—31页。
(39) 这篇遗书未见发表,据佚名的《郁达夫先生遇难前后》,它由蔡成达(清竹)保管。后来蔡君已回中国。引文录自佚名的文章。
(40) 这张遗嘱发表在《郁达夫集外集》,第229—230页。
(41) 温梓川,《郁达夫别传》,《蕉风》,161期,第46页。
(42) 佚名,《郁达夫先生遇难前后》,《郁达夫集外集》,第242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