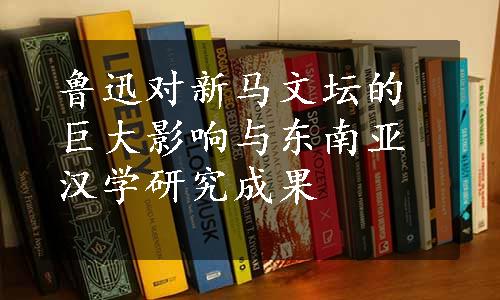
南治国
新马新文学的源起,是与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密切相关的。方修先生认为马华新文学就是接受中国五四文化运动影响,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婆罗洲)地区出现的,以马来亚地区为主体,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华文白话文学;它渊源于中国文学,且属于同一语文系统,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渐渐地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自成一个系统。(1)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先驱和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创者,其创作手法和思想高度,均对中国新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仍可以“世纪冠军”冕之而少有异议。(2)鲁迅并没有来过新马,但他对新马文坛的影响却巨大而持久,用章翰先生的话来说:“鲁迅先生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中国现代作家。”(3)与其影响相对应,新马文艺工作者对鲁迅的研究亦起步很早、用力最勤、影响最大和成果最丰。本文将按年代顺序梳理新马文艺工作者对鲁迅的著作和思想的理解及接受的大略轨迹,并概述他们在鲁迅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开篇之作。它以悲怆的格调和写意的笔墨,抨击了全部旧历史和整个旧社会的吃人本质,概括和寄托了中华民族的血泪和希望。(4)鲁迅的所谓“寂寞的悲哀”是久而有之,但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他“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5);既不是“主将”,他似乎也不在“前驱”之列;到1926年编选《彷徨》之时,因先前的主将们“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影响到他——两间之余卒——就有“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感觉”,(6)只得“荷戟”独自“向黑暗里彷徨于无地”。(7)心灰意冷若是,《彷徨》忝列“乌合丛书”,自在情理之中。
“三·一八”惨案(8)之后,鲁迅由津浦路乘车南下上海,再改水路到厦门,彷徨之中,分明还有一些的凄怆和仓惶。然而,厦门大学亦非久留之地,不到半年,1927年1月,他假道香港,“抱着梦幻”抵广州,但好景不长,国民党的“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9)让他经验到“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恐怖,“被血吓得目瞪口呆”(10),鲁迅借避于上海,颇有退隐书斋,埋首著述之意,其时已是1927年10月。可是,在上海,等待他的依然是“苦境”;仅三个月后,他就成了创造社和太阳社左翼文人集体讨伐的“封建余孽”和“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11)。
在中国国内,二十年代的鲁迅虽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的创作无可争议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12),甚至让文学革命的主帅陈独秀都“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13),但其生活劳顿奔波,其创作思想和成就亦惹非议,他的境遇,用“颇多坎坷”来表述,应不为过。那么,在新马,鲁迅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总的来说,在二十年代的马华文坛,鲁迅是寂寞的。
1926年4月的《星光》周刊的第46期上,有由南奎执笔所写的《本刊今后的态度》一文,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我们深愿尽我们力之所能地扫除黑暗,创造光明。我们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决不是登高一呼,万山响应的英雄,只不过在这赤道上的星光下,不甘寂寞,不愿寂寞,忍不住的呐喊几声“光明!光明!”倘若这微弱的呼声,不幸而惊醒了沉睡的人们的好梦,我们只要求他们不要唾骂,不要驱逐我们,沉睡者自沉睡,呐喊者自呐喊,各行所是。那就是我们唯一的祈求。……这样黯淡的星光,这样微弱的呼声,思想是这般的幼稚,文字是这般的粗率,竟能得到社会的如许的同情,我们那得不努力,那得不兴奋,那得不振作,那得不使这暗淡的光,照澈这阴霾的宇宙,那得不使这微弱的呼声,惊醒酣睡的人群?(14)
显然,最早发表在1923年8月21日的《晨报·文学旬刊》上的鲁迅的《‹呐喊›自序》,已最迟在1926年4月传到了新马,引起了新马作家的注意,并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和创作,因为上段引文中的“呐喊”“酣睡”,还有这“人群”,都令人不禁想及鲁迅的《‹呐喊›自序》,而且,这文字里,这情绪中,也分明藏有鲁迅的影子。根据手头搜集的资料,我推断这是鲁迅与新马新文学的首次的“影的接触”,其时是1926年4月。
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中论及了不少中国作家,但“鲁迅”二字出现时,已是上卷的第311页,马华新文学也已经走到了1930年的3月:
……这是一位署名“陵”的作者提出的。他写了一篇《文艺的方向》,说道:
“……我觉得十余年来,中国的文坛上,还只见几个很熟悉的人,把持着首席;鲁迅、郁达夫一类的老作家,还没有失去青年的信仰的重心,这简直是十几年来的中国文艺,绝对没有推向前一步的铁证。本来,象他们那样过重乡土气味的作家,承接十九世纪左拉自然主义余绪的肉感派的东西,哪里能卷起文艺界的狂风?……
“现代文艺,决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我们不当象恶魔派一样,专门描写丑与恶,虚伪和黑暗;我们不当象唯美派一样,沉沦于颓废的倾向,而不自振拔;我们不当象自然派一样,专门描写肉;我们不当象写实派那样太理智化,冷酷而没有同情;我们不当象乡土派那样太狭隘,太小气,而忽略民族精神。……一言以蔽之,我们以后,要努力建设Positive(肯定的)文学。”(15)
这是发表在《星洲日报》文艺副刊《野葩》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时间是1930年3月。这位署名“陵”的作者明显受了当时中国国内由创造社和太阳社发起的围攻鲁迅的声势浩大的文化论战的影响,而且,其措辞、观点亦附和当时国内围攻者的论调,如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的观点,对此,王润华教授和章翰先生都有详细肯綮之论述,我就不再赘述。(16)我想特别指出的是,这位作者似乎并没有读多少鲁迅的作品,对其作品的理解亦较幼稚。而差不多和他同时的另一位叫“悠悠”的作者,在随后的《野葩》副刊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南国的文艺的方向》中,竟然将鲁迅和张资平相提并论,他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理解,恐怕已不仅仅是幼稚了:
欧亚交通的要道的南国,是否适合象鲁迅的《阿Q正传》的忍耐的文艺?是否适合张资平的沉醉于恋爱的小说?现在的文艺已由性的问题走向食的问题方面去了。因为大多数的群众都在饥饿;食的问题既得不到解决,哪里还准许你谈到性的方面。这时代是普氏与布氏针锋相对的阶段,鲁迅的《阿Q正传》的忍耐的文艺,张资平的沉醉于恋爱的小说,在南国都不适合。南国只有建设一种独立的,能代表南国各民族的特性的,能表现南国地方色彩的新兴文艺。(17)
在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史稿》中,在论及新文学之发端时,便已提及唐弢、周钢鸣(第13页)、徐调孚、顾均正、严敦易(第16页)、郭沫若、陶行知、李守常、郑振铎(第26页)等一大批中国作家。而对马华新文学影响最大的鲁迅竟要迟至第258页才作为批斗和误读的对象姗姗登场。由此可见,鲁迅在二十年代的马华文坛,不只是挨了寂寞,交的还是华盖运。
受二十年代末中国国内太阳社和创造社围攻鲁迅的文化论战的影响,三十年代初,鲁迅在新马的形象几乎为负面,从上文所引的几位新马文艺工作者的文章中便可略知一二。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团结了大批的进步作家,左联成为了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堡垒。作为左联这一进步团体的领袖,鲁迅赢得了中国现代文坛的广泛尊重,并影响了一大批进步作家。
在新马,鲁迅的形象也随之改变,由落后而倾左,马华文艺界有不少人视鲁迅为导师,在写作时引用鲁迅的辞令以加强自己的论据,或在分析问题时断取鲁迅的章句为准衡。这种对鲁迅的认识的急剧转向无疑是中国国内情势使然,但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一些南来新马的中国作家对鲁迅及其思想的宣扬。事实上,马华作家也的确开始重视鲁迅的创作和思想。章翰就指出:“在三十年代中期,马华文艺界不少人花了很大的功夫熟读鲁迅的书,学习鲁迅的思想和斗争经验。”(18)而马华文艺界在三十年代中期提出的“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实则是周扬的“国防文学”和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的余绪。尽管新马的文艺工作者之间也有激烈的辩争,但他们中的多数,是站鲁迅一边的。“民族自由更生的大众文学”也基本上与鲁迅的思想一致。(19)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消息传来,马华文艺界迅速作出了反应,短短几天内,星马各华文报刊发表了大量的纪念文章,《南洋商报》《星洲日报》《新国民日报》《光华日报》及《中华晨报》等主要报刊都特别编辑了“鲁迅纪念专号”,以寄托对鲁迅无尽哀悼和崇高敬意。下面是《星中日报》于10月20日在第二版刊出的对鲁迅先生逝世的报道:
名震世界之我国文坛权威
鲁迅昨在沪逝世
上周写作过劳老病加剧遂致不起
噩耗传出后各地智识界莫不悲悼
这是一篇简短的标题新闻,但字里行间,充弥的却是强烈的悲痛之情。而在其后几天赶编出来众多的“鲁迅纪念专号”,有诗歌、照片、木刻、评论和专论等等,数量之多,内容之充实,令人感动和钦佩。对鲁迅先生的纪念是马华文艺界纪念文艺家最隆重、最庄严的一次。(20)
鲁迅逝世后,马华文艺界对他的认知趋同,对其创作和思想崇敬有加。我这里列出的仅为部分纪念文章的标题:
《文化界的大损失》(紫凤,《南洋商报》副刊《狮声》,1936年10月22日)
《吊唁群众的导师——鲁迅》(曙明,《星中日报》副刊《星火》,1936年10月23日)
《现代第一流作家鲁迅》(佐藤春夫,《星中日报》副刊《星火》,1936年10月24日)
《向鲁迅先生之灵致敬》(军笳,《星中日报》副刊《星火》,1936年10月24日)
《这样的战士》(阿生,《星中日报》副刊《星火》,1936年10月24日)
《集体主义旗下的鲁迅先生》(马达,《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1936年10月25日)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学之父》(陈祖山,《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1936年10月25日)
《我们要向鲁迅先生学习》(作者不详,《星洲日报》,1936年10月26日)
《我们要踏着他走过的血路》(侠魂,《星洲日报》,1936年10月26日)
《悼导师鲁迅先生》(戴隐郎,《南洋商报》副刊《文漫界》,1936年10月25日)
《导师·鲁迅》(英浪,《南洋商报》副刊《文漫界》,1936年10月25日)
我相信,仅凭这些纪念文章的标题即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最晚是在鲁迅先生逝世之时的1936年,他已确立了其马华文坛上的至尊的地位,“鲁迅神话”亦应运而生——鲁迅成了“一面旗帜,一个徽章,一个神话,一种宗教仪式”;(21)他是战士、巨人、导师、严父;他是新文学之父,中国的高尔基,普罗文学的英雄……
1937年10月19日举行了“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出席的社会团体多达34个;大会主席胡守愚在致词中说:我们纪念鲁迅,不在于形式上的纪念,而贵在学习鲁迅的奋斗精神。鲁迅的伟大,在于他一生不为恶劣势力所屈服,自始至终不断以最坚强的精神与恶势力搏斗,至死不渝,这是我们青年所应该学习的。(22)而1947年10月19日的鲁迅逝世十一周年纪念会更为热烈,更加隆重。大会主席汪金丁在致词中说:
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十一周年,当不胜悲痛,悲痛的不仅是失去了伟大的导师,而更大的却是民族苦难未过去而且日胜一日。但另一方面,今天纪念鲁迅先生又感莫大骄傲,鲁迅先生是民族的光荣,他的战斗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表现……(23)
在这次会议上,胡愈之也发表了演说,他强调:“鲁迅不仅是中国翻身的导师,而在整个亚洲亦然,他永远代表被压迫人民说话,对民族问题(的主张)是一切平等,教人不要做奴隶。”(24)(www.zuozong.com)
两次纪念会,相距十年,但主题、情势却是何其相似!王润华教授认为,鲁迅在新马1930年以后的声望,主要不是依靠对他的文学的阅读所产生的文学影响,而应归功于移居新马的受左派影响的中国作家与文化人所替他做的非文学性的宣传。(25)他的确是看准了所有“浮华”之后的“困乏”:当所有喧嚣淡逝,鲁迅在三四十年代留在新马的只是一尊高高在上的苍白“塑”像……
在这一时期,尽管鲁迅神话仍在继续,但新马的文艺工作者对鲁迅的创作及其思想的研究有了明显的进步,其代表人物是方修和章翰。
方修是五六十年代的马华文坛上的鲁迅精神和形象的最虔诚和最坚定的捍卫者,其探讨问题,著书为文,多以鲁迅的章句为圭臬,任鲁迅的思想为指归。他在1955年至1956年间写成的鲁迅式杂感文集《避席集》最能体现他对鲁迅先生的推崇。(26)到了七十年代,章翰先后完成了《文艺学习和文艺评论》(1973)和《鲁迅与马华新文艺》(1977)等两部著作,继续推崇“左派”的鲁迅精神,坚持认为无论是学语言、为人做事、思想、或探讨如何搞表演艺术活动,都需要向鲁迅学习。他对鲁迅的崇敬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鲁迅是对马华文艺影响最大、最深、最广的中国现代文学家。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鲁迅对于马华文艺的影响,不仅是文艺创作,而且也遍及文艺路线、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的改造等各个方面。……不仅是在文学领域,就是在星马社会运动的各条战线,鲁迅的影响也是巨大和深远的。长期以来,确切地说,自鲁迅逝世后的四十年,鲁迅的高大形象,一直鼓舞着人民为正义的事业而奋斗。鲁迅一直是本地文艺工作者、知识分子学习的光辉典范。我们找不到第二个中国作家,在马来亚有象鲁迅那样崇高的威信。(27)
方修和章翰都是新马知名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多建树。他们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研究,虽然仍有公式化和概念化痕迹,但他们毕竟都深入精读了鲁迅作品,深度揣摩了鲁迅思想,并能融入自己的体悟,较大程度上推进了新马的鲁迅研究。
此外,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学者还有郑子瑜先生。早在1955年他就完成了《‹阿Q正传›郑笺》(28)和《鲁迅诗话》两部专书,开始冷静地将鲁迅的作品当作文学经典,认真探究。在出版方面,除了《文艺行列》《荒地》《沙漠风》《耕耘》《生活丛刊》和《行动周刊》等刊物刊载的“鲁迅纪念专辑/专栏”外,1976年出版的鲁迅逝世40周年纪念文集《俯首集》也是一部不应忽略的鲁迅研究论文集。
最近二十年来,新马的鲁迅研究开始有了不同的途向:马来西亚仍沿承传统,鲜有突破,更令人担忧的是,鲁迅研究似乎后继无人了。吴天才(即江天)教授1991年从马来亚大学中文系退休之后,至今,该系仍没有开设任何与鲁迅研究相关的课程。而且,更让人吃惊的是,马大中文系自1972年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至今,竟然没有一篇学位论文是关于鲁迅的。现在,马华文艺界只有许德发先生等较少学者仍坚持鲁迅研究,许德发的研究方向是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
反观新加坡近二十年来的鲁迅研究,却别是一番景观。新加坡的学者在关注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的同时,更多地融入了世界性的学术研究大势,开始客观、理性地从事鲁迅研究,并在鲁迅思想的探寻、鲁迅作品的诠释和鲁迅语言艺术及修辞手段的研究等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代表学者就是王润华教授和林万菁教授。他们每年都在高校开设鲁迅研究的课程,并鼓励学生以鲁迅研究为论文写作的方向,仅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的研究鲁迅的学位论文就有十几篇。林万菁教授的代表著作《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格律》从修辞学的角度来探讨鲁迅的作品,认为鲁迅的作品中有其独特的修辞风格,其基本特征就是矛盾力所构成的“内摄”兼“外铄”的特殊风格;全书共分三编十章,旁征博引而不避烦屑,创获甚多。至于王润华教授,从1976年发表第一篇研究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论文《西洋文学对中国第一篇短篇白话小说的影响》至今,鲁迅研究一直就是他最为专注的学术领域。其学术专著《鲁迅小说新论》和《从周树人仙台学医经验解读鲁迅的小说》《回到仙台医专,重新解剖一个中国医生的死亡》等学术论文揉合学人的严谨与诗人的才情,多角度、多层面地探寻鲁迅的艺术和精神世界,展示了他宏阔的学术视野和专博的中西学养,是新马和东南亚鲁迅研究的最新成果,代表着现在,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鲁迅研究方向。也有一批作家,如云里风、黄孟文、吐虹等,也开始把左派的鲁迅文学观进行调整和修改,尝试破除被神化了的鲁迅的规范性和正确性,重新为中文和文本定位。(29)
以上是对鲁迅在新马的影响和新马的鲁迅研究的一个概述。总的来说,鲁迅的创作及其思想在新马,由二十年代的寂寞和被误解开始,经过很长一个阶段的喧嚣(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被误解),到了八十年代方始摆脱“左倾”的索套,被视为客观的学术对象,从街头走向大专学府,褪去浮华,返归本真,新马的鲁迅研究者也因此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这过程,虽多曲折,但终归令人欣慰。
(本文曾发表在新加坡《亚洲文化》2001年第25卷。)
(1) 方修《马华文学史论》,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6年,第8页。
(2) 王润华《从反殖民到殖民者: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第144种,2000年,第1页。
(3) 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风华出版社,1977年,第1页。
(4)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60页。
(5) 鲁迅《‹呐喊›自序》,《晨报·文学旬刊》,1923年8月21日。
(6) 鲁迅《‹自选集›自序》,《鲁迅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
(7) 鲁迅《影的告别》,《语丝》第4期,1924年12月8日。
(8)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屠杀赤手空拳请愿的市民和学生,死伤甚众。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9)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右派从上海开始,实行清党,大肆捕杀共产党和进步群众;接着广州发生“四·一五”大屠杀。鲁迅在《答有恒先生》中说:“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
(10) 转引自支克坚主编《简明鲁迅词典》,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0页。
(11) 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见陈漱渝主编《鲁迅论争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4页。
(12)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见蔡元培等著《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上海书店影印,1982年,第125页。
(13) 陈独秀《致周启明(1920年8月22日)》,见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58页。信中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
(14) 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上),星洲世界书局,1971年,第60—61页。
(15) 陵《文艺的方向》,《星洲日报》副刊《野葩》,1930年3月19日。亦见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上),星洲世界书局,1971年,第311—313页。
(16) 请参阅王润华《从反殖民到殖民者: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第144种,2000年,第3—5页;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风华出版社,1977年,第2—5页。
(17) 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上),星洲世界书局,1971年,第316—317页。
(18) 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风华出版社,1977年,第6页。
(19) 同上,第8页。
(20) 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风华出版社,1977年,第25页。
(21) 王润华《从反殖民到殖民者: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第144种,2000年,第9页。
(22) 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风华出版社,1977年,第46页。
(23) 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风华出版社,1977年,第48页。
(24) 同上,第46—48页。
(25) 王润华《从反殖民到殖民者: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第144种,2000年,第6页。
(26) 同上,第13页。
(27) 章翰《鲁迅与马华新文艺》,风华出版社,1977年,第48页。
(28) 关于《‹阿Q正传›郑笺》的出版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该书完稿于1945年,郑子瑜当时将书稿寄给在厦门大学执教的朋友叶国庆先生,转请郑振铎先生撰写书序,并介绍出版处。郑振铎收到了书稿,亦答应作序,但不久,郑振铎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书稿不知所终。到了八十年代,书稿竟在街头出现,几经周折,还奇迹般地回到了郑子瑜手中。1993年,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终于将它印行出版。
(29) 王润华《从反殖民到殖民者:鲁迅与新马后殖民文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第144种,2000年,第19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