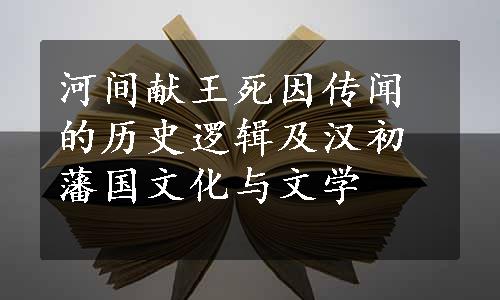
河间献王刘德在位二十六年而薨。关于刘德的死因,《史记》《汉书》本传均无明确记载,《史记·五宗世家》裴骃集解引《汉名臣奏》则作了如下说明:
杜业奏曰:“河间献王经术通明,积德累行,天下雄俊众儒皆归之。孝武帝时,献王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问以五策,献王辄对无穷。孝武帝艴然难之,谓献王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听乐,因以终。”[10]
然而上述说法却引发了后人的争议。怀疑者有清人何焯、王先谦以及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等,支持者有梁元帝萧绎以及近人徐复观、钱穆等。
何焯认为刘德获得“献王”的谥号证明汉武帝不可能对之施以迫害:“王身端行治,宜谥曰献王。献王,策谥之辞,褒崇若此,五宗世家注中杜业之语,知其无稽。”[11]王先谦指出刘德死于汉武帝迫害之说纯属误传:“史表,武帝元光五年献王来朝,即王之二十六年也,归后即薨,此自当时流传之误。”[12]泷川资言则引何焯之语以示认可[13]。
由此可见,尽管怀疑派的依据不完全一致,但确实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刘德卒于公元前130年,司马迁大约生于公元前145年,两人生活的时代相距很近。如果刘德之死果真是汉武帝施加政治压力的结果,那么作为良史的司马迁没有任何理由不记载这一事件,除非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根本就对这一事件一无所知。但是,如果司马迁和他的同时代人对这一事件一无所知,那么生活在西汉后期的杜业又是如何知道的呢?当然,退一步讲,司马迁等多数人不知道的事件,杜业不一定也不知道,可毕竟孤证难立,故杜业之言引人怀疑实属正常[14]。另外,东汉班固《汉书》本传也没有关于刘德是死于汉武帝施加政治压力的结果的任何信息,这就更让人怀疑杜业之言了。
当然,支持派也不乏其人。萧绎通过简单引用杜业之语以示认同[15]。徐复观则指出根据谥号判断刘德并非死于汉武帝迫害说的不可靠性:“按刘德非以罪死,而系以猜嫌忧愤而死。既死则猜嫌消而猜嫌之迹可泯。死后赐谥,乃当时之常例。而政治上表里异致,实古今之所同;猜嫌者其里,死后褒崇者其表。此在今日犹随处可以举例。何焯小儒,对政治全无了解,其言至可鄙笑。”[16]钱穆分析认为汉武帝可能因为猜忌刘德从而对其施加迫害:“则献王之见忌于武帝,盖视淮南尤益甚矣。考景帝子十四人,惟献王与栗太子同母。栗太子废而献王于诸子年最长,又得贤名。武帝之忌献王,有以也。献王即以来朝之年正月薨,其时朝十月,盖归而即卒;杜业之奏,非无据矣。”[17]
平心而论,支持者的理由也并非空穴来风,毕竟历史上的确发生过多起由于与最高统治者发生矛盾致使受害人因心情压抑而不得善终的事件。如战国时期信陵君遭魏王猜忌被剥夺兵权后,最终郁郁寡欢而死:“公子自知再以毁废,乃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饮醇酒,多近妇女。日夜为乐饮者四岁,竟病酒而卒。”[18]如汉惠帝为保护赵王刘如意而不惜与母后吕雉抗衡,但吕太后仍然找到机会鸩杀了刘如意,又残害其母戚夫人并使之为“人彘”,不久又召惠帝前往观看,使惠帝身心大受刺激,最终怏怏不乐而死:“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19]如汉景帝时期刘德之胞兄废太子刘荣“坐侵庙壖垣为宫”,被传至中尉府受审,最终因恐惧而死:“荣至,诣中尉府簿。中尉郅都责讯王,王恐,自杀。”[20]汉初这种因与最高统治者发生矛盾从而心情压抑的现象在汉武帝时期的藩王群体中更加普遍性地出现了。汉武帝即位以后,延续了汉景帝时期削弱藩王的政策,采取了包括任用酷吏打压藩王等在内的各种手段,使得藩王们感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压力:“武帝初即位,大臣惩吴楚七国行事,议者多冤晁错之策,皆以诸侯连城数十,泰强,欲稍侵削,数奏暴其过恶。诸侯王自以骨肉至亲,先帝所以广封连城,犬牙相错者,为盘石宗也。今或无罪,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证其君,多自以侵冤。”[21]刘德异母弟中山靖王刘胜甚至在汉武帝的宴会上闻乐声而泣下:“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鸿毛之重,群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22]武帝朝这种中央政权与地方藩国之间关系的不正常状态,的确不能不让人怀疑刘德之死是汉武帝施加政治压力的结果。
总之,怀疑派以《史记》《汉书》本传并无刘德死因的明确记载为基本依据,却没有充分考虑到历史事件往往充满复杂性与偶然性;支持派虽然注意到了极有可能导致刘德之死的政治因素,却无法圆满解释《史记》《汉书》本传为何没有明确记载刘德死因的原因。
由此看来,杜业关于刘德死因的说法可谓既查无实据又事出有因,所以如果单从考据的角度审视杜业之言,则其历史价值甚微。但是,如果联系汉初特别是汉武帝时期的社会政治状况,就能够发现这段话其实揭示出了隐藏在刘德死因背后的某种历史逻辑。换句话说,无论杜业关于刘德死因的说法是否为真,其所揭示出的历史逻辑却是客观存在的,而这也正是杜业之言的价值所在。
简而言之,隐藏在刘德死因传闻背后的这种历史逻辑就是汉武帝时期河间国醇儒所传承的先秦传统儒学与帝国贤良之儒所创造的汉初新儒学之间产生矛盾的历史必然性,以及这一历史必然性所导致的汉初醇儒之学必将走向衰落的结局。具体地说,汉武帝前期河间国醇儒所传承的先秦传统儒学与汉帝国贤良之儒所创造的新儒学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组思想观念的对立:(www.zuozong.com)
其一是相对君权与绝对君权之思想观念的对立。先秦传统儒学根植于东周乱世,看待君臣关系时素来主张君权只具有相对性。如孔子就认为君臣关系的产生与否应该以这种关系是否合乎“道” 为根本前提,而且君臣之间是互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孟子则更进一步认为君权不是绝对的,君臣之间完全是互为对等的关系[23]。河间献王醇儒学术团体传承先秦传统儒学时,在理论上不可能不继承这种相对君权的思想观念,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亦不可能不受其影响。例如刘德受封河间王之后,前来长安朝觐皇帝一共只有四次,其中汉景帝期间三次,分别在公元前154年、公元前148年和公元前143年;汉武帝时期一次,在公元前130年[24]。按照传统礼制,诸侯每五年朝觐一次天子。汉初对于藩王朝觐皇帝的时间节点虽然没有统一规定,但藩王参照、效仿周代礼制也是可行的[25]。这样看来,刘德朝觐父亲汉景帝的时间节点尚属正常,但首次朝觐异母弟汉武帝的时间节点却实属蹊跷,竟然是在汉武帝即位的第十一年,这明显与刘德崇尚先秦传统儒学的性情很不相符。至于刘德迟迟不朝觐汉武帝的原因,并无历史材料明确说明,但客观上却表明了刘德以藩王身份面对当朝皇帝时所采取的保留态度,以及先秦传统儒学相对君权之思想观念对于刘德的影响。
有趣的是,汉初相对君权的政治局面正好与先秦传统儒学相对君权的思想观念相吻合。汉初的帝国最高统治者一直都面临着君权相对性的困境。刘邦做皇帝的八年间,藐视皇权的事件就不断发生:汉高祖五年,“故临江王欢为项羽叛汉”,“燕王臧荼反”,“利几反”;汉高祖六年,“人有上变事告楚王信谋反”;汉高祖七年,“匈奴攻韩王信马邑,信因与谋反太原”;汉高祖八年,“高祖之东垣,过柏人,赵相贯高等谋弑高祖”;汉高祖十年,“赵相国陈豨反代地”;汉高祖十一年,“豨将侯敞将万余人游行,王黄军曲逆,张春渡河击聊城”,“淮阴侯韩信谋反关中”,“梁王彭越谋反”,“淮南王黥布反”;汉高祖十二年,“上使辟阳侯迎绾,绾称病。辟阳侯归,具言绾反有端矣”[26]。正因为皇权不稳固、天下不安宁,刘邦才借《大风歌》抒发感伤之情。汉惠帝时期,朝中大权完全被吕太后把持。汉文帝以庶子身份登上皇位后,不得不倚重刘邦时期的军功集团,并且对刘氏诸王采取怀柔政策。汉景帝初期爆发的吴楚七国之乱,表面原因是藩王抗拒削地,实际上亦是君权不伸的结果。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即位之初,武帝在位的前六年,欲有所作为却时时受到窦太后的牵制。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自然不会容忍这种相对君权政治局面的长期存在,最终决定采纳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贤良之儒所创造的主张绝对君权的新儒学为汉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这种新儒学以大一统为政治目标:“《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27];以天人感应为基本特征:“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28];以三纲等理论为实施手段:“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29],企图建立一个“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大小之职”的绝对君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30]。汉初贤良之儒所创造的这种新儒学顺应了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显然会与河间献王醇儒学术团体所传承的先秦传统儒学产生思想观念上的对立斗争。最终,这场斗争以汉武帝支持新儒学而宣告终结。
其二是传统礼乐治国与霸王道兼顾治国之思想观念的对立。先秦传统儒学崇尚礼乐治国的思想观念[31],刘德为首的河间国醇儒学术团体传承了这种思想观念,十分重视礼乐之教化功能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32]。为此,刘德不仅注意搜集、整理先秦传统儒学关于“礼乐”的资料,还积极向汉武帝推荐:“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33],“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34]。但是,汉武帝却钟情于地方音乐以及时人所造的新乐,“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圆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如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动心焉”[35],而对刘德所献雅乐采取了漠视的态度:“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36]。
显然,刘德与汉武帝之间存在着推崇先秦雅乐与推崇汉初新乐的分歧。表面看来这只是个人喜好的不同,然而进一步深究,则可发现这更是二者治国思想之不同的反映。“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37],礼乐虽然主要地表现为形式方面的属性,但由于其具有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从而能够起到有效传播最高统治集团政治诉求以及树立个人和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如汉武帝“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进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说”[38],汉武帝喜好新乐而被刚直的汲黯毫不留情地批评,可见天子对于音乐的选择是一件关乎治国安邦问题的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大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汉武帝对先秦雅乐与汉初新乐的选择实际上是对相应治国思想的选择。
“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于伦理者也”,“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39]。先秦雅乐中正平和,因此刘德推崇先秦雅乐,表明其治国思想“是地道的儒家淑世思想,其核心主张即通过礼乐教化来推进政治”[40];汉初新乐如同郑声[41],因此汉武帝推崇汉初新乐,表明其治国思想有求新求变的特点。这种求新求变的特点体现为汉武帝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采纳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贤良之儒所主张的霸王道兼顾的治国思想,以便最终达到“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的完美境界[42]。
汉武帝霸王道兼顾的治国思想的产生是汉初中央集权之时代要求的客观反映,顺应了社会发展的潮流,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与此相反,刘德没有认识到汉初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只是盲目地向往和提倡先秦儒家富于乌托邦色彩的礼乐治国的思想,这种一味复古的做法确实显得“迂阔而远于事情”。
总之,汉武帝前期河间国醇儒所传承的先秦传统儒学与汉帝国贤良之儒所创造的汉初新儒学之间,既存在着相对君权与绝对君权之思想观念的对立,又存在着传统礼乐治国与霸王道兼顾治国之思想观念的对立,再加上刘德本人因“修学好古”、大力延揽儒士而声望甚隆,其领导之下的河间国醇儒学术团体已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地方政治文化势力,所以汉武帝尽管表面上对刘德礼遇有加,但实际上采取了淡然处之的态度,甚至还极有可能产生强烈的猜忌心理[43]。
由于历史资料的缺失,刘德的死因现在已经无法明确,但刘德去世后,曾盛极一时的河间国醇儒学术团体也随之走向没落的历史事实却是确凿无疑的。河间国醇儒学术团体的没落,标志着汉初醇儒之学的衰落。从此,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贤良之儒占据了汉初儒家这个思想成分芜杂的学派的首席位置,而贤良之儒所创造的新儒学也成了汉帝国最高统治集团认可和支持的官方主流思想意识形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