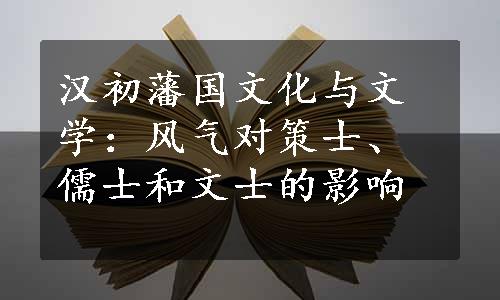
汉初士人群体之所以表现出浓郁的纵横风气,首先是因为汉初郡国制政体很大程度上复原了战国时期那种诸侯分治的政治格局,这在客观上为汉初士人创造了游说诸侯的空间。其次,汉初士人群体之所以表现出浓郁的纵横风气,与这一时期的汉初士人普遍怀着积极入世的心态紧密相关。士人们常常采取游说或者上书言事的方式去赢得统治集团的注意,在游说或者上书言事过程中为了打动对方而有意借鉴战国士人那种纵横捭阖的方式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最后,汉初士人群体之所以表现出浓郁的纵横风气,还与汉高祖刘邦的个人喜好有着莫大的关系。“意豁如也”“廷中吏无所不狎侮”的刘邦在反秦之前就是一个性格粗豪颇好纵横的人[36],如在家乡沛县参加酒宴时,竟然诈称“贺钱万”,其实“不持一钱”[37];反秦之后,刘邦也时常表现出好纵横的个性特点,机智破解项羽烹杀刘太公的要挟以及见机行事分封韩信为“真王”这两件事即是其例[38]。作为掌握着士人生死荣辱大权的最高统治者,刘邦好纵横的性格特征不可能不对汉初士人产生很大的影响。
就总体而言,汉初士人群体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即策士、儒士和文士[39]。当然,由于汉初时代的特殊性,这三种类型之间的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有些士人可能同时兼具其他类型士人的特点,如郦食其本乃儒士,却更多地带有策士的色彩;与之相反,儒士陆贾虽具有策士的身份,但却是作为汉初重要儒士而闻名于后世的。正因为汉初士人的身份往往具有多重性特点,因此本书在进行分类时,主要以士人的主观意愿及其在历史上的主流定位为基本依据。汉初这三类士人尽管具体的生存状况不同,但他们的言行事迹均明显表现出了重功利、通权变、尚雄辩的战国纵横风气。
策士是指在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为统治集团出谋划策并积极投身现实政治实践的士人。从事游说活动是策士的基本特征,因此汉初策士自然而然就沿袭了战国游说之士的纵横风气。楚汉相争时的陈留人郦食其即是其中的早期代表人物。《史记》本传记载郦食其“好读书,家贫落魄,无以为衣食业,为里监门吏。然县中贤豪不敢役,县中皆谓之狂生”[40],可见他是一个既生活落魄又昂扬自信的儒生。为了得到“不好儒”的刘邦的重视从而谋取功名富贵,郦食其一改传统儒生知书达礼、刚毅木讷的姿态,初见刘邦就大模大样地“长揖不拜”,接着故为惊人之问:“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41]有意激起刘邦怒气后,郦食其转而正色告诫他:“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42]于是刘邦不怒反敬,客气地请郦食其上坐。郦食其则趁势投其所好,“因言六国从横时”,从而赢得了刘邦更大的尊重:“沛公喜,赐郦生食,问曰:‘计将安出?’”[43]郦食其便献上攻打陈留之策。郦食其的策划最后果然变成了现实,他本人也因此得到刘邦的犒赏:“于是遣郦生行,沛公引兵随之,遂下陈留。号郦食其为广野君。”[44]
“伏轼掉三寸舌,下齐七十余城”[45],汉初策士群体中像郦食其这样“以舌得官”、颇具纵横之风的著名人物还有蒯通、娄敬、晁错以及主父偃等人。蒯通, 范阳人,秦末大乱时游说范阳令徐公,开口就故作惊人之语云“闵公之将死”,紧接着又“贺公得通而生”[46],通过这种一惊一乍的方式转眼掌控了二人谈话的主导权。徐公言听计从之后,蒯通便从容周旋于徐公和武臣之间并最终大获成功。后来蒯通又劝说韩信背汉,以与刘邦集团和项羽集团形成鼎足而立的局面,并力争夺取天下,但韩信没有接受这一主张。韩信被诛后,刘邦得悉蒯通劝说韩信背汉的往事,准备烹杀蒯通,此时蒯通又用三寸不烂之舌成功打动刘邦从而安然脱险。娄敬,齐人,在汉高祖五年求见刘邦,力谏弃洛阳而定关中为都城,声称此举可“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47];刘邦采纳了娄敬的建议,并“赐姓刘氏,拜为郎中”[48]。后来娄敬又向刘邦献上和亲匈奴之策,并建议迁徙东方六国贵族后裔于关中,以达到削弱东方六国贵族旧势力并充实关中地区政治经济力量的目的。晁错,颍川人,以能言善辩被誉为“智囊”,多次上书汉文帝,或言兵事,或言“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以及“募民徙塞下”之事[49],深得文帝嘉许。后来晁错又向汉景帝献削藩之策,结果遭到杀身之祸。主父偃,齐国临淄人,是汉初具有纵横之风的策士群体的后期代表人物。主父偃早年“学长短从横术”[50],因家贫而游历各地,但始终不能改变窘境,于是“上书阙下”出谋划策,被汉武帝赏识,拜为郎中,后连续升任谒者、中郎、中大夫,“岁中四迁”,一时风光之极。主父偃多次献策,如“谏伐匈奴”,颁布“推恩令”,徙“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于茂陵以严密监控[51]。主父偃扬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亨耳”[52],表现出了赤裸裸的功利思想。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汉初策士群体不仅积极投身现实政治实践,而且还有理论的建树,如被《汉书·艺文志》归入“纵横家”类的就有《蒯子》五篇和《主父偃》二十八篇[53]。
儒士是指以先秦儒家学说为宗而积极参与学术活动或者国家思想理论制度建设的士人。汉初统治者一改秦王朝钳制文化的政策,诸子之学得以复苏,儒家学派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一部分儒士专注于传承先秦儒学,另一部分儒士则积极参与汉帝国思想理论制度的建设,并表现出了浓厚的纵横风气,陆贾、叔孙通、贾谊和东方朔等人即是汉初纵横之儒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积极参加新国家建设以成就个人功名的时代浪潮的推动下,汉初的纵横之儒一方面以儒学为宗,一方面积极借鉴战国游说之士的纵横之术,以便在最高统治集团“不任儒者”的不利社会环境中取得成功。被班固称颂为“附会将相以强社稷,身名俱荣,其最优乎”的楚人陆贾便是汉初早期著名的纵横之儒[54]。陆贾继承并发挥了荀子的思想,著有《新语》十二篇。《新语》纵论古今,主张治国当以仁义为本,对汉初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刘邦对《新语》一书“未尝不称善”,陆贾也由此成为汉初重要的思想家。作为汉初大儒,陆贾积极入世以成就功名,曾随刘邦打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55]。刘邦初定天下后,陆贾又奉命出使南越,劝服南越王尉他对汉称臣。面对傲慢无礼的尉他,陆贾并没有苦口婆心地晓之以抽象的儒家君臣大义,而是完全从现实利害的角度出发,义正词严地告诫他必须向汉称臣。尉他听后不得不“蹶然起坐”。接着陆贾又进一步对比两国的国力,指出“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56]。这一番对比使尉他心悦诚服,“留与饮数月”,陆贾“卒拜尉他为南越王,令称臣奉汉约。归报,高祖大悦,拜贾为太中大夫”[57]。陆贾说服南越王尉他的整个过程,充分表现出了重功利、通权变、尚雄辩的特点,这一特点后来在他暗中帮助陈平和周勃诛灭诸吕之事上也得到了鲜明反映。
薛人叔孙通也是汉初的著名儒士,他糅合古礼与秦仪,制定了一套朝仪,初步解决了西汉开国之初宫廷礼乐制度一片空白的问题。刘邦对此极为满意,感叹自己现在才真正体会到身为皇帝的高贵。后来叔孙通又辅佐汉惠帝,主持宗庙仪法等方面的事务,影响与日俱增,终成“汉家儒宗”。在追求功名的过程中,身为儒士的叔孙通表现出了鲜明的纵横色彩:为了脱离虎口,他不惜面谀秦二世;为了讨好刘邦,他居然“变其服,服短衣,楚制”[58];为了保全刘盈的太子之位,他敢于力辩汉高祖。从秦末到汉初,“知时变”的叔孙通始终都能做到“进退与时变化”[59],结果官运亨通,先后被拜为太常、太子太傅,深得汉高祖和汉惠帝的倚重。
作为汉初杰出的儒士,洛阳人贾谊年少成名,后来还主导了汉文帝时期的礼法制度建设:“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谦让未皇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60]。与汉初具有纵横之风的策士和儒士一样,贾谊也有重功利的一面。但策士和儒士多重个人功利,或者是个人功利和国家功利兼顾,贾谊则是一心忧国,全然不顾权贵集团的嫉恨和汉文帝的日益疏远,他所重的完全是国家的功利:“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61]贾谊自然也通权变、尚雄辩,但策士和儒士的通权变、尚雄辩特点多在现实政治实践中体现,而贾谊因为鲜有参与现实政治实践的机会,所以他的通权变、尚雄辩特点多在上疏言事的“谋虑之文”中得以体现:(www.zuozong.com)
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阳包陈以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亡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62]
贾谊充分认识到梁国和淮阳国之于中央政权的重要性,因此建议汉文帝要么扩大两国的封地以壮大其实力,要么徙亲子刘武镇梁。贾谊的话高瞻远瞩、条分缕析、切中时势,颇有说服力。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后一条建议。果如贾谊所料,汉景帝前元三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梁国成为拱卫中央政权的中坚力量:“吴、楚、齐、赵七国反,先击梁棘壁,杀数万人。梁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与太尉亚夫等相距三月。吴、楚破,而梁所杀虏略与汉中分。”[63]
仕于汉武帝时期的齐人东方朔不以实际功业扬名,而以诙谐滑稽名世。东方朔所学甚杂,曾自言十三岁学习文史,十五岁学习击剑,十六岁学习《诗》《书》,十九岁学习孙吴兵法[64],但其思想倾向还是以儒家为主。作为儒士,东方朔既倡导“以道德为丽,以仁义为准”的儒家之道[65],又断然抛弃儒家传统的重义轻利观念,直言修身的目的就在于谋取个人功利,认为“苟能修身,何患不荣!太公体行仁义,七十有二乃设用于文武,得信厥说,封于齐,七百岁而不绝”[66]。他秉承了儒家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愿为“天子大臣”成就一番功业,然而汉武帝仅视其为宫廷俳优。尽管如此,东方朔还是利用自己经常接触武帝的机会,多次力谏朝廷采用儒家思想安邦治国,从而直接参与了汉初宫廷的思想文化建设。如他曾谏止武帝扩充上林苑:“故务苑囿之大,不恤农时,非所以强国富人也”[67];曾谏止武帝召董偃饮酒于宣室:“夫宣室者,先帝之正处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68];曾当面批评武帝奢侈多欲的生活方式:“上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69]。为了达到既直谏又保身的目的,东方朔平时常常以诙笑逗乐的方式拉近自己和汉武帝之间的情感距离,并尽量做到“观察颜色”,以减轻汉武帝的抵触情绪。这种通权变的方式果然收效甚大,汉武帝每次被谏后不仅不生气,反而更加亲近东方朔:“上乃拜朔为太中大夫、给事中,赐黄金百斤”[70],“复为中郎,赐帛百匹”[71],“赐朔黄金三十斤”[72]。作为汉初宫廷最具影响力的纵横之儒,东方朔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展现了自己重功利、通权变、尚雄辩的特点。
文士是指出于纯粹的文学兴趣而以文学创作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士人。汉初的文士虽然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远远不及策士和儒士,但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汉初文士群体长期在中央政权不得志的原因,主要在于汉初的最高统治集团大多不好文学。刘邦虽有《大风歌》传世,但并非出于纯粹的文学创作兴趣,只是见景生情、即兴演唱的产物而已。汉惠帝、高后、汉文帝和汉景帝则无文学创作。汉武帝即位后,雅好辞章,重视和提倡文学,于是汉初最高统治者不好文学进而不好文士的状况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随着大批文士集中在汉武帝周围,汉初文学中心最终完成了从地方藩国向帝国宫廷的转移,并形成了汉帝国宫廷文学彬彬之盛的局面。
由于最高统治者的不重视,汉景帝时期活跃在帝国京都并以文学创作为人生旨趣的著名文士唯有蜀郡人司马相如[73]。与贾谊等人不同,司马相如人生兴趣的着眼点不在于参与现实政治生活,而在于从事纯粹的文学创作,所以初遇邹阳、枚乘和庄忌之后他才可能顿生相见恨晚之感,并不惜辞官,离开繁华的京都来到相对冷清的地方藩国,伴随邹阳等人进行文学创作:“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74]
由于藩王的礼遇,这个时期的地方藩国汇聚了汉帝国的大部分文士,其中又以淮南王刘安之淮南国、吴王刘濞之吴国以及梁孝王刘武之梁国的文士数量居多而且影响力较大。淮阴人枚乘就是活跃于汉初藩国文士群体之中的杰出人物,他不喜仕途,只好文学创作,体现出了一个纯粹文士的精神风貌:“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孝王薨,乘归淮阴。”[75]
在时代氛围的影响下,以司马相如和枚乘为代表的汉初文士群体也表现出了鲜明的纵横风气。司马相如少时就敬慕战国时期的蔺相如,而蔺相如便是一个富于纵横色彩的人物,“有智谋”,能言善辩,出使虎狼之秦而能完璧归赵,辅佐赵王渑池之会而能“不辱于诸侯”,避免与廉颇相争而能使廉颇负荆请罪[76]。司马相如少时对蔺相如的敬慕以及由此更名为“相如”之举实际上已经充分显露了他自幼好纵横的习性,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则是他好纵横个性的必然反映,如闻卓文君新寡“而以琴心挑之”[77],献《天子游猎赋》而被拜为郎,奉命出使西南而功成名显,上书谏猎而汉武帝善之。由于好纵横的个性使然,身为文士的司马相如作文时笔端常带辩士风采:“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78],“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而乐,出于万有一危之涂以为娱,臣窃为陛下不取也”[79];写赋时则极喜铺张扬厉,希望“以文采干政事,试图通过赋作来表达其匡正天下、经世致用的思想”[80]。与司马相如类似,枚乘两次上书谏止吴王谋反,不仅老谋深算地分析了局势,而且辅之以对比说理的方式,其中自有一股逼人的气势,如对比谋反的两种结局:“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太山”[81],如对比双方军力的强弱:“夫举吴兵以訾于汉,譬犹蝇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齿利剑,锋接必无事矣”[82]。枚乘作赋时亦表现出“膄辞云构,夸丽风骇”的特点[83],自有一股动人的力量,如《七发》以七事来感触楚太子,极尽渲染之能事,终使“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8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